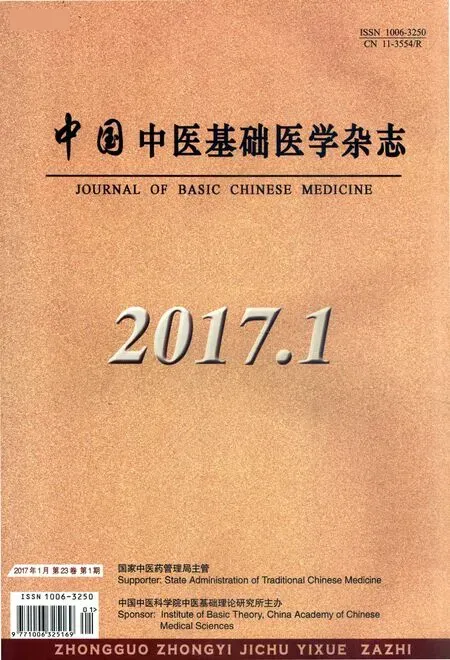马元仪《证论精微》学术价值探骊*
钟 微,杨奕望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上海 201203)
马元仪《证论精微》学术价值探骊*
钟 微,杨奕望△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上海 201203)
《证论精微》是清初名医马元仪所著的医论类著作,现仅存的民国抄本藏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全书1卷,载医论33篇,撷取历家精华,结合其50余年临证经验求精启微,从病因脉证、治法方药等方面逐一阐释。《证论精微》重视病源病机的分析,理法有度、稳中求新,诊治闭结、咳嗽、腰痛、健忘等病证均有独到见解,对于当今中医临床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证论精微》;《病机汇论》;马元仪;名医经验;学术特点
马元仪(约1634~1714),名俶,江苏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康熙年间江南名医,著有《证论精微》《印机草》《马师津梁》等。晚年与门下众弟子倾力校订先师遗作《病机汇论》18卷[1],有口皆碑。时人赞叹马元仪批语为沈朗仲《病机汇论》阐发精要,却对《证论精微》所知甚少。目前,仅有一些大型中医药文献工具书保留此书著录,如《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第838页)、《中国医籍通考》(第2924页)、《中国古医籍书目提要》(第1407页)、《中国医籍大辞典》(第1324页)、《中国中医药学术语集成·中医文献》(第683页)等,但均未作详述。为此笔者初探马元仪原著《证论精微》并析其要义,冀望对中医理论与临床有所裨益。
1 马元仪的医学源起
马元仪本儒家子,后攻医术,师从吴中名医沈朗仲先生。沈朗仲(名颋)受教于明末儒医大家李中梓(字士材,号念莪)。故马元仪得同事沈、李二师,又游学于江西喻嘉言(名昌,号西昌老人)[2]。匠门名儒张大受曾言:“吾吴元仪马先生,精于医者也,而其学独出于云间沈、李二家。凡辨凉温,施补泻,一本古人而析于理。[3]”马元仪获益于名师传教,勤于医学,终得治病之道,临证50余年医名籍甚。马氏亲传弟子众多,著名者如朱绅、盛笏、项锦宣、吕永则、俞士荣、江承启等皆得其学[1]。尤怡(字在泾)乃马元仪最得意弟子,同朝名医徐大椿褒扬尤氏:“博雅之士也。自少即喜学此艺,凡有施治,悉本仲景,辄得奇中。[4]”马氏之学渊源有序,后启津梁,被誉为“士材学派乃至清初江南医学承启的枢纽”[5]。惜马元仪著述存卷不多,故《证论精微》实为马氏学术难得之传世明证,值得深入研究。
2 《证论精微》的版本
《证论精微》仅存之版本,为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的1922年抄本[6]。馆藏抄本两种,一为秀水李氏“半闲散人”所抄,简称“李本”[7];一为秀邑德钧重录,简称“德本”[8]。除“李本”少量虫蛀、残破外,两部抄本版页完整,字迹清楚。二者皆以线装,内含目录并带有眉批。封页正中全部直书“证论精微”4个大字,正文版面每半页9行,每行21字,全书约2万字。两种抄本亦有差别,“德本”版心上标书名和目录、下注页码,“李本”则仅含目录。“德本”扉页右上方醒目题写“吴门马俶元仪著”,“李本”则标注于正文第一页清晰表示原著者。“德本”扉页背面注明“中华民国十一年壬戌季春月题”,而“李本”扉页右上方所题“壬戌夏月抄”,同样抄录于民国十一年,但有数月的时间差距。因为抄录者不同,两部抄本在签章上迥然而异。“德本”扉页左下角印有“意在笔先”字样,正文页右下方尚有“李福同享”“尌滋”两处印章,“李本”的两方印章右下是“嘉兴李”、左下为“秀水李氏所藏”。笔者通篇逐字核对两部抄本,发现除“德本”夹携抄者的少量批注、“李本”有个别字句遗漏外,所抄录的正文内容基本无异。
3 《证论精微》的学术特色
《证论精微》共载33篇医论,涉及中风、中寒、暑、湿、燥、火、气、血、郁、痰饮等病证。每证先引《内经》及张仲景、刘河间、朱丹溪等诸家学说,后详述病证的病因病机、治法方药。以恶寒证为例,马元仪将病因分为六端:“有风寒外感者、有痰饮内留者、有阴盛阳微寒从中生者、有阴虚阳盛格阴于外者、有卫气虚衰不能温分肉而实腠理者、有脾胃素虚时值新凉而阳气不伸者”[8],随后把不同症状、脉象、治法逐一阐述,如“风寒所感,多头痛脊强,其脉必紧,宜辛温以达其表;痰饮内留,多背寒如冰,其脉必弦,宜甘淡以蠲其饮[8]”。诸证论治,无论内外上下表里虚实,擘肌分理,平脉辨证,立对应治法要则,马元仪反复强调“所因不同,证治各异”[8]。
《证论精微》与《病机汇论》内容不乏相似之处,编写体例亦大体相同,《病机汇论》是对先师遗作的增订,而《证论精微》所体现的是其本人学术特色、诊疗经验,无疑更为丰富。
3.1 未尽者,毛举缕析
《证论精微》引用先贤之言,发现疏漏者往往结合自身临证经验,阐发未尽之意。如闭结一证,马元仪首先肯定金元·李东垣分证之详细,并指出“独于虚秘一端,则犹有未尽”[8]。对于虚秘,李东垣仅言“胃虚而秘者,不能饮食,小便清,厚朴汤主之。[8]”马元仪认为胃虚气秘确为虚秘的一种,然而胃尚藏津液,又为肠之司,胃虚津枯同样产生便结。随后,进一步补充临证更为常见的肾虚便结之证:“试观年老虚人,多有便结之病。盖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起居衰矣。愈老愈衰,精血日耗,肠胃干涸,故成此证”[8]。紧接着提出相应治法、用药:“当峻补精血,如益虚润燥丸、苁蓉润肠丸之类,择而用之”[8]。最后指出用药宜忌:“此证惟伤寒阳明实热,可行攻下之法,其他非係气血之亏,即津液之耗,不可概用硝黄等药,以取速效,而重伤根本,或愈通而愈结,或一通而不止。[8]”马元仪在李东垣基础上,补充虚秘理论使之趋于完善,并提出虚秘治法,当润补不宜猛攻,为后世医家所谨记。
3.2 庞杂者,化繁就简
医学典籍汗牛充栋,历家医论各具千秋,常常让后学无所适从且陷入佳径难求的苦恼。古来咳嗽患者难以计数,然各论太繁,医者寡效,无成法可师。明代大家张景岳驭繁入简,将咳嗽分为内伤、外感两端,深受马元仪赞誉。并对此逐条剖析:“外感之证有表里。寒郁其热,寒为表而热为里也,先以辛温解其寒,后以甘寒除其热。内伤之证有标本,上热下寒,寒为本而热为标也必以重剂补其下,微以轻剂滋其上。”[8]并进一步总结外感咳嗽与内伤咳嗽的致病特点,外感之咳起病急,不宜强行收敛而留邪;内伤之咳病势缓,不宜贸然发越而伤正,可谓深得临证精髓。此后抽丝剥茧、细致分析咳嗽脏腑传变之理,“外感之咳,其重在肺,以皮毛为肺之合,皮毛受邪,必传于肺也。故解表之中必当以清肺为急。内伤之咳,其重在肾,以肾为肺之子,水涸金乃枯,子能令母虚也。故治肺之中,尤当以补肾为主[8]”。经马元仪娓娓道来,咳嗽的分型、病机、治法化繁就简,让后学者登堂入室、了然于心。
3.3 失当者,直抒胸臆
医论之多,众讼纷纭,研清其理尚且不易,所见不同难得直抒胸见。试以腰痛为例,世人皆以为肾虚所致,马元仪认为并不尽然。并主张溯本求源,详考《内经》以求其全:“凡足少阴、足太阳、足厥阴及督脉为病,皆足令人腰痛。又有六经腰痛形证之别,故其病有表里虚实之不同。”[8]另外,“跌扑闪挫,以致血脉阻滞,筋骨不和,发为腰痛者,此其病在经脉,又与表里之病不同。”[8]分析腰痛病因病机,并与临床诸证逐一对应:“凡悠悠戚戚,屡发不已者,肾之虚也;遇阴雨或久坐痛而重者,湿也;遇诸寒而痛,或喜暖而恶寒者,寒也;遇诸热而痛,及喜寒而恶热者,热也;郁怒而痛者,气之滞也;劳动即痛者,肝肾之衰也。当辨其所因,然后施治。[8]”马元仪辨证审因的学术特色可见一斑。
又如健忘之证多认为是心肾不交所致,历来却难明言心肾不交之道。马元仪深入探讨水火不济之因:“若其烦劳太过,则心阳亢而上炎;嗜欲无穷,则肾阴弱而下趋。阳亢者阴不生,而心中无阴,将何以下通于肾?精去则气亦去,而肾中无阳,将何以上交乎心,此不交之道也。[8]”进一步提出阴阳互根、水火既济之理?“人知心之火肾之水,而不知水中之火,火中之水也。人知心之火降,肾之水升,而不知心中之阴始能降于肾,肾中之阳始能交于心也[8]”。论及治法马元仪直抒胸襟,对使用天王补心丹抑心火和用六味来滋肾水的方法提出异议:“欲心之交须养其血,欲肾之交必固其气,岂抑心火滋肾水之谓哉?[8]”他认为,“故虽治其心肾,又必调养中州,始得以胜通上澈下之任也。”[8]心肾相交多受助于中焦脾胃之力,则健忘可愈。马元仪之学,可谓洞悉补土之王道。
《证论精微》1卷33篇言简意赅,条目清晰,撷取各家医论所长,更多独到之见地。马元仪旁征博引,结合50余年临证经验,未尽者毛举缕析,庞杂者化繁就简,失当者直抒胸臆。《证论精微》阐述病因脉证、治法方药,注重病证源候的分析,理法有度,求精启微,对于当今中医临床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苏州市档案局.吴中名医录[M].苏州: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133-134.
[2]刘时觉.四库及续修四库医书总目[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556-557.
[3]沈颋,马俶,增定.病机汇论[M].陈熠,点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
[4][日]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626.
[5]杨奕望.清初江南名医马元仪的学术承启[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6(3):157-160.
[6]薛清录.中国中医古籍总目[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838.
[7]马元仪.证论精微[M].民国十一年半闲散人抄本,1922.
[8]马元仪.证论精微[M].民国十一年秀邑德钧抄本,1922.
R2-52
A
1006-3250(2017)01-0044-02
2016-05-26
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上海中医药大学“科学技术史”规划项目(071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中医药重点学科——中医史学(国中医药人教发[2012]32号)
钟 微(1989-),女,广东湛江人,在读硕士,从事中医医史文献研究。
△通讯作者:杨奕望(1974-),男,广东大埔人,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医史学研究,Tel: 13041627427,E-mail:yangyiwang@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