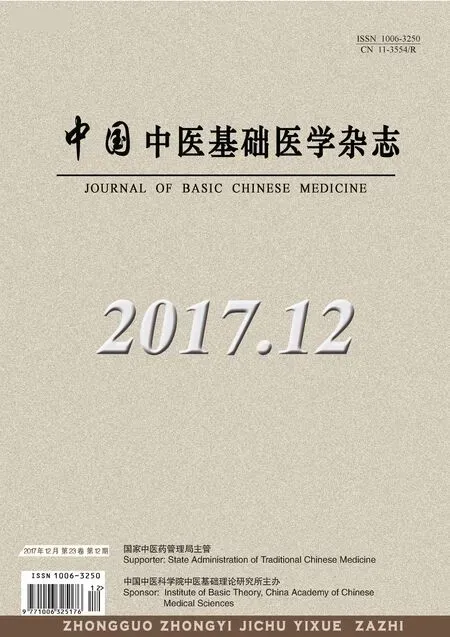中医术语英译的“约定俗成”与“走出去”*
董 宁,邓珊珊,刘 轻
(河北中医学院英语教研室,石家庄 050000)
1 引言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华夏子孙的文化瑰宝,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健康服务资源。中医不仅起源于中国,数千年来也扎根于国外越来越多的国家,惠及世界各国民众。早在公元前1世纪,中医就传到朝鲜、日本和中国的远近邻国,传入欧洲已有350多年的历史。目前,澳大利亚、美国也均以立法的形式承认了中医的合法地位。中国的中医药产品出口到16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近200家公司致力于中草药的研发,中医已经成为国际医学界关注与探索的热点。近年来,我国也大力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2015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医药“十三五”规划,规划在推动中医国际化方面,强调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必要性。值得一提的是,规划同时提出中医药服务贸易重点项目,即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遴选可持续发展项目,与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中医药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国际影响力。因此,如何把握机遇、传承古丝绸之路、助推我国中医文化“走出去”,推进中医药服务贸易,成为中医相关从业者思考的热点问题。
英语作为国际第一语言,中医药对外交流贸易首先碰到的就是英语沟通的障碍,因此中医英语翻译发挥着重要桥梁作用。但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不过区区百年,却成为主流医学。反观中医药,在国外却发展缓慢,沦落为辅助手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医药的英译未能真正传达自身的医学理念和厚重的文化内涵。跨文化交际,对应语的缺乏、中医特殊的语言文化特点和没有规范化标准是当前中医英语翻译发展的难点。对英语翻译策略的不同选用,将直接改变中医药术语的内涵特征和文化承载。本项目尝试从语言文化传播角度出发,探讨中医英译翻译“约定俗成”策略的选用。
2 “约定俗成”的力量
1999年,张普在研究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的第一篇论文“关于大规模真实文本语料库的几点理论思考”中,就提出“语言不是静止的,语言在运用中不断地产生变化,语言的生命力就在于这种稳定中的变化。这些变化的端倪就隐藏在大规模的真实文本(无论他们是经典的还是非经典的文本)之中,甚至就隐藏在那些非规范现象里。一切新词、新义、新用法一开始总是不在约定和规范之中,通过‘对话’和‘讨论’,利用‘已知’对‘新知’作出‘解释’或‘纠错’,新知一旦被大家接受并广为传播,最终将进入约定或规范,这就是语言发展的辩证法和规律(张普:“关于大规模真实文本语料库的几点理论思考《语言文字应用》1999 (1):第37页)。”语言不是静止的,它无时无刻不在动态之中。任何语言的创造,只要有了大众的跟从和社会的传播,就能生根发芽成为一个新的语言成分。即使看上去不合理的语言成分也可以生存下来,甚至成为标准和规范。
如“非典”和“SARS”这一组词中,语义上合理、贴切的是“SARS, 即“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他告诉我们这种疾病是什么。而“非典”是“非典型性肺炎的简称”,它只告诉了我们“不是什么”。但在某网站的统计分析中, “非典”这个词语的流通远远高于“SARS”,所以最终词典收录了“非典”一词。无论语义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某些术语的翻译迅速经历了社会的“约定”而“俗成”了一个新的语言成分,这就是语言“约定俗成”的力量。
就规范和标准而言,今天的任何规范和标准都有一个研制或制定过程,经过若干严格规定的程序,最终由相应职能部门来颁布推行。目前关于中医用语英译国际标准化,已经推行的标准有《WHO西太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WHO针灸经穴名称国际标准化方案》《世中联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等。这些标准的形成过程是怎样的,一个“新知”究竟是如何“最终进入”社会大众约定的?或者说这些术语的英译“约定”究竟是如何“俗成”的? 在翻译家们致力于将大量的中医术语的英译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中,体现了这种标准化形成力量的正是本文要探讨的“约定俗成”策略。
在中医用语英译国际标准化过程中,应遵循“约定俗成”这一规则,即对一些目前已经通行但并不十分准确的译法可以适当予以接受。如将“艾灸”译作“moxibustion”。该译名早在17世纪就由荷兰人译出,至今仍被人们广泛使用。“moxi”来自于“moxa”,是日语里“艾”的发音,这一译法是艾灸传入西方时,西方医生按照日本医生的发音用拉丁语写出的。我国学者曾希望用汉语拼音“ai”来替换“moxi”,将其改为“aibustion”,用以说明艾灸起源于中国,从而澄清其在传入西方时的误解。但事实情况是,“moxibustion”的意义已与中医针灸相联系,且西方字典已收录“moxa(艾绒)”词条,改译反而造成混乱。在历史条件局限下,有些中医译名的翻译在语义上确有不合理之处。但这些译名已在实践中被海内外学者和民众广泛接受,所以依据语言“约定俗成”的规律,我们以通用约定俗成的译法作出统一并作为标准。
3 什么是“约定俗成”
名指名称。荀子的名辨思想,对名与实(客观存在)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荀子在《正名篇》中提出的两个制名原则 “缘天官”和“约定俗成”。荀子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 “缘天官”指直觉的语言经验是言语交流中判断的起点,而 “约定俗成”即所谓达成共识。墨子也曾说过:“瞽不知白黑者,非其名也,以其取也。”意思是说盲人不辨黑白,并非因为不知黑白这两个名称,而是不知黑白所指的意义。可见,墨子认为名与实没有必然的联系。换言之,“以名举实”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现象。不难理解, 我国先秦诸子的语言“约定俗成”观体现了我国古代对语言的认知意识。
关于语言的“约定俗成现象”,西方主要语言学家也持同样的观点。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do Saussure)是这样定义语言的:“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是一种社会制度,同时又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陈明芳:“论索绪尔和萨丕尔的语言观”,《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95)。”索绪尔提出了语符的“任意性”和“规约性”,他的理论为语言的约定俗成论提供了理论基础。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形式与所表示的意义没有天然的联系,也就是说语言形式和语言形式所指(概念)之间的联系不是必然的,无任何规律可循。如汉语把桌子的概念称为“桌子”,而英语称之为“desk”,这种选择是偶然的,取决于原始的约定者。但也正因为如此,语言的“任意性”要求语言具备 “规约性”,也就是说语言形式和语言形式所指之间必须有约定俗成的关系。说汉语的人必须遵循原始约定者的传统将桌子这一概念称为“桌子”,而不能随心所欲的选择。任意性使语言有潜在的创造力,而规约性又使语言规范和标准(胡壮麟:《语言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
在语言研究中,“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这一观点在现代语言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是“约定俗成”在语言学界形成的普遍理解和共识。正名篇的本来思想与现代的语言学解释其实是有所出入的。张普在“关于“约定俗成”的约定俗成”(参看《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2004:132-137)一文中探讨了“约定俗成”在语言学领域中的解释,并对约定俗成的定义作了语言学领域的理解。张普认为,(约定俗成)这种观点已经多加转引,在语言学界成了一种差不多是不言自明的认识。那么不管它是否背离了荀子的古意,我们都可以将其作为“约定俗成”的另一个现代义项或语言学义项(张普:“关于“约定俗成“的约定俗成”,收于《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34)。
4 中医翻译的约定俗成策略
就翻译而言,翻译的过程也具备语言的“任意性”和“规约性”的特点。作为不同国家和种族产生共性的一环,翻译是一个 “约定”的文化重构过程,相当于语言的原始约定者,它必须遵循语言的规约性。翻译如果不经历“约定”,就相当于语言毫无规范和标准,也无法发挥语言相互交流沟通的功能。这不仅是我们如此重视译语标准化规范化的原因,也是我们重视“约定俗成”策略的一个理由。
既然“约定俗成”遵循语言发展的规律,在中医英译过程中采用约定俗成的策略就是可行的,因为首先“约定”必须经历“俗成”的过程。
如中医对疾病的发生发展与预后,有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论和观点。但“名物不同,传实不易”,中医文化在西方文化中没有对应,西方读者难以领会,“火”的译法便是如此。在WHO的标准化方案中和世中联的标准中,中医的“火”或是“热”被译为fire (火,火邪),heat (热,热邪),heart fire (心火),liver fire (肝火),wind-fire eye(风火眼)等等。 “上火”从中医理论解释属于中医热证范畴。在给外国人解释上火时,会使用“inflame”一词帮助解释,因为西方医学本身也有“inflame”(发炎)这个术语。“flame”是“火焰”,“in”是“在内”,“in-flame”就是在火之内。既然有对应语,选择inflame去解释似乎是必然的。但实际上在中西医学中,二者所涵盖的范畴不同,翻译者在中医翻译过程中尽量避免将二者等同。中医认为人体阴阳失衡内火旺盛即会上火。而现代医学的inflame(发炎),主要表现为患病部位发红、肿胀、发热和疼痛等。早在清朝,中国在引进 “inflammation”的时候,翻译家们就认为用“上火”来翻译是不科学的,所以使用了新词“炎症”。今时今日,翻译家们在中医的对外翻译中,仍未采用inflame来对应中医的“上火”,道理也基于此。如何翻译这些西方缺乏对应语的术语,曾是困扰中医翻译界的一大难题。早期“心火”“风火眼”这些译法曾使西方读者颇感困惑。但这些译语的形成经过几十年来中医在西方的传播和应用,经历了“俗成”的过程,西方读者基本理解了这些概念,接受了这些译法。因此,以约定俗成的策略翻译这类术语,逐渐在海内外形成了共识。
其次,语言的“约定俗成”具备再次“约定”的特性,这将为中医术语译语形成提供更充分的量化数据。翻译的实践表明,翻译是人们在漫长的时间中经历不断探索和完善的一个过程。翻译会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以及译语在广度上的传播发生变化。因此翻译是可以变化的,它可以在一轮一轮的“约定俗成”过程中使译语不断得到完善。
如“三焦”的翻译,在早年的标准中其译语被定为triple energizer(3倍的气的激发)。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我国的学者不断提出质疑,因为这一译法和“三焦”的实际意义相差太远。“三焦”是中医藏象学说中一个特有的名词,把三焦译为“气的激发点”是不合理的。但是在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WTO)西太区开始制定中医术语国际标准时,中方专家对“三焦”的翻译提出重新讨论的要求,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但是随其在实际应用中引起了多质疑和混乱,这一译法终于在2010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国际分类东京会议上得到改正。“三焦”被一致同意音译为“sanjiao”。这就是“约定俗成”对语言再次约定的作用。
5 结语
一个译语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流传,必须在实践中经过大众的“约定”才能“俗成”为规范和标准。“约定俗成”不是某一个人的活动,它需要社会群体的共同创造,它需要传播途径才能完成覆盖和渗透,覆盖面越广,渗透力越强,语料库就越大,由此我们获得“约定俗成”的量化数据就越准确。中医术语语料库的形成对中医英译标准和规范的形成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医起源于中国,几个世纪以来中医扎根于国外越来越多的国家,惠及世界各国民众。中医的第一轮传播在文明史上持续了几个世纪。但在当今时代下,得益于我国不断推进的中医药全球化的战略,中医的传播速度和效率已经是过去无法想象的。“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一带一路”作为中医对外传播的通道,成为一种新的传播途径,在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方面改变着中医文化传播的进程。借此,中医译语的“约定俗成”周期将大大缩短,基于获取的“约定俗成”量化数据,我们可以建立中医术语英译语料库,中医英译标准化进程也将被大力推进。
总之,我们强调“约定俗成”的意义,在于尊重“约定俗成”在中医“走出去”过程中的力量。在“一带一路”的机遇下,我们应加速中医术语英译语料库的建立,获取“约定俗成”的量化数据,为中医英译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的依据,为我国中医“走出去”提供策略性的支持,从而加速我国中医“走出去”的进程。
[1] 陈明芳.论索绪尔和萨丕尔的语言观[M].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92-95.
[2] 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李永安.约定俗成在中医名词英译标准化中的作用[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05(3):71-72.
[4] 李照国.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英译国际标准化研究[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5] 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13.
[6] 张普.关于“约定俗成“的约定俗成[C].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2004:132-137.
[7] 张普.关于大规模真实文本语料库的几点理论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1999 (1):35-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