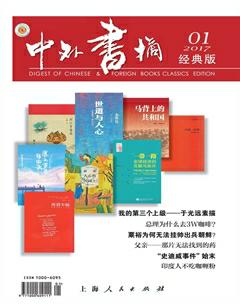蒋介石的两次日本体验
野岛刚+芦荻
19岁初次来日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4月,19岁的蒋介石头一次踏上日本土地。来到日本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日语。
在来日本之前,据说蒋介石将自己的辫子一把剪了下来。辫子是清朝,或者说是满族文化的象征,满族入关之后,将这样的习俗强加在汉民族头上,时间超过两百年。
蒋介石剪掉辫子的行为,意味着他这时候已经萌生了打倒清朝的志向,同时,毫无疑问也象征着下定重大的决心。不过也有一部分证言指出,蒋介石剪掉辫子,其实是更后来的事情了。只是不管怎样,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剪掉辫子就是表明决心,要向古老的中国告别。
不过,蒋介石第一次在日本停留,只有八个月的时间。他原本是为了学习军事而前往日本留学的,没想到,如果没有母国,也就是清朝陆军部的推荐,是不能进入日本相关军事院校就读的。而蒋介石在来日本之前,对此似乎一无所知。对这个几乎从未踏出过浙江省境的乡下青年来说,这次不得其门而入的经验,可以说是人生最初的挫折。
据台湾当局的资料记载,蒋介石这时在日本就读的学校是“清华语言学校”;只是,清华语言学校似乎并不能算是纯粹的“语言学校”。
清华语言学校的前身是1899年由梁启超所创立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东京高等大同学校”设立之后,因为财政困难改名为“东亚商业学校”,但经营仍旧不见起色,最后移交给了清代驻日公使,校名也改为“清华语言学校”。
据说,蒋介石就是在这所学校学习日语。不过,这所“清华语言学校”基本上是一所供华侨子弟就学的学校,所以里面虽然或许有日本语的授课,但其实所学的东西,应该不只是语言而已。
就在蒋介石旅居日本的这段时间,日本发生了一件中国革命史上相当重要的大事。那就是“中国同盟会”(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成立。中国同盟会日后演变成国民党,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组织领导者。
陈其美与孙文
整个东京简直就像是被点燃沸腾了一般,到处都充满着炙热的革命气息。在那里,当时还不满20岁的蒋介石,也飞身投入这股热潮当中。想必是革命的热情火焰,同样点燃了隐藏在蒋介石内心之中的火苗吧!
可是,蒋介石当时还是太年轻了一点。就在孙文抵达日本的8月,各个分散的革命团体统合在一起,结成了日后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但在这时候,蒋介石还没有资格参与其中。
不过就在这时,蒋介石结识了自己的同乡革命志士陈其美,两人后来还成为结义兄弟。拜陈其美所赐,蒋介石得到孙文的引荐,从而踏入革命运动的中枢,这不能不说是相当幸运的一件事。
关于这段20岁左右青春时期的日本体验,蒋介石自己在1917年开始撰写的日记当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总结:我原本是立志前来修习陆军,但是日本陆军的入学限制非常严格,若是没有本国陆军部的推荐,是不可能获得陆军学校入学许可的。
就在这年,我在宫崎(滔天)的家中,经由陈英士(其美)的引荐认识了孙总理。此后,我与旅居东京的革命志士多有交流,对于民族的感情也日渐深厚,同时心中对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渴望也愈发无可抑止。
阅读这段文字可以清楚发现,这短暂的第一次访日,对于以复兴中华民族为毕生职志的“政治家蒋介石”的诞生,可以说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入学“振武学校”
蒋介石的第二次访日,出乎意料地很快就实现了。回国之后,蒋介石进入了清朝设立的“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校”(即后来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学。这是步调慢半拍的清朝为了对抗革命派,聘请诸多外籍教官进行近代军事教育授课的一所教育机构。蒋介石当然不是清朝的同路人,只是为了以军人身份前往日本留学,他才以保定军官学校当作跳板。蒋介石的努力确实收到了效果,在62个前往日本留学的军校生名额当中,他获选为其中之一。1908年,蒋介石从大连搭船前往日本,在那里就读日本陆军为中国学生专门设立的教育机构“振武学校”。
1903年创立的“振武学校”,它的旧址位于东京都新宿区(当时的牛込区市之谷河田町),振武学校的地位,相当于为了进入陆军士官学校而设立的预备校。当然学生需要自己付学费,不过其他方面的经费则是由日本外务省与陆军省来负担。清朝在学校设立时也提供了20000元的资金。当时振武学校的留学生几乎都没有上过日语课程,因此授课基本上都是以中文进行。
高田连队
对蒋介石而言最为深刻的“日本体验”,毫无疑问应该就是他在新潟县的高田作为一名士兵的这段经验吧!
虽然蒋在高田的时间不过短短一年,但这是他军人生涯的原点。同时,这段经历也对他此后一生的行动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白团的诞生,其导火线正是源于蒋介石对于日本军人及日本军事教育的信赖。
蒋介石自振武学校毕业后,于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12月5日被派任到驻屯于现在新潟县上越市高田的陆军第13师团野战炮兵19连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第13师团以日本第一支正式引进滑雪装置的部队而闻名,当时的师团长是在日俄战争关键的203高地争夺战中立下赫赫军功的长冈外史。之后,继承了该师团一部分的驻地——如今在高田这里,仍然有陆上自卫队第五施设群及第二普通科连队大约一千人规模的自卫队员驻屯。
根据同样来自高田驻屯地的资料记载,蒋介石是作为“清国留学生队”的一员,以一等兵的身份搭乘军用列车自东京来到高田的。当时蒋介石所使用的名字,是他的学名“蒋志清”。同期的中国毕业生,有15人被配属到高田这边。
蒋介石在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6月升任上等兵,同年8月升任伍长,但到了同年10月,所有其他的同期士兵都已经升任军曹了,却只有他一个人还没能升职。
事实上,蒋介石在这段时期的成绩也绝对称不上优秀,在19连队的所有中国学生当中,他的成绩总是排在倒数几名。
不进陆军士官学校,而是投身革命
然而,这种苦恼的日子没持续多久,蒋介石在高田的军事生涯就随着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突然画上了句号。
当时,以蒋介石为首,有好几位留学生表达了归国的意愿,并与长冈师团长直接展开了交涉。不过长冈却劝这些学生“在日本好好锻炼成优秀的军官再回国不是比较好吗?”没有答应他们自动退役的请求。退役既然不被许可,蒋介石便假借休假偷溜出了连队,动身前往中国。他在10月8日到达上海,正好赶上参与革命。
另外,日本当时的记录上则写着,蒋介石于1911年11月11日,“因为事故而退队”。从蒋介石明明逃亡却没有其他人遭到连坐处分这点看来,当时的日本人还算是宽宏大量的……
蒋介石原本一心期盼着能够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就读。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就读,是当时中国所有年轻军人最向往的一件事,也是他们冲破种种难关前往日本留学最大的理由。如果蒋介石没在此时选择回国的话,他应该会以第一种学生(有意成为各兵科军官者)的身份,在1911年高田连队的训练期间结束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吧!
然而,蒋介石却选择了参加革命这条路。这样选择的结果是,蒋介石在日本的军事资历比其他人都要差,却因为参加革命的缘故,获得了一张踏上中国政治舞台、闪耀光辉的通行证。
对于想出人头地的蒋介石来说,比起留在日本,投身革命明显更有意义;这也就是说,在1911年这个极端重要的时刻,蒋介石被迫做出的这个人生重大决定,就结果而言可以说是相当正确的!
只是,对当时的中国军人而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可以说是一种品牌保证的标志,简单说就是所谓的“最高学历”。日后成为有力将领的阎锡山与孙传芳,是陆军士官学校6期的毕业生;蒋介石的部下张群是陆军士官学校10期的毕业生,何应钦、谷正伦则是11期的毕业生;如同群星闪耀般的人才,都云集在陆军士官学校的课堂之中。
可是,在台湾的资料中,却屡屡可以见到“蒋介石曾在陆军士官学校就读”这样的记述。就连蒋介石身份证上的“教育程度”这一栏,填的也是“日本士官学校”。
蒋介石诈称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这件事,虽然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某些知情者心照不宣的秘密,但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时代,没有人敢针对这件事情大声批判。从学历这件事情,也可以窥见蒋介石自尊高傲甚至到了虚荣的一面。
当时在高田担任19连队连队长的飞松宽吾,在1936年(昭和十一年)的《朝日新闻》一篇以《高田的青年蒋介石》为题的报道中,对于当时的蒋介石有着这样的回忆:蒋与张君等14名同学一起来到我的队上,投入到严格的营内生活中;大概因为蒋在众人之中年纪最长的缘故吧,他很自然就成为同学之中的领袖。现在回想起来,或许从那时候开始,蒋介石就已经隐隐展现出他作为领导者能力的一面了吧!只是,关于蒋介石的日语能力,飞松的评价却相当严厉:明明同样是在东京学习日语,和张君(张群)的流畅比起来,蒋介石简直可以说是糟糕透顶。
当时,学生每隔两三天,就要轮流把打饭的容器摆到连队长的面前,这是军训方法的一环,然而,因为蒋介石一向无法用言语好好表达,所以遇到这件事情时,他总是显得相当痛苦。和停留在日本的长时间相比,蒋介石的日语实在是相当不流利;飞田的证言,赤裸裸地指出了这个事实。
他究竟学到了什么?
据说,当时蒋介石曾经因为没把马匹照料好,在牵马回到马厩的时候,遭到长官强烈的斥责,甚至一度被禁止骑马。当时的战场上,骑兵仍然是主要的战力,马的价值也非常高,在军队里甚至有“士官、下士官、马、兵卒”这样的说法。
另外,在谈到自己在高田的寒冬体验时,蒋介石是这样说的:“像那样的大雪,即使在中国北方也是很少见的,”“不管天气有多寒冷,也不管雪有多大,我们都得在每天早上5点不到就起床,然后端着自己的脸盆到水井前面,用水井里的冷水洗脸。”“比起谈论若是要复兴民族、报仇雪恨,该怎样获得武器之类的话题,我们最优先的事情,就是用冷水洗脸,然后沉默不语。如果连这点小事都无法胜过日本人的话,那其他的就根本不用提了。”经过上述的体验之后,蒋介石总结出了这样一个强烈的教训。
对蒋介石而言,寒冬用冷水洗脸这样的行为,正象征着日本的道德观与精神性,同时也意味着他所理解的最根本的“日本经验”。即使称呼侵略中国的日本为“倭寇”,并在抗日战争中和日本死战到底,蒋介石也没有失去对于日本军人的尊敬。究其根底,毫无疑问应该就是来自他在高田的体验吧。
日本这种家长式的严格教育,虽然可以追溯到中国儒家的阳明学派,不过对于在清朝末年的保守家庭中长大、受儒家教育熏陶的蒋介石来说,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心有戚戚焉吧!
超越“爱恨交加”这个陈腐解释
所有讨论蒋介石与日本关系的作品大概都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为蒋介石日后以飞黄腾达的政治家身份所做的关于日本的发言,都是立足于他的日本观之上。
因此,这便使得以下的解释广为流传:“蒋介石对日本,其实是怀着某种矛盾的感情,或者也可以说是‘爱恨交加吧!”
确实,蒋介石对日本的善意常常被拿出来加以强调,而他在中日战争期间也的确是一直扮演着与日本敌对、和日本不断交战的角色。
可是,我认为,所谓蒋介石的“对日爱恨论”,未必就能正确地反映出蒋介石的对日观。
“爱恨交加”这个词,很容易给人一种仿佛男女关系般,爱恨纠结、缠绕不清的感觉。可是,蒋介石对于日本的评价与批判,很明显是经过仔细梳理后的论述。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几乎无法感觉出蒋介石的内心之中,有任何对于日本的“爱恨”所产生的纠葛存在。
面对当时的动荡局势,蒋介石先后投身上述的清华语言学校、振武学校,以及高田第19连队。据他自己宣称,当时在日本的艰苦生活,不只奠定了他日后成为政治家与军人的基础,同时也让他变得更加坚强。
根据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师——庆应大学荣誉教授山田辰雄的说法,蒋介石“似乎希望从留日的记忆中,找寻出日本人乃至日军强大的根源。从这当中,他体认到了中国的弱小,并从而展现出一种期盼中国变得更强的情感。”
换句话说,蒋介石的日本体验在他心中,是被转换成一种“中国非得学习日军的强悍,以及日本民族的优点不可”的论点而存在的。
蒋介石在日本发现了“灭清兴汉”的思想,并且展开了他作为革命军人的事业起点。对蒋介石而言,最优先的目标就是洗雪中国因为近代化过程落后惨遭欧美及日本蹂躏的“耻辱”,达成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在这层意义下,学习抢先一步迈入近代化之林的邻国日本,自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撇开好恶的问题,蒋介石的一生可以说是与日本有着切也切不断的“缘分”。这并不只是限定于蒋介石个人,而是生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管愿不愿意都无法不去面对、时时刻刻来自邻国日本的“时代的邀请”。
在蒋介石的人生当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当时日本与中国关系的显著投影。因此,我认为,研究蒋介石与日本的关系,也就等于是探索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