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个帝国叫葡萄牙
张明扬
“大家”阅读
互联网时代,读者并不缺乏信息,但一些真正具有传播价值的内容,却往往淹没于信息洪流之中。力求将最有价值的信息,最有锐度、温度、深度和多维度的思考与表达,最值得阅读的网络优质原创内容,快速呈现给读者,是《世界文化》与腾讯《大家》建立合作的初衷与共同努力的方向。【“大家”阅读】每期将臻选《大家》所汇聚的中文圈知名学者、专栏作家的最新文章,与读者分享“大家”眼中的“世界文化”。

作为历史上的第一个全球性帝国,葡萄牙帝国在中国的认知度与存在感都过于低调。要不是因为有澳门回归这件并不久远的大事件,国人可能压根都不知道葡萄牙这样一个蕞尔小国竟然还曾有过帝国时代。
与先前的大帝国诸如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拿破仑帝国等相比,葡萄牙帝国的比较优势并不体现在军事力量与领土面积上,而是体现在“广度”上,它的帝国网络曾长达地球一圈的四分之三,从欧洲本土到非洲西海岸再到印度果阿,从南美的巴西到东亚的马六甲和澳门,整个海洋上几乎都被葡萄牙帝国布局了各种商业(军事)据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葡萄牙帝国才被视作“第一个全球性帝国”。
从多个角度来看,葡萄牙帝国可能是近现代各版本西方帝国(西班牙帝国、荷兰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等)中最不可能成就帝国霸业的那一个。拿人口来说,15世纪初葡萄牙本土的人口仅为100万左右;从商业势力上来说,既没有像英国和荷兰那样各自拥有一个“东印度公司”,也从未拥如荷兰“海上马车夫”式的浩大远洋商船队;从技术革命上而言,葡萄牙帝国还没等到工业革命开始就已走上急速的下坡路;从军事上而言,葡萄牙帝国只能说在海上拥有一些并不构成压倒性的优势,人口存量更决定了它无法在陆地上四处投放有实质意义的军事力量。
正如大卫·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中所说,葡萄牙帝国是一种“超越常理的非理性的跳跃”。
那么,作为“最不可能的帝国”,葡萄牙帝国是如何在世界史上率先开启“葡萄牙时间”的?是如何在缺乏各种资源禀赋的前提下崛起的?这也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言,“一个像葡萄牙这样人口和资源都很有限的国家,怎么能航行如此之远并取得如此之多?”
这个答案至少在中文世界是很稀缺的,你甚至在网络书店中很难找到这样的书。我之所以敢于在这里高谈阔论,也只不过是刚刚读完了这本叫《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的新书而已。
《征服者》几乎整本书都只与海洋有关,而这正是葡萄牙帝国的真相。书的一开始就是20世纪葡萄牙大诗人佩索阿充满民族傲娇感的句子,“有界限的海,或许属于希腊或罗马;没有界限的海,属于葡萄牙”。
也是因为有关海洋,这本书由“地中海三部曲”的作者罗杰·克劳利来写也再合适不过,只是,这一次的主题是无远弗届的,“没有界限的海”。
葡萄牙帝国的最初崛起可能要追溯到1415年。这一年,葡萄牙攻占了摩洛哥的港口:休达,这可以看作是葡萄牙人,也是欧洲人向外扩张的开端。《征服者》对此的定性是:这场惊人的战役让欧洲的竞争对手们知道,葡萄牙王国虽小,却自信满怀,精力充沛,而且正在大举出动。
休达之战也让亨利王子走上了历史舞台。这位被誉为“航海者亨利”的王子不仅是葡萄牙崛起的第一个关键性人物,也是世界史上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毫无争议的先行者。正是在亨利王子手中,葡萄牙成为欧洲的航海中心,以举国之力率先迈出欧洲,到未知世界进行冒险。
即使在亨利王子去世后,已被成功洗脑的葡萄牙精英阶层也层出不穷地诞生着新一代的航海英雄。1488年,葡萄牙人又迎来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迪亚士在远航中发现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好望角。
不过,领先了上百年的葡萄牙人很快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哥伦布为西班牙人发现了新大陆。《国富国穷》极具历史感地比喻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消息震惊了葡萄牙人,就像苏联人造卫星震惊了美国一样。”
但大卫·兰德斯也像鄙视苏联人那样鄙视了哥伦布与西班牙。在他看来,相比葡萄牙数十年的艰难和耗资巨大的探索,哥伦布第一次试航就发现新大陆不过是运气好罢了。葡萄牙在整体航海制度上的领先优势仍然不可撼动,更具有可持续性,“每一次航行都带来经验,刺激着技术的革新”。
就像美国在航天上对苏联的报复一样,葡萄牙人也很快就做出了漂亮的回应:1498年,达伽马“发现”印度。作为《征服者》中前半部分最重要的主人公,达伽马的成功被克劳利写得格外煽情,“达伽马时代的历史开启了西方扩张的五百年,释放出了如今正塑造我们世界的全球化力量”,“达伽马结束了欧洲的孤立,大西洋不再是一道屏障,而变成了一条将两个半球连接起来的通衢大道”。
然后,就是一连串的发现与标志性时刻。1500年,葡萄牙航海家卡布拉尔发现巴西;1510年,葡萄牙占领果阿,这也是其在亚洲获得的第一块领土;1511年,占领马六甲;1513年,进入红海;1543年,来到日本。

葡萄牙人的确是拼命了。用《征服者》中的说法,葡萄牙人举全国之力在印度洋进行争夺永久性立足点的生死斗争,“动员了全部可动用的人力、造船、物资供给,以及抢在西班牙人做出反应之前把握和利用机遇的战略眼光”。
当然,仍然需要英雄。阿尔布开克是《征服者》的后半部分的主人公,是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第一个在亚洲建立帝国的欧洲人。“阿尔布开克手中的人力始终只有几千,只有临时拼凑的资源、虫蛀的船只,却凭借着令人瞠目结舌的雄心壮志,赠给曼努埃尔一世一个印度洋帝国,其由一系列要塞的网络支撑。”
是什么驱动着葡萄牙人的“雄心壮志”?自然,葡萄牙人的帝国冲动首先是来自“商业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葡萄牙帝国就是一个“海上贸易帝国”,许多要塞与殖民地的选址都基于对港口以及海路交通枢纽的控制,从地图上看,这个帝国就是沿着海上贸易商路而构成的。
但是,宗教狂热也是驱动葡萄牙人的“雄心壮志”的主要因素。他们无论到哪儿,任何一艘船上都带着神职人员和修士。当达伽马抵达印度时,当地统治者曾问他想要什么,他答道:“基督教徒和香料。”在葡萄牙人的信仰世界中,上帝的旨意是让葡萄牙成为一个大国,葡萄牙现在是新的上帝选民,担负着上帝赋予的伟大使命。
不过,《征服者》似乎并未提及宗教狂热对帝国引发的负作用。大卫·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中指出,宗教信仰对葡萄牙帝国的商业扩张造成严重而不利的影响,“它给那些本来应该比较顺利的,可以使双方都获益匪浅的接触中加入了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因素”。

更严重的是,这引发了许多不必要的战争,导致葡萄牙人在印度洋沿岸处于一种四面受敌的状况。在多数状态下,葡萄牙人几乎只有在军队的保护之下,才能安全地开展贸易活动。
而这种高成本的贸易活动收益也就可想而知了。《国富国穷》讽刺道:“难道有别的新来者比这些葡萄牙人更起劲地给自己制造麻烦么?”
反讽的是,他们的基督教兄弟——西班牙、英国和荷兰正在一点点地蚕食着葡萄牙帝国。在印度洋上,荷兰人和英国人几乎是开展着合法化的海盗行径,大肆劫掠葡萄牙商船。而更致命的威胁是,依靠军事优势直接夺走葡萄牙的殖民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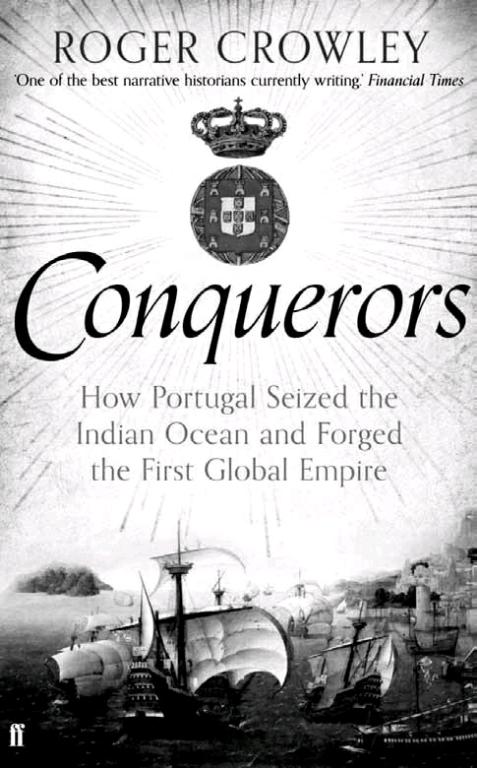
在大卫·兰德斯看来,对于葡萄牙帝国的衰落而言,宗教狂热还要负上一些更为本质的责任。与西班牙一样,葡萄牙人的精神生活逐渐陷入了“盲从、狂热和讲究血统纯净的境地”。在宗教狂热的驱动下,葡萄牙国内大肆打击所谓“宗教异议分子”和异端,而科学与科学家则遭受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毁灭式打击。到了16世纪初,葡萄牙科学界的领头人都出走了,连好点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都找不到了。
当一个国家没有人敢冒险讲授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的学说时,这个国家的科学水平的停滞乃至倒退也就不言而喻了。到了17世纪末,由伟大的亨利王子开创,曾一度在航海理论和实践上独步天下的葡萄牙已经成为落伍的蹒跚者,葡萄牙甚至沦落到要雇佣外国人做船只领航员的地步。
大卫·兰德斯说了句很刺耳的话,“如果说商品上的互通有无很重要,那么思想上的互通有无更重要”。
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人卡蒙伊斯曾用诗如此描述祖国的黄金时代,“如果世界更大,他们也会发现它”。作为帝国崛起时期的见证者,卡蒙伊斯绝对无法想到,曾一往无前的祖国后来竟有过这样的时代,“世界就在身边,他们谁都装作看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