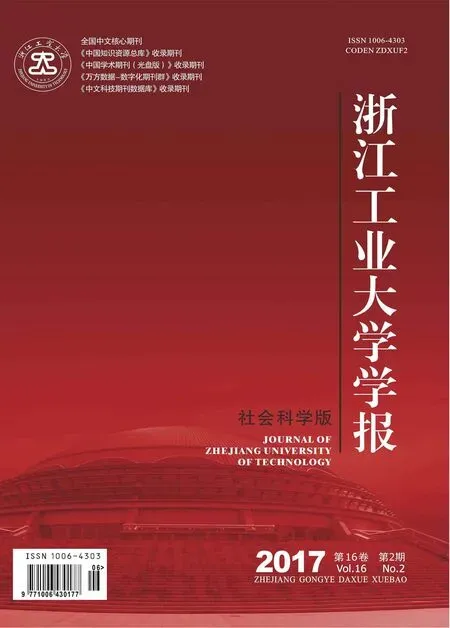魏金枝乡土小说的创作历程、审美特征及艺术渊源
刘家思,刘桂萍
(1.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2.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社科部,浙江 宁波 315800)
魏金枝乡土小说的创作历程、审美特征及艺术渊源
刘家思1,刘桂萍2
(1.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2.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社科部,浙江 宁波 315800)
魏金枝的乡土小说创作始于“五四”时期,终于“文化大革命”前夕,可分为沉滞的乡土叙事、人性化的革命叙事、乡村讽喻与暴露和“新中国乡村颂歌”等四个时期,形成了四个鲜明的审美特征:以连续性书写体制创造史诗性效果,追求叙事的诗性化和复调性,对人性进行深层探索和浓郁的浙东乡土特色,主要接受了契诃夫、鲁迅、郁达夫等中外作家的影响,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乡土文学;魏金枝小说;创作历程;审美特征;艺术渊源
魏金枝是浙东山区诞生的一个孤独而惨淡的文学精灵。他的人生道路非常曲折,从而形成了质朴、憨实、坚硬、忠信和进取的文化个性。这种精神性格使他在艰难中不妥协、不放弃,而是诚恳做人,踏实做事,艰难行进,不断追求,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坛一个成就较高、影响较广的知名小说家。除《七封书信的自传》《奶妈》《白旗手》《制服》《魏金枝短篇小说集》《魏金枝选集》等小说集之外,他还有不少作品散落于尘封的报刊中。他以深切的人生体验和深沉的主观情感进行艺术表现,不仅在描写老一代中国人的人生方式与文化心理上有卓越的成就[1],而且在描写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乡村知识分子的孤独处境和悲剧命运上表现非凡,更在描写中国人民投身社会革命时的主体精神与人性魅力上笔力奇异,还在描写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新型的人民形象和新的社会关系上眼光独到,深刻地展现了20世纪前60多年的中国乡村不同历史时期各社会阶层的生存状态和利益冲突,反映了乡土中国从封建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揭示了国民心理、性格与精神及其演变轨迹。因此,其小说受到鲁迅好评,“堪与台静农媲美”[1]。本文试图对其小说创作历程、审美特征及其艺术渊源做一些梳理和把握。
一、魏金枝小说的创作历程
魏金枝的乡土小说创作开始于1920年,但集中创作是1924年开始的,至“文革”前结束,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30年和建国17年的文学史,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早期特征,但又显示了自身的独特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它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沉滞的乡土叙事时期
1920—1928年是魏金枝乡土小说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主要小说有《七封书信的自传》《留下镇上的黄昏》《小狗的问题》《沉郁的乡思》《祭日致辞》《裴君遗函》等。这些小说以越乡叙事为中心,以乡镇小知识分子为视点,开拓了“五四”乡土文学的题材领域,显示了重要的成就。这些小说不仅表现了乡镇小知识分子的清苦生活和悲惨遭遇,而且暴露了封建家族统治者的专制、残忍与野蛮,展示了社会的沉闷、黑暗和丑恶,描绘了乡村沉滞、沉郁、沉寂的死相,表现了浙东底层民众的苦难人生。《七封书信的自传》描写彬哥因为反对族长将小学变私塾而招致命案下狱,最后越狱,走向了武装反抗统治阶级的道路,不仅表现了乡村小学教师彬哥的悲惨人生,也批判了以族长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垂死性和残暴性,深刻地反映了浙东山区守旧、落后、专制和颓败的社会现实,被鲁迅称为“优秀之作”[2];《祭日致辞》描写了封建专制家族对年轻媳妇的损害及其带给漂泊外乡的底层知识分子的痛苦;《留下镇上的黄昏》展示了乡村小镇凝聚着的沉滞之气,受到鲁迅的充分肯定。这些小说深刻地表现了浙东乡镇野蛮与文明、封闭与开放、传统与现代、愚昧与开化、怯弱与坚韧、麻木与清醒、封建专制与自由民主的对立,反映了乡镇知识分子情与理、灵与肉、自私与奉献的冲突,暴露了浙东乡土社会的现实罪恶,反映了乡村中国向现代转型的艰难,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势力的不满情绪。周作人曾指出,文学“可以因了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希望中国新文学“自由地发表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魏金枝的小说都是描写越地的世态苍生的,但鲁迅以越地水乡村镇为视阈,而魏金枝小说则是以浙东山区为对象,有其独特的个性,是对越地书写的补充和完善。
(二)人性化的革命叙事时期
1929—1935年是魏金枝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时期,以人性化的革命叙事为主。1928年,革命文学兴起后,推动了左翼文学主潮的到来,魏金枝追赶着这种潮流。1929年,他的《校役老刘》描写勤杂工老刘被师生损害的命运,标志着他的小说由关注、同情乡镇知识分子到关注、同情底层农民和批判知识分子的转向。1930年,他开始创作左翼文学,先后发表《奶妈》《白旗手》《桃色的乡村》《报复》《制服》等小说,描写底层农民,表现无产阶级革命,但仍坚持“五四”文学传统,突出人性描写,开创了人性化革命叙事路向,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些小说在左翼文学中别开生面,摆脱了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端,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左翼文学艺术。《奶妈》写出了革命英雄的人性真实,显示了很强的艺术张力,是对当时“革命加恋爱”的概念化模式的突破;《白旗手》描写勤务带领士兵哗变,揭示了个体欲望对主体行为的影响力,显示了人性的力量与强度;《桃色的乡村》描写了农民暴动的分裂,显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前哨兵》描写农民革命从庸常性到神性的成长历程,展示人性在特定情境中正负能量的转换。这些小说显示了艺术描写的深度与力度。在左翼文坛,魏金枝与张天翼、沙汀、蒋牧良、周文等人齐名,但他在人性描写上是独具一格的。“左联”成员金丁指出,左翼文学克服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倾向,是“柔石、张天翼和魏金枝的小说,给读者开辟了新的视野”[4],而魏金枝是以其人性化叙事为左翼文学做出贡献的。
(三)乡村讽喻与暴露时期
1936—1948年是魏金枝小说创作的第三个时期。这时期,他既呼应着“国防与抗战小说”,又延承着“五四”乡土文学传统,致力于讽刺与批判乡村丑恶现象。魏金枝是“九一八”之后最早呼唤抗日的作家之一,他的《磨捐》《羞明》《想挂朝珠的三老爷》等小说呼应着国防文学与抗战文学的潮流。但是这时期他的讽喻和暴露乡村现实丑恶的小说更突出。日寇入侵后,国民党当局仍然腐败和专制,压迫和剥削民众,激起了人民的不满,于是讽喻与暴露文学潮流兴起。魏金枝以犀利的笔锋直指国民党基层官僚的腐败与罪恶,推动了这种创作潮流。《凑巧》描写悦来杂货店老板王德昌做保长后一心向上爬的喜剧人生,揭露了国民党兵役制度的腐败,批判了国民党官僚营私舞弊、贪污腐败的丑恶行径,可与沙汀的讽刺小说媲美。在《将死的人》《竹节命》《死灰》等“保长系列小说”中,他批判了国民党基层统治者的残忍无道和旧社会将人变成鬼的黑暗现实。他还通过描写民众的苦难来暴露和批判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坟亲》描写阿乜的悲惨人生,史诗性地反映了20世纪前50年中国乡村底层民众的深重苦难。与以往不同的是,作品既呈现了全景式的特征,又显示了电影蒙太奇和特写的特征,深刻地揭示了造成民众苦难的根源,批判了统治者的罪恶。他的作品不仅表现了底层民众坚韧地面对苦难,如《客气》,而且歌颂了他们面对苦难时的忠义侠气、舍己为人的品格,如《蜒蚰》。这些小说是他小说创作的新发展。
(四)“新中国乡村颂歌”时期
1949—1966年是魏金枝小说创作的第四个时期。这时期,歌颂是文坛的主流话语,魏金枝的创作也呼应着这种主潮,歌颂新时代,但又明确反对公式化和概念化。他说:“创作是不应该有什么‘清规戒律’的,有‘清规戒律’的就不是创作,而是‘教条’。创作是不应该有一定格式的,有一定格式的就不是创作,而是公式。……作家只能用最科学最敏锐最深刻的观察研究,才能得出结论来,决不能用教条和公式来代替它”[5]。他自觉寻求艺术与政治的和谐统一,显示了一个“五四”老作家的审美追求。他以浙东的民俗风情融入创作中,以民间情调和地方色彩来冲淡作品的政治色彩,强化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活路》《跟着他走》都表现了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主题,但前者用方言体写作,以民间性弱化了政治性对艺术性的遮蔽;后者以历史的书写和对嵊县土匪题材的变形消释了政治性,避免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时代病痕。同时,《老牯和小牯》《两个小青年》和《礼物》等作品致力于表现社会新气象和年轻一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显示新中国的生机与活力,但也总是以民间情调来减弱政治色彩,强化艺术氛围。即使是直接歌颂党和毛主席的作品,如《义演》,也是借助浙东社戏活动来反映主题,仍有较强的艺术价值。魏金枝虽然紧跟时代,但他不去正面歌颂,不去写高大全的人物和革命英雄,而是努力描写活生生的小人物,以生活质感形成艺术魅力,对后来茹志鹃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魏金枝的小说创作以其执着的现实书写,反映了20世纪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表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较高的审美价值,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图景,是不可忽视的文学遗产。
二、魏金枝小说的审美特征
魏金枝的小说创作坚持现实主义的审美路向,对20世纪前60年余年的历史巨变进行了独特的书写,深刻地描写了底层民众的苦难人生,展示了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的交锋,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演变轨迹,昭示了底层民众不屈的生存意志,揭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这些小说叙事圆润,结构严谨,描写细腻,人物鲜活,乡土色彩浓郁,富于人性深度。涂光群说魏金枝“最擅长于短篇小说”,“每篇都是精心构思,又讲求文字技巧,决不草率从事”,“质量上乘”[6]。的确,魏金枝有坚定的艺术追求,其小说彰显了独特的审美特征。
(一)以连续性书写体制创造史诗性效果
魏金枝的小说创作贯穿着“五四”文学的审美传统,执着书写现实人生,关注底层苦难,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虽然都是中短篇作品,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前60余年中国乡村社会普通民众的人生状态,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60年的沧桑巨变,在一定意义上说构成了连续性短篇体式,显示了史诗性特征。整体上看,他的现代小说是一部20世纪前60余年的中国乡村社会演进史。《官衙》以幕府寂寞无聊的人生反映了辛亥革命之前的现实;《七封书信的自传》展示了封建势力与现代进步力量的殊死搏斗,反映了辛亥革命之后到“五四”之前的社会现实;《留下镇上的黄昏》《校役老刘》《奶妈》等描写了20年代乡村中国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死相与污浊气,展示了革命的自发性以及农民与革命的隔膜;《白旗手》《前哨兵》《制服》《野火》等描写了30年代社会革命中乡村世界的黑暗现实,反映了社会革命的基本情势以及革命者的成长历程;《家庭琐事》《山地》等表现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显示了30年代前期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磨捐》《凑巧》《想挂朝珠的三老爷》《羞明》等反映了三四十年代日寇入侵带来的灾难及其造成社会道德的崩坏和主体精神的裂变,暴露了汉奸的罪恶,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愿望与意志;《将死的人》《竹节命》《死灰》《客气》等对40年代后期黑暗的现实予以了讽刺和鞭挞,呼唤和平与民主,也深刻地反映了底层民众的苦难。《坟亲》长镜头地描写了20世纪前50年浙东乡村社会的演变历程,表现了守坟人等底层民众的苦难人生,史诗性特征尤其典型[7],在现代中短篇小说中非常罕见。他的当代小说反映了建国17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活路》《跟着他走》《老牯和小牯》等显示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民众走向新社会的心路历程,表现了紧跟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崭新气象;《两个小青年》《礼物》等表现了5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的新气象;《一个危险的计划》《义演》等描写了60年代初的社会政治情势,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核心领导作用。魏金枝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中国60多年的历史风云及其向现代化迈进的曲折历程,反映中国现代民族心理的演变轨迹,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30年和建国17年文学的发展状态,显示了史诗性的艺术价值。
(二)追求叙事的诗性化与复调性
魏金枝的小说打破了故事完整单一的传统叙事模式,以先锋性的探索精神展开了个性化的书写,不仅将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与限制性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融合起来,形成故事套故事的双重或多重文本,而且总是在现实主义描写中交织着浪漫主义的主体激情,甚至是现代主义的艺术风致,追求诗性化的叙事效果,形成了明显的复调性。因此,他的小说产生了比较丰富的审美意蕴,能够比较广泛地满足读者的阅读兴趣。《七封书信的自传》是一篇书信体小说,采取了转述的叙事方式,首先用《引》来交代:彬哥给了“我”七封信后便死了,“我”将它们串贯起来做他的自传,“以他的言语转告诸位读者”。彬哥写信是他自己叙述的,是第一人称。而“我”在小引中交代这七封信也是第一人称,但讲述的是第三者的故事,这就巧妙地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不同的叙事视角结合起来了,形成了彬哥体验的故事和“我”看彬哥的故事两个文本。同时,“我”又说“至于他的是非曲直,让诸位读者各自评定吧”,这又形成了一个隐藏文本——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建构的主观性文本。于是,小说既结构严密,又意蕴丰富。这种双重或多重文本叙事形态在《奶妈》《自由垃圾桶》《颤悚》等作品中都表现出色。《奶妈》就建构了“一个三重文本共存的先锋性的文本系列”,“形成了一种复调效果”[8]。魏金枝总是根据题材与主题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叙事方式,但诗化叙事是他一贯的自觉追求。他提炼出具有强烈表现力的审美意象,创造浓重沉郁的审美意境,并在传统叙事中融入诗性,凸显主观色彩和抒情特征,赋予作品以诗意,强化了艺术效果。《留下镇上的黄昏》《野火》《山地》《颤悚》等都出色地运用诗化叙事。如《山地》表现了农民与土地的紧密关系,山地、坟墓、乌鸦、老农以及曲折的小路和皑皑白雪等等,都构成了意象美,意境独特,诗意强烈。魏金枝文体创新意识强,注重叙事艺术,有的作品看似没有任何技巧,但实际上形成了明显的复调效果。《白旗手》《校役老刘》《坟亲》都是这样的名篇。《坟亲》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题材领域,其双重叙事视角形成了复调效果,赋予了作品的思想艺术张力[7];《白旗手》按照时间进程推进情节,又以意识流主导情节的推进,可谓独具匠心。黄献文说:“魏金枝在小说创作上的先锋性,使他与现代派有几分相近,所以施蛰存把他囊括在‘现代之群及其后继者’之内”[9]。这是他的小说叙事艺术带来的效果。
(三)对人性展开深层的探索
魏金枝的小说创作以人物为轴心,总是精心地描写人物性格,真实地展示人物的命运历程,深刻地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展开了浙东乡镇生动的各类人物画廊:共产党员、革命青年、乡村教师、苦闷青年、下级军官、封建家长、信士、巫女、土匪、乡长、保长、地主、保丁、学生、老板、汉奸、囚徒、士兵、农民、农妇、衰老者和残疾者以及历史人物,等等。但其艺术描写始终以人性为视角,寥寥数笔就能展示其精神个性,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魏金枝总是逼视人物的灵魂,挖掘人物心灵深处的审美力量。他既用漫画勾勒式的笔法直击人物丑恶的心地,也用细腻的描写层层烘托与渲染人物崇高的品格,还先抑后扬地表现民众优秀的品质。三老爷是横行乡里的恶霸和汉奸,他先是偷割麦穗,成为汉奸后明目张胆地成片横扫稻麦,灵魂极其丑恶;奶妈是一个共产党员,鹏飞先生和无聊旅客的误会不断烘托和渲染了她坚贞的革命信念、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和深藏心底而最终爆发的母爱;蜒蚰是个老婆被人强占了也不敢吭一声的怯懦者,可他当壮丁开小差逃回家后又为迫于生活的老袁和老李去当壮丁,其侠义精神和美好心灵感人至深。这些人物显示了感人的艺术魅力。他致力于写出人性的复杂性,既赋予人物鲜活性,也对社会进行批判。阿乜一生备受屈辱,为了生存而苟且偷安,别人与他妻子有关系,村民上山种植时玩弄他妻子,土匪欺负他妻子不成而将她打死,他都不敢反抗,但他将妻子被杀的地点牢牢记住,又对主人忠心耿耿,并埋藏一些番薯,期望度过这个冬天;勤务没有家室,跟着老李招兵多年却一点好处都没捞到,心里想着的乌狗老婆也被老李霸占了,这使他非常气愤,就与老李闹矛盾,最后带领新招来的士兵哗变。在这里,友情与爱情,性欲与义气,情感与理性,善与恶,好和坏,彰显了人性的多色调。人性是复杂的,角色不同,时空不同,都会呈现出不同状态。在现代作家中,始终进行人性的深层探索,并与时代情势统一起来,魏金枝是突出的。他将外视角和内视角相结合,写出人性的复杂性,富于深度,展示强劲的人性力量,艺术上很成功。
(四)浓郁的浙东乡土特色
列维·布留尔指出:“每个图腾都与一个明确规定的地区或空间的一部分神秘地联系着,在这个地区中永远栖满了图腾祖先的精灵,这被叫做‘地方亲属关系’”[10]。这个论断揭示了地域文化对人类的深刻影响。鲁迅描写鲁镇,沈从文描写“湘西世界”,老舍描写“北京城根世界”,都是地域文化影响的结果。魏金枝在浙东山区——嵊县(今嵊州市)黄泽镇的白泥坎村生活了17年,这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底色。他说:“只要我能在相当时期内回家去住上一阵,甚或找些到外地来的同乡人谈谈聊聊,讲一些乡间新发生的故事,讲一些熟人们的生活状况,我就马上能够把家乡的印象复活起来,而且顺当地把它延续下去”[11]。他的小说始终以浙东山区的村镇社会为表现中心,深刻地表现了浙东山区的人生苦难,反映了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巨变和世事沧桑,显示了浓郁的的乡土特色。首先,充溢着浙东山区的乡野之风。山峰梯田、溪水老井、青松修竹、年糕粽子、黄酒番薯、豆荚花生、笋干腌菜、山道田埂、篱笆草囤、土墩坟地、茅屋农舍、村夫农妇和集镇山寨等等,都显示了浙东山区特有的乡风情韵。《父子》以浙东典型的山地风情与乡民苦难的生活境况构成小说全篇,山地贫穷萧条凄惨的景象,以及山多田少,以番薯为粮,闹灾荒时,民众无米就去山地里寻找番薯根的生活状态,显示了浓郁的浙东乡土特征。其次,其小说人物显示了浙东文化个性。浙东文化是由刚硬劲直的“山文化”和宁静平和的“水文化”构成的,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性格。浙东山区孕育了“山文化”,山民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励志图强、剽悍善斗、宁折不弯、矢志复仇、行侠仗义、劫富济贫、求真务实、稳厚朴诚的主体性格;即使是外表很柔弱的人,其骨子里还是刚健任侠的。从《七封书信的自传》开始,其小说都反映了这种民气心性。如《跟着他走》中的庞大海为筹钱帮助夜校老师营救被捕的老婆,便回到宁波绑票克扣自己工钱的舅父,表现了嵊县山民行侠仗义的文化性格。第三,其民俗风情也显示了浙东文化特征。越剧是嵊县的民俗文化,最初称为“的笃戏”。魏金枝深受越剧的影响,不仅越剧活动成为其小说的艺术情境或重要情节,而且成为增强艺术价值的重要技巧。《义演》就是通过描写浙东民间的社戏风俗而弱化了时代政治的强势,坚守了小说的艺术取向,以乡土色彩增强了艺术效果。第四,方言俗语的运用,更显示了鲜明的乡土特色。运用方言创作,不单是选择语言工具的问题,也涉及到作者的思想表现和审美追求。周作人指出:“我们说到地方,并不以籍贯为原则,只是说风土的影响,推重那培养个性的土之力。……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3]。魏金枝运用越地方言创作,提高了作品的审美价值。《活路》用嵊县方言创作,既活化了人物性格,又增强了审美性。他的《白旗手》《校役老刘》《坟亲》等许多小说,总是巧妙地运用方言土语,收到了惊人的艺术效果。显然,魏金枝小说的乡土色彩既能展现了生活的原始美感,又增强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三、魏金枝小说的艺术渊源
一个作家的成功都取决于两方面:一是深厚的生活基础和敏锐的文学审美能力;二是前人的文学创作经验的启发和引导。作家只有在广泛吸收文学营养的基础上才能逐步走向成熟。魏金枝的小说创作除了自己扎实的生活基础与敏锐的文学悟性之外,还得益于中外文学的艺术滋养。探寻其小说创作的艺术渊源,我们认为魏金枝主要接受了契诃夫、鲁迅、郁达夫等中外作家的影响。
(一)契诃夫等外国作家的影响
20世纪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在吸收西方近代文学的营养中诞生。鲁迅明确说其小说吸收了外国文学的营养。魏金枝的小说创作自然也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启示,接受了西方文学大师的影响。从其小说创作和评论中可以看出,他明显受到雨果的影响,如他塑造了一些外表丑陋却心地善良美好、有着非凡精神品格的人物形象,这与《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形象加西莫多十分相似。但相对来说,契诃夫对他的影响更大。从《编余丛谈》可以看出,魏金枝对契诃夫非常推崇。他不仅对小说《套中人》《小公务员的死》等小说评价很高,而且对契诃夫的文学主张也有深刻的理解和认同。他认为契诃夫短篇小说“趋向于朴素无华”,初学写作的人“先走契诃夫”那一路比较稳健。契诃夫要求作家抓到故事的典型情节,人物的典型性格,活动的典型意义,他认为抓到了这些,“也就抓到了作品的生命”[12],就将这些写人的主张教育引导文学青年。显然,他接受了契诃夫的文学观念的影响。同时,他也接受了契诃夫的小说创作模式与技巧的影响。例如他的小说故事性不强,重在小说环境的表现,与契诃夫的小说十分相似。无论哪一篇小说,他都没有集中描写人物的外貌,而是在人物的言行进程中不断完成的,这与契诃夫的人物外貌描写是一致的。而且,契诃夫描写的是小人物,魏金枝也以描写小人物为主。《校役老刘》中塑造的勤杂工老刘,明显接受契诃夫的影响。老刘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为着饿便从故乡里流浪出来,在这高深而神秘的学校里做校役,地位十分卑微,很少有人和他说话,而他又想和人交流,因此他常常只能对着那些替学生管理的农具倾吐心声。老刘的这种生命状态,与契诃夫小说《苦恼》中的老马夫姚纳极为相似。姚纳刚刚死去儿子,心里非常痛苦,没有谁能够倾听他的心声,所以只能对着他的小母马诉说自己的痛苦。可以说,老刘是契诃夫笔下的老马夫姚纳的原型置换。在魏金枝的小说中,对于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艺术处理,也和他所论述的《小公务员的死》的方式是一样的。如《奶妈》《坟亲》《死灰》《客气》等等,在批判现实社会时,并不正面去写环境的黑暗和丑恶,而是通过人物的性格去反映。契诃夫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很广泛,魏金枝的小说创作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
(二)鲁迅、郁达夫等人的影响
魏金枝是从“五四”走向文坛的,也接受了“五四”小说的影响。“五四”小说一开始就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创作和以郁达夫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创作两种路向。魏金枝的小说创作不仅受到鲁迅的影响,也受到郁达夫的影响,形成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特征。鲁迅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全面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魏金枝可以看成是鲁迅小说“直系的传代者”。他不仅自觉地继承了鲁迅的文学精神,而且发扬了鲁迅的艺术传统,在鲁迅开拓的艺术路向上取得了重要成就。这不仅体现在国民性批判与人的价值关怀的主题上,而且体现在人性探索与表现的深切上,还体现在小说文体的创新与探索上[13]。我们曾专门对此展开过论述,这里不再赘述。郁达夫自叙传小说对魏金枝小说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魏金枝早期小说也是自叙传式的,主观抒情性强,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后来的小说也始终笼罩着一层浪漫的抒情气氛,显示出一定的唯美性特征。这种审美取向,与郁达夫的自叙传抒情小说的影响有关。“自叙传”主观抒情小说是以《沉沦》为代表的,主体意识很强,通常叙述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与命运,塑造忧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充满着悲愤的情绪与深挚的情感,主观性和抒情性很强。魏金枝最初的乡土小说与众不同,以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书写和心灵解剖为中心,反映封建乡村的沉滞之气和封建主义的腐朽之气,主人公总是向人们倾诉自己的亲历见闻和悲惨命运,显示了非常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如《七封书信的自传》《祭日致辞》《裴君遗憾》《沉郁的乡思》《小狗的问题》《香袋》《留下镇上的黄昏》等等,都显示出悲愤的情绪,主人公的孤寂、苦闷、忧伤与《沉沦》中的主人公十分相似。然而,他的小说与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又有一些不同。首先是没有郁达夫小说的病态美,其次是有浓郁的诗意。魏金枝小说的鲜明特点是不乏诗情,饱含着浓郁的诗意,与郁达夫自叙传抒情小说忽视诗意不同。这与魏金枝首先是一个“五四”诗人有关系[14]。魏金枝认为:“一切文学形式的作品,都应该有诗意,这就是文学的美学原则”[15]。这种文学观念,也成为魏金枝小说创作基本的审美立场。
魏金枝作为“五四”第一代作家,他接受了中外文学的影响,始终忠诚于文学,是一个创作特色鲜明、文体意识自觉、艺术追求执着、文学成就较高并具有一定影响的优秀作家。在创作中,不管时代情势如何变化,他总是能够尽力保持独立、自主的创作姿态。即使是政治情势非常急迫的时候,也没有放弃文学创作上的自由精神,始终都追求文学的审美价值,发扬了鲁迅的传统。他的创作不仅感动着一般的受众,感动了鲁迅,还感动了毛泽东。“1956年,魏金枝作为上海地区的人民代表和文艺界的代表,曾赴北京开会。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接见过他,与他一边握手,一边说起他写的某些文学作品”[16]。周作人指出:“我们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了一切的束缚,任情地歌唱,无论人家文章怎样的庄严,思想怎样的乐观,怎样的讲爱国报恩,但是我要做风流轻妙,或讽刺谴责的文字,也是我的自由,而且无论说的是隐逸或是反抗,只要是遗传环境所融合而成的我的真的心搏,只要不是成见的执著主张派别等意见而有意造成的,也便都有发表的权利与价值。这样的作品,自然具有其特性,便是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也即是他的生命”[3]。这句话用来估定魏金枝小说的成就与价值,还是比较准确的。
[1]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98,299,291.
[2] 鲁迅.我们要批评家[C]//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1.
[3] 周作人.地方与文艺[C]// 张明高,范桥.周作人散文:第2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12-214.
[4] 汪乔英,汪雅梅.金丁文集:我仿佛在梦中[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291.
[5] 魏金枝.反对教条和公式主义[C]// 魏金枝.文艺随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39.
[6] 涂光群.上海老作家们——十位上海老作家侧记[J].新文学史料,2004(1):100-108.
[7] 刘家思,周桂华,周宜楠.论魏金枝四十年代的小说代表作《坟亲》[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2):46-51.
[8] 刘家思,刘璨.左翼文学中的“另类”风景——魏金枝短篇小说《奶妈》的文本解读[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5(2):70-74.
[9] 黄献文.论新感觉派[M].湖北:武汉出版社,2000:14.
[10]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84.
[11] 魏金枝.谈谈失败的经验[C]//魏金枝.编余丛谈.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136.
[12] 魏金枝.漫谈短篇小说中的若干问题[C]//魏金枝.编余丛谈.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46.
[13] 刘桂萍,刘家思.论魏金枝小说创作对鲁迅小说的继承和发展[J].鲁迅研究月刊,2014(4):39-47.
[14] 刘家思,刘桂萍.论魏金枝“五四”时期的新诗创作[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93-100.
[15] 魏金枝.写诗随谈[C]//魏金枝.文艺随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73.
[16] 孙琴安.毛泽东与中国文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247.
(责任编辑:薛 蓉)
On the creative experiences,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art originof Wei Jinzhi’s local novels
LIU Jiasi1,LIU Guiping2
(1.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xing 312000,China;2.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Branch, Ningbo Polytechnic, Ningbo 310058, China)
Wei Jinzhi’s local novels begin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and end on the ev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consist of several stages including periods of dull local narration, personalized revolutionary narration, allegory and exposure of country, and country ode of New China. Distinct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re developed in his novels. First, his successional writing system creates an epic effect. Second, these novels pursue the polyphony narrative effect. Third, a deep exploration of humanity is carried out. Fourth, these novels with distinctive local characteristics are of high aesthetic value. His novels are mainly influenced by a number of well-known writers such as Chekhov, Lu Xun and Yu Dafu.
local literature; Wei Jinzhi’s novels; creative experiences;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rt origin
2017-04-12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09JDYWO1ZD);浙江省省级出版资助项目(015CBB09)
刘家思(1963—),男,江西宜春人,教授,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绍兴文史研究;刘桂萍(1963—),女,黑龙江鹤岗人,教授,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I207
A
1006-4303(2017)02-02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