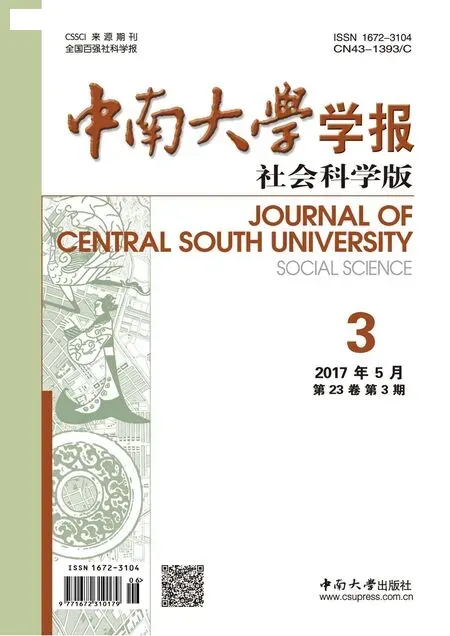国有企业特殊法制在现代公司法制中的生成与安放
李建伟
国有企业特殊法制在现代公司法制中的生成与安放
李建伟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102249)
回顾国有企业法制在现代公司法制背景下的生成历程,不能离开现实国情来把握国有企业法制的发展趋向。国企法制作为一种深具中国国情的现代企业法制安排,首先要遵循现代公司法制尤其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同时也要积极探索适合国情与国企现状的治理模式。在此话语背景下,坚持党对国企的领导不动摇与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是全面从严治党在国企改革的题中之意,关键要坚持在现代公司治理的制度框架内来落实党的领导方式,以形成现代公司治理框架下的国企治理模式,而非另起炉灶来构建迥异于现代公司治理模式与精神的党管治理模式。一项新的法制课题是,作为基本法律的《民法总则》关于营利法人治理结构安排的最新规定,为国有企业治理模式框定了新的基本架构。
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法制;党的领导;公司治理;营利法人
2015年6月5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若干意见》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提出要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体现和加强。对于《若干意见》的各种政策解读一时迭出。有引经据典证明“加强党的领导”为我党领导国企改革的一贯主张,此次会议乃是党建工作的例行的周期性强调,也有称之为“旧瓶新酒”不乏新时期崭新意蕴的,也有积极肯定“加强党的领导”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还有不同声音称之为国企改革又要开始重申“党要管企”、重新“回潮”走老路的,甚至有国企改革退步论的担忧等等[1−7]。对一项政策举措的多重价值判断本属正常,但从另一个视角看可能也增加了人们的评判力和彷徨感,甚至有人担心为此影响了人们深化国企改革的动力和信念[8]。那么,就《若干意见》关于在国企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之主张,之于国有企业治理模式及其制度安排的法律影响力如何,以及其具体的政策措施如何获得法律机制上的恰当生成与安放,需要展开深入的讨论。
一、国有企业法制在我国现代公司法制体系下的特殊性
近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一直与国有企业改革密不可分,且多数时间都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与此相适应,国有企业法制也是我国公司法制绕不过去的重大课题,可以说国有企业法制是中国最大的公司法制问题。回顾三十多年来国有企业法制的生成,可谓路径多元[9]。自1979年至今,我国渐次形成了二元企业立法模式:一是按所有制进行企业立法,分别制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企业法、私营企业法、“三资”企业法等;二是按现代企业制度立法,分别制定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问题是,后一立法体系实施后,前一立法体系并未废止,于是出现国有企业同时适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1988)、《公司法》(1993)的状况,但两部立法在基本层面上具有重大的制度差异。2008年颁布《企业国有资产法》,意图实现从国有企业主体立法到国有资产立法的重大范式转型,即不再把国有企业当作特殊主体,而将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视为规范客体,实现从管主体到管资产的转变。但这一转型并没有收获如期的成功,其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国有资产法》仅仅适用于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数量庞大的国有金融资产并不适用;另一方面,从管主体到管资产的转变,是一种重大的治理范式转型,需要深层次的配套制度生成与诸多体制改革措施相配套,但从目前来看后者跟进乏力。
在国有企业治理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方面,自1993年颁行《公司法》以来,总体上朝两个方向努力。
一是朝着现代公司法制的方向努力。这包括两个基础性制度的建构: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改制、产权重组、上市、股权分置改革、混合所有制等重大举措,努力实现竞争性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众所周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建立在产权多元的基础上,不论是家族企业还是国有企业,若产权单一,很难建立多元利益、权利制衡的公司治理体系。另一方面,以委托代理机制为中心,通过建立股东大会、监事会与董事会等“新三会”,董事会试点、引入独立董事、外部董事、独立监事等重大举措,来初步建立符合现代公司法制的制度架构与精神的法人治理制度。2016年10月中央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强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正是对于这一方面的制度努力的最新肯定。但是,截至目前,虽然国有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真正符合委托代理机制精神的现代公司治理运行机制在多数国有企业并没有运行起来,在取得真正的制度实效方面尚任重道远。
二是强调国有企业治理制度与运行机制的特殊性,并在此方面渐次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比如,以《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确立的外派监事制度为基础,形成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体系。这些制度努力的基本背景是,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在国有企业生成之后,也出现了诸多水土不服的现象,有些制度安排非但没取得预期效果,甚至南辕北辙。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对于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监督制度、机制的设计与实践上出现了较严重的问题。如何切实有效地监督国有企业领导人,预防与惩治其管理腐败与管理低效,成为一个突出的棘手问题,长期影响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这就需要在现代公司法制之外另辟蹊径,积极探索符合中国现时“国情”、国有企业“企情”的有效治理机制。多年来,国有企业在此领域探索过,做过多种努力,比如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强调企业纪委与工会的监督职能,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引入外部监事会制度,施行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等。这些制度举措有的坚持实施了几十年,有的正在试运行,总 之都是在现代公司法制之外进行的宝贵探索。总结来看,目前在多个层面与领域内进行的国有企业特殊法制,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就是党的领导地位在国有企业治理制度中的安放,这也构成了各项制度生成的一条主线。
二、国有企业治理面临的主要矛盾与问题分析
尽管我国在立法形式上只有一部公司法,但在实质制度运行意义上存在三部公司法制。一是普通公司法制,即指1993年颁布并施行至今的《公司法》。这部《公司法》几经修订,目前关于国有企业的特殊规范安排已很少了,关于上市公司的特殊规范也仅有5个条文,实际上这部公司法是以普通公司(主要是民营企业、非公众公司)为假设主体对象的,构成了我国普通公司法制。二是上市公司法制,主要是指中国证监会、深沪证交所等颁布的以《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为代表的庞大法律规范群(包括“软法”规范),其制度安排更接近于美国等发达资本市场的公众公司法。三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法制,不仅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更庞大的法律规范则是由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工信部以及地方人大与政府等主体发布的行政法规、规章群组成,以外部监事会制度、试行董事会制度等特殊制度设计为代表,还包括中国共产党颁布的关于坚持与强化党在国有企业中的领导地位为核心的一系列党内法规[10]。所有这些关于国有企业的法律规范群,在普通公司法制之外生成了适用于国有企业的一整套法律法规体系,可谓之为国有企业特殊法制。
那么,在普通公司法制之外生成与运行的国有企业特殊法制,主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一问题的回答众所周知,解决国有企业的治理问题。如前所述,国有企业在进行现代公司改制过程中,或者在模仿现代公司制度构建新的法人治理结构的过程中,基本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或者类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成绩卓著①。但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依然存在突出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是由国有企业特殊的“两权分离”即“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造成的。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先天性缺位,经营者缺乏必要的产权约束,导致经营者实际上享有了所有者的多数权力,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导致国有企业易于陷入“内部人控制”。事实上,国有企业的贪腐与低效问题都比较严重,“九龙治水”式的监管机制尽管多头治理,但功效不显,甚至很多时候如同虚置,出现整体性失灵。总之,所有者单一导致了委托代理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所有者实质缺位导致了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要解决上述问题,除了坚持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之外,还需要强化对于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监督制约机制。关于后一方面,经过多年的艰苦摸索与制度创新,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成为最重要的制度建构共识,也是国有企业治理的核心制度配置。
三、国有企业治理特殊模式论:国有企业法制的重大发展方向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不仅仅作为产品、服务的提供者这一经济组织而存在,还具有更多的政治功能担当——国有企业关乎国家经济的命脉,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②。这些政治功能担当,客观上需要国有企业有充分理由在现代公司治理模式之外植入若干特殊治理制度元素,形成独具中国现实国情的国有企业治理特殊模式。
所谓独具中国现实国情的国有企业治理特殊模式,基本原则与核心制度设置就是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2015年先后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政策文件,是引领近期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依据。在2016年10月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这一基本原则,并系统论述了加强党对于国有企业领导的重大意义与举措。这给国有企业法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围绕着“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这一基本原则,国务院国资委等主管部门连续出台的若干文件都在沿着这一方向而进行制度设计。关键是,在国有企业制度尤其是法人治理实践中如何正确理解与切实落实“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这一基本原则?
按照目前的制度设计,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一项重大政治原则。国有企业特殊法制,“特”就特在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发挥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②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被视为国有企业特殊法制的应有之意,也是国有企业特殊治理模式的内核,要在现代公司法制框架下正确理解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需要申明以下几个基本立场。
第一,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首先,按照目前的制度设计,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可以归纳为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权、权力监督权与重大人事决定权等三个方面,重心落在强化党组织对国有企业治理的领导作用。其次,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这是一个政策引导,不会也不应该去触及或否定董事会作为现代公司治理经营决策权这一中心。质言之,党组织这个“核心”与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中心”之间不能冲突与矛盾。再次,可以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的章程,明确党组织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创新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和方式。最后,党的领导在国有企业中的落地机制是一个前置决策程序,加强党的领导在实际操作中的度不容易把握,弄不好就易于挤压董事会的原有决策权利,所以不仅要有原则性规定,还要有细致化操作指南,更要积累治理机制的新经验,在实践中及时总结与归纳,明确相关机构与领导人的权力,强化责任机制。
第二,坚持权力和责任相统一的原则。加强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对于现代公司治理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与挑战在于权力、责任如何对应的问题。党作为决策者的责任如何纳入公司法治理结构内既有的信义义务体系?《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8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企业中的基层组织,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实行保证监督。”由此可以看出党作为权威的监督者,不存在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如党组织成员在前置决策出现了问题,可以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对责任人进行处分。如董事会决策出现问题,则凭借公司章程、公司法追究法律责任。那么,可否考虑将加强党组织领导理直气壮地写进国有企业章程、法律文件的同时,从法律层面设计好违反党规党纪与公司法上的承担违信责任的制度衔接?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第三,内嵌入既有的公司治理机制,坚持制度自信。从国际市场看,强调党的领导可能会造成境外对我国国有企业形成党企不分的印象,导致国有企业境外并购困难等。为此,一方面要稳步推进竞争类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也要勇于公开宣称国有企业的独特领导机制,并加以法制化、制度化,坚持制度自信。因为执政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是一致的,党组织及其特殊治理机制“嵌入”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可以构成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公司法》第19条早有规定,“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这一规定被视为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必然要求,体现了依法执政的理念[11]。既然《公司法》对所有公司的党组织设立给予了合法地位与活动空间,那么对国有企业而言更不必说,关键是要据此加以制度化,早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第四,全面从严治党政策适用于国有企业,具有内在的积极反腐败价值。在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与“若干意见”一并通过的还有《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简称“防流失”文件)。因为与“防流失”文件的一并出台,自然使得“若干意见”深具国企“反腐”的深刻背景。国有企业不是执政党政治治理体系的法外之地,全面从严治党的政策措施适用于国有企业,对于当前一个阶段内预防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抑制国有企业的腐败,具有积极的制度价值。“加强党组织建设,在于强化国有企业党组成员的政治责任、主体责任”[12],发挥党组织在国有企业内部的强大组织约束力,增强党组织成员的政治意识、核心意识,有利于建立适合国有企业“企情”的内控机制。
要之,要正视国企产权结构与治理模式制度设计的先天性特性。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先天性缺位,经营者缺乏必要的产权约束,导致经营者实际上享有了所有者的多数权力,而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导致国有企业易于陷入“内部人控制”。那么,党对国有企业领导这一核心制度安排果真能解决所有者实质缺位所导致的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客观事实吗?如果可以,现行此种特殊制度安排怎样才能与普通公司法制即在产权多元、两权分离与代理理论等基本制度假设基础之上的现代公司法制的前提下进行衔接?如果无法实现无缝衔接,也要追求退而求其次的较好衔接?这就是我国国有企业治理模式及其制度设计面临的基本挑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换,改革课题如何表述与设置,数十年来可谓万变不离其宗。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改革任务设置的重点与攻坚方向略有差异而已。数十年来,国有企业治理改革的基本面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法制发展与改革的探索过程一直在持续。
四、《民法总则》关于营利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规定及其落实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二部分“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的“(四) 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此,要“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我国民法典编纂是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己任的,而企业制度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微观基础,民法典关于企业法人的法律规范属于基本法律的规定,不能不引人注目。
按照有关立法规划,民法典编纂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制定民法总则。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民法总则》全新规划了法人分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的组织形式不断出现,法人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民法通则关于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的分类已难以适应新的情况,有必要进行调整完善。草案遵循民法通则关于法人分类的基本思路,适应社会组织改革发展要求,按照法人设立目的和功能等方面的不同,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3类”③。这就废止了1986年《民法通则》关于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的分类模式,而将法人划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与特别法人,营利法人又进一步区分为公司企业法人与非公司企业法人④。据此,已经完成公司改制的各类国有企业为公司企业法人,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国有全资公司以及国有控股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尚未完成公司改制的国有企业也即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属于非公司制企业法人。比如,中石油集团系统内的上千家各类企业集团中,处于金字塔塔尖也即控股地位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按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设立的国有企业,即为非公司制企业法人,属下最大的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制企业法人,是按照《公司法》设立的国有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一家上市公司。公司制国有企业法人与非公司制国有企业法人原来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实行截然不同的法人治理模式:前者适用1993年颁布且其后经多次修订的《公司法》,被要求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机关,包括股东大会(股东会)等权力机关、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等执行机关、监事会或者监事等监督机关;后者适用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试行经理(厂长)负责制,以总经理(多数兼任党委书记)为企业负责人(法定代表人),股东大会(股东会)等权力机关,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等执行机关,监事会或者监事等监督机关都不被要求建立。具言之,由于非公司制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单一(名义上为国家,实际上为各级国资委代行出资人职责),所以也就一直不存在股东大会(股东会)等权力机关。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非公司制国有企业开始实行外派监事会制度⑤,算是对内部不建立监事会的一种弥补措施。究其制度实质,无论从起源、发起过程还是从其建立的社会基础看,都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特点,本质上是一种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安 排[13]。其后,在国务院国资委等多部门推动下,部分非公司制国有企业模仿现代公司制度开始尝试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组织结构,如部分央企和地方国企试行董事会制度⑥。但总体而言,多年来绝大多数非公司制国有企业法人并未实行现代公司治理模式。
但是,按照《民法总则》的统一规定,所有的营利法人,无论采用公司制与否,都要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包括设立三类法人机关:一是权力机关。《民法总则》第80条规定,“营利法人应当设权力机构。权力机构行使修改法人章程,选举或者更换执行机构、监督机构成员,以及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二是执行机关。第81条规定,“营利法人应当设执行机构。执行机构行使召集权力机构会议,决定法人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决定法人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以及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执行机构为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的,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担任法定代表人;未设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的,法人章程规定的主要负责人为其执行机构和法定代表人”。三是监督机关。第82条规定,“营利法人设监事会或者监事等监督机构的,监督机构依法行使检查法人财务,监督执行机构成员、高级管理人员执行法人职务的行为,以及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上述规定的重大制度价值有三:一是统一各类营利法人的法人机关设置,凡营利法人皆须设置权力机关、执行机关与监督机关,这就消除了此前不同类型的营利法人适用不同治理结构的做法;二是从立法上明确了各类法人机关的法律地位以及彼此之间的权责关系,为构架“权责明晰”的法人治理结构奠定法律之基;三是对照目前的非公司制国有企业法人的治理 结构现状,要求其尽快完善尚缺位的诸法人机关的 设置,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以符合《民法总则》的立法要求。
关于上述第三点,对于建立健全非公司制国有企业法人的法人治理结构而言,具体包含了三个重要而紧迫的法律课题。其一,尽快建立法律规范意义上的董事会制度。虽然此前部分非公司制国有企业法人试行了国资委推行的董事会制度,但其法律依据仅仅在于国资委的一份行政规章,法律文件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均为不足,在实践中的效果也未尽如人意,并未真正成为现代企业制度意义上的公司执行机构、决策机构[14]。但在《民法总则》生效后,非公司制国有企业法人建立董事会制度所依据的法律规范的权威性与位阶性已全然不可同日而语,构建真正规范意义上的董事会制度不仅应该成为全体(而非试点单位)非公司制国有企业法人的要求,而且是一项基于国家基本法律的要求。其二,如何建立权力机构?按照前引第80条的要求,国有独资公司以及非公司制国有企业法人作为营利法人也要设立权力机构,权力机构行使修改法人章程,选举或者更换执行机构、监督机构成员,以及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但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不同于公司制国有企业法人的是,国有独资公司、非公司制国有企业法人都不具有多元的股权结构,出资人单一,无法建立由两个以上的法人成员(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或者股东会制度。目前按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使出资人(相当于公司股东)职权的是各级人民政府的国资委。基于国资委的代议制、外部性抑或单一性的特性考虑,如从立法规定的文义解释立场出发,实在难以充当上引第80条所规定的国有独资公司、非公司制国有企业法人的“权力机关”。那么,如何建立国有独资公司、非公司制国有企业法人的权力机关,一条现实的可行性出路就是尽快实现这些国有企业的现代公司改制,改制为股权多元的公司制企业法人之后,再依法顺理成章地建立股东大会(股东会)等权力机关。问题是,如果最终仍有个别的国有独资公司、非公司制国有企业法人不改制为股权多元的公司制企业法人,其符合第80条规范意义上的权力机关如何设立,尚需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或者依赖立法规定的再完善,或者确立更具灵活性的立法解释规则。其三,外派监事会制度的出路,改制抑或废止?实行了十几年的非公司制国有企业外派监事是否符合上引第82条关于营利法人监督机关的规定,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笔者认为,虽然依照第82条的文义解释,非公司制国有企业的外派监事被解释为是一个符合本条规定的监督机构也是可行的,但究第82条的立法意旨,以及现代企业法人机关的基本法理,包括权力机关、执行机关等在内的所有法人机关都应该是内生性的机构设置,监督机构也不应例外,所以外派监事会至少不是规范意义上的监督机构。外派监事会的未来制度出路:一是大力推动非公司制国有企业改制为公司制,然后设立合乎《公司法》的规范也合乎《民法总则》第82条规定的内设监事会制度,外派监事会自然终止;二是在非公司制国有企业早日实行内设监事会制度,由《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规定的外派监事会制度应该被明确为一项暂时性、应急性的制度安排,不应也不能长久持续下去。
最后,还要指出,《民法总则》关于营利法人治理的制度设计,除了上述关于法人机关的规定之外,还有不少治理行为规则是将现行《公司法》规范中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条款上升为适用于所有营利法人的规范,考虑到公司制企业法人本来就适用这些规定,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非公司制企业法人适用与公司制企业法人共同的治理规则。这些规定主要有:①章程必设制度:设立营利法人应当依法制定法人章程(第79条,《公司法》第11条有同样规定)。②出资人滥权赔偿制度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不得滥用出资人权利损害法人或者其他出资人的利益,否则,给法人或者其他出资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也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损害法人的债权人利益,逃避债务,严重损害法人的债权人利益,否则,应当对法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83条,《公司法》第20条有同样规定)。③禁止不公平的关联交易:营利法人的控股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法人的利益,否则,给法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84条,《公司法》第21条有同样规定)。④决议可撤销制度:营利法人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作出决议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法人章程的,营利法人的出资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议,但是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第85条,《公司法》第22条有同样规定)。⑤营利法人承担社会责任: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第86条,《公司法》第5条)。以上诸规定,乃是关于营利法人的治理行为规则,其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是强制性地提升非公司制国有企业法人的治理水平,尤其是关于强化非公司制国有企业出资人的法律责任的多处规定,将有利于推进政企分开。二是将非公司制国有企业与公司制国有企业的治理适用于同一法律规范,将推进所有的营利法人治理制度与治理水平的一体化。
五、余论:坚持推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与治理分类改革
前述三类公司法制体系的划分目的在于厘清现有企业法制的各类主体,构建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法律制度。问题是,是否将所有的国有企业都纳入国有企业特殊法制体系?国有企业的范围在很多立法场合下是比较模糊的,现存的国有企业至少有5种: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全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等。国有参股公司是否也一并适用国有企业特殊法制体系?相关政策与法律文件要么语焉不详,要么相互冲突,故无讨论之必要。从长远来讲,既然将国有企业法制定位于特别的企业法制,应充分保证普通企业法制的实施空间,这就不能将所有类型的国有企业不分程度、不分轻重地一体纳入其中。应该说,鉴于国有企业存在状态的复杂性与繁复性,法律适用上要避免“一刀切”。为此,长远来看,仍有必要讨论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核心与基本路径就是坚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的多元化改革。如没有产权多元化,现代公司治理机制难以真正运行,适用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的结构安排,是区分市场与计划的制度安排。事实上,我国国有企业整体经历了从全资、到控股、再到持股的产权多元化进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进行产权改革,继续促进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深入开展。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这类企业可以采取国有独资形式,具备条件的也可以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等方式,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经营。”⑦需要厘清的是,适用国有企业特殊法制的对象,将来主要是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包括核工业、航天、军工、石油、电力、自来水等极其特殊的行业。适用国有企业特殊法制的应否包括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目前的回答无疑是肯定的。但长远来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国有经济的改革规划,改革方向是将竞争类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坚定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革,其将来应当更多地适用普通公司法制。
注释:
① 2015年度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有110家,数量上居世界第二,其中83家是国有企业。引自《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2日,04版。
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0月10日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原文。
③ 引自李建国副委员长2017年3月9日在十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
④ 《民法总则》第76条规定:“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等出资人为目的成立的法人,为营利法人。营利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等。”
⑤ 国务院2000年颁布《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其第2条规定:“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以下简称监事会)由国务院派出,对国务院负责,代表国家对国有重点大型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实施监督。”
⑥ 2004年6月7日,国资委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建立和完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工作的通知》,由此开启非公司制国有企业引入董事会的试点工程,在10多年间先后有60家左右的国企试行董事会。
⑦ 引自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1] 人民日报评论. 深化国企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EB/OL]. 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6−10−09.
[2] 李景治. 深化国企改革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J].学术界, 2016(8): 5−17.
[3] 王金柱. 如何在深化国企改革中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5(11): 44−46.
[4] 冉令军. 深化国企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现实思考[J].改革与开放, 2016(7): 56−57.
[5] 朱继东. 深化国企改革为什么必须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J]. 红旗文稿, 2015, (19): 72−77.
[6] 李烈满. 建国以来国企领导体制沿革与党的建设的回顾与思考[J]. 党史研究与教学, 1998(5): 39−45.
[7] 王梓木. 党企结合是体制上的倒退[EB/OL]. http://finance.sina. com.cn/hy/20130825/110516554512.shtml, 2017−01−03.
[8] 安林, 王彪. 深化国企改革“加强党的领导” 不是“党企不分”、“党要管企”[J]. 董事会, 2015(7): 84−85.
[9] 李建伟. 中国企业立法体系改革:历史、反思与重构[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4.
[10] 强世功. 从行政法治国到政党法治国——党法和国法关系的法理学思考[J]. 中国法律评论, 2016(3): 35−41
[11] 马怀德. 依法执政与公司法第19条的规定[J]. 党建研究, 2006(7): 52−53.
[12] 人民日报评论. 把国有企业党建责任扛起来——三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讲话精神[N]. 人民日报, 2016−10−14(03).
[13] 冯梅. 国有独资企业外部董事、外派监事会制度:一种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安排[J]. 生产力研究, 2006(3): 192−193.
[14] 赵嘉妮. 央企董事会制度试行十年,更多流于形式[N]. 新京报, 2014−07−01, (B08).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Es’ special legal system in the modern company law
LI Jianwei
(School of Civil, Commercial and Economic Law,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2249, China)
Reviewing the generation process of SOE’s legal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company law, we find that we cannot go away from our real national conditions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se legal systems. The legal systems for stated-owned enterprises, as special legal systems for modern company with strong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hall first follow modern company laws, particularly rules of modern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On the other hand, governance models shall be explored more actively for stated-owned 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conditions of China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is discourse context, it is advisable for strictly gover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y sticking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enforc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of these enterprises, and the key is to develop governance models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y insisting on the leadership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in modern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rather than to take off in a new direction in building a party supervision governance model, which is profoundly different from modern corporation governance model and spirit. A new topic of law is that, as a new basic regulation about the governance model of profitable legal person, frames a new basic structure of state-owned corporation’s governance model.
state-owned corporation; modern company laws; Party leadership;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fitable legal person
[编辑: 苏慧]
D912.29
A
1672-3104(2017)03−0041−08
2017−01−10;
2017−04−11
中国政法大学“商法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项目(2015-2018)
李建伟(1974−),男,河南周口人,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经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