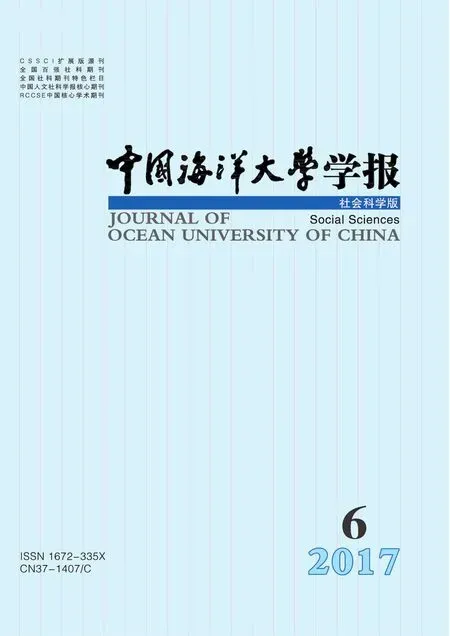19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中的闯入者形象及其叙事伦理*
曹丙燕
(1.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2.山东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510)
19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中的闯入者形象及其叙事伦理*
曹丙燕1,2
(1.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2.山东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510)
“闯入者”是城市文学中具有共名性和隐喻意义的文学形象,他们主要由外省知识青年、农裔及部分小城镇青年构成,其中女性闯入者也是不可忽视的群体。闯入者带着世俗欲求和梦想闯入城市,但他们从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场域进入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场域,文化上的断裂感使城市“闯入者”成为城市“异乡人”。闯入者的悲剧叙事不具有宏大的悲剧力量,却因个体自由叙事立场而获得了抱慰生命的叙事伦理价值。
城市文学;闯入者;异乡人;叙事伦理
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中,城市外来者形象因数量众多且具丰富的阐释性而倍受关注,“农民工”“乡下人”“打工者”“城市外来者”“城市移入者”“闯入者”“漂泊者”,作为文学批评概念,研究者给予这类文学形象的命名不一而足。笔者更认同“闯入者”的指称:一方面,“闯入者”更具概括性,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社会结构形态的丰富,城市外来人口在构成上早已由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农民工群体,变为由农民工、职场白领、各类自由职业者等共同构成的庞杂群体;另一方面,“闯入者”更能生动展示外来者“他者”化的生存样态,他们闯入城市的行为貌似是主动的、理性的选择,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认清“自我”与“城市”的关系,只是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进入城市,最终成为流浪在城市的“异乡人”。
一、城市文学中三类“闯入者”形象
对于城市文学,主体形象至关重要,它很大程度上承载着城市文学的风貌特征,大量形象驳杂、身份不一的“闯入者”形象的出现,正体现了处于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学的基本特点。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根据闯入者在城市中的阶层状况、生存处境及性别等方面的因素,大体分为以下三类:
一类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职场白领、艺术青年、创业者等知识青年,他们大都来自异地的中小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有知识、有能力、有明确梦想——作家梦、明星梦、发财梦、创业梦,以寻宝或寻求人生价值的姿态来到大城市,对于他们而言,城市象征着财富、自由、机遇、成功,《手上的星光》里初来北京的乔可和杨哭,尽管不名一文却信心满满,因为他们相信机会“就像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漂亮的小鱼一样多”。[1](P1)《啊,北京》里梦想着成为作家的“我”毕业后坚定地做了“北漂”,因为“人人都说北京是个机遇遍地的地方,只要你肯弯腰去捡,想什么来什么。”[2]这些年轻的闯入者将自己全力投掷到繁华喧嚣的城市生活中,摩拳擦掌、奋力拼搏,凭借青春的闯劲和悟性,他们有能力在城市拥有体面的工作、可观的收入,能够出入各种娱乐社交场所,闯入城市仿佛并不是个难题。但是这类闯入者的城市梦不止是世俗层面的成功,还要展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像乔可所说“我想我们在这里得到的不只是名利、地位,还有爱情和对意义的寻求。”[1](P2)因此,城市被这类闯入者视为生命的目标和方向,承载着自我价值实现与建构的意义,这让他们闯入城市的行为具有了审美意义和乌托邦性质。但是现代城市以商业文化、消费文化为主导,购物中心、娱乐会所、大酒店、高级公寓、别墅、时装、酒吧这些浮华躁动、光怪陆离的城市文化符号,刺激着闯入者的世俗欲望不断膨胀,他们很快就发现“一切梦想和浪漫在远离我,我发现原来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原来每一个人都是在为房子、票子和位子而活着。”[1](P161)“在现代社会,人的需要和欲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需要和欲望颠覆了理性在整个世界和社会秩序中的统治地位,他们不再自下而上构成了对于理性的威胁,而是成为了理性的主宰。”[3]在消费理性的主导下,人们对物质的占有已不是生存的需求,而是存在的标志,是人的意志力的凝聚,正如卢卡奇所说“物化了的世界最终表现为唯一可能的、唯一从概念上可以把握住的、可以理解的世界,即为我们人类提供的世界。”[4](P79)对于这些雄心勃勃的闯入者,对物质的占有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最直接最可靠的方式,《行为艺术家》(邱华栋)中的我,因为“开始自由出入这座城市的巨型购物中心、大饭店、酒吧、地铁、银行、国家机关、医院、大学校园、快餐店而毫无陌生感,我有三张信用卡、一张本市身份证、一个邮局保密箱、一个汉字寻呼机、两张电话磁卡、一个数字式大哥大”,[1](P62)对于这些城市文化符号的占有,使“我”自信已经成为城市的主人。但是这种建立在物质符号上的自足感是脆弱的,鲍德里亚认为“在作为使用价值的物品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作为符号和差异的那些深刻等级化的物品面前没有丝毫平等可言。”[5](P85)消费社会物质的符号价值取代了实用价值,对物质占有的等级差异等同于人的自我价值的等级差异,黄红梅对我的两居室房子的嫌弃瞬间解构了“我”作为城市主人的存在感;叶晖因为拥有了别墅和名车而理所当然成为闯入者中的英雄(邱华栋《所有的骏马》)。这种新的等级秩序造成了闯入者欲望的无限膨胀,在现代城市里只有不断的追求者,没有成功者。这些外省青年本是为了实现梦想、完成自我闯入城市,却在现代城市物化法则的挤压下放逐梦想、迷失自我,那些谙熟了城市法则的闯入者取得了世俗的成功,却陷入了精神的虚无,沦为城市的平面人、空心人、没有历史的人;那些不能完全接受城市法则的闯入者则成为城市的游离者,在理想与现实、精神与欲望之间左右徘徊。
另一类闯入者是农村及小城镇青年,以农民工为主体,包括少数通过考学入城者。他们是数量庞大的群体,但是由于在意识观念、生存资本等方面的局限,只能争扎在城市底层:流水线工人、三轮车夫、建筑工人、小商贩、捡垃圾人、办假证者等等。城市对他们的吸引首先来自生存层面的优越性,“城里真是好啊,要是我们不到城里来,哪里知道城里有这么好,菜场里有好多青菜叶子可以拣回来吃,都不要出钱买的。”[6]“我在北京天天捡破烂,挣的钱比俺们的县长还要多哩。”[1](P140)涂自强和母亲住在武汉最贫民窟的地方,但是不用烧柴,不用担水,晚上有电灯,吃饭有泡面足以让母亲爱上了城市生活,“她就觉得跟山里比,她这过的才叫日子”。[7]这种廉价的满足感映射出农村的极度贫乏和城乡发展的巨大不平衡。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8](P640)而我国于195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则从制度上固化了城乡差异,在诸多具体政策上,如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方面资源配置长期严重不合理,更重要的是这直接造成了农村人与城市人身份上的等级差异。199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迅猛发展,不仅没有给乡村带来改观,反而加快了农村的凋敝。来自农村的闯入者并不能触及繁华鼓噪的城市肌理,甚至不能取得城市底层市民的生存保障,然而仅是生存层面的相对便利,已足以引发他们心灵和精神的震动,安土重迁的传统价值观在生存的本能和欲望面前分崩离析,像候鸟一样往返城乡是迫于生存的需要,而改变身份、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则是这类闯入者至高的梦想。《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父亲说:“只要你不离开瓦城,我们村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比不上你,不管他们读过什么书,只要他们还住在村上,他们就永远也比不上你。”[9]这种信念是农裔闯入者的普遍心理。城乡差序体制赋予城市身份高于农村身份的等级意义,对拥有城市身份的执着追求,是生存压力下的必然诉求,也因为闯入者的坚韧执着具有了解放自我、超越自我的形而上意义。但是这种城乡差异既是激发闯入者超越自我的动力,也是阻止他们融入城市的限制力。农村人的标签意味着贫穷、落后、愚昧,这些在熟悉的土地上生龙活虎的男女青年,在城市面前情不自禁呈现出卑微、胆怯、讨好的姿态,鞠广大因为和城市人挤公交车被打翻在地,从此看见挤公交车的场面膝盖就条件反射般发抖(孙惠芬《民工》);谭鱼听到城市人说乡巴佬就敏感地觉得是在说自己,难堪得无地自容(墨白《重访锦城》)。在强势的城市面前,这类闯入者不得不自觉地放低姿态,选择隐忍的生存哲学,隐忍脏乱的生存环境,隐忍高强度劳动廉价报酬的不平等待遇,隐忍各种轻蔑和歧视。“在城市里活,你知道没有根基的人是什么?我告诉你:是蛆。是一条没尾巴蛆。蛆要什么,蛆要一条缝儿,一条小缝儿。有了这条小缝儿,你就能活下去。”[10](P28)但是即便放低姿态,他们依然很难挤进城市的门缝,《北京候鸟》(荆永鸣)中来泰历尽千辛万苦积攒下开饭馆的钱全部被骗走;《泥鳅》(尤凤伟)中的国瑞英俊善良、有理想、有能力,却稀里糊涂做了城市权贵的替罪羊;涂自强根本无法和他的城市同学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尽管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生活的种种不公,依然被逼迫着节节败退,直至被疾病夺走年轻的生命(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我的生活质量》(邵丽)中的王祁隆、《城的灯》(李佩甫)中的冯家昌是少有的成功立足城市的农裔闯入者,但是在他们成功的背后是以付出人格、道德、尊严为代价的精神悲剧。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城市并没有因为历史的选择而给予他们自由平等的机遇,因袭着城乡不平等的历史惯性,他们无法和城市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勤劳、善良、隐忍、顺从这些乡土社会的优秀品质不仅救不了他们,还常常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的障碍,要么他们被抛出城市的轨道,要么这些优秀的品质被扭曲和吞噬。
在上述两类闯入者之外,我们不得不把女性闯入者单独提出来,这不仅因为她们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更因为她们在闯入城市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于男性的生命形式和更为强烈的生命意识。女性闯入者面对城市,既不像那些自比为拉斯蒂涅的知识青年那样摆出征服者的姿态,也不像农裔青年那样背负着种种传统的负荷、步履维艰。她们以弱者的姿态出现,需要男性的发现和帮助,但比男性更柔韧、更理性,更懂得顺时处变。王安忆说:“与‘人类出生地’相比,城市是‘更富于生存源泉的世界’,更为适合女性生存。”[11](P410)现代城市一方面为女性的独立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让她们承受了传统女性不曾经历的压力、困惑和考验。
女性闯入者也是怀着梦想进入城市的,在真正接触城市之前她们的梦想跟她们的心灵一样单纯美好,崔喜从没去过真正的城市,但从城市人身上“看见了天堂一样的生活”[12];初到北京的黄红梅“就想挣一点钱,回到四川家乡去养猪、种花,叫家乡的女孩也一起致富”。[1](P90)但是当梦想在城市碰壁时,她们很快知道怎样调整自己与城市的关系,在一个一切都商品化、利益化了的世界里,“交换”是基本的生存方式,就像黄红梅所说“我明白了只要我敢于交换,我就会得到我想要的东西。”[1](P89)对于她们而言,青春的身体是能和城市交换的最大的资本,黄红梅用身体交换到在北京的起家的资本;林薇得到成名的机会(邱华栋《手上的星光》);眉宁交换到自己十年才能挣到的房子(邱华栋《生活之恶》);孟叶换来杂志社稳定的工作(邱华栋《天使的洁白》)。而那些来自破败贫穷的农村的乡下打工妹,最大愿望就是用婚姻去换一个城市户口,香香死缠烂打嫁给了丧妻、年近五旬的城市人刘德民(李肇正《傻女香香》);崔喜用尽心机嫁给了丧妻秃顶的宝东(李铁《城市里的一棵庄稼》),而更多的乡下女性付出了自己的身体并没有换来她们想要的东西,而是做了发廊女、按摩女,用身体换取廉价的生存保障。戴锦华曾说“作为商业化大潮的首当其冲者——女人,她们不仅仍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主体与推进者,而且无可回避地成了商业化的对象;商品社会……必然在此以女人作为其必要的代价与牺牲”。[13]在市场化的城市里,女性的身体也可以成为商品和消费品,但是这些为男性付出肉体的女性,已经不同于文学史上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在她们眼里男性并不是命运的安排者和掌控者,她们利用男性并不依赖男性,借助男性作为第一性的盲目自信来化解城市对女性闯入者的排斥力,林薇、廖静茹、黄红梅都借助男性闯入了城市的上流社会,香香和崔喜也是用这种俘获男性的办法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城市户口。但是她们也不同于文学史上那些靠出卖色相维持生活的堕落女性形象,她们有强烈的自主意识、有情感、有梦想、有奋斗的勇气,并非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者,她们不乏真爱,如林薇与乔可,廖静茹与杨哭,黄红梅与“我”,崔喜与大春。但在爱情和利益只能选其一时,她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城市的法则教会了女性闯入者把个人的欲望与情感分离,身体的堕落并没带给她们有多少道德的负罪感。对于女性闯入者的生存样态,简单的批判或是同情都是无力的。“消费社会作为颠倒的社会,并不是靠稳定的规则而运作,相反的,是靠其不稳定而运作。”[14](P717)梦想、青春、爱情虽然美好,但都飘忽不定、不可依恃,唯有金钱与物质实实在在,只有掌握了消费社会的法则才能在现代城市生存下去,面对新的生存法则,传统的道德观念又是多么苍白无力。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她们与城市合谋,完成了对男性话语体系的颠覆。但是她们开放的性观念并不是基于个性解放,而是不得已的生存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女性闯入者既是城市气质的展现者,又是城市法则的受害者。
二、从“闯入者”到“异乡人”
闯入者的城市梦包括外在处境的改善和内在自我的和谐。但是城市没有让他们朝着梦想的方向发展,而是用城市的法则改造和挤压他们,推搡着他们走向现实与梦想的断裂地带,陷入生存的困厄与精神的困顿,他们或在欲望与梦想夹缝中挣扎徘徊,或被城市冷酷地拒之门外,那些取得了世俗成功的闯入者又陷入自我迷失的虚无。闯入城市的行为最终变成理性缺席状态下的盲目挣扎,无法融入又无处逃遁,无力批判也不得救赎,从城市的“闯入者”变成游荡在城市的“异乡人”。
城市对于闯入者首先是生存之地,融入城市需要自我认同感的建构,根据泰勒的观点:“我对我的同一性的发现,并不意味着是我独自做出的,而是我通过与他人的、部分公开、部分隐藏在心的对话实现的。我自己的同一性根本上依赖于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15](P49)城市归属感的获得不是来自闯入者自身,而是在闯入者与城市的互动关系中得以建构。在闯入者的经验中,城市像“绞肉机”“老虎机”、像飞速旋转的“大轮盘”、像“猛兽”,而闯入者则像微尘、像细菌、像蚁群、像鼠群、像候鸟,在两者的关系中城市强大残酷、闯入者渺小无力,闯入者融入城市的过程就是被城市挤压、控制、异化的过程,在这种紧张关系中,闯入者无法获得精神上的归属感,因而他们成为“异乡人”群体中的一员。
“异乡人”(也译作局外人或陌生人)概念最早由盖奥尔德·西美尔提出,他认为“异乡人”“不是今天来明天去的漫游者,而是今天到来并且明天留下的人,或者可以称为潜在的漫游者,即尽管没有再走,但尚未完全忘却来去的自由”。[16]( P152)西美尔从现代社会的时空秩序角度揭示了“异乡人”精神流浪的特质,现代社会时间与空间分离,空间成为心灵活动区域,因而空间距离造成了人们的心理距离,异乡人脱离了既定的地域空间成为时空紊乱的精神流浪者,因此对家园的怀念也总是处于精神层面。城市文学中的闯入者也是从熟悉的环境中脱离出来,把自己投掷到陌生的城市中,这种空间的跨越给他们带来的是精神和心理的断裂冲击。在闯入者与城市的关系上有一点不容忽视,尽管闯入者所属的社会阶层不同、文化背景各有差异、怀着不同梦想奔赴城市,但他们都是从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场域闯入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场域,故乡与城市间的等级差别是先在的,这使他们不由自主地以渴望与仰视的姿态面对城市。闯入者从各自经验出发对城市进行了乌托邦式的想象:“这座城市巨大、庄严而又森严壁垒,一些铜马和石狮子守候着深宅府第的门口,镶有巨大铜钉的朱漆大门紧紧闭着。”“一些古老的天象仪停在空地上,旁边的沙漏在不停地泄露着沙子”。[1](P159)边红旗来到北京的第一个夜晚“来到了天安门前,见到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时,眼泪又下来了。从小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现在竟然就在眼前了,像做梦一样。”[2]敦煌“梦里除了数不完的钱,就是迎风飘扬的国旗,他能听见仪仗队咔喳咔喳的脚步声整齐划一地经过他的梦境。”[17]“铜马”、“石狮子”、“朱漆大门”、“天安门”、“毛主席画像”、“国旗”,这些意象显示了闯入者城市想象中的历史文化情结和政治意识情结,这是传统城市意识的延续而非消费意识形态下的现代城市。闯入者并没有弄清楚现代城市是什么,融入城市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认识的错位、行为的盲目,导致闯入者既栖身于城市又无法融入城市的精神流浪结局。从根本上来说,这种错位和盲目源自故乡与城市在现代化程度上的差异,文化差异产生的断裂感是无法通过物质与欲望的满足来弥合的,所以无论闯入者是否取得世俗层面的成功,都无法逃脱成为异乡人的结局。
在西美尔之后,鲍曼又发现了“异乡人”矛盾性、不确定性的特点,他认为“异乡人”是“不可决断者家族中的一个成员”,“既非朋友也非敌人”,“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他们有可能什么都是”。[18](P84-85)这使异乡人对本土文化产生两难处境:一方面,“留下来”渐渐会“将他的临时寓所改变成一个家园——正像他的其他的即‘原初的’家园退回到过去,或者完全消失一样”;另一方面,“他保留着离去的自由,因而能够以本地人很难具有的平静之心来察看本地状态”。[18](P90-91)也就是说,选择融入本土文化就意味着否定和放弃自我赖以维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以本土的文化观念重新建构;而坚守原来的自我,又使他们始终都是“此在”的他者,游离在本土文化之外,两种选择无疑都是痛苦的。19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中,闯入者并不打算在城市面前刻意坚守自我,他们的痛苦在于融入城市过程中自我的撕裂与迷失。谙熟了城市的规则的格林说,“咱们得挣它一大笔钱才行。感伤有什么屁用?妈的,这是一个物质世界,得先占有了物质才能蔑视它。”而后格林“嚎啕大哭了起来,如同曾经失败的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一样。”[1](P175-176)在这一瞬间庸俗不堪的格林仿佛有了鲁迅笔下魏连殳的意味:在城市面前胜利了,却又真的失败了。他们顺应了城市的消费文化观念却并不能与之融为一体,那个按照传统观念建构的自我时常跳出,站在道德的高度审视现在的自我和城市,导致闯入者城市生存状态的分裂——喧哗与孤独、沉迷与厌恶、狂欢与救赎,如同《午夜狂欢》(邱华栋)中的四个人,白天是正派的汽车经销部门经理、电视制片人、出版社编辑、信托公司部门经理,晚上变成了失意的人、说谎大师、超级骗子、神经质、恐惧者和狂欢的人,迷恋接近死亡的狂欢——卧轨、飚车、吸毒、高空飞行,“通过恐惧和接近死亡的体验促进了一种颠倒了的生命感。”[19] (P308)而对于底层闯入者融入城市的痛苦不仅在于对自我的否定与撕裂,还要面对城乡差序文化带来的身份歧视,《谁能让我害羞》(铁凝)里送水少年为了引起女主人的好感,穿着偷来的衣服——皮鞋、西装、领带,把自己打扮成城市人的样子,扛着50斤的水桶爬上8楼。少年以自己理解的方式努力靠近城市,却让女主人对他更加鄙夷和嫌恶,尊严被彻底践踏时他本能地以暴力方式表示对抗,却被女主人的假枪震慑住,又被女主人5岁儿子一个电话送进了警察局。铁凝以问题小说的方式提出“谁能使我害羞”,但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制度和文化问题,送水少年的虚荣、猥琐、盲目无知,并不是他自身的人格缺陷,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把农民阻止在现代化之外,两者之间的差距不仅是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问题,甚至是两种文明程度的差异,这样的精神鸿沟不是农裔闯入者的个人努力就能弥补的。
闯入者在城市惶惑无依,必然会促使他们寻找灵魂的栖息地。那些要征服城市的外省青年们并没有前现代的经验可以依恃,他们所做的就是找寻,“找寻”在他们身上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环境戏剧人》(邱华栋)中的胡克,以对艺术的追求与坚守作为对抗物质化的城市的武器,把“爱达荷”作为青春寄存地的象征,四处寻找能够和他一起演“回到爱达荷”的龙天米,最终只找到了死亡的龙天米;《所有的骏马》(邱华栋)中的乔可像一匹失群的骏马,在快餐化的城市里寻找生命中坚实可靠的、永恒的爱情,但是这样的爱情他既不能给予也无法获得;《天使的洁白》(邱华栋)中的袁劲松在实用主义盛行的城市寻找超越物质与欲望之上的生命的意义,最终以死亡达成对虚无的超越,而作者又用一则程式化的“晚报消息”解构了袁劲松死亡的超越现实的意义。闯入者的找寻和救赎成为没有结果的游荡。对于农裔青年,记忆中的故乡常常是他们在城市困境中的精神慰藉,但是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农村的极度贫乏比城市精神上的漂泊更难以忍受,所以他们的思乡不过是一种仪式,即便暂时回去也会重新逃离。女性闯入者比男性更有抗争精神,她们从异乡闯入城市,从边缘奔向中心,在这样的追求和抗争中并没有真正实现自我,而且也无法回到当初的自我,对于这样的境遇他们甚至没有救赎的念头,这让女性闯入者比男性闯入者更复杂,悲剧色彩更浓烈。因此,闯入者是双重的“异乡人”:一方面,对于此在的城市,他们是他者化存在;另一方面,闯入者经历了现代城市文化,不可能再退回故乡的生存状态,无论对于城市还是故乡,闯入者成了无所归属的“异乡人”。
“城市的空气带来自由的感觉”,[20](P498)闯入者之所以对城市心向往之,历尽种种苦痛仍然充满留恋,是因为在当下这样的差序社会,他们坚信城市相比故乡能给予他们更多改变先赋身份约束、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城市像黑洞一样把千千万万个来自农村和小城市的人们吸引进来,但是它并没有呈现出多元包容的气度,而是用城市的法则异化和改造他们,“大批涌入城市的农民或其他移民,则难以保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他们是城市的‘他者’,必须想尽办法尽快适应城市并生存下来。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些新移民最大的特征,他们的焦虑、矛盾以及不安全感是最鲜明的心理特征。”[21]在文化转型时期,他们是没有归属感的一代人,从“闯入者”到“异乡人”的精神历程,象征着我们民族从乡土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迈进的心路历程,展示了文化转型时期城市外来者无法抗拒的悲剧命运。
三、闯入者的叙事伦理
闯入者的叙事具有一定的悲剧性,文明的进步总是以一部分人的血泪为代价,闯入者的悲剧命运是个体无法抗拒的时代症候,但是在这类文本的叙事中,作者选择的不是基于时代和历史趋向的宏大叙事,而是基于生命伦理的个体叙事。
闯入者的悲剧既是生存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他们强烈认同城市却得不到城市的包容与接纳,武月月以堕胎捍卫了农村人的尊严,但是忍辱负重经营多年的城市婚姻也因此化为乌有(荆永鸣《出京记》);敦煌对夏小容仗义相救却因此再次入狱(徐则臣《跑步穿过中关村》);城市唤醒了闯入者的主体意识,激发了他们向上的热情,却无法实现他们的梦想:明惠在自我意识觉醒后选择了自杀(邵丽《明惠的圣诞》),眉宁得到了房子却失去了爱情(邱华栋《生活之恶》)。但是这样充满张力的故事在叙事中产生的不是时代悲剧的大震撼,而是感受了个体生命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无奈、追求与失落后产生的希望与虚无、温暖与清冷、慰藉与疼痛交织的复杂情感。这种复杂的情感,源于作者的叙事态度和立场。作者放弃了精英式的理性叙事姿态,既不做时代价值的审判者也不做人物命运的指引者。一方面,作者对待城市的态度是暧昧的,他们虽然借主人公之口批判了城市的冷漠、残酷、魅惑,但无法跳出当下的社会形态给予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他们已经无法像沈从文、张炜那样立场鲜明,那样信赖乡土文明,以乡土文明之“善”对抗城市文明之“恶”。城市“闯入者”的创作者从经验出发,对乡村失去了信任,认定城市文明代表了现代性的方向,认同世俗欲望的合法性,认同物质之于人的第一性存在,所谓“梦想”“价值”“自由”这些精神层面的追求都是以生存需求的满足为前提条件的。因此,作者对消费主义盛行的城市文化感情上是逆反的,理性认知上是顺从的,闯入者的叙事“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的现代性的顺应式的进化与建构,而不是逆反性的破坏与抗争。”[22]因此,这类叙事不能够对现代城市文明的破坏性和异化性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另一方面,创作者对笔下的人物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不能为无望的人们指出光明的道路,却对他们的悲剧命运表现出切肤之痛的理解、尊重和抚慰,对于闯入者的现代化诉求方式和在这个过程中爆发出来的生命力量给予肯定。《行为艺术家》(邱华栋)中的黄红梅从一个清纯美丽的打工妹,变成了被金钱和物质攫取了的黄经理,名利双收后惨死在自己豪华的别墅中。在她短暂的城市经历中,靠着聪慧谙熟了城市的生存法则,用这法则征服了城市同时又被这法则毁灭。这一过程中,她的贪婪、自私、心狠手辣和她的美丽、聪慧,不知疲倦、一直向上的热情一样闪烁着生命的魅力。徐则臣笔下的“北漂者”、荆永鸣笔下的“外来者”是典型的城市底层闯入者,在陌生的城市他们毫无仰仗,只能在城市的夹缝里挣扎求存,过着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作者没有因为闯入者身上所拥有的勤劳、善良、执着上进的美德而期许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冷酷地否定了他们改变自己身份与命运的可能,但是这类叙事既没有批判生活的不公,也没有沉浸在命运的残酷里,而是对闯入者在困境中展现的生命的韧性给予抚慰和赞赏。荆永鸣说“在创作外地人系列小说时,我没有过多地去描写这个群体的苦难,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那些卑微人物进入城市之后复杂的精神境遇,关注他们在城市夹缝中的生存能力和精神承受力,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内心冲突及精神嬗变。”[23]徐则臣也说,“我写他们,也包括我自己,与简单是非判断无关。我感兴趣的是他们身上的那种没有被规训和秩序化的蓬勃的生命力,那种逐渐被我们忽略乃至遗忘的‘野’的东西。”[24](P2)《出京记》(荆永鸣)中武月月的婚姻里,爱情的成分远没有现实的计较多,但是作者通过武月月对婚姻的经营展示的是她的聪慧、理想和努力,从进京到出京,武月月的努力是失败的,但是作者的着力点却在于武月月迷途知返的悟性和为尊严而放弃的勇气。《啊,北京》(徐则臣)里怀着诗人梦的边红旗,在北京住合租房,从事办假证的违法工作,提心吊胆朝不保夕,他的生活和流光溢彩的都市现代化毫无关系,却依然真诚地赞叹北京的美好。边红旗从小城镇的教师变成了大城市里的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办假证者,落魄的生活并没有消磨掉边红旗身上非常本色的诗人的激情、男人的豪爽和几分落拓不羁的魅力。闯入者困境中的人性闪光并不能够照亮他们的灰色人生,但是这样的悲喜人生却能唤起芸芸众生的道德自觉和情感共鸣,这正是个体生命叙事所彰显的叙事伦理价值。
闯入者的悲剧精神历程大都相似:“闯入——争扎——失败”, 这也成为城市闯入者叙事的基本模式。这种并不悲壮的叙事之所以能够打动读者,就在于作品具有自由叙事伦理的力量。刘小枫把叙事伦理分为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不提供国家化的道德原则,只提供个体性的道德境况,让每个人从叙事中形成自己的道德自觉。”[25](P7)“从一个人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的生命感觉来摸索生命的应然。”[25](P5)实际上,在社会的转型期,闯入者是夹缝中的群体,在理性和行为选择上追随以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为表征的现代城市文明,而在心理和情感上又难以与之契合,这也是文化转型时期必然经历的心灵阵痛。文化冲突带来的感性与理性、精神渴求与行为选择的矛盾与分裂,以及由此导致的生命的不自由正是“闯入者”叙事所关注的重心,也使得“闯入者”这一文学形象具有了共名性和隐喻意义,彰显了这类创作的价值和意义。(致谢:感谢山东科技大学应用型立项建设专业(群)经费资助。)
[1] 邱华栋.闯入者[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
[2] 徐则臣.啊,北京[J].人民文学,2004,(4):52-83.
[3]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256.
[4] (匈)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 范小青.城乡简史[J].山花,2006,(1):50-58.
[7] 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J].十月,2013,(2):4-47.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鬼子.瓦城上空的麦田[J].人民文学,2002,(10):2-42.
[10] 李佩甫.城市白皮书[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
[11] 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A].漂泊的语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12] 李铁.城市里的一棵庄稼[J].十月,2004,(2).4-20.
[13] 戴锦华.奇遇与突围——九十年代女性写作[J].文学评论,1996,(5):95-102.
[14] 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下卷[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15] (加)查尔斯·泰勒著,韩震等译.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6] (德)西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7] 徐则臣.跑步穿过中关村[J].小说月报,2007,(1):48-73.
[18]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邵迎生译.现代性与矛盾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9] (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等译.城市文化[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20] (加)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21] 孟繁华.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J].文艺研究,2014,(2):5-14.
[22] 张未民.中国“新现代性”与新世纪文学的兴起[J].文艺争鸣,2008,(2):6-22.
[23] 荆永鸣.一个外来者的城市书写[J].当代作家评论,2015,(2):128-131.
[24] 徐则臣.跑步穿过中关村·自序[A].跑步穿过中关村[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25]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TheImageofMigrantsintheCityLiteraturefromthe1990sandNarrativeEthics
Cao Bingy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510, China)
The migrants in the city literature are the representative and metaphorical literary images. They consist of provincial educated youth, rural and small town youth, and among them the female migrants are the important parts. The migrants move to the city with worldly desires and dreams but they are the strangers in the city because they come from the backward culture. Novels of this kind are not devastating tragedies but have consolatory ethical value because of the individualistic narrative style.
city literature; the immigrants; the strangers; narrative ethics
高 雪
2017-04-1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0后’作家小说创作研究”(16BZW149)的阶段性成果
曹丙燕(1977- ),女,山东新泰人,吉林大学文学院 2012级博士研究生,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专业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6.7
A
1672-335X(2017)06-012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