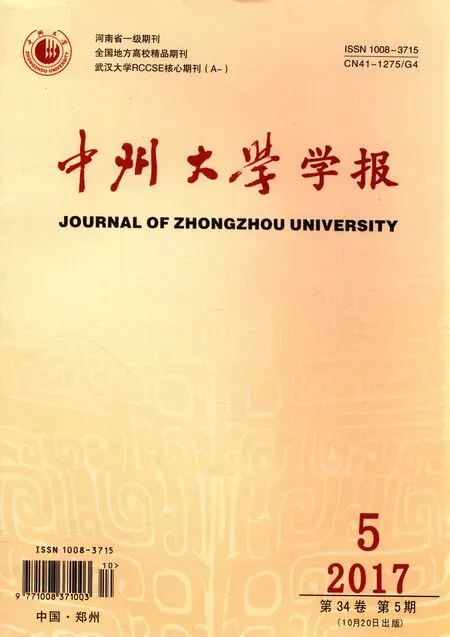谈《沱河记忆》中的农事记忆情结
李 欣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郑州 450044)
谈《沱河记忆》中的农事记忆情结
李 欣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郑州 450044)
《沱河记忆》是一部知青题材小说。曾经是知青的作者董克林用独特的视角,用平实朴素的带有豫东特色的语言回忆了知青到农村插队的美好往事,记录了知青和农民的深厚感情,描绘了那一代青年人的热血青春和理想追求。《沱河记忆》中的农事记忆是文学描述,更是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有价值的文献。它不仅是知青题材的小说,更是中国农村发展和变迁的历史缩影;它不仅是作者的个人记忆,更是能激发群体认同感的社会记忆。小说具有一定审美境界和历史文化价值。
《沱河记忆》;农事记忆;情结;审美境界;文化价值
描写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知青题材的小说众多。80年前后有描写知青苦难历程的“伤痕文学”,如叶辛的《蹉跎岁月》,竹林的《生活的路》,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80年代前期有讴歌青春和理想的,如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张曼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张承志的《黑骏马》,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80年代中期以后有“反思文学”,如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张抗抗的《隐形伴侣》,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老鬼的《血色黄昏》,李锐的《合坟》;之后,有更多沉思和温暖成分的知青小说出现,如刘海的《青春无主》,梁晓声的《知青》。董克林先生的长篇小说《沱河记忆》属于最后一类。
《沱河记忆》这部小说没有史诗般的宏大叙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更没有华丽的词句。它用平实朴素的带有豫东特色的语言回忆了知青到农村插队的美好往事,记录了知青和农民的深厚感情,描绘了那一代青年人的热血青春和理想追求。读来让人温暖,令人感动。“如果说语言是思想的工具和材料,记忆则是思想的源流。”[1]知青生活是那一代人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他们人生故事里重要的情节。正像作者本人所说:“返城三十多年来,在沱河岸边庄稼地里摸爬滚打的场景慢慢变成了发黄的老照片。但是,这种镜头一直使人魂牵梦绕,心中总有一股力量在冲动,时时激励着我提笔书写那段流逝着、沉淀着铁质的岁月。”[2]321小说描写的是20世纪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山”时期,京港市18位知青(小说中的18位罗汉)到沱河县沱河岸边的李楼大队劳动四年多时间里发生的故事。小说开头,讲到18位知青(9男9女)乘坐大客车来到李楼大队,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已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饭,而且提前为他们新盖了三间草房。看到草房、树木、果实和田野,他们充满新鲜和好奇,“九枝花”开心的把他们的草房称为“千金店”,九弟兄晚饭后迫不及待的跳入沱河,在河里嬉戏打闹游成了欢乐的“浪里白条”。他们的青春活力、阳光开朗也给偏僻的乡村带来了清新和生机。“石榴树枝头挂满了带有红脸蛋儿的果实,高高的柿子树上结满了嫩绿的青果儿。累累果实在风中摇曳,在太阳下微笑,好像在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2]4这是小说开头引子里的描述,为本书奠定了清新、明亮而又温暖、向上的橙色和绿色交织的色彩基调。
《沱河记忆》是一部长篇纪实散文体小说。小说除了引子,有二十一章:十个“和尚”和“一小撮”、地锅馍和“独腿烧鸡”、制止敌台、种麦、房东、雪中的大白鹅、大队书记的酒坛、章来打架、参加整党工作队、捉老鼠、九公里事件、盖新房、收麦打场、木雨伞、棋“生”棋子、闹鬼、车祸、吃大鱼、王引河会战、红芋活、知青调研。这二十一章故事各自相对独立,前后既没有时间上的承前启后,又没有故事情节的逻辑关联,每一章都是人物情节相对完整的短篇小说,在栩栩如生的描述中昂扬着积极向上的力量。内容有劳动和生活中的逸闻趣事,也有矛盾冲突和意外事件,其中关于农村农事、农活儿的描写占了大量篇幅。例如第四章种麦、第十二章盖新房、第十三章收麦打场、第二十章红芋活,其他章节里也不乏农事、农活儿的片段描写。这些农村农事的描写既表达了曾是知青的作者对农民、对农村深深热爱的情结,又表现了作者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和教育家对农事的文化思考。
一、《沱河记忆》的农事记忆具有景真情切的审美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3]5意即作家写作要写真景物、表达真感情,要真切地写真,才叫有境界,否则就是无境界。董克林是有境界的作家,他眼中的农事真实自然,他面对农活不是被动抱怨而是主动学习掌握,他笔下的农事、农活儿不仅有意义而且有情趣。第四章“种麦”中详细描写了多种农事、农活儿:沤粪、上粪、打坷垃、耙地、打畦田、耩麦等等。作者通过生动的人物对话和细致入微的描述把所用农具及使用方法、技巧、使用效果、出现的问题全部记录下来,可以说是“种麦的农具农活大全和教科书”。比如作者对耩麦的耧的介绍,如果不是亲眼见过、亲自用过,就不会把它的结构描写得如此细致和具体,因为如今这些农具已鲜为少见。在第十二章“盖新房”中,作者用12000字,描绘了从钉木线橛子、挖地基、打夯、和泥、砌砖、垒墙、上梁、铺房顶等环节到新房盖成的全过程,讴歌了村民们代代相传的聪明才智、盖房工艺和友爱协作的精神,表达了村民们对知青的关爱和盖新房的喜悦之情。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不一会儿,村里的建房高手、青壮劳力‘云集’工地,参加建房‘会战’。高金顶是全大队手艺最好、最权威的‘把式’,小学生似的站在徐队长身旁,‘老队长,只等您发话了,恁说干,俺就下手。’”[2]151“干活的社员个个都是艺术家,他们光着膀子,耍着家伙,胶泥在他们手里好像有了生命,特听使唤。……泥里露出的麦秸茬都齐刷刷地头朝外,泥墙成了艺术品。”[2]161作者描写的劳动,从字里行间传递出的不是苦而是快乐,这既表现了当时的劳动场景的确是欢乐的,同时也表达了作为知青的作者对劳动的认知和体验也是快乐的。这源于作者对劳动和村民们的深情和热爱,也源于作者对劳动的审美态度,给读者带来了审美上的愉悦感受。
《沱河记忆》小说通篇充满真善美和人性的光辉,其中关于农事劳动的描写也充满了真善美。王泽龙教授为《沱河记忆》所作序文中说:“真、善、美——就学理而言,分属哲学、伦理学和美学中最基本的范畴,也都属于美学研究中的基本课题。所谓真,就是客观事物的存在及规律性,人们只有尊重客观事物存在及其规律(真),才能自由地进行造福人类的活动(善),从而显示出人的本质力量(美)来。”[2]1农事劳动是本真,在劳动中体现善和美,这是作者具有高度的审美境界和自觉所致。在第十三章“收麦打场”和第二十章“红芋活”中,作者同样如教材般详尽描写了这两种农活的程序,但效果又比教材生动和灵活。作者巧妙的以徐队长及村民和知青们一问一答对话的方式,把收麦打场及翻红芋秧的原因、细节、技巧展现出来了。作者对农事劳动的描写也颇有意境,颇具美感。“庞大爷接过扫帚,左脚在前,右脚在后,身体像个中心轴,随着上半身扭转,手中的扫帚不紧不慢地围绕着庞大爷的身体画着弧。一扫把、两扫把、三扫把……扫过之后,麦秸在上,麦粒都乖乖地留在地面上。”[2]177“这个麦季,正像安国夸庞大爷菩萨心肠那样,一周艳阳眷顾了诚实劳作的社员,直到麦子装袋入仓。”[2]179在作者眼中,农活儿是美的,干农活儿是快乐的。在第十九章“王引河会战”中,作者用轻松幽默的文字生动描述了劳动后的快乐心境。“太阳落山,工地放工,吃饭算是摸黑‘晚宴’。社员头顶挂着星星的碧空,用欢声笑语把饭场搅和得五味俱全,用诙谐幽默的智慧装点出一个偌大的晶莹透亮的天然宴会厅。老少爷们尽情地说啊、笑啊、闹啊,享受着释放疲惫之快乐。”[2]269
读者从书里描写的农事劳动中不仅感受到了真善美,也感受到了快乐。除了中国农村农事本身传递的美学意象之外,作者的文学功底和审美境界令人叹服。
二、《沱河记忆》的农事记忆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
以苦难知青生活和蹉跎青春岁月为题材的知青小说很多,它们浓墨重彩讲述的多是知青们的生活和情感经历。而像《沱河记忆》这样能欢快表现丰富的知青生活、温情讲述知青和社员和谐美好感情、详实记录农村农事活动的比较少。董克林先生撰写的《沱河记忆》为人们认识和了解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生活多了一个角度和窗口,为社会记忆提供了独特的资料,也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定印记。很赞同清华大学郭于华教授在《社会记忆与人的历史》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就中国社会而言,贯通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并由此重建社会记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之一……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重量!每个人的记忆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1]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和教育家,董克林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他想把个人历史、个人记忆融入社会记忆,想让具有青春纪念碑意义的“知青”生活不仅成为自己的人生财富,而且把那一代人甚至中国某一阶段的历史记忆变成可以翻看和咀嚼的文字,同时也为当代青年提供活生生的、可以借鉴的社会实践素材,倡导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的良好风尚。
不仅如此,《沱河记忆》还是一部生动的农事教材。作者描写农活儿、农具的农事记忆不仅是作者个体的,更是社会的记忆,其历史文化价值值得重视。社会发展与乡村变迁使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农耕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传统的农具、农活儿正逐渐消失,即将成为历史和文化记忆。在这种时间节点上,《沱河记忆》的农事记录无疑是具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价值的。耧是一种播种的农具,现在已被播种机取代很少见到了。书中这样描述:“它有三个上下高度约1米的圆木棍,上端有一根横杠,是扶把;耧扶手即两根木料,长1米多,一端向人力车扶手,把手下面与三个圆木棍呈110度衔接,三跟圆木棍下面部分俗称黄瓜筒,黄瓜筒是空心,麦种从漏斗进入筒里经过下面的耧铧脚落到土层里。与三根圆木棍衔接的两根木料有一个口大底小的漏斗,斗底有一个踏门,踏门引出三个空心筒与黄瓜筒连接。耧铧脚是铁质的,前尖后宽,扎在蓬松的土壤里,前行的同时播下种子。”[2]55这一段文字是用过或见过耧的农民和知青能读懂的,其他人读后一定不知其为何物。现在耧和织布机一样已被抛弃或作为农耕文化的象征成了历史陈列品,以后也许只能在博物馆和陈列室才能见到。第二十章“红芋活”就是一堂红芋的科普文化课。小说先叙述红芋的重要作用:对于20世纪70年代中原农村的农民来说,“一年红芋就是半年粮”,“红芋汤、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之后详细描写了知青学翻红芋秧、学做红芋粉条、晾晒红芋片的全过程。最后还进行了概括总结:“红芋的食用方法还有很多。红芋片可做白酒…可制作淀粉;淀粉能制成粉条、粉皮;红芋渣是喂猪的好饲料。经过霜打的红芋秧变成黑色,把它和豆腐、红芋煮在一起,便成为一种叫做‘懒豆腐’的主食。”[2]300
这种浓郁的农事记忆和乡村情结是知青们的乡愁,也是中国农民的乡愁。农事成了乡愁的载体,而当实际生活中农事发生变迁或消失的时候,这些关于农事的文字记载也成了乡愁的载体和传世的史料,其意义已远不是个人记忆和个人情结了,它是一种社会记忆和历史的文学再现。美国史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指出:“物质器物、宗教知识、科学著作、文学作品等都渗透着传统社会记忆的踪迹。”[4]所以,《沱河记忆》中的农事记忆是文学描述,更是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有价值的文献;它不仅是知青题材的小说,更是中国农村发展和变迁的历史缩影;它不仅是作者的个人记忆,更是能激发群体认同感的社会记忆。
[1]郭于华.社会记忆与人的历史[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08-20.
[2]董克林.沱河记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
[3]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2016(11).
[4]郑杭生,张亚鹏.社会记忆与乡村的再发现[J].社会学评论,2015(1).
(责任编辑谢春红)
StudyontheComplexofFarmWorkMemoryinTuoheMemory
LI X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TuoheMemoryis a novel with the theme of educated youth.Dong Kelin, the author of this novel, with his unique perspective as an educated youth himself, he recalled his glorious memory,which was educated youth learned from the countryside with the natural and simple Eastern Henan language.The novel records the deep feeling of farmers and educated youth, depicting the passionate and pursuits of that generation.The agricultural memory ofTuoheMemoryis not just a literature description, but also a social, historical and valuable literature.It is not only the novel of educated youth, but also the historical epitom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vicissitude of China’s rural areas.It is not only the personal memory of the author, but also the social memory that can stimulate the identity of the group.The novel has a certain aesthetic judgement,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TuoheMemory;memory of farm work; complex; aesthetic state; cultural value
2017-09-05
李欣(1964—),女,河南武陟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02
I207.67
A
1008-3715(2017)05-0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