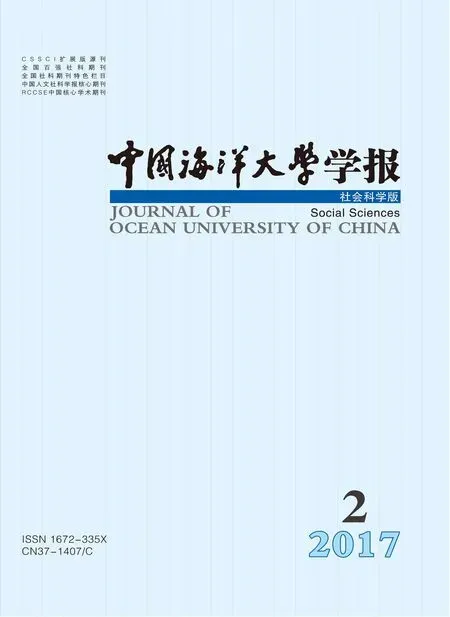《一九八四》的后人类生命政治解读
支运波
(1.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2.上海戏剧学院 艺术研究所,上海 200040)
《一九八四》的后人类生命政治解读
支运波1,2
(1.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2.上海戏剧学院 艺术研究所,上海 200040)
奥威尔的政治小说《一九八四》是一部后人类主义生命政治的当代小说。这一书写特性的理由在于:作者并非仅仅满足于大洋国恐怖政治环境的构建和老大哥的政治治理实施;小说给予的恐怖警示不止于温斯顿人性消失所引发的对于政治生存环境的担忧;奥威尔的真正意图是通过大洋国的艺术性虚构启发人们思考人类从来都是生存于由政治和技术构筑的环境中的。小说在政治权力对温斯顿造成的离身性和科学技术对温斯顿具身塑造的双重塑造中引发人们思考人类生命本身根本价值和意义何在的问题。
《一九八四》;后人类;生命政治;人性伦理
反极权主义、反乌托邦,抑或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映射……,如此等等,都未能或不足以能探索到奥威尔经典政治小说《一九八四》在当前时代语境中的深刻性。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林林总总的认识都是在小说的内容层次上去就事论事的,而且也因为单纯的这类看法不足以解答这部作品为何具有这般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这个现实问题。事实上,《一九八四》写就于1948年却总能回响于后世的缘由或许很大程度上在于这部小说应和了人类的普遍性命运。而这种命运的普遍性乃是在于人从来都没有逃离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人是政治动物的见解,也没有逃离福柯所说的“人是因政治而披上人类外衣的动物”[1](P208)的现代断言。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九八四》的最根本意义在于作者洞见了人类自始至终就是后人类(post-human)的,即人类是由政治与技术所塑造的社会生物物种,而绝非一个遵循自然规律的隔绝自然生物,这么一个人类生存的密码。
一、什么是后人类
“后人类”(Post-human),也称为超人类、非人类、半人类等。据考证,早在1888年,布拉瓦兹基(H. P. Blavatsky)在《秘密教义》(The Secret Doctrine)一书中就曾使用“后人类”(Post-Human)一词。它作为一个学术名词,通常认为是源自1988年史蒂夫·妮可思(Steve Nichols)所发表的《后人类宣言》(Post-human Manifesto)一书。*一说认为它始于哈桑(Ihab Hassan)1977 年发表在《乔治亚评论》上的《作为表演者的普罗米修斯:朝向后人类文化》一文所提出的人文主义正转向后人类主义的观点。(Ihab Hassan, “Prometheus as Performer: Towards a Posthumanist Culture”, Georgia Review, 31.4(1977), p843.)但引发重大反响的则是佩普勒尔(Robert Pepperell)在1995年出版的专著《后人类状况》。作者在该书中提出后人类是视人类的“存在为延展的技术世界的一种形态”[2]的观点。当代著名后人类主义学者沃尔夫(Cary Wolf)在《什么是后人类主义》(What Is Posthumanism)中,将后人类主义认为是类似利奥塔的后现代的东西:“诞生于人文主义之前与人文主义之后”。他说在诞生人文主义之前意思是说人类不仅具身和嵌入到他的生物世界,而且也包括技术世界;在诞生人文主义之后是指后人类主义表明了这样的历史时刻,在这个时刻人类越来越难以忽视被自身叠加的来自技术的、医学的、资讯的以及经济网络所抛弃(decenter),以及作为历史特殊现象的后人类主义的历史趋势,诸如指向新理论范式必要性,随着文化抑制与文化幻想而来的思想新模式,哲学协商与回避等。[3]
这样看,后人类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有关人类之后的时间概念或文化概念。学术界基本上把它看作是一种主张由人的后天作用而成的生物,而反对将人视为一种本质的、内在的和先天如此的生物的观点。就像罗斯所认为的那样:“人从来都不是‘自然的’,至少从创造语言开始,我们就在凭借知识、物质和人类技术增强我们的能力”。[4](P94)对于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的谱系,学界一般也将其追溯到福柯,或者德里达等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那里。尤其是,福柯关于人的消亡和人是历史建构物的观点对后人类主义理论家们影响颇大。但是后人类主义思潮成为最近一二十年人文学科热议的新兴议题,则是与两位美国当代学者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的开创性研究分不开的。哈拉维提出的“赛博格”(cybory),这样一个混杂性的生物概念迅速成为“理解当代文化经验与后人类情境之重要概念”。[5](P220)海尔斯呢,则在文学(尤其是科幻小说)与科学之间进行了先驱性的研究。在《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赛博格、文学以及信息学中的视觉身体》(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中,海尔斯提出了后人类主义所应具有的四个方面的特质。这四个方面分别是:生命的本质不在身体,而在信息;意识对人类进化起次要作用;后人类认为身体并非自然物;人工智能机器和科技装置与生物有机体无本质差异。[5](P3)海尔斯与哈拉维一样都比较倚重后人类的历史/文化情境作用,坚持一种生命之外的社会决定论。比如,海尔斯就认为当人类进入后人类时,“旧人类的法则与知识将完全被抛弃,不再有任何价值与意义”。[5](P223)
不管人们是否承认或赞成当今已进入后人类社会,也不管后人类理论存在多少分歧,但人类都不可否认的是人逃离不了成为现代技术挪用与塑造的宿命,也改变不了人类从一开始就是受外界影响而不断生成的,而非一个自足生物的历史,这样一个历史的必然性。对此,罗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人类生命力的很多方面已经成为技术的,可以在手术室、诊所、教室、军队和日常生活中被操控、被改变”。[4](P304)从天生,或生理赋予的角度去理解生命(身体与精神)的健康、自由以及伦理维度的方式逐渐地被一种生命可被规划的趋势所打破。即“生命不是背设想为一种不可改变的、确定的禀赋。生理不再是命运。生命力现在被理解为……可描述的技术关系,……在原理上能够被‘重新设计’”。[4](P47)后人类已普遍应用于形容现代人日渐分歧、复杂的生命期许和差异的身份认同,它带来的本体论转向是人的技术化与物技术人格化的相互介入与弥合。我们说起源于对人文主义批评和科技发展反思的后人类思想是人类历史上新近掀起的再一次启蒙运动,它给我们提供了思考人类在技术社会、控制社会以及生物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人类去中心化”[3]和超越“人类长期孤立在自我想像的独特性之中的隔离主张”[6](P196)的利器,它也将有助于启发我们去探索如何在未来社会中解答与人性相关维度诸多方面的尖锐难题。
二、后人类的《一九八四》
小说从一开始,奥威尔就致力于温斯顿受老大哥政治权力惩戒与生物科技书写的生命过程。温斯顿在小说篇首便是以一个动作缓慢、身体患病的形象现身于英社的电幕监控之下的。随后作者就接二连三、不厌其烦地呈现了温斯顿在日常生活中难以逃避的科技装置(例如巡逻机、窃听器、忘怀洞、电刑等),生物技术(像人工授精、注射器、鼠型以及再造人等)以及政治思想改造(比如新话、双重思想、爱老大哥等)等一系列针对生命本身的惩戒装置。在小说篇末,温斯顿被奥勃良施以电刑、鼠型以及身体注射液体等一系列基于生物医学的技术改造,结果他被重新塑造为一个似是而非的新温斯顿。而在被捕之后,温斯顿才恍然大悟:他与裘丽娅约会的地方一直就在老大哥的电幕监视之中。作者在这里是要让人们意识到温斯顿的生命自始至终都是老大哥政治权力的治理对象和算计对象。而如果当政治算计不能奏效时,老大哥便会依靠权力借助生物技术将温斯顿的生命作为改造的直接原料。例如,奥勃良对温斯顿说:“你要明白,即使他侥幸不死,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们可以使他成为另外一个人。他的脸,他的举止,他的手的形状,他的头发的颜色,甚至他的声音也会变了。你自己也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我们的外科医生能够把人变样,再也认不出来”。[7](P157)
如果仅仅只是着眼于政治统治,那么老大哥就势必只对人的惩戒实施感兴趣。可事实并非如此。老大哥根本不满足于消极地服从,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既区别于“以往的专制暴政的告诫”,也不同于“极权主义的告诫”的权力新装置,他的根本目的是塑造一个新人类,即他说的“你的是”[7](P232)的被治理者。表面上看,温斯顿痛恨、烦躁、压抑于老大哥的电幕监听、思想控制、情感消除。可事实上,作者在小说中透露出老大哥的这些管治方式对温斯顿所产生的惩戒功能的发挥作用很小。因为,温斯顿熟悉如何规避电幕监控,理解人间真情,懂得老大哥管治思想和治理技术,还具有丰富的想象能力以及清醒的自我意识。大洋国充斥的各种标语、口号和招贴画,各种英社党组建的组织同盟,以及或明或暗的告密者,他也能应付自如。作者还透露了温斯顿对此是如何一一进行抵抗的。但是,温斯顿的抵抗要么是跑到贫民区以远离电幕监控区域,要么是凭借写日记、发挥想象与回忆的方式反抗思想控制,要么是靠婚外情、性暴力与性幻想等不正常行为来反对老大哥的情感消除。可以说,这些抵抗行为基本上还只是停留在温斯顿的内心与头脑中,它与老大哥特别具体的暴力治理手段相比,显得非常无力、甚至于荒唐可笑。但另一方面,温斯顿不得不对电幕做出愉悦的表情,并且在电幕下行为变得更加规范(做操),温斯顿对裘丽娅由最初认为是核心党员到后来渐渐喜欢上了她,特别是他对英社党主要头目奥勃良由恨而爱,爱上了老大哥,成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温斯顿。这耐人寻味,又颇让人深思。
经过监狱里电刑、鼠刑和注射药物改造之后,变化了的一个新温斯顿,一个有“爱”的温斯顿,作者让他接受了2+2=5的知识。这里的温斯顿,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这个新人类的诞生,显然并不是奥威尔随便塑造的。相反,而是作者从一开始就精心构筑的一个受技术与政治搭建的生存语境。温斯顿的工作场所,私人空间和社会活动领域处处充斥着政治渗透和权力符号,除了睡觉和做梦之外无一避免权力之眼的监视。正常的人不可能长久地保持不受这种无盲点的政治背景影响,我们也不能确定奥威尔是否是通过这种艺术虚构的方式告诉世人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其实就是这样的。在温斯顿对这种政治环境感到不适,并试图要冲破它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然的人类。在这种物质性的身体监控以外,奥威尔又设置了老大哥的以“新话”、“双重思想”、篡改历史为特征的思想监控策略。也就是说,权力要直接进入人的身体内部去占领头脑,通过重塑历史与知识系统去改变人的思维进而实现塑造出听命于权力的新主体。知识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后天的东西,而非原生性的。再者,就是老大哥的情感消除。英社党积极组建少年反性同盟、培养儿童密探揭发亲人来消除快感与家庭伦理,“除了爱老大哥以外,没有其他的爱。……没有其他的笑。不再有艺术,……不再有好奇心。……一切其他乐趣都要消灭掉”,就是说,老大哥——作为一种权力象征性隐喻——是“全能的”,即“权力是上帝”,它要“不再有生命过程的应用”。[7](P253,243)奥威尔赋予电幕既恐怖又具自由(以电幕而不是以直接的暴力实施为手段)的双重性,赋予知识体系以双重矛盾性(接受本来就相矛盾的事物),赋予温斯顿婚外情—性暴力—爱情—背叛的非常理的情感模式,甚至是爱上了他开始就痛恨的英社党头目这样一种近乎同性恋倾向的古怪情节,不得不令人深思。如果不是作者刻意在强化人类的生存环境以及塑造人类自身的形成问题的话,那么就难以从极权主义或者常理上进行理解。
置身于政治权力环境,人类就不得不受到政治权力的渗透和铭刻。可是,如果人要反对无处不在的政治权力会如何呢?按照奥勃良说的,那也就不得不准备接受像温斯顿被投进监狱,并遭受医学技术和科技技术的改造。结果是:他“所表现的情感不是他内心感到的情感”,而他外在身体的变化比他的内心变化还要大——“一个患有慢性痼疾的六十老翁的躯体”。[7](P246)他既是他自己,也不是他自己。老大哥利用电刑、注射器和仪表(即科技)彻底实现了新人类塑造,一个符合政治要求的没有鉴别力、思考力和友爱的生物。而且,对于这种生物,温斯顿意识到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在老大哥的电幕监控中。它寓言我们每个人从一开始就身处政治与技术之中。奥威尔所感慨的“欧洲最后一个人的消失”的深刻意义恐怕正在于此。人类的感觉、思维、器官都是被后天塑造的,无人幸免,且世界本来就是如此运转的。
老大哥对治理者生命塑造的技术是通过政治权力和生物方式实现的,但这两者对人类的改造并不完全相同。我们在温斯顿身上看到,老大哥政治权力的实施显然主要针对的还是温斯顿的物质身体,或者说完整性的身体组织。在小说中表现为只要温斯顿没有出现违反老大哥的异端行为出现,那么他就会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完整的状态,比如像裘丽娅那种较为正常的生活方式。但他也在另一方面,即与政治驯服行为相反人的正常状态之间存在着断裂:温斯顿在政治权力惩戒下反而是一个身心分离的人,或者说权力以否定性力量的方式去强制主体的服从。因而,此刻的温斯顿是离身性的(disembodiment)。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就阐释了主体离身性是何以产生的。如果政治权力未能有效获得它所期望的状况,它便会“在精神上,通过操纵文化的记忆来导致我们动机结构的根本改变来获得,其中包括改变和提高对情绪的控制,以及对性欲的倾向、强度和频率的控制”。[8](P124)作者描述温斯顿一切的痛苦、不适、反抗与变化都是来自老大哥的政治权力运作,亦即展现了温斯顿的离身性及其没有归宿的状态。而科技与生物对生命的作用则与之完全不同,它直接以重造为目的。肉体物质性的抵抗,在技术和生物模式一律成为“统一模式下的普遍性的身体”。[9]即是说,使温斯顿在政治权力下诞生的离身性以及他寄希望于无产者的即身性(embodiment)拯救突然之间失去了任何意义。这从温斯顿在监狱里对身体疼痛的屈服,对变化了的自己的认可以及从“抵抗—感激—爱—相信”老大哥的转变给出了明确答案。温斯顿对于具身性的找寻失去了意义,新主体(新人类)改变了一切旧有的东西,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三、后人类的生命政治
大洋国的英社党既不赞同德国纳粹的政治权力方式,也不赞同像俄国斯大林酷政那样的方式去强调权力的死亡特性以制造殉难烈士。而是采取一种更为高明的针对生命改造的权力观。不是要毁灭生命和满足于消极的服从,而是要争取人的内心,是要人成为权力的有效拥护者。是从专制暴政和极权主义向“你得是”的肯定性转变,这才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塑造的大洋国的恐怖政治环境:温斯顿不反抗(或无法反抗)老大哥还不够,老大哥要温斯顿真正“爱”上老大哥才是目的。所以人们看到奥勃良折磨温斯顿的目的不是要杀死他,而是以暴力的方式改造让他爱上老大哥。这种治理技术凸显出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是英社党对积极权力功能的追求,即寻求一种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权力观。而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实质上是一个有关后人类的生命政治学,它揭示的是大众生命的一切都是由政治(知识与权力)所塑造的,并且权力遍布意识形态、身体以及身体之外;第二是政治权力的暴力属性和死亡威胁时刻伴随着人民生命本身,而且“成为指导行使政治权力的至高标准”;[4](P67)第三是权力如何实现一个具有顺从权力基因的新主体,知识、情感与语言等本属于人性方面的东西也被权力所操控与改写。特别是这个时候,科技成为权力的最大帮凶。这三个方面迫使权力的新主体不得不去直面“某种与死亡毗邻的政治与超越传统道德的伦理要求”。[5](P18)奥威尔在大洋国中塑造的老大哥对温斯顿的政治治理实质上提出了人类到底是生理人性还是政治/技术人性,这个人类将要面临的根本问题。
与温斯顿生命有关的一切都受到了权力惩戒、社会监控以及国家政治的毛细血管似的渗透时,在自然人性不断消除和新的生命形式逐步被塑造的过程中,温斯顿的生存伦理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图景呢?按照文学伦理学的观点,要求“再现现实社会中的伦理道德现象”[10]去研究文学中“客观存在的伦理性质”。[11]对于老大哥在实施具体、物质权力形式对人行为、话语进行监控和惩戒,即福柯的惩戒社会治理范式中时,温斯顿还可在内在性上进行自我解释与自我管理(自我意识、自我想象以及自我调节),被允许能够拥有回忆老大哥统治以前历史时期的自由,从而给予了他部分的生存真理;而在老大哥的权力以虚拟、象征的方式渗透入身体内部进行性、知识、情感的调节,即进入了德勒兹意义上的控制社会而专注于对生命的调节时,温斯顿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保持一个整体性的身心了。他开始作为一个分裂的主体或者说残缺(prosthesis)者而被作者赋予了小说的修辞策略。由老大哥实施调节生命的技术所形成的控制社会语境中的温斯顿作为残缺者,这也就获得了推动叙事运作的文本动力,同时具有了文本隐喻与社会隐含意,并且成为构成这两者的真实联结。也就是说,这时的温斯顿是一个分裂者的后人类者形象,视觉、感觉和意识不再是自足的独立存在,这些感觉都被身体的物质改变和切肤痛感所占据,他是一个离身者,而不再是一个整体性的人了。在小说的结尾,奥勃良向温斯顿描述了一个每个人都“接受它,欢迎它,成为它的一部分”的政治所塑造的“胜利的世界,也同样是个恐怖的世界”。[7](P243)当温斯顿站在镜子前时,他已辨认不出自己;而他的内心也和他外表的变化一样大:温斯顿出现了幻觉,背叛了裘丽娅,爱上了他一直憎恨的老大哥。就像奥勃良说的,“如果你是人,温斯顿,那你就是最后一个人了。你那种人已经绝迹;我们是后来的新人。……你处在历史之外,你不存在”。[7](P245)奥威尔告诉了我们一个后人类生命政治中伦理的空白。
在由权力制造的裸命中,奥威尔描述了各种人的伦理断裂:温斯顿抢食家人活命的食物使血缘伦理断裂,被老大哥进行思想灌输的儿童诬告陷害父母使价值伦理丧失,压抑于大洋国的政治监控而寻求婚外恋的温斯顿又在鼠刑中背叛情人使爱情伦理毁灭,同事之间相互倾轧,家庭内部互有提防,爱人之间没有信任,邻里之间没有关爱……,本来被认为自然而然的人性在权力之下出现了巨大断裂和矛盾。英社党要构筑的理想社会“是一种庞大、可怕、闪闪发光的东西,到处是一片钢筋水泥、庞大机器和可怕武器,各个是骁勇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团结一致地前进,大家都思想一致、口号一致,始终不懈地在努力工作、战斗、取胜、迫害——三亿人民都是一张脸孔”。[7](P67)这必然要打破历史、真理与伦理的固有秩序,以权力强迫被治理者接受2+2=5的有悖于真理的矛盾。如何实现人之所是呢,权力对此无能为力,但科技却可以再造一个新的组织器官。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就特别强调这个重要特征,即人的生物性(如人的生理、物种属性)而非人的政治性(如人的物质地位、财产权力等),即是说人成为一个基于安全为目的的可用权力算计与生物改造的表面。在小说中,从开始温斯顿对电幕的身体抵抗,到与裘丽娅约会的性暴力想象到最后辨认不出自我的身体,他已经完成了从无感知身体到德勒兹的“无器官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的重大转变。在由生物技术主导的大洋国,温斯顿不再有自我思考的可能,他甚至辨认不出自我了。政治与技术扼杀自由、情感之后,《一九八四》告诉我们人性的伦理和价值尺度都将失去意义。
四、结语
《一九八四》不是,或不仅仅是政治现实的隐喻之作,它给予人的恐怖性更不只是停留在极权主义的恐怖之上。远比这更为根本的是对于生物的人、人性、社会人的伦理以及人的身体组织等进入一个后人类时代现实的深刻揭示。后人类并不是一个指涉时间概念的词,也不是一个指涉异质于人类的一个状态,而是“一种对于自我与历史情境的觉醒与认知”。[5](P6)小说并不擅长大洋国国家治理技艺的细密性描述,也不以极端的血腥暴力场面著称。在未来社会,像温斯顿这样命运的自我意识才是在大洋国政治气候下作者提醒人们所应关注的。小说忧虑“欧洲最后一个人的消失”(如福柯所宣称的人已死了)的意义在于引发人们思考如何“在后人类时代重新定义‘人’,重新找回‘人’的意义”,[5](P5)这样一个人类共同体所面对的普遍问题。在人类已经成为一个过去式的后人类社会中,人们掩卷之余挥之不去的沉重忧虑是在政治与技术对生命形塑的离身与具身的命运中思考它会不会给我们带来福音,即,为何美好生活内在性地成为了问题,这样一个人类所要面对的现实。
[1] Hubert L. Dreyfus,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2.
[2] 肖明文.身体、机器与后人类: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救人就是救自己》[J].文学理论前沿(第十二辑),2014,(2).
[3] Cf. Cary Wolfe,WhatIsPosthuma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4] 尼古拉斯·罗斯著,尹晶译.生命本身的政治: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 林建光,李育霖.赛博格与后人类主义[M].新北:华艺学术出版社,2013.
[6] Bruce Clarke,PosthumanMetamorphosis:NarrativeandSystem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8.
[7] 乔治·奥威尔著,董乐山译.一九八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8] 迈文·伯德.远距传物、电子人和后人类的意识形态[A].曹荣湘.后人类文化[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9] 冉聃,蔡仲.赛博与后人类主义[J].自然辨证法研究,2012,(10).
[10]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外国文学研究,2004,(5).
[1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
责任编辑:高 雪
The Posthuman-Bio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NineteenEighty-Four
Zhi Yunb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rts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Theatre Academy, Shanghai 200040, China)
The posthuman biopolitics was reflected in Orwell's political novel Nineteen Eighty-Four. The reasons are based on the following points: First, the writer was not simply satisfied with constructing the Ocean's terrifying political condition and the Old Brother's governance implementation; second, the warning given by the novel is no more than a worry about the political living environment; third, Orwell's real purpose is to set people thinking about human's living in the environment which is constructed by politics and technology. The novel, which shapes disembodiment coming form political power and embodiment coming from technology, is aimed to make people notice human lif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Nineteen Eight-Four; posthuman; biopolitics; ethics of human nature
2016-10-23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2016M590433);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1601126C);“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高原学科建设计划Ⅱ高原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理论”资助
支运波(1980- ),男,安徽怀远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在站博士后,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研究所副教授,高原学科专家组成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艺术理论研究。
I106.4
A
1672-335X(2017)02-01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