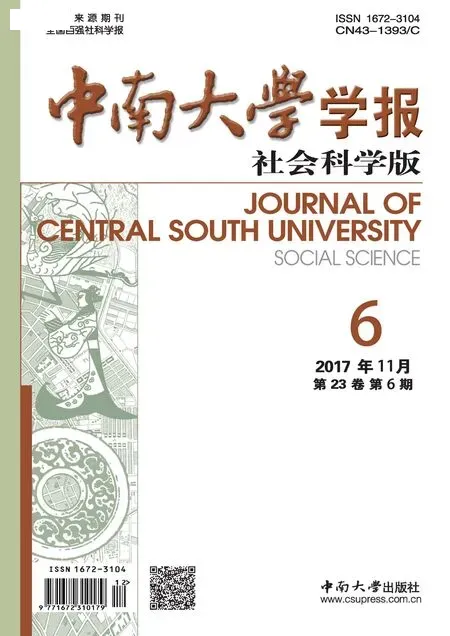回避怀疑论的另一种方式
——托马斯·内格尔的理性主义认识论
贾可春
回避怀疑论的另一种方式——托马斯·内格尔的理性主义认识论
贾可春
(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1800)
从实在论的本体论出发,内格尔认为认识论上的怀疑论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用自我超越的概念来取代它。内格尔指出,认识的客观的进步的可能性源自主体内部的先天成分,而认识论的希望则在于逐步确立一种能与个体视角共存并能理解它的超然的视角。与康德在承认知识的客观性的基础上探讨认识的可能性的做法不同,内格尔主要是在承知识进步的基础上探讨这种进步是如何可能的。通过强调人的先天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内格尔不仅有效回避了怀疑论,而且合理解释了部分科学知识的产生。
内格尔;认识论;怀疑论;客观;自我超越
作为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在批判认识论的还原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极富创见的理性主义认识论,为认识论的研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内格尔的认识论内容艰深、语言晦涩,本文旨在重构其论证过程,并以近代以来的哲学史为背景对其加以阐释。
一、客观性与怀疑论的悖论
在内格尔看来,认识论的中心问题是关于相信什么以及如何证成一个人的信念这样的第一人称问题。认识的主体即自我,天生会追求客观知识,内格尔把具有这种追求的主体称为客观的自我,有时直接将其等同于客观或客观性①。内格尔认为,对客观性的追求本身往往会导致认识论上的怀疑论。作为客观的自我,我们必须如其本然地描述我们被包含在其中的实在的世界,而我们由之认识世界的现象产生于我们与世界的其余事物的相互作用,所以我们必须理解自身的构造对现象产生了哪些影响,并努力确立一种不受个人视角影响的关于世界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因为是由我们确立的,所以也是我们与世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走不出自身的影子,“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客观的观点将不得不依赖于一种未经检验的主观基础”[1](75),而这样一来,我们就有理由怀疑我们的观念是否是客观的,对知识的怀疑自然而然也就不可避免了,那种认为主体可以一步一步地接近实在的观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所以,内格尔明确指出:“传统认识论的怀疑论就依赖于理性的客观性。”[2](92)
尽管怀疑是不可避免的,但知识问题在哲学史上仍得到了积极而充分的探讨。这样的探讨有三类:怀疑论、还原论及英雄式。以休谟为代表的怀疑论认为,我们关于世界的日常信念或科学信念的内容超越了其自身的根据,内容与根据之间存在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还原论者则认为,我们的信念所论及的并不是世界本身,而是向我们显现着的世界。还原论者努力把我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解释为关于可能的经验主张,或者像康德那样,认为某些信念描述了所有可能的经验的界限。英雄式理论,如柏拉图、笛卡尔等人的理论,试图在承认信念的内容与根据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前提下来解决问题;柏拉图提出了理念论及回忆说,而笛卡尔则在对上帝存在进行先天证明的基础上,对人类知识的可靠性进行了辩护②。
内格尔本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他认为,怀疑论的问题并非产生于对标准知识的意义的误解,而是产生于它们的实际内容以及在关于世界的信念的构造中所包含的超越自身的企图;在本体论上,内格尔坚持一种实在论,认为存在一个我们不可能完全经验到的真实的世界,他反对认识论上的还原论;至于英雄式的理论,内格尔把它描述为不切实际的空想;也正是因为他既坚持实在论,又承认认识主体自身的局限性,所以他认为一种普遍的怀疑论是合宜的。怀疑的可能性表明,世界完全不同于它向我们显现的方式,因而我们的认识就难免出错。在笛卡尔看来,错误的产生或许是因为一个恶魔正作用于我们的心灵,或许是因为我们正在做梦。内格尔则从实在论的角度指出,世界在我们无法想象的方面不同于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我们的思想和印象是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产生的,我们无法从自身所在的位置出发来获得实质上正确的关于世界的观念。
怀疑论从古至今都存在,但反怀疑论的声音也一直存在,且占据主导地位,毕竟怀疑论是与我们的直觉相悖的。内格尔站在实在论的立场上,对反驳怀疑论的论证进行了分析和再反驳。日常语言学派的思想先驱乔治·摩尔曾简单地通过举起两只手来证明物质对象的存在,并以此反驳怀疑论。内格尔认为,摩尔的反驳回避了实质性问题,因为如果没有物质对象,他就没有两只手,所以也就没有为反驳怀疑论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内格尔指出,摩尔的反驳若要有效,就必须成功地使人怀疑自己是否有两只手。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日常语言论证认为,关于世界的陈述的意义由它们在其中被典型地使用的情况所揭示,因此我们通常认为其正确的关于世界的绝大部分陈述,不可能都是错误的。对于日常语言论证,内格尔重点分析了人们对普特南缸中之脑思想实验所提出的反驳。
缸中之脑实验意在表明认识问题上怀疑的可能性。对于一个被从身体上切割下来并被置入装有营养液的缸中的大脑,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机程序向其输入信息,以使其保持一切正常的幻觉:对它来说,周围的一切都还正常存在。那么,我们如何证明自己不是这样的缸中之脑呢?这个论证其实就是笛卡尔的恶魔论证及梦幻论证的现代科学版。反怀疑论者反驳道,假设我是一个缸中之脑,在接受刺激时认为自己看到了一棵树,那么我的语词“树”并不指称我们现在称之为树的东西,而指称别人用以制造刺激并导致我认为“有一棵树”的任何东西;因此,当我这样思考时,我就是在思考真实的东西。换言之,假如我是缸中之脑,我的语词“缸”将不会指称缸,并且我的思想即“我或许是缸中之脑”就不会是真的;假如它是真的,那么它就会是假的。但在内格尔看来,反怀疑论者的反驳并不有效:这里我用“树”所意指的东西,并不只是从原因上产生了我关于树的印象的某种东西,或者看起来、摸起来像树的某种事物,或者我们依据传统而将其称为树的某种事物;怀疑论只是表明,那些事物在想象中可以不是树,任何断言它们一定是树的理论都是错误的。这表明,在内格尔这里,怀疑或怀疑论是可理解的。
事实上,因为认识论上的怀疑论天然地假定了本体论上的实在论,并自称超越了经验,故怀疑的可能性根植于我们的日常思想。怀疑是认识我们的处境的一种方式;怀疑论的批评者们所提出的各种语言运作理论,如意义的可证实性理论、指称的因果理论及宽容原则,都被怀疑论的明显可能性及可理解性所反驳。每一种怀疑都代表着关于世界的一种可能性,“我们能够想象的传统的怀疑的可能性,代表着我们不能想象的无限的可能性。”[1](82)在认识的过程中,我们所获得的关于世界的观念,不管多么复杂,都是世界的一个片断的产物;我们所相信的任何东西,都一定悬挂在怀疑论的巨大的黑暗洞穴之中。
二、作为怀疑论的替代性选择的自我超越概念
在认识论上,尽管在内格尔看来怀疑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仍然认为怀疑论并非最好的选择;毕竟,追求一种超然的关于世界的观念是客观自我的本质任务。相对于怀疑,他提出了一种可供替代的选择,那就是确立一种自我超越的概念。内格尔指出,这种自我超越的概念应当完美地解释以下四个问题:(1)世界像什么样子;(2)我们像什么样子;(3)为什么在某些方面世界向类似我们这样的存在物所显现的样子与其本来的样子一致,而在某些方面又不一致;(4)类似我们这样的存在物如何才能获得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里,第四个问题实际上说的是我们是如何使用理性能力来构造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的。在内格尔看来,这个问题是客观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对世界及自我做出解释的同时,也必须解释我们是如何解释世界及自我的,换句话说,必须描述人类自身如何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事实上,在西方哲学史上,从古代的柏拉图开始,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大量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但内格尔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独树一帜。
内格尔指出,客观性所追求的目标在于获得一种关于世界的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必须包含一个人自己的观察角度。不过,这种包含并非实质性地包含,而是作为工具来包含的;换句话说,理解(understanding)的形式对我们自己来说是特殊的,但其内容并非如此。内格尔认为,人类知识是在对客观性的这一目标的追求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这种增长可以在两种情况下实现:一种情况是客观性没有取得进步,另一种情况是客观性取得了进步。
在人类探求知识的历史中,我们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在客观性没有取得任何进步的情况下获得的;也就是说,它们往往只是在业已存在的层面上补充了另外的知识,或者说,这些知识只是在填充一个业已存在的理解框架。在科学史上,许多科学成就,甚至卓越的科学成就,如新行星的发现、DNA结构的发现、某种疾病的原因的发现等等,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关于人类与世界之间认识关系的观念;换句话说,这些卓越的科学发现,虽汇集了科学天才的智慧,但并不意味着客观性的进步。
那么,客观性的进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内格尔指出,“客观性若要取得进步,那就需要业已存在的理解形式自身成为一种新的理解形式的对象,而且需要这种新的形式也去理解原有形式的对象。”[1](83)在他看来,客观性在上升途中的任何一步都是这样迈出的,即使它并未达到解释它自身这样的更有抱负的目标。客观性所取得的每一次进步,都把我们先前对世界的理解纳入对我们与世界的精神关系所做的新的描 述中。
接下来的问题是,取得这样的进步是否可能,或者说,我们能否获得这样的一种自我超越的概念?通过考察哲学史上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及科学史上狭义相对论的创立,内格尔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内格尔认为,这两个例子特别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如何能把自己置身于对世界的一种新的描述中。因为这两个例子在内格尔对客观性进步的论证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发端于古代的原子唯物论者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及卢克莱修等人,但近代英国经验主义者洛克对这一区分进行了系统的哲学论证,并使其成为近代哲学中一个意义深远的话题。在洛克看来,物体既拥有广延、形状、动静、数量等一类性质,也拥有颜色、声音、滋味等一类性质。人们往往会把这两类性质混同起来,并认为它们都是事物的内在性质。然而,经过仔细研究发现,事物是在向我们显现的过程中才拥有后一类性质的,比如,是红的只不过意味着,在现实世界的正常知觉条件下,对正常的观察者来说,有某种东西看起来或将会看起来是红的;所以,对颜色性质现象的最好解释将不会把它归属于具有内在颜色属性的事物,因为我们发现颜色既随物理条件也随心理条件而变化。而另一方面,像形状这类性质却自然而然地构成了可变的形状现象的一部分,它能用来解释关于对象的许多事情。于是,我们就可以推断:后一类性质现象是由对象的前一类性质引起的,而且我们因此就能尝试着去发现前一类性质,并越来越把更少的后一类性质归属于物体。洛克把前一类性质即物体的形状、大小、组织等叫第一性质,而把物质微粒作用于感官并使人产生颜色、声音及滋味等感觉时物体所具有的能力叫第二性质,有时也直接把相关感觉叫第二性质。两种性质都是物体在人体上制造相应的感觉的能力,但第一性质与其所产生的感觉完全相似,第二性质则与其所产生的感觉完全不相似。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之所以能对这两类性质做出区分,原因就在于,以往的观点因承认物体除了拥有第一性质以外还拥有内在的颜色等性质,故没有能力解释自身即解释事物为什么是以本然的方式向我们显现的,从而就使得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概念,以便既能解释先前的现象,也能解释新的印象即它本身是真的。
科学史中的一个例子,即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则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内格尔所说的客观的进步是否是可能的。以牛顿为代表的古典力学确立了关于事件、事物及过程的绝对时间和空间关系的观念,但狭义相对论表明,事件的同时或相继、事物在尺寸上的相等或不等,都非绝对的,而是相对于一个参照系而言的。事实上,必须用相对论的时-空来取代绝对时间和空间。内格尔就此评论道:“从一个参照系即从一个世界的视角来看,先前被看作客观的绝对时间和空间概念的东西,仅仅被揭示为一种现象”。事件被客观地(即不依任何参照系)定位在相对论的时-空中,而如果要把它们划分为单独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则要依赖于一个人的观察角度;因此,在狭义相对论中,爱因斯坦通过对电动力学现象的反思,表明依个人视角而获得的绝对时间和空间必须被超越。[1](85)
从上述两个例子,我们看到,认识主体逃避自身境遇的方式,不仅在于从不同的视角看世界,还在于上升到某些新的层面,而从这些层面出发,我们就能理解并批评先前的视角的一般形式。客观性的进步就是依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取得的。内格尔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通往一个新的视角的步骤都是认识论上的洞察力的产物。
知识进步的意义就在于客观性本身的进步。一种客观的进步可以被一种新的客观的进步所取代,并且后者反过来又把前者还原为一种现象。后者可以解释前者,但前者却无法解释后者,比如相对论的时−空理论可以解释关于绝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论,而反向解释却不行。但是,这两者本身并不处在同一个层次上,后者又是通往后继者的一个必要步骤。
在内格尔那里,自我超越本身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无论我们的认识处于什么阶段,我们都可以期待着客观性的新进步;在认识发展之途中,我们始终处于过渡阶段;现在的知识将不断为后来的发现和理论所抛弃。内格尔指出:“曾被看作具有最大程度的客观性的实在概念,都已作为现象被包含在一种更客观的概念中。”[1](86)我们的认识需要不断前进,而且事实上,通过自我理解的方式所取得的进步至今仍然是最低限度的。
三、客观的心灵的可能性
在认识论上,内格尔的思路颇类似于康德。在康德那里,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即先天综合命题已经存在,问题在于“先天综合命题是怎样可能的”[4](32);而在内格尔这里,哲学史及科学史的例子表明客观的进步已是事实,问题在于这种进步是如何可能的。但二者所问的问题本身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康德所瞄准的是认识主体的一种自我理解,即从内部对我们所有可能的经验和思想的形式及限度所进行的理解,而内格尔则要从一种超然的或者说非人类的观察角度来理解心灵的运作,即对获取客观知识的可能性做出解释;内格尔认为他站在比康德更高的层次上[1](87)。问获取客观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其实就是问客观的心灵或者说心灵的客观能力是如何可能的。对内格尔来说,解释这种可能性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些人对心灵的客观的能力做了进化论的解释,内格尔对此持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解释了在那些已经产生的生物体的可能性中间所做出的选择,但并未解释那些可能性本身;它试图通过在既定条件下出现的一组可能性来解释进化将会采取的路线;作为一种历时性理论,它也许解释了具有认识能力即能进行想象或推理的生物为什么会生存下来,但没有解释这种能力本身是如何可能的;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超时间的解释。内格尔明确指出,人的高级理智能力极不适于做进化论的解释,而且我们也找不到依靠进化论而进行解释的理由,所以对我们的理论化能力所做的进化论的解释绝不会确认其发现真理的能力。内格尔所批判的进化论解释的靶子其实是斯宾诺莎的智力进化说,尽管斯宾诺莎的思想早于达尔文所开创的进化论两个世纪。斯宾诺莎说过:“知性凭借天赋的力量制造理智的工具,再凭借这种工具获得新的力量来从事别的新的理智的作品,而由这种理智的作品又获得新的工具或新的力量向前探究,如此一步一步进展,直达智慧的顶峰为止。”[3](28-29)内格尔认为,斯宾诺莎的解释没有任何值得我们相信的理由,这种解释只是试图将一切都还原为自然的东西。
在否定智力进步的进化论解释的同时,内格尔又坦承自己也无法提供解释这个问题的理论。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借助于纽拉特的船喻对此提出了一些猜测性的判断。当一艘在公海上航行的轮船出现破损时,水手们不可能将其开到干涸的船坞进行拆除,并在那里用最好的材料将其修复,而只能在航行过程中一块船板接着一块船板地进行改装。纽拉特把知识整体比作一艘船,把科学家比作水手,他认为科学家们在建成知识之船时也是通过点点滴滴的方式做到的,而这正如水手们一块船板接着一块船板地改装轮船。然而,内格尔对这个比喻做了自己的解释:我们在把旧船改装成新船时确实需要吸收旧船的某些部件,然而我们是从自己身上搜集了绝大部分的改装材料。这意味着,我们取得客观进步的可能性源于主体自身的某种先天成分。不过,我们不要认为内格尔又要回到康德的先验哲学。他并没有指出这种成分是什么,而只是说,我们在修建知识之船时就占据着它,但也许不可能达到它。在这看似矛盾且晦涩的表述背后,内格尔想说的是,我们可能发现不了这种成分,但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我们离不开它或者说是在实际使用着它的,而且它本来就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内。因此,在内格尔这里,主体自身就是取得客观的进步的源泉。
内格尔把自己的观点称作理性主义的,但此种理性主义不同于以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等人为代表的近代理性主义。作为经验主义的对立面,近代理性主义认为,我们拥有关于世界的天赋知识,而且我们是从清楚明白的观念或“真观念”出发并通过理性演绎来获得科学知识的;而内格尔的理性主义却意味着,我们有能力提出一些假设来解释世界大体是什么样子,而且关键在于,这种能力不是基于经验的。内格尔还进一步认为,即便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的精神能力可以完全反映实在,但仍可假定,我们全都潜在地在自己的头脑中携带这种与生俱来的可能性。因此在他看来,绝大部分真实知识的基础一定是先天的,并且是从我们自己内部获得的。“特殊经验的作用,以及世界经由个体的视角对我们的影响所产生的作用,都只能是选择性的,尽管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1](92)经验知识或经验信念最终都必须依赖于主体自身内的先天成分。
由此出发,内格尔像乔姆斯基和波普尔等人一样,断然反对各种关于心灵运作方式的经验主义解释,并大胆断言,“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自己想起了全部的世界万物。”[1](93)在像牛顿的万有引力说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样的重大科学理论进步中,理性证据和经验证据之间之所以存在极高的比率,也正是因为经验证据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主体自身的理性是更为关键的。有时,即便理论的经验方面的预言非常丰富,它们也是在相对有限的观察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的,而且不可能从那些材料中演绎出来。
内格尔认为,当用心灵来思考世界时,我们就是在确立一种蕴含在自身的精神及物理构成中的与世界的关系,而之所以有可能确立这种关系,正是因为在我们自身内部存在着某种先天成分。这种成分象征着我们自己与世界之间的某种融洽,我们不能对这样的融洽做出解释,但它是思想产生知识的必要条件。在近代理性主义者笛卡尔那里,这样的成分是上帝。内格尔当然没有在认识论中为笛卡尔的上帝留有位置,但他认为我们自身内的这种先天成分起到了笛卡尔的上帝所起的作用。在他看来,尽管我们目前无法知道这种东西的性质,但若要毫不含糊地坚持我们的信念,且要使人类的知识成为可理解的,我们就必须相信存在着这样的东西。因此,内格尔对自己的理论做了这样的定位:“我的观点是理性主义的和反经验主义的,这不是因为我认为我们的信念的一种坚实的基础可以先天地被发现,而是因为我认为,除非假设它们 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某种全局性的事物中有一种基础,它们就是无法理解的——而它们确实是可理解的。”[1](94−95)
内格尔指出,认识论旨在逐步解放受困于人类经验的个体视角之中的沉睡着的客观自我,并试图获得一种充分的实在概念。但在客观的进步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困难:一方面,人既是一种具有普遍特征的客观自我,亦是一种拥有经验视角及个体生命的主观自我,另一方面,实在本身也非仅仅是客观的实在,因此,我们既能构造关于某种事物的客观的概念,亦能同时拥有关于那种事物的主观的概念;但由于“客观的及主观的自我的要求似乎都太强了”[1](99),这两种概念往往不能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容易产生主客观的冲突问题。在认识论中,这种冲突就表现为心灵没有能力同时坚持怀疑的可能性和充满于生活的日常信念。内格尔认为,要解决这种冲突,就必须确立一种能与个体视角共存并能理解它的超然的视角。那么如何确立?这里可以再次用洛克关于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区分的例子来说明:现在,第二性质与第一性质的冲突变成了现象与客观的实在的区分,这种区分成了一种新的混合理解的对象,而此种理解结合了主观的及客观的成分,并且是以对第一性质的客观性的认识为基础的,于是冲突消失了。事实上,在内格尔看来,通过把先前的理解的某些方面置于现象领域,然后站在更客观的立场对其加以理解,不仅是客观的进步的唯一出路,也是认识论的希望所在。
四、评价
从近代以来的哲学史看,内格尔为认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首先,为认识论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地。近代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分别强调经验和理性在认识中的根本性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认识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近代的康德和现代的胡塞尔则从一个更深的层次来探讨认识论问题,他们在承认知识的客观性的基础上力图解决认识的可能性问题:前者着重阐明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根据何在,后者着重阐明超越的实在的对象如何在认识行为中被切中,或者说,如何在主观性中构建客观性。而正如前文指出,内格尔在探讨认识论问题时则又处在比康德(当然也包括胡塞尔)还深的一个层次上:他要在承认知识的获得及知识的进步这些不争的事实的基础上来探讨知识进步的可能性。在内格尔哲学中,因为知识的进步意味着获得知识的能力的提升,进而又意味着客观自我的进步,所以若用其特有的语言来表达,认识论的任务就是要回答客观自我的进步是如何可能的这一全新的认识论问题。新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新的认识论研究领域的打开。其次,有效避免了认识论上的怀疑论。从培根到休谟的西方近代经验主义发展史表明,完全从经验主义出发最终必然导致怀疑论,这样不仅解决不了知识进步的可能性问题,甚至连知识的客观性本身也成了问题。因此,相比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强调人类先天理性的作用就从另一侧面凸显了内格尔认识论的价值,这种强调不仅回避了怀疑论,而且本身也体现一种逻辑的合理性。再次,可以合理地解释部分科学事实。诚如内格尔本人所说,他的理性主义强调在知识的构成中理性因素比经验的贡献更大,从而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科学家时常能从很少的经验材料中获得大量的知识。
但是,对于内格尔的认识论,值得商榷的是:为了解释这现象即科学家能从很少的经验材料中获得大量的知识,一定要采取理性主义路线吗?答案是否定的。这里,可以把内格尔和蒯因做一简单的对比来加以说明。理性与经验在形成科学理论时的贡献占比问题,正是逻辑实用主义哲学家蒯因特别关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能在“贫乏的”感觉刺激的基础上产生“汹涌的”输出即我们关于世界的丰富理论。非常有趣的是,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内格尔和蒯因尽管都承认能从少量的材料中获得大量的知识,但两人的基本哲学路线却是截然相反的:蒯因是典型的经验主义者,他力图摆脱亚里士德的第一哲学及康德的批判认识论,承认观察在认识中的基础地位以及观察句在理论中的证据和语义作用,最终把对人的认识能力的研究归结为对语言学习过程的研究,进而又把认识论视为“自然科学的一章”[5](410)。相反,内格尔坚持的是理性主义,他始终停留在先天的层面上来提出和探讨问题。但这种理性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独断论,内格尔一方面否认可以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解释客观自我进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承认自己也无法提出一种可以解释这种可能性的理论,甚至说“至少还要再经历数千年的时间,科学及其他方面的发展才能将其揭示出来”[1](93)。因此,内格尔仅仅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也可以说,其理论本质上只是一种可以解释部分科学事实的思辨性假说,这样的一种理性主义认识论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蒯因所批判过的“第一哲学”或批判认识论的路线上去了。
注释:
① 在内格尔的哲学中,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客观或客观性是在多重意义上被使用的,它既指客观的自我,也指知识所应具有的那种非个人化的特征,有时还指主体获得客观知识的 能力。
② 这里需要特别解释一下英雄式理论。内格尔所说的“英雄”,其实就是“大胆”的意思,它意味着持有这种理论的人不会像还原论者那样努力去填平信念的内容与根据之间的鸿沟,而是无视这种鸿沟的存在,或者说勇敢地去跨越它。柏拉图的理念论和回忆说意在表明,感觉是不真实的,人们关于真实的永恒的理念的知识只能通过回忆而获得;笛卡尔则认为,清楚明白的观念是上帝先天印入人类心灵的,而从这类天赋观念出发并通过理性演绎,我们就能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真理性知识。显然,柏拉图和笛卡尔都没有“理会”鸿沟的存在,也可以说,直接跨越过去了。
[1] 托马斯·内格尔. 本然的观点[M]. 贾可春,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 托马斯·内格尔. 理性的权威[M]. 蔡仲, 郑玮,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3] 斯宾诺莎. 知性改进论[M]. 贺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4] 康德.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 庞景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5] 涂纪亮, 陈波. 蒯因著作集(第2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Another way of avoiding scepticism
JIA Kechun
(College of Marxism,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211800, China)
From the ontological view of realism, Nagle thinks that the epistemological scepticism is unavoidable, but we can substitute a self-transcendent conception for it. He points out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objective progress about the matter of cognition is derived from an a priori element within the subject, and the epistemological hope 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detached perspective which can coexist with and comprehend the individual one. Different from Kant who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cognition on the basis of acknowledging the objectivity of knowledge, Nagel mainly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rogress of knowledge on the basis of acknowledging such progress. By stressing the role of man’s innate reason, Nagel not only avoids scepticism effectively, but also explains reasonably how some scientific knowledge comes into being.
Nagel; epistemology; skepticism; objective; self-transcendence
[编辑: 谭晓萍]
2017−05−25;
2017−06−26
贾可春(1967−),男,江苏宿迁人,哲学博士,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西方哲学
B712.6
A
1672-3104(2017)06−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