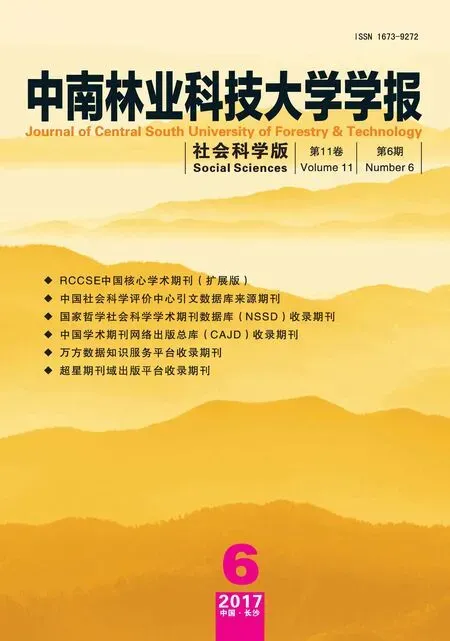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模式探究
黎 敏,刘俊月,焦小楠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政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模式探究
黎 敏1,刘俊月2,焦小楠3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政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伴随着区域一体化的纵深推进,长株潭城市群将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一体推进成为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与必然要求。当前,传统的以政府单维主导为核心的环境治理模式、平行政府间的利益分割、政府官员执政理念缺失、生态一体化立法存在诸多局限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群生态一体化进程。因此,从意识、制度以及行为等三个层面探讨了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模式的最优策略选择,力图构建起一种由政府主导、法制化的生态协同治理模式,即长株潭城市群内平行政府间协同治理和包含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治理,以期形成长株潭城市群经济建设与生态治理良性互动与发展的新格局。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模式
伴随着区域一体化向纵深推进,经济的竞争与发展并不再以单一城市为主体,而更多地表现为具有集聚经济效应的城市群之间的角逐。2012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这无疑是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中重要一环的长株潭城市群又一历史性发展机遇。传统的一体化发展往往重视城市群内各城市的经济一体化发展而忽视其他方面的一体化进程,甚至将经济一体化发展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与牺牲环境的基础之上。从长远来看,环境问题的凸显也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面对跨区域环境污染事件的愈演愈烈,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治理模式俨然已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如何走出区域环境治理的“公共困境”已然成为城市群发展必须直面的难题之一,亦与其治理模式的选择休戚相关。
一、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的缘起
所谓城市群生态一体化,即城市群内的各个城市间通过某种方式突破传统行政区划障碍,形成相对完整的生态治理单元,基于同一体系与机制相互合作,形成合力,从而实现对城市群内跨界污染的有效治理,提高城市群环境治理,改善其生态服务功能,为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奠定良好的环境基础。生态一体化涉及各平行政府间的相互融合,贯穿于生态环境规划、环境监测布局以及环境管理监督等完整的治理过程,需要从多层面探讨分析,构建起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的创新路径。
长株潭城市群是以长沙、株洲以及湘潭三市为核心,辐射周边包括岳阳、常德、益阳、娄底以及衡阳在内的五市区域。作为湖南省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带,长株潭城市群的一体化进程始终受到湖南省决策层的高度重视。早在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推行之时,长株潭的经济一体化便已初见端倪,其后陆续有学者提出建立“长株潭经济区”抑或组建“长株潭规划办公室”等建议,并针对性地开展了一些初步活动,但在1986年后由于意见分歧,该计划也暂时搁置;直至1997年,“长株潭座谈会”的召开才标志着长株潭一体化进程的重新启动;而在1998-2005的短短八年间,由湖南省计委牵头,相继颁布并实施了多项规划,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进程也取得了重大进展。2007年,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其中,“生态同建”与“环境同治”两个概念的提出更是赋予了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新的内涵,反映了将经济与生态建设一体化的客观要求,即“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其含义有二:一是构成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的重要部分之一,则在其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与生态建设必须同步推进;二是鉴于长株潭三市在地域上是由湘江为纽带而自然联结而成的生态整体,其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则必须统筹规划执行。
二、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现状
长株潭城市群作为我国重要的发展区域之一,在其不断的发展建设过程中,无可避免地暴露出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大气污染防治任务依旧艰巨,以株洲清水潭、湘钢工业区为典型的重化工业区大气污染以扬尘和煤烟型为主,而长沙市芙蓉区、天心区等中心城区由于人口密集、交通繁忙,因而产生大量油烟污染与尾气排放,而南北走向的湘江谷地地形作用下,长株潭城市群大气污染相互叠加,空气质量堪忧;其二,水环境污染严重,连接长株潭三市的湘江主要污染源在于长沙市人口众多带来的大量生活污水排放、株洲与湘潭老工业区过去工业废水排放带来的重金属污染累计沉淀以及湘江丰水期航运活动频繁所造成的石油类污染物排放问题等,水污染的复合作用与叠加效应加剧了湘江治理的难度;其三,区域土壤环境污染蔓延,长株潭三市核心城区覆盖面广且地理空间布局上呈相连趋势,株洲、湘潭常年以冶金、火电以及化工的高排污产业为主导,累计沉淀的三废排放经沉降作用造成周围土壤的严重污染与扩散,重金属污染严重超标[1];其四,潜在问题突出,受经济利益驱使,城市用地的迅速扩张带来了生态“绿心”遭蚕食、电子垃圾污染、噪音污染等新的污染形式更为突出,大有加剧之势,亟需得到重视。
长株潭城市群在其区域生态一体化治理中所暴露出的问题:首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盲目,在承接一些东南沿海的产业转移时,竞相降低其环境准入标准以获得这些“两高一资”(即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企业的青睐;其次,当前的长株潭城市群环境监管体制亦有缺失,体制设计不善使治理问题在生态同建与环境同治的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等各个环节极易出现矛盾与纠纷,不仅起不到事前预防的效果,连及时止损都尚有难度,同时环保部门执法力度不一、违法成本与守法成本不相平衡等现状也与监管体制的缺失须臾不可脱离;再次,交界生态功能区由于受到行政地域分割等影响,出现分别保护抑或一方开放、一方保护等相脱离局面,无法得到统一的治理与协同保护从而影响了生态一体化进程;最后,由于高污染企业所带来的治理成本高、难度大等问题,当前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所需资金数额较大,筹措存在难度,而现行的环境投融资体制以及传统的以政府单维主导为核心的环境体制都限制了整治资金的筹集,近、中期的生态一体化治理自然受阻。
三、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困境分析
(一)政府官员执政理念缺失
随着环境保护在国民经济建设上地位的逐步提高,不少地方也相应地在官员考核制度中纳入了环境政绩指标,然而由于多数官员任期相对较短,囿于眼前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经济人”价值取向,各行政区地方政府为迅速提高在任期间经济增长绩效而牺牲城市群环境保护也不足为奇,特别是在一些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地区是长株潭区域工业重镇,同时亦是常年污染重灾区,在两型社会未正式提出之前,以株洲和湘潭为例,化工、冶金等重污染行业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分别高达52%和63%左右,其结果可以想见。[2]密集的重化工业布局在带来GDP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湘江带来了沉重的污染负担。尽管“绿色风暴”不断荡涤长株潭三市的“两型社会”建设,但局部生态的好转并未改变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因此,纠正官员执政理念,从根本上树立起“环境保护优先”观念迫在眉睫。
(二)生态一体化立法存在诸多局限
当前,我国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规章已经大致成型并有了相对完善的体系,即它是以《宪法》为核心,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的一套完整的法律框架,但地方政府主导治理模式下的环境立法仍然存在诸多局限。
首先,城市群作为环境法规执行主体的完整性被人为割裂。保护城市群整体环境生态的执行主体碎片化,综合治理与市域治理矛盾丛生,长株潭三市按自己的法规对其区域内环境问题进行治理,无法打通行政区划隔阂,市域规章与城市群总体规划存在出入,环境治理难以取得预想成效。[3]其次,环境立法相对滞后,立法内容存在一定的空缺与诸多法律盲点。当前,湖南省环境法制的水平尚待提高,关于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地方立法仅有22部,并且,提出建设“两型社会”以来所颁布的关于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方面的法律规范也是屈指可数。同时,在具体的立法内容上亦存在一定的空缺:尽管湖南省针对长株潭城市群环保问题出台了《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保护条例》,其后省政府颁布了《湖南省湘江长沙株洲湘潭段生态经济带建设保护办法》,其中对生态绿心区、湘江长株潭段都做出了比较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但是,其他诸如大气、生物资源保护、固体废弃物等领域都处于真空状态,或仅有规范性文件规定条款,而缺乏执行性行为的规定。最后,环境法规内容存在冲突,运行失灵。例如在对于湘江流域的水资源环境管理方面,对水质与水量的监测由不同的部门执行。另外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之间亦存在交叉重叠,部门的职权划分不明确、职权交叉等问题对其统一监管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困难。
(三)各自为政、行政地域分割等现象阻碍生态一体化进程
就我国当前的环境治理实践来看,仍然是以传统的行政区划为环境治理的基本单位。因此,长株潭城市群的环境治理困境之一正是在于:以市为界的行政区单位与城市群区域在空间上并不耦合,于是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在制定相应环境规章时往往着眼于本地区利益,而忽视邻近区域以及长株潭城市群整体区域的长远利益。当前,一方面长株潭在生态一体化立法上尚未形成系统的规划体系;另一方面,立法权限设置不平衡造成了长株潭三城市的立法权不平等的直接结果,长沙市制定的法规无法在株洲、湘潭两市适用,而对于长株潭区域两型试验区管委会的工作性质,地方法律文件中也并未给予明确的解释。因此,城市群环境保护机构地位得不到合法承认自然治理低效,加之各长株潭三市的无序竞争问题,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也只能滞留于“坐而论道”的层面上。
(四)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绝对主导者使其他主体陷入选择性失语
生态一体化治理未取得根本性突破的原因之一在于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掌握了过多过大的权力。一方面,公众对于政府环境信息的了解并不充分,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相应地社会力量的监督十分薄弱;另一方面,对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缺少明确而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以及利益化的激励。[4]因此对于政府以外的其他主体往往在环境治理问题上过度依赖前者而选择集体失语便不难解释。
四、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模式构建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模式应当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合作架构,强调政府在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中所扮演重要的治理角色,在此基础上鼓励企业、公民及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以实现协同治理。
“协同治理”涵盖两层内涵:一是长株潭城市群内平行政府间协同治理;二是包含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治理。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与企业。目前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环境治理现状而言,与企业合作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可供挖掘,可以通过签订单边协议、合同委托等方式使部分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化被动为主动,如此能够大大提高环境治理成效;第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化治理逻辑之下,政府应当寻求与非政府组织在环境治理问题上的磋商解决,提供制度与政策上的支持,将其公益性志愿融入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的实践中来;第三,政府与公民。从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实践来看,其先后建立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与环境听证制度都无一例外表明其听取公众意见的理性认知。然实际上公民参与并非其主动行为而是政府依赖型的非自觉行动。因此政府必须以环境公众利益为切入点,寻求真正意义上的政府与公民的通力合作,从而真正实现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化协作治理。此外,协作治理的另一要义在于府际协同治理,其中独立而具有权威性的跨区域生态治理机构成为生态一体化治理中的关键一环。如前所述,当前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的梗阻之一在于地方政府的“经济人”取向造成了各自为政、主观上不合作的一体化危机。基于此,可通过一个直接向省政府负责并接受其指导的独立性跨区域生态治理机构,由其统一管理城市群层面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克服单一政府生态治理意愿缺失的现实,赋予其必要的权威则可以从制度层面保障地方政府间生态合作的有序而稳定推进。
再者,良好的法治环境应当成为长株潭城市群未来生态一体化治理模式中的重要环节,法律的规范与协调作用毋庸置疑。因此,城市群综合协调治理模式所强调的法制化上至全国性的法律条文、下至各地区具体的环保制度在内的环境法规、政策等都应力求从机构设置、职责配置、权限划分以及责任追究等各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与明确,以营造一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有序法治环境,从而谨防生态一体化治理走入抢救模式。
五、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模式构建的路径选择
(一)意识层面:加强生态意识教育,树立城市群生态一体化观念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模式的优化必须首先诉诸于意识层面的改变,即理念先行,应切实扭转过去有所偏重的发展观,树立起生态文明理念,为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首先,加强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内各地方政府及官员的生态意识教育,明确其在城市群整体发展中所应担负起的环境责任,在治理现有环境问题的基础上,切实树立起“环境保护优先”的可持续发展观,即为了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环境的整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作出宁可牺牲本行政区经济发展与以GDP为主导的政绩考核的决心,切实树立起生态一体化观念,如此才有望消解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矛盾问题。
其次,加强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内各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生态环保教育,企业作为长株潭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同时往往也是环境污染的主要相关责任主体,其中尤以重化工业企业为主。因此,提高企业及其内部员工的环保理念势在必行,使企业在享受其权利的同时承担起相关环境保护义务和社会责任。
最后,增强公众(包括各种民间组织)环境意识。就当前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的公民参与情况来看,公民参与环境管理意识淡薄,且很大程度受限于主管的行政部门,参与广度与深度均较弱。公民与社会团体作为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多元主体的中坚力量,其环境管理参与的热忱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体化治理的成败。
(二)制度层面:推进并完善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制度建设
长株潭城市群应坚持在本地区实际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与规章制度,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完善生态一体化治理的组织制度建设,强化跨区域的环境治理机构的地位与作用。当前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困顿的重要弊病在于:现有长株潭区域两型试验区管委会作为城市群区域管理组织,在相关的地区法律文件中却并未对其性质及地位做出明确界定,使得其在履行环保政策、进行城市群环境治理的实践中往往受制于多方面因素;同时,当前的两型试验区管委会原则上主要负责从省级向市级合作的纵深推进,因此,相应的三市地方政府间合作则缺乏专门的组织与制度保障。针对这一问题,重视与加强跨区域环境治理机构尤为重要。具体而言,即在不改变行政区划界线的前提下,明确赋权于长株潭区域两型试验区管委会,并在相应的规章文件中予以地位保障,长株潭三市在此基础上达成原则性共识,建立起长期的磋商谈判机制,进而对城市群区域生态环境实际问题进行协调。
另一方面,整合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内现有的法规制度。长株潭三市中只有长沙市有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三市地区合作时常受制于各地具体实施细则与文件相冲突的现实矛盾。因此,长株潭三市地方政府应当从城市群整体的大局利益出发,对现行生态一体化治理的有关规章文件进行必要的梳理,做好冲突规章文件的清理整合工作,从而打破区域利益分割,便于城市群整体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体化治理。
(三)行为层面:实现生态一体化治理多元主体的行为生态化
理念层面抑或制度层面的建设,最终仍要诉诸于行为主体的具体实践行为中去,因此实现生态一体化治理多元主体的行为生态化将是长株潭城市群环境治理模式优化的最终落脚点。
首先,必须力求实现政府及其官员的治理行为生态化。具体而言,即推动建立包含经济与环境等相关要素在内的综合政绩考评细则,即便是短期在任绩效考核亦是如此。将资源环境的的核算纳入考评之中,具体而言即可以将生态项目的规划与实施以及污染治理效果纳入指标之中,同时适当引入生态法律意识以及环保宣传的普及掌握情况等维度,如此必然能够规范政府以及官员一味追求GDP而忽视环境治理的“经济人”行为,进而引导和规范其行为模式向“环境治理优先”转变,协调好长株潭三市政府间由于地区经济利益冲突所造成的隔阂与矛盾,最大程度地优化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成效。
其次,实现企业行为生态化,对长株潭环境治理问题承担起必要的社会责任。毫无疑问,企业的经济生产活动对于该区域的生态环境意义重大,其中例如株洲与湘潭的重化工业企业必须率先完成生产方式转变,努力转变传统的生产、消费方式。对环境产权配置中的权力义务关系进行明确,从而严格规范污染者的污染排放行为,进而促使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以实现污染控制、承担起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除此之外,还应当鼓励企业通过发布环境责任报告、绿色采购等行为途径践行环境保护义务,自觉参与到生态一体化治理的建设中来。
最后,实现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内公众行为的生态化,从而为生态环境公共事务治理奠定现实基础。生态环境的公共性特征以及环境保护的公益性等都从根本上决定了公众参与生态一体化治理的必要性与必然性。为改变当前长株潭区域公众环境管理参与低的问题,可以通过鼓励环保非政府组织独立、自由地开展专项环保活动以及环保科研工作,同时鼓励公民个人在了解环保情况的基础上采取环保行动,向环保主管部门以及相关机构反映问题,利用当前长株潭三地已有的环境听证会等平台,提出意见,参与决策。[5]
[1] 何 甜,帅 红,朱 翔.长株潭城市群污染空间识别与污染分布研究[J].地理科学,2016(7):1081-1090.
[2] 张成福,李昊城,边晓慧.跨域治理:模式、机制与困境[J].中国行政管理,2012(3):102-109.
[3] 杨星灿,陈广益.长株潭两型“试验区”区域法制配套研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6(3):63-68.
[4] 邓集文.试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兴起[J].东南学术,2012(3):128-136.
[5] 黎 敏.协调治理视域下企业环境管理机制创新研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0(4):13-16.
Study on Governance Models of Ecosystem Integration of Chang-Zhu-Tan Urban Agglomeration
LI Min1, LIU Junyue2, JIAO Xiaonan3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Hunan, China)
Along with the further promoting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t has become essential for Chang-Zhu-Tan urban agglomeration to tak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s a unit in making overall plans and promo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At present, problems like the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led unilaterally by governments, pro fi ts division among parallel governments, of fi cials’ lack of governing philosophy and various limitations on legislation of ecosystem integration, have hindered the ecosystem integration proces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oice of the strategically optimum governance model of ecosystem integration of Chang-Zhu-Tan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erms of consciousness, system and behavior. It seeks to build a government-oriented, legislative and coordinated ecological governance model that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mong the governments inside the Chang-Zhu-Tan urban agglomeration as well as the multi-subject governance including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attempting to form a new pattern in which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inside the Chang-Zhu-Tan urban agglomeration positivel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soundly develop.
Chang-Zhu-Tan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ecological integration; models
F205
A
1673-9272(2017)06-0018-05
10.14067/j.cnki.1673-9272.2017.06.004 http: //qks.csuft.edu.cn
2017-06-22
湖南省科技厅科技计划一般项目“基于协同政府理论的环境治理实证研究——以湘江流域为对象”(2014SK3207)。
黎 敏,副教授;E-mail:cslm2000@163.com。
黎 敏,刘俊月,焦小楠.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模式探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11(6):18-22.
[本文编校:罗 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