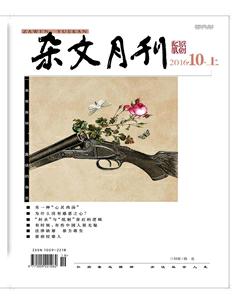三言两语(Z)
车甲
“音乐家席勒”
有一位著名文艺工作者于今年春节期间病逝。说其“著名”,毫无争议。但对其从事的工作或曰职业的定位,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说法。有的媒体称其为“著名文学家、词作家、剧作家”(《光明日报》2016年2月16日),这是不错的。但还有一些媒体(我看到三家《晚报》)却称其为“作曲家”“音乐家”“著名音乐大师”等等,说明搞报道的记者完全不了解他们所宣传之人,完全不了解音乐家和文学家的区别。这些媒体甚至说这位著名文学家“创作了《江姐》《党的女儿》《长征颂》《红旗颂》《我爱祖国的蓝天》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深受大众喜爱”(《北京晚报》2016年1月8日),给人的感觉是这一位文学家“独自创作了”这些作品,完全不提“创作了”这“一大批”作品的主要作者还应该是一些杰出的作曲家,因为从文艺作品分类和人民群众熟悉的方面讲,这些作品通常都属于歌剧或者歌曲(也含有文学成分),它们能够“脍炙人口”的原因首先(当然不是唯一)是它们的旋律优美动听,音乐家的作用和贡献功不可没。现在不说都要把音乐家的名字排列在最前面,至少你在提到有关作品的时候也要表示一下“这位著名文学家和作曲家一起创作了《江姐》……”云云吧?
说到这里估计有人要抬杠,“难道这些歌词不优秀,难道歌词不重要吗”?在音乐作品中,文字当然重要,我也从未对人讲过这些歌词不优秀。但我们遵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讲究凡事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吗?在音乐作品中,这个“主要方面”无疑就是旋律。决定一首歌曲影响大小(即是否“脍炙人口”)的主要因素还是旋律,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解放军的军歌之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旋律居然是借用了“国军”军歌的旋律。而后者的旋律也非“原创”,而是借之袁世凯军队。“袁军”又借之“德皇威廉练兵曲”。歌词改来改去,面目全非,但旋律几乎不变,说明这个旋律受到了政治态度不同的各方欢迎,所以它才最具生命力(脍炙人口)(上海《联合时报》2009年8月25日)。
当然,这个问题与上述那些“误以为”文学家是“音乐家”的还是有所不同,那些记者完全漠视音乐家的作用。打个比方,席勒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诗人,他创作的诗歌《欢乐颂》非常“优秀”,但也是在被贝多芬谱上那雄壮美好的曲子以后,才迅速传播到了全世界。看到《欢乐颂》如此流行,估计有人就忍不住要称“伟大的音乐家席勒”了——那些记者就是犯了类似的错。
计划与经济
改革开放以前,号称的是“计划经济”,但平心而论,我们感受得太多的恰恰不是“计划”,而是领导人的“不计划”和随心所欲。的确,那时候从中央到地方都挂起了“计委”(计划委员会)的牌子,还有神圣的“五年计划”,可常常是有人辛辛苦苦编制的“计划”墨迹未干,领导人脑子一热,随便说几句,或是在文件上批几个字,所有一切“计划”就都不作数了。认真“计划”的人如果仅落个“白干一场”还算是幸运,可他们往往还要为此而“负责”。周恩来1956年坚持按“计划”发展而受批评而认错,党史上称为“反反冒进”,便是典型一例。1957年的钢产量是535万吨,1958年的“计划”本来是624.8万吨,增长17%,是考虑了煤炭、铁矿、运输、电力等等各方面条件“进行综合平衡之后提出来的”。结果有个领导一拍脑袋,质问为什么不能“翻一番”?于是马上就改成了1070万吨,不多不少刚刚为1957年的一倍,根本不考虑任何现实条件(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692页、700页)。其他如“十五年超过英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乃至“文革”把国民经济弄得接近“崩溃”,无一不是这种“随心所欲”的结果。
相反,看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虽然“计委”没有了,但我们感受得最多的恰恰正是“计划”。每一个企业的老总在拍板下达指令以前,都要小心万分地计划和计算,唯恐“赔本”。——当然,有些官员和国企老总还是喜欢“随心所欲”,那是因为他们正如彭德怀当年怒斥的李德,他们的瞎指挥是“崽卖爷田”,反正不心痛,赔了本叫人民买单。假如这些打水漂的巨款完全是领导辛辛苦苦挣来的私房钱,他们怎么舍得稀里糊涂地乱糟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