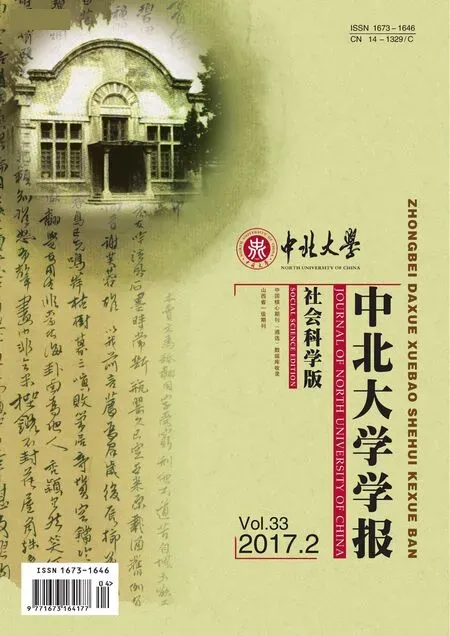贺凯文学史观再认识
——以《中国文学史纲要》为中心
苏 哲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贺凯文学史观再认识
——以《中国文学史纲要》为中心
苏 哲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贺凯所著《中国文学史纲要》统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以阶级论分析方法解读文学。 本文分别论述贺凯文学史观的形成及具体实践, 最后联系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史学理论, 反思唯物史观及阶级论在文学史著述中的缺憾。
贺凯; 《中国文学史纲要》; 文学史; 唯物史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受胡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论观念影响, 文学史著述更为关注文学新旧之演进。 20世纪20年代~30年代, 国内大量引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这种史学观念很快被文学史编著者吸收应用。 贺凯所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便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成果之一。 全书分为三编, 以《诗经》为源, 梳理至1930年左联文艺运动。 1953年, 周扬视察山西大学时, 在大会上公开赞扬了这一成果: “贺教授在30年代师大读书时, 写了一本《中国文学史纲要》, 这本书是我们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 具有划时代的价值。”[1]266当代学者黄霖具体分析道: “贺凯的这部《中国文学史纲要》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立场和唯物史观说明中国每个时代的社会形态, 阐发文学的发生和嬗变与社会发展过程的关系。”[2]21
本文立足于现当代文学史, 以此书第三编“帝国主义侵入后的文学转变”为重点, 论述贺凯唯物文学史观的形成与实践, 并联系布罗代尔“长时段”史学理论, 对唯物史观及阶级论进行反思。
1 贺凯唯物史观的形成
贺凯能较早地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 与他青年时代的经历密不可分。 贺凯生于1899年, 1922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 经高君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旋即担任师大党支部书记兼北京市工会秘书, 开展学生革命运动, 出版《政治生活》 《教育与革命》两个刊物, 并组织读书会, 团结当时北京南城一带的大中学生, 每周一次在北师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3]505参加革命运动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观点, 为贺凯形成明确而清晰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打下了基础。
1933年1月, 由新兴文学研究会出版, 斌兴印书局刊印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便是贺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阶级论分析方法在文学史编著上的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 新兴文学研究会正是当时北平左翼团体之一, 这个团体曾在1932年3月1 日参加过由北方左联发起的“成立鲁迅等被捕后援会”[4]1297。 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能由这个左翼团体出版, 即是对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著述文学史的认可和鼓励。
当时的时代大氛围也给贺凯营造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环境。 1924年5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大钊的《史学要论》, 此书被称为“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史学理论著作”[5]931。《史学要论》指出: “历史是亘过去, 现在, 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 换句话说, 历史是社会的变革。 再换句话说, 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 那些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 必欲称之为历史; 只能称为记述历史, 决不是那生活的历史。”[6]7-11接着他提出史学三要义, 总结起来就是: 第一, 史学要以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 人事为考察对象; 第二, 用历史事实证明、 论说社会、 人事发展的真相, 这是历史研究的特色; 第三, 将历史事实看作有机整体, 在其中寻求事物之间互为因果的普遍联系, 这是治史的目的。 在方法上, 《史学要论》强调治史要真, 要有理有据, 要将历史事实作为有机整体; 而治史的对象一定是变革中的社会。 真实的历史存在于不断变革的社会中, 认识到这一点才算是真正打开了探索历史的大门。
李大钊的这些治史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随之流产, 社会陷入迷乱, 急需新的理论思想作指导。 适时, 李大钊等一批革命先导所大力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注意, 并得到很多左翼知识分子的响应, 贺凯和他的文学史著述便是顺应了这一洪流。
如果说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更侧重史学观念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 得出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指导历史学研究发展的结论, 那么, 同样受到广泛关注的樊仲云的《唯物史观与文艺》则开宗明义地将唯物史观和文艺联系在了一起。
《唯物史观与文艺》是樊仲云于1930年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新兴文艺论》上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 樊仲云把艺术作品看作是艺术家对社会意识的表现, 所以在分析文艺作品、 现象时, 社会、 艺术家本人、 作品就成了三位一体互相联系的要素。 社会是艺术家赖以生存的环境, 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 这也是其表现的主体; 艺术家本人的风格气质则影响着表现社会的方式和结果; 作品就是承载这一切的最终成果。 社会生产力所形成的物质经济条件决定了作家心理、 作品思想等相关的精神条件, 即物质决定精神。
这篇文章所造成的影响, 许建平称:“仲云的《唯物史观与文艺》, 是本世纪国内发表的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文学艺术之关系的理论文章……该文提出的观点构成了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学研究模式的理论基础, 它不仅塑造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占有独特的至高无尚地位的社会学研究模式, 而且也造就了社会学研究模式的文学史著作。 其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无论在对一个时代文学现象的研究, 还是对具体作家、 作品的研究中, 所出现的时代背景、 作者生平、 作品分析的三段式分析方法。 二是重视作品的政治思想价值的评判, 而轻视艺术价值的分析。 三是将文学现象置于整个社会现象之中加以把握, 增强文学史研究的连贯性、 整体性和分析的透彻性。 文学的社会功能被突出了出来。”[7]93
以李大钊、 樊仲云所发表的这两份代表性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 结合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文艺社会学理论大量译介的背景,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进行的文学史编著实践, 可谓水到渠成之事。
2 贺凯对唯物史观的实践
在时代大趋势的召唤下, 贺凯进行了用唯物史观著述文学史的实践工作。 由《中国文学史纲要》出版时刊登的新书介绍可以反映出时人对此书的期待: “用社会学的眼光, 确定并说明每个时代的社会形态, 以及该时代所产生的作品和作者的社会背景, 然后再来估定这一作品的价值……似乎还没有看见……无疑地, 《中国文学史纲要》的编著者贺凯先生在这方面是开辟了坚实而光明的路径了。”[8]贺凯以《中国文学史纲要》向文坛展示了他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治文学史的实践努力。
此书《自序》中提出:“至于文学, 为社会基础最上层的建筑物, 是无可否认的。”[9]自序4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 而社会意识形态又被社会生产关系影响决定。 贺凯所阐明的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 由此, 他的这部文学史在编选作家作品时, 以“反映被剥削者痛苦生活”为基准; 分析作品时, “按作品中反映的阶级意识及社会背景, 分析它的存在价值与时代的关系”[9]自序4。 在绪论中, 贺凯进一步明确了唯物史观在文学史编著中的应用: “现在我们所要求的新时代底文学史, 是从社会进化的阶段中, 寻求文学的推演与转变, 由物质生活所反映的意识形态中, 而求出文学的产生与存在的价值。”[9]2
在贺凯看来, 新时代的文学史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 在明确社会进化本质的前提下, 对物质生产关系可能产生的意识形态范畴的文学进行考察, 探索出文学在不同时代环境中具体的历史意义, 这也是贺凯实践于《中国文学史纲要》的史学观和方法论。
以下笔者从此书的文学史分期以及贺凯对新文学领袖胡适、 陈独秀以及鲁迅的评判中探知一二。
2.1 《中国文学史纲要》分期
《中国文学史纲要》论史横贯古今, 单从大标题上就可看出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断代的痕迹: 本书第一编为绪论, 第二编题为“封建社会的文学演进”, 第三编题为“帝国主义侵入后的文学转变”。 贺凯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本书从《诗经》起到帝国主义侵入以前, 这一段落是自然的推演, 是适应封建生产关系的。 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 封建生产关系因受外来的力量, 根本动摇, 反映到意识上, 是向突然的转变, 这是本编时代的划分。”[9]自序3-4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下的“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变, 贺凯运用这种概念为文学史断代, 突出了社会变革在文学史编写中的分期导向作用。
细观对现代文学史开端的界定, 贺凯的尝试有别于以往文学史著作。 1922年, 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将“近五年的文学革命”(按原文, “近五年”自1916年起)作为宣告“古文学已死, 新的白话文学必将到来”的标志; 1929年, 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将戊戌政变、 辛亥革命作为新文学产生的背景, 而将《新青年》时期作为新文学发展的开端; 1930年, 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要》也认为是由《新青年》造势而形成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推倒了已是强弩之末的古文霸权。
从上述例证可以看出, 这些先于贺凯出版的文学史代表作, 都选择了《新青年》创刊, 胡适、 陈独秀的宣言这样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作为新旧文学转变的节点, 而贺凯却选择以“帝国主义侵入”作为中国新文学开启的标志。 因为在贺凯看来: “中国的文学, 是适应封建生产关系而产生的意识形态, 停留在半封建社会的中国, 直到前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封建农村的堡垒, 开始被资本帝国主义的商品所摧毁, 于是中国社会便向资本主义的路上进行, 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 因此反映到文学上也是一个大变化。”[9]3显然, 贺凯是把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下的中国文学作为新文学的开端, 他认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进程。
第三编“帝国主义侵入后的文学转变”的章节排列也完全按照引起社会经济基础或意识形态变化的历史事件而展开。 绪论里就明确指出: 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革命, 戊戌政变, 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 五卅惨案, 1927年的革命, “这都是中国社会基础剧变的表现, 而文学也因基础动摇而表现了错杂翻新的形态”[9]8。戊戌政变引发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抬头, 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鼓吹自由平等, 要求思想解放; 辛亥革命摧毁了封建王朝的统治; “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是对封建思想文化残余的彻底反抗, 如此的资产阶级文学革命, 产生了鸣人间疾苦的血泪文学和个人主义伤感颓废文学的并驾齐驱之态; 五卅惨案和1927年北伐革命催生了被压迫阶级的呼喊反抗, 于是革命文学运动起航; 1928年世界新兴文学潮流汇入中国, 普罗文学运动在中国安营扎寨; 1930年上海“左联”的成立为集体的功利主义斗争文艺的发展提供了更大平台。
贺凯所叙述的新文学, 从甲午战争后新体诗人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 古岂能拘牵”写到1930年上海“左联”的成立, 虽然时间跨度大, 但历史主线明确, 选择的时间节点都被认为是动摇了当时社会经济基础, 改变了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继而影响了社会意识形态的节点。 这样的文学史分期处理, 是唯物史观与文艺高度结合的实践。
2.2 对新文学领袖的评判
除了文学史分期的与众不同外, 贺凯对于胡适、 陈独秀这两位新文学革命倡导者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的评述, 竟是贬多于褒。
在第二章“五四运动与文学革命”的第一节中贺凯专门论述了胡适和陈独秀这两人。 在其说明性标题中, 胡适与陈独秀被冠以“新兴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名号。 由此, 他们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用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平等、 科学民主思想来为资产阶级代言罢了。 在这样的定性下, 看重无产阶级、 拥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贺凯, 对此二人自然不会有积极的评述。 贺凯认为他们没有认清形势, 不懂得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威胁, 资本主义无论在政治、 经济、 文化哪方面都救不了中国, 自由平等、 互助友爱这类资产阶级思想更是空谈。
胡适更是被贺凯称作“老胡”而“左右不顺眼”: 胡适作为“五四”时代领导群众的革命者, 居然只有“尝试”的态度, 这本身就是“缩头缩脑没勇气的表现”; 而后又“钻在烂字纸堆里‘咬文嚼字’的整理国故”, 果然“尝试成功自古无”[9]285-291。
关于鲁迅, 贺凯承认他是“‘五四’以来创作界的权威”, 但更开宗明义地指出, 彼时的鲁迅和“五四”时期的鲁迅不可同日而语: 鲁迅没有发现彼时新兴资产阶级的观念体系已经动摇, 时代潮流已经发生转变, 而他没有跟上时代前进的方向, 所以“无论怎样的‘呐喊’”, 结果只能是无奈的“彷徨”而已。 当然, “五四”时期的鲁迅, 是抨击封建恶势力的能手, 但到了《呐喊》时期, 则在“回忆”里感到寂寞而哀伤, 终究生出了“人道主义的怜悯与同情”, 并以此作为其作品的出发点, 而这正是小资产阶级的论调, 是早已成为过去的“五四”余风, 不值一提。 鲁迅的《彷徨》更是因为没有看到中国革命已走向工农阶级为革命主导的趋势, 依旧徘徊在“青年旧梦”里而彷徨。 《野草》是呐喊彷徨后仍觉现实阴森黑暗而生出的悲观意念。 《朝花夕拾》就是对现实的诅咒, 对过去的缅怀而已。
纵观贺凯对鲁迅创作各阶段的评价, 仿佛值得一提的只有《狂人日记》 《阿Q正传》 《孔乙己》这类明确批判、 抨击封建势力的作品。 《呐喊》和《彷徨》都是鲁迅没有认清形势的自怨自艾, 没有揭露社会黑暗面的气势, 更没有为现实革命摇旗呐喊的自觉, 所以失去了贺史正面评价的资格。 1928年, 鲁迅对革命文学所作的批判, 也被看作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点”的“尖酸刻薄”的嘲骂, 所以“不必赘述”[9]303。
鲁迅的“消极落后”, 贺凯不愿多评, 倒是对1930年鲁迅组织促成“左联”成立而大加赞赏, 说他终于赶上了时代的脚步, 正将继续以反封建的精神来反抗布尔乔亚, 日后更期待鲁迅成为“新时代文艺的战士”。
胡适、 陈独秀以及鲁迅, 在贺凯所著文学史中都有不同以往的形象, 评判标准就是其是否紧跟时代变化趋势, 是否反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贺凯用唯物史观的评判标准重新定义了新文学的领袖们, 在现在看来, 结论不免有失公允, 但却证明了贺凯以唯物史观治史的努力。
贺凯在《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努力践行唯物史观, 立足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 用社会阶级划分的原理推进了文学史的叙述, 从文学史分期、 代表作家作品评点上都可见一斑。 这是他顺应时代潮流、 向左翼文化靠拢的积极实践, 保留了当时左翼文化思潮下左翼知识分子的史学视角。 既然是左翼文学的单一视角, 势必有偏颇疏漏之处。 然而单纯指出问题所在, 有事后诸葛亮之嫌。 所以, 反思唯物史观在当时的滥觞, 对现今治文学史提出有益的启示才是本文最终的归宿。
3 反思唯物史观及阶级论
贺凯用唯物史观和阶级论的分析方法对文学进行了历史梳理, 得出的结论在现在看来实在有失偏颇, 但是以唯物史观阶级论分析的角度来说又是有理可依的。 所以, 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唯物史观阶级论存在的问题。 下面笔者将联系布罗代尔的历史“长时段”理论进行论述。
“长时段”一词, 在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发表的一篇题为《历史与社会科学: 长时段》的文章中被明确提出。 “长时段”实际是针对“短时段”和“中时段”而言的。 历史时间中, 短促又易发生变化的“事件”所占用的时间就是“短时段”, 比如以重大事件为中心进行的历史研究, 都是“短时段”历史研究; “中时段”的历史跨度较长, 在此跨度中形成了一定的态势、 周期和间周期, 这种时段被看作是“事件”发生、 发展的基础, 以“中时段”为跨度进行历史研究的有经济史、 社会史等。 相对于“短时段”和“中时段”, 布罗代尔认为, 只有“长时段”历史才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规律及根本原因。
布罗代尔为我们把握“长时段”概念提供了两把“钥匙”, 其一是由“中时段”演化出的“百年趋势”, 其二就是“结构”, 这是一把更加有用的钥匙。 对此布罗代尔解释道: “该词(指结构)在长时段问题中居首位。 ‘结构’是指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 严密的和相当稳定的关系。 对我们历史学家来说, 结构无疑是建筑和构架, 但更是十分耐久的实在。 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 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它们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 另有一些结构较快地分化瓦解。 但所有的结构全都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10]94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在总结继承前辈历史学家经验、 吸收相关社会科学成果的基础上, 对于现代的历史认识论是一个飞跃, 充分地提醒我们不要只注意细枝末节的表层现象(这正是传统史学的软助, 也是传统史学面临诸多社会科学的责难而难以辩护的地方)。 ‘长时段’理论还告诉我们历史研究重视的是深层的东西。”[11]缓慢的、 几乎静止的地理时间, 是布罗代尔把握的根本, 社会时间是历史波动的趋势面貌, 个人时间则是丰富历史的微观日常。 历史研究需要重视的是深层次的东西, 不能只注意表面的细枝末节, 因此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把握和解释一切历史现象, 只有借助于长时段历史观, 才能够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人类生活的全貌。
与“长时段”理论相对照, 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就是在“中时段”与“短时段”下观察历史的结果。 贺凯应用唯物史观, 以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关系结构了文学史, 在具体表述中, 又是以戊戌政变、 辛亥革命等事件作为文学史转向的关键, 以阶级划分评价作家作品。 唯物史观也好, 阶级分析方法也罢, 这些统摄全书的历史观念本来就是左翼文化潮流下的产物, 是一时兴起, 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转而一瞬, 是“短时段”中“事件”的代表, 是治史应该谨慎择取的部分。
贺凯以唯物史观及阶级论的分析方法为无产阶级文学著史, 以此意图解释历史, 就会强调经济因素对历史的影响甚至是决定作用。 然而, 构成文学史的还有人、 地理、 社会风俗、 文化等多方面因素, 它们在文学著述中即使不是显性的, 也是不能够被忽略的。 否则, 浮于表面而又单一的历史视角, 注定造成不全面、 不深刻的历史著述。 同时, 文学史不一定是线性的连贯, 用一种史学观念解读文学的发展, 用史学观念的逻辑推演代替历史真实的演进, 这是用逻辑代替历史, 是观念的历史, 遮蔽了历史的真实。
贺凯应用唯物史观和阶级论的分析方法著史, 适应了20世纪20年代~30年代除旧布新的社会变革。 然而, 历史长河里的每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就是不可比拟、 不可超越的。 经过历史的淘洗沉淀, 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事件, 在历史的无限演进中, 都会褪去当时治史留下的溢美或谪贬, 而变得越来越中性, 这是历史的宿命, 从某种角度上说, 这也是历史无法弥补的缺憾。 因此, 站在科学角度上, 中性化的史学是必要的, 即使是文学史, 在兼顾文学现象丰富多变、 偶然掺杂必然等特性的同时, 还是要落实在历史叙述的科学严谨上。
曾经再波涛汹涌的变故, 于现在、 未来都不过是点缀历史叙述的事件或故事。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于文学史也许太过生硬, 毕竟文学是人参与创造的, 不是地理、 经济基础这样简单的划归。 “长时段”理论之于文学史编写的意义在于, 拉开历史的距离去审视历史, 找出历史中与文学恒常的联系, 以平静客观的眼光去理解过去、 发现历史, 避免让文学的热闹遮蔽了背后的深意。 热闹是一时的, 历史留下的是洗净铅华后的真实, 即使脱离时代背景也同样具有普遍意义的真实。
文学史观在不断地发展, 文学史的著述也不是恒定不变的。 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记录了左翼风潮下文学史的叙述, 这是文学史的一笔财富。 文学史的编写, 体现了文学史观的革新, 这之间距离的把握值得每一个治文学史的人深思。
[1]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山西通志: 第39卷·社会科学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2]黄霖.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总论卷[M]. 北京: 中国出版集团, 2006.
[3]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山西通志: 第48卷·人物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4]韩泰伦. 目击天安门[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5]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6]李大钊. 史学要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7]许建平. 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文精粹: 文学史方法论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8]欧阳成. 新书介绍[J]. 出版消息, 1933(15): 26-28.
[9]贺凯. 中国新文学史纲要[M]. 北平: 新兴文学研究会, 1933.
[10][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资本主义论丛[M]. 顾良, 张慧君,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11]王伟. 布罗代尔史学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2.
The Rethinking of He Kai’s Viewpoints of Literature History——TakeOutlineofthe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as the Center
SU Zhe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He Kai’sOutlineofthe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 based on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terprets literature with the Theory of Clas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of He Kai’s historical viewpoints of literature and their specific practices. This paper finally rethinks the dis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Theory of Clas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writings in combination with Braudel’s historical theory of “Long Time”.
He Kai;outlineofthe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 literature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673-1646(2017)02-0097-05
2016-10-23
苏 哲(1991-), 女, 硕士生, 从事专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9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7.0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