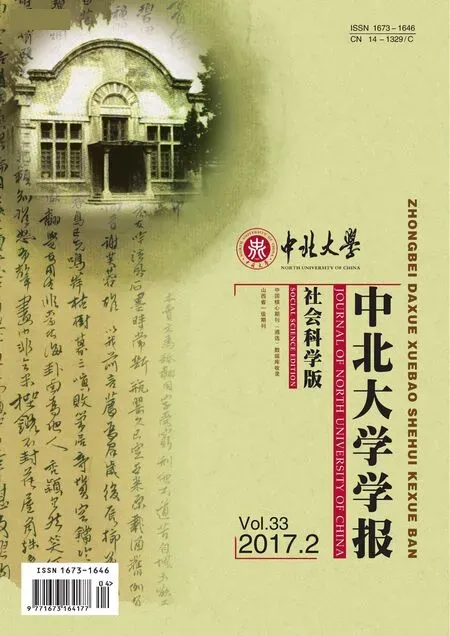冯唐《飞鸟集》译本召回事件的伦理探讨
郝俊杰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应用外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0)
冯唐《飞鸟集》译本召回事件的伦理探讨
郝俊杰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应用外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0)
冯唐《飞鸟集》译本召回事件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整体翻译观上的认知误区和价值偏差。 从翻译伦理角度出发, 围绕“冯唐能不能这样译”探讨翻译伦理对译者自由的约束, 围绕“译本能不能这样出”探讨传播伦理对文学功用的规定, 围绕“译本能不能这样评”探讨批评伦理背后折射出的社会翻译观念, 发现当下针对冯唐《飞鸟集》译文的批评意见反映出社会整体翻译观的滞后。 翻译研究者有责任和义务向社会各界普及翻译界普遍认可的对文学翻译的认识和理解。
《飞鸟集》; 冯唐; 翻译伦理
0 引 言
翻译界的争论, 大多是“茶杯里的风暴”, 社会关注度不高。 如冯唐《飞鸟集》译本召回这样高调进入公众文化视野的翻译事件, 可算是“风暴”溢出了“茶杯”。 2015年12月28日, 浙江文艺出版社宣布, 在全国范围内的书店及网店将冯唐《飞鸟集》译本暂时下架, 待有关专家审定之后再做处理。 消息一出, 文化翻译界与读者大众哗然, 原本就存在的讨论更为热烈, 褒贬不一的各种意见激烈交锋。 有评论称, 冯唐翻译《飞鸟集》不啻是对翻译界的一次“恐怖袭击”。 还有评论称, 冯唐译本“乃不知有信, 无论达雅”。 赞誉之辞如社科院的李银河所说, 冯唐的《飞鸟集》翻出了诗意, 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 冯唐本人则回应:“历史和文学史会对此做一个判断。 时间说话, 作品说话。” 总之, 一个译本演变成了文化事件, 并从中折射出社会各界对翻译的普遍认识, 其中反映出的相关翻译伦理问题, 值得引起翻译界深思。 结合各种评论, 我们不妨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对此次事件作如下的伦理探讨: ①冯唐能不能这样译, 即翻译的伦理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约束译者的自由? ②译本能不能这样出, 即传播的伦理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规定文学的功用? ③译本能不能这样评, 即批评的伦理在何种程度上受制于社会整体的文学翻译观?回答这三个问题, 不仅是对此次召回事件的思考, 也有助于我们认清翻译伦理与译者选择、 传播机制、 出版机制以及社会翻译观之间的关系, 拓展翻译伦理学的研究范畴。 再进一步讲, 它也有助于对文学翻译本质的探寻, 对社会广泛流传的一些不乏谬误但影响广泛的翻译观念起到纠偏去蔽之效。
1 翻译的伦理与译者的自由
翻译伦理即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应遵守的规范或法则。 翻译伦理在几千年的翻译历史中逐渐形成, 它在某种程度上划定了译者翻译行为的疆界。 辩证地来看, 翻译伦理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 事实上在不同历史时期、 不同翻译情景、 不同翻译客体下, 它的要求可能是有所不同的。 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就不会以简单划一的标准, 如“忠实”“达意”“信达雅”等来要求译者。
泰戈尔的《飞鸟集》是诗歌, 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学形式, 对它的翻译也无疑是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的本质何在?这个问题不只是中国译界几千年来苦苦探寻的话题, 也是西方译界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对象。 “求信” “神似” “化境”这些翻译标准就是对文学翻译本质探寻过程中的副产品,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就因其洗练精辟而长期被文学翻译工作者奉为圭臬。 随着翻译研究的进步, 我们对文学翻译本质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由从对翻译产品的标准要求过渡到对翻译过程的客观描述。 如“翻译是艺术与科学的统一”, 文学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创造性叛逆”[1]59。 这种过程导向的理论视角让我们认识到文学翻译事实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创造过程, 翻译家的翻译也是一种创造行为, 而绝不仅仅是两种语言间的信息传递与形式转换。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认为, 理解行为是一种读者视域与作者视域的融合, 固定意义上的作者本意是不存在的, 理解是一个动态的、 主体的、 流动不居的过程。 理解不可能脱离阐释者的主体身份和主体意识。 谢天振教授认为, 尽管完全遵照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将导致不可译论, 但它有关理解的历史性的观点对翻译不无启发。 翻译作为一种典型的阐释行为, 同样不能说可以完全地、 原原本本地复制作者及原文的全部意旨, 它一定是译者理解与原作意义的融合, 是一种历史的相遇。[1]188简言之, 当我们阅读翻译作品时, 看到的不仅是作者, 同时也有译者。 正如读傅雷译的巴尔扎克的作品,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巴尔扎克, 也有傅雷。 同理, 读冯唐译的泰戈尔的作品, 你看到的也不只是泰戈尔, 也有冯唐。
明确了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后, 我们就不能以简单的语言形式对等的忠实观来要求文学译者。 语言形式的对等是双语字典就能完成的工作, 如果我们以此标准要求并评判文学翻译, 那文学翻译也就不复有存在的价值。 况且将忠实作为译者在面对原文及作者层面上的第一原则, 问题就随之而来, 何谓忠实?不同译者心目中的忠实概念可能大相径庭, 有人认为要忠实于原文的字、 词、 句式, 有人则认为要忠实于原文的精神内涵, 因此也就衍生了直译和意译两派贯穿历史的纷争。 动态对等理论则提出忠实的对象是所谓读者反应, 但正如有论者提出的, 国别不同, 文化相异, 时代变迁, 读者反应焉可等量齐观?由此可见, 完全以忠实来要求文学翻译, 存在许多疑问。 文学翻译当然有它的评判标准, 因为我们读到不同的译文, 会有明显的高下优劣之分, 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标准观在发挥作用。 但与文学翻译的策略取向一样, 评判的标准也是主客观的统一, 是自在与自为的融合。 社会整体的文学翻译观,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它对文学翻译的期待, 反映了它的集体心理与集体审美观。 简言之, 社会的普遍观点认为, 翻译是创造还是复制, 会影响它对文学翻译作品的价值判断。
如果我们承认翻译是一项创造的艺术, 并以此为出发点来揣度译者心理, 那么, 对于译者某些看似异乎寻常的翻译选择, 或许我们就会多一份同情之理解。 创造必然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叛逆, 而文学的创造, 是译者艺术心理与才情的再现, 源出于译者的整体识见和价值立场, 而倘若我们要求文学翻译中规中矩、 亦步亦趋, 那么极大的可能是译者在前怕狼后怕虎的重重顾虑之下才情全失。 因此, 反观翻译伦理对译者自由的限制, 翻译伦理要求译者以认真严肃之态度对待翻译, 以创造之心态再现心目中的原作艺术。 这并不意味着译者不能有自身的判断和选择。 没有思想的独立与自由, 创造又如何可能?没有主体的统一与完整, 谈何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因此, 翻译伦理更多是一种整体上对译者的期待和要求, 但它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指导与约束译者翻译过程的微观选择。 因此, 我们不能因为冯唐把“mask”翻译成“裤裆”, 把“hospitable”翻译成“骚”, 就由此判定冯唐挑战与违背了基本的翻译伦理。 “同一原著的不同译品之所以千姿百态, 必然是因为译家在翻译过程之中, 对翻译的本质, 有一种先验的理念, 因而形成一种主导的思想。”[2]7要理解冯唐的选择, 我们需要宏观的分析视野, 需要对冯唐的创作理念、 翻译思想、 价值取向有所了解, 需要对冯唐心目中的泰戈尔有所了解。
我们无意评判冯唐译作的优劣, 而只是探讨他是否具有翻译选择的自由。 从翻译研究对文学翻译本质及译者主体性的基本共识出发, 我们对第一个问题“冯唐能不能这样译”得出的结论与当下流行的“批冯论”恰好相反, 即作为文学翻译工作者, 冯唐有权这么译, 而且他的这种权利应该得到尊重。 套用伏尔泰的名言, 我或许不同意冯唐翻译的每一句话, 但我誓死捍卫他这样翻译的权利。 以上辩护还远不足以对抗现实世界对冯唐译本的口诛笔伐。 冯唐之遭遇, 除了其翻译的“乃不知有信, 无论达雅”, 还在于他对性禁忌的突破违反了中国社会一些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传播规则。
2 传播的伦理与文学的功用
冯唐《飞鸟集》译本2015年7月出版, 至2015年12月28日下架, 流传不过五个月, 在图书出版领域也属罕见。 事出有因, 按照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的说法, 冯唐的译本在语言的雅俗上是存在争议的。 “虽然《飞鸟集》不是青少年作品, 但毕竟有青少年在读泰戈尔的诗, 我国图书市场目前还没有分级阅读制度, 难免会对青少年产生误读和误导。” 根据郑重先生的描述, 提出意见的主要是一些青少年阅读推广机构和公众读者。 其实这压力不仅来自青少年阅读推广机构和热心读者, 也来自诸多的网络评论和媒体报道。 众口烁金, 积毁销骨, 社会舆论的压力和保护青少年心理的正义号召迫使浙江文艺出版社做出了一个“政治正确”的召回决定。
然而, 所谓的召回是难以真正实现的。 译本一经出版, 便已成事实。 在读者手中流传, 在媒体上热议, 如何召回?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召回”之举, 更多是一种妥协的姿态, 尤其是要避免“对青少年产生误读和误导”。 其实, 这个理由不能成立, 这要从文学的功用谈起。 文学的功用是中西方讨论了几千年的话题。 在中国, 就有“诗言志” “文以载道” “我手写我口” “文学救国论” “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等说法; 在西方, 从柏拉图提出的“快感”功能到亚里士多德的“教育” “净化”功能, 从马克思的审美社会意识形态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取向, 至少可以看出, 文学的功用是多层次、 多方面的, 它包含了审美、 价值、 伦理等多种功能。 熏陶青少年心理、 规范青少年行为只是文学伦理功能的一个方面, 而不能成为一种标准来要求所有文学作品。 将对青少年心理与行为的引导功能加诸于一本非青少年文学的翻译文学作品之上, 是不应该也不合理的。 文学作品除了要发挥伦理规范的引导作用, 也需要深刻反映社会生活、 描绘现实、 反映人性、 体现艺术创造性、 体现丰富的审美层次。 而且从历史上看, 也只有那些具有极大创造性和丰富审美层次的文学作品才能长久流传。 如果以不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为由将《飞鸟集》下架, 以此标准推论, 在我国没有阅读分级制度的前提下, 还有多少书能自外于事?四大名著中, 除了看似老少咸宜的《西游记》之外, 《红楼梦》涉及风月, 《水浒传》暴力泛滥, 《三国演义》则充斥着诡诈之术。 中学生必学文学常识中的“三言二拍”, 情色凶杀的描写俯拾皆是, 作为中学教科书选文来源的《聊斋志异》, 蒲松龄笔下的男女之事则更如家常便饭。 汉语古典作品如是, 现代作品也不例外。 茅盾文学奖作品、 中学生推荐书目中的《白鹿原》, 性描写的尺度远超《飞鸟集》译本。 诺贝尔奖得主莫言仅《丰乳肥臀》一个书名就让人不敢直视。 贾平凹、 王小波、 张贤亮这些当代文坛响当当的名字, 其作品的尺度哪个不能将《飞鸟集》译本远抛身后?因此, 为青少年带来精神误导, 其实只是个说辞, 构不成说得过去的理由。
为什么尺度更大的许多作品安然无事, 而偏偏冯唐的《飞鸟集》译本要下架呢?并非是因为书中“弥漫的荷尔蒙”, 根本原因在于《飞鸟集》是翻译。 因为公众对翻译作品的期待, 不同于对原创作品的期待。 很明显, 冯唐的翻译, 触动了一部分人的神经, 挑战了他们对于泰戈尔及其诗作的固有理解, 让其倍感难堪、 亵渎、 以致愤怒。 冯唐心中的泰戈尔不是他们想要的泰戈尔, 因此诟骂纷至, 其目的就是要修补其心目中“诗哲”之形象。 冯唐作为一个欺世盗名的登徒子, 必欲逐之而后快。 全书中引起争议、 可称“低俗”的主要就是以下几句, 不妨一观: 第3页“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 第13页“心呐/听吧/这世界和你做爱的细碎声响”; 第70页“无止地/狂喜地/射出那么多花朵/这力量的源头到底在哪儿呢?”; 第90页“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 第119页“白日将尽/夜晚呢喃/‘我是死啊, /我是你妈, /我会给你新生哒’”; 第236页“烟对天吹牛逼/灰对地吹牛逼/他们是火的兄弟”[3]。 熟悉冯唐的人都能看出, 这几页诗行, 只可算是冯唐为译作打上的个人标签。 因为以其文字功底, 将这几句话改成四平八稳的诗句轻而易举, 但他没有这么做, 可见这几句引起争议的诗行是他刻意为之。 谈及雅俗问题, 冯唐回应:“雅俗, 只是一个词汇而已。 一部翻译作品是否存在译者的烙印, 这是读者自己的体悟, 我不可能按照别人的要求做, 我认为我翻译的风格, 就是我理解的泰戈尔的风格。”
那么针对第二个问题, 即译本能不能这样出, 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回答, 即译者按照自己心目中能够呈现的最好方式将译本贡献出来, 获得了出版机构的认可, 通过了相关机构的审查, 那么这样的译本就是合法的, 它有权按照译者希望的方式存在于世。 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召回之举, 实无必要。 此番的轩然大波, 并非全是冯唐之罪, 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了社会价值观与翻译观的滞后与偏狭。 这种滞后与偏狭, 则衍生出诸多似是而非、 有着相当反驳空间的批评声音。
3 批评的伦理与反驳的空间
学界对冯唐《飞鸟集》译本的批评声音是多重的。 其中公众较多接触到、 影响较大的基本来自网络批评者与报刊媒体所采访的文学译家。 如有人从语言角度批评:“冯唐译本的一部分诗里, 包含原诗中不存在的下半身语言、 押韵和突兀的网络语言。” “文学翻译就应该用标准的汉语和文学语言。”有人从韵律角度批评: “冯唐的押韵, 翻出来是个二人转。”有人从译者主体性角度批评: “冯译并不尊重原文, 重点是要表现自己, 其实是让读者看到冯唐而不是看到泰戈尔。”有人从文学创作论的角度出发, 认为“再创作的权力是作者独有的”, 而译者不能“随心所欲”, “冯唐的这些内容, 是自己的创作, 应该叫‘冯唐诗选’, 不应该盗用泰戈尔的名字”。 以上批评意见大致归纳如下: ①冯唐在语言使用方面不加检点, 使用了下半身语言与网络语言; ②冯唐在翻译中融入了自己的创作, 打上了个人的烙印, 有欺世盗名之嫌。
关于第一点, 即翻译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 这个问题相当复杂。 “标准的汉语和文学语言”其实是一种理想的存在。 一般认为, 现代汉语书面语系统有三个主要来源, 一是口头语, 二是文言文, 三是翻译文体。[4]67-68所谓“标准”的汉语, 只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 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演变的系统, 方言、 俗语、 网络用语等都可能脱离其边缘地位, 进入标准汉语的语言库。 汉语的丰富与弹性, 也是在吸收各类语言、 表达各类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 因此不能简单认定, 凡不登大雅之堂之词句必不能用于文学翻译。 事实上, 据现代汉语形成的历史可知, 翻译中的文字创新和文体实验是现代汉语的一个重要源头。 许多我们熟知的日常词汇, 正是在翻译这个语言实验场中诞生的。 如前文所析, 冯唐译本中的语言, 是一种刻意为之的结果, 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字张力与语体张力的实验。 这种实验总是存在为人诟病的风险, 不说冯唐的语言实验成功与否, 至少是勇气可嘉。 作为译家楷模的傅雷, 就曾指出成型的书面语缺乏活力和文艺价值, 而语言中最鲜活的部分, 恰是俚俗口语。[5]40再者, 翻译使用什么语言也取决于译者对原作的理解, 倘若译者通过阅读、 体悟、 查证, 认定原作就是俚语村言, 难道翻译中也要使用“标准的汉语和文学语言”吗?因此, 恰当的做法是不要对翻译语言过多限制, 随需取之即可。 冯唐带给人们的, 是语言、 词汇、 语体、 文体的创新与心理的冲击, 而从某种意义来讲, 这也是翻译的一个功能所在。
关于第二点, 即译者有没有“再创作”的权利, 这是个已有定论的问题, 如今广为接受的文学翻译本质观就将文学翻译认定为一种“创造性叛逆”。 正如傅雷所说, 一件艺术作品, 如果翻译时不能还它一件艺术作品, 就不要去译。[5]14因为艺术是创造的结果, 所以译者不仅要有“再创作”的权利, 而且必须有“再创作”的心态和能力。 或许, 我们应该回到谢天振教授提出的那个国人习焉不察却偏又争议不断的命题, 即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或者广义上国别文学的一部分。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翻译文学的创造性。 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 也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 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取得了它的相对独立的艺术价值”[1]121。 冯唐《飞鸟集》译本既是泰戈尔的, 也是冯唐的, 因为它融入了冯唐的创造。 译者的“再创作”冲动也是复译的最大动力。 冯译之前, 《飞鸟集》在中国已经有几十个译本, 如果我们要看的是泰戈尔, 那么之前的选择已经够多了。 其实每个译本呈现的泰戈尔都各自不同, 或者说每个译本都是译者眼中的泰戈尔。 冯唐的《飞鸟集》有着明显的个人印记, 这是理所当然之事。 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黄友义就此事发表意见:“我觉得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 要允许译者推陈出新, 有他自己的特色。 从这个角度看, 我认为, 冯唐用一些大家不熟悉的, 过去没用过的这种表达方式, 是可以理解的。”[6]
综合以上两点, 我们还可以归纳出一种以偏概全的批评心态。 翻译又称“不完美的艺术”, 也即翻译中出现与原文的偏差是一种必然现象。 从几万乃至几十万字的翻译中寻找几处失范之处, 这样的事不只专业批评家, 就连普通读者都不难做到。 但仅凭个别失范现象便从整体上对翻译定性, 对译者是不公的。 目前对冯唐的一些批评意见, 往往是执其一点, 或从个别字句的翻译入手便判定译文的整体格调, 或从个别诗句的处理便判定冯唐的押韵是“二人转”式的。 这些批评无疑都不具有整体意义上的翻译批评价值, 因为这种随意而为的零碎意见表达, 有悖于翻译批评追求的客观性与公正性。[7]
冯唐《飞鸟集》译本下架事件, 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公众对翻译认识上的心理误区和价值偏激。 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对翻译文学地位的认识误区。 对原作和原作者的膜拜, 导致公众认定译作一定要无限忠实于原作, 要做原作的“仆人”。 其实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司空见惯之事, 西方的文化界及阅读大众, 对于文学翻译中的这种叛逆, 相对我们来说有着更为宽容、 正面、 积极的心态。 如英国的菲茨杰拉德, 出于对柔巴依这种波斯诗歌的兴趣, 以极其自由的方式译出了一批英国式柔巴依并编纂成集。 尽管诗集出版之初备受冷落, 但受到慧眼识珠的英国诗人好评后, 销量大增, 甚至成为拍卖场上的珍本, 而这本诗集本身也成为英国诗歌中的精品。[8]202-203以翻译中国诗著称的庞德, 依靠其“不忠”的英译, 却开了英美意象诗派的先河。[9]莫言的御用翻译葛浩文, 就坦言翻译中的创作是译者的任务之一, “其‘创作’的例证在其译著中俯拾皆是”[10]。 葛浩文对于莫言的获奖可谓居功至伟, 也鲜有听到西方文化界及读者公众指责其对莫言原文的不忠。 国人对于葛浩文翻译莫言作品中的创造津津乐道, 引为佳话; 而对于冯唐翻译泰戈尔作品中的创造, 则苛责备至。 两相比较, 引人叹惋, 难道真的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回到引言中的第三个问题, 即译本能不能这样评?答案是: 译本既出, 任人评说, 但最好评得有理、 有据、 有建设意义。 并不是说冯唐《飞鸟集》译本完全就没有问题, 也不是说不能批评冯唐, 批评只要讲得有道理, 有什么不可以?但倘若从根本上不认同翻译文学的价值, 看不到译者的用心, 只管祭起“原文至上”的大旗, 抓住几句不合意之处便口诛笔伐, 也难说有什么建设意义。
4 结 语
综上所述, 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就冯唐《飞鸟集》译本的翻译理念和翻译方法而言, 显露出一种与传统文学翻译理念和方法不同的特征, 这集中体现在冯唐从作家身份转换至译者身份时, 呈现出与传统意义上译者的不同。 但这种不同, 尚不足以构成对翻译伦理的颠覆。 尽管它足以引发我们反思翻译伦理的疆界在哪里, 翻译与创作的界限又在哪里, 而回答这些问题,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文学翻译的本质。 其次, 冯唐《飞鸟集》译本接受过程中的褒贬不一, 也体现出时代审美理念、 价值取向、 阅读趣味的变迁。 冯唐《飞鸟集》译本得以顺利出版、 部分读者公众对它的认可, 也说明经历了后现代主义及解构思想洗礼的社会文化界, 在审美理念与阅读趣味上趋于后现代化, 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 无论从社会伦理、 文学伦理还是翻译伦理来看, 如今的争端各方, 孰是孰非, 都难以一言道尽。 正如黄友义所言:“我觉得冯唐作为一位作家, 愿意从事翻译, 是值得肯定的, 他做了一件勇敢的事情, 至于译文好不好, 那也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从学术上可以讨论的事情。”[6]最后, 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看, 时代发展到今天, 翻译对社会的重要意义和巨大贡献早已是人所共知, 我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加深, 但这些最新的认识大多还停留在翻译圈内。 冯唐《飞鸟集》译本事件折射出的社会流行的翻译观便是明证。 翻译界, 尤其是翻译研究界有责任也有义务向社会各界普及翻译领域内的一些重要共识, 例如应该如何看待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家, 以加深我们的监管方、 出版方、 读者方对翻译的认识和理解, 从而促进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
[1]谢天振. 翻译研究新视野[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
[2]金圣华. 桥畔译谈新编[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
[3][印度]泰戈尔. 飞鸟集[M]. 冯唐, 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
[4]何九盈. 汉语三论[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7.
[5]傅雷. 翻译似临画[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
[6]黄友义. 2016-03-10[--]. http: ∥www.catl.org.cn/2016-03/10/content_37990456.htm.
[7]蓝红军. 翻译批评的现状、 问题与发展[J]. 中国翻译, 2012(4): 15.
[8]黄杲炘. 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 英语诗汉译研究[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9]吕敏宏. 英美意象派诗歌的中国情结-从庞德诗歌看英美意象派的创作原则[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2): 52-56.
[10]孟祥春. 葛浩文论译者-基于葛浩文讲座与访谈的批评性阐释[J]. 中国翻译, 2014(3): 72-77.
Ethical Discussion on the Recalling of Feng Tang’s Translation ofStrayBirds
HAO Junjie
(School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Teachers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Guangzhou 510640, China)
The recalling of Feng Tang’s translation of Tagore’s Stray Birds is a reflection of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value deviation of the society’s conception of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ethic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ree questions. The first question is “if Feng Tang has the right to translate in this way”, relating to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nslation ethics and translators’ choices; the second question is “if a translation can be published in this way”, relating to the impositions of communication ethics onto literary functions; the third question is “if a literary translation can be commented in the current way”, relating to current criticism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conception of translation. The criticism toward Stray Birds shows that China is lagging behind in terms of social conception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cholars have the obligation to show the world how we should view literary translation.
StrayBirds; Feng Tang; translation ethics
1673-1646(2017)02-0068-05
2016-12-2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当代荷兰文论家米克·巴尔文化分析思想研究(13YJA752021);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应用翻译研究科研团队项目(粤外艺职院科〔2015〕301号,2015KYTD01)
郝俊杰(1982-), 男, 副教授, 从事专业: 翻译学。
H315.9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7.0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