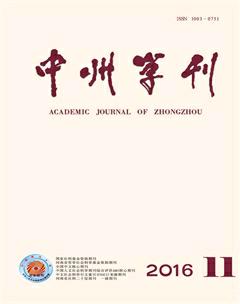汉武帝元光中河决滑县辨析
杜冠章
摘要:汉武帝元光年间“河决瓠子”是黄河史上的著名事件,但《史记》和《汉书》的有关记述都没有说明“瓠子”的具体位置。河南省滑县古有瓠子堤,濮阳县古有瓠子河,从文献资料和地理形势上分析,决口处应当在滑县瓠子堤。关于“瓠子”的位置之所以会出现“滑县说”和“濮阳说”两种,一是因为后人对《汉书》文字的误读和《水经注》记载的不准确,另外也因为滑县曾属于濮阳国,故在记事时出现以大地名代替小地名的情况,造成后世的误读。
关键词:元光;瓠子堤;滑县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1-0119-05
汉武帝元光年间“河决瓠子”,是黄河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史记·河渠书》曰:“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于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窴决河。”“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①《汉书·沟洫志》也有文字相同的记载②,但《史记》和《汉书》都没有具体说明“瓠子”在什么地方。河南省滑县古有瓠子堤,濮阳县古有瓠子河,遂使后世关于“瓠子河决”地望问题出现“滑县说”与“濮阳说”两种,而“濮阳说”是主流。《辞海》③《辞源》④都认为“河决瓠子”的具体地点是濮阳瓠子河。但笔者认为“瓠子河决”当在滑县,本文欲就此问题提出辨疑,以就正于方家。
一、“瓠子河决”在滑县
1.瓠子堤在东郡白马县
地处豫北的滑县,旧治滑台城(今滑县城关镇),秦于此置白马县,隋置滑州,古黄河即从滑台城下流过。滑台城与北岸大伾山下的黎阳古城(今浚县东)隔河相望,形成历史上有名的白马津。滑县瓠子堤,即古黄河南岸大堤,属古大金堤的一段,故又称“瓠子金堤”,至今仍有故迹可寻,素称“滑州土脉疏,岸善溃,毎岁河决南岸,害民田。”⑤
虽然《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没有具体说明瓠子所在,但在《汉书·武帝纪》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注曰:“服虔曰:‘瓠子,堤名也,在东郡白马。苏林曰:‘在鄄城以南,濮阳以北。”⑥“东郡白马”就是汉东郡白马县。苏林所说的“濮阳”,有“鄄城以南”作参照,是指汉濮阳县无疑。濮阳县亦为东郡属县,且为东郡治所所在地。服虔和苏林分别是东汉末年和三国曹魏时期人,他们的解释应是关于这一问题最早的解释,也是“滑县说”和“濮阳说”最早的源头。从二人生活年代来说,服虔早于苏林,且服虔家居黄河岸边的荥阳东北,离瓠子堤所在的“东郡白马”较近,对黄河的这段历史掌故应该更为熟悉。虽然我们尚不能据此肯定二人的说法孰对孰错,但至少可以说,“滑县说”比“濮阳说”出现得更早,其可信度或许更大一些。
所谓“禹河旧迹”,亦即上古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在《尚书·禹贡》中有记载:“导河积石”“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⑦《汉书·沟洫志》也有更明确的记载:“道河自积石”“及盟津、洛内,至于大伾。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酾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洚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迎河,入于渤海。”⑧“洛汭(一作内)”为洛水入河处,“大伾”即与滑县瓠子堤隔河对峙的大伾山,在滑县旧治西北。据此可知,古黄河东过洛汭后,自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东北流,经滑县白马津,至今浚县大伾山下。大禹治水时,为减缓河流坡度以减杀水势,由大伾山下向北开挖两条引渠,引黄河沿着太行山东麓北行,在今河北曲周县南,接纳自西而来的漳水(“降水”即漳水),然后向北流过大陆泽(“大陆”即大陆泽),在冀中平原漫流形成多股河道,由于河口潮水倒灌顶托,成逆流之势流入渤海。清人胡渭的《禹贡锥指》则比较清晰地指出了“禹河旧迹”所经:“河自濬县(今浚县)西南折而北,历内黄、汤阴、安阳、临漳、魏县、成安、肥乡、曲周、平乡、广宗,至巨鹿县,大陆泽在焉。此即禹河‘北过洚水至于大陆之故道也。”⑨这条“禹河旧迹”直到宋代还在,《宋史·河渠志》载:“惟禹故渎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间。”⑩“禹河旧迹”远在濮阳县西方百里之遥,由于西高东低的地势要产生相当的落差,如果河决瓠子发生在濮阳县,要从那里“道(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是由低处导向高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滑县瓠子堤对岸即是大伾,正是禹河旧迹所经。如果瓠子河决发生在滑县,堵塞后要“复禹旧迹”,的确是简便易行之策。由此可知,瓠子河决的位置只能是滑县老城即滑台城附近的瓠子堤,而不可能是下游百里之外的濮阳瓠子河。
3.“滑县说”的其他文献证据
河决瓠子“滑县说”,除了上述史料之外,很多文献也有记载。
《后汉书·王景传》载:“浚仪令乐俊复上言:‘昔元光之间,人庶炽盛,缘堤垦殖,而瓠子河决,尚二十余年不即拥塞。”唐李贤注:“瓠子堤在今滑州白马县,武帝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李贤明确指出“瓠子河决”的地点是“滑州白马县”的“瓠子堤”。
《晋书·地理志》:“濮阳国,故属东郡,晋初分东郡置。统县四:濮阳、廪丘、白马、鄄城。”并在每个县下注明其境内的著名古迹。其中白马县下的注文是:“有瓠子堤。”《晋书》把瓠子堤列为白马县而非濮阳县的著名古迹,无疑是因为瓠子河决的著名事件是发生在白马县而非濮阳县的缘故。
《宋史·河渠志》综述古代治河史曰:“(河水)自滑台、大伾,尝两经汛溢复禹迹矣。”以笔者的孤陋寡闻,所见由滑台、大伾导河“复禹旧迹”的史料仅有汉元光年间和唐宪宗元和八年两次。《新唐书·薛平传》:“始,河溢瓠子,东泛滑,距城才二里所。平(薛平)按求故道出黎阳西南。因命其佐裴弘泰往请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正许之。”“疏道二十里,以酾水悍”,“自是滑人无患”。古黎阳城就在大伾山脚下,这里所言“出黎阳西南”的“故道”,即所谓“禹河旧迹”。而《宋史》所言黄河“自滑台、大伾尝两经汛溢复禹迹”,除了元和八年的一次,就只能是汉武“瓠子河决”那一次了。《宋史·河渠志》的作者是认同“河决瓠子”的地点在滑台瓠子堤的。
清《开州志》“宣房宫”条载:“在州西南”。“《史记河渠书》:‘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汉书作宣防(防与房古字通)。旧志:‘在州西十七里瓠子堤上。”又载:“宣房宫,在滑县北苖固堤上,汉武帝塞瓠子堤,筑宫。”
此外,尚有历代诗文的记载。如北宋刘跂《宣防宫赋》云:“余以事抵白马,客道汉瓠子事。”“元封天子,既乾封,临决河,沈璧及马,慷慨悲歌。河塞,筑宣防之宫。”元末明初人刘三吾《白云茅屋赋》云:“大名滑邑”“西南三里即瓠子堤,宣房宫在焉,北去大伾半舍余。”说明宣房宫元末明初尚存,其位置就在“北去大伾半舍余”,即大伾山南约十五里的地方(古时三十里为一舍)。
二、“濮阳说”成因辨析
1.“濮阳说”源自对《汉书·武帝纪》相关文字的误读
“濮阳说”之所以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对《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文字的错误解读。这段文字是这样说的:“(元光)三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渤海。夏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后为列侯。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发卒十万救决河。起龙渊宫。”这次的“河水决濮阳”规模甚大,与河决瓠子那一次相仿佛,而且据后世的记载,濮阳的确曾经有过一座“龙渊宫”,于是,《汉书·武帝纪》中的这一记载就被认为是河决瓠子“濮阳说”的重要依据。
但是,把这次的“河水决濮阳”认同于“河决于瓠子”,只是一种推断而已。这里有四个疑点:第一,这次的“河水决濮阳”时间是在元光三年五月,而《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记述河决瓠子的年份只说是“元光之中”和“元光中”,并没有确指是“元光”哪一年。而年号“元光”共有六个年份,元光三年的“河水决濮阳”并不能肯定与“元光中河决于瓠子”是同一事件。第二,退一步说,即使“河决于瓠子”与“河水决濮阳”同在元光三年,仍然不能肯定就是同一事件,因为黄河一年两决甚至数决的记载很多。仅在元光三年这条记载中就有春天的顿丘和夏天的濮阳两次决口。第三,“河决于瓠子”后筑的是“宣房宫”,而在《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的文字中却没有关于“宣房宫”的记载,只有“起龙渊宫”的记载(而这点属于后人的错误解读,详说见后)。如果“河水决濮阳”与“河决于瓠子”是同一次决口,不大可能同时筑起两座宫殿。如果真是同时筑起了两座宫殿,《史记》岂能只记其一?第四,如果“宣房宫”与“龙渊宫”是一宫两名,那么“宣房宫”已由汉武帝亲自命名,(汉武帝《瓠子歌》中有“宣房塞兮万福来”之句),这座对皇帝有纪功意义的“神圣”建筑岂可随便更名?因为有此四疑,所以不能据此认为“河决于瓠子”是在濮阳。
其实,濮阳的“龙渊宫”,很可能只是由于后人错误解读《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的文字而附会生造的产物。这段文字原本是记述了发生于元光三年的四件事,即河水徙顿丘东南、封高祖功臣后、河水决濮阳、起龙渊宫。《汉书》记事文字简要,往往如此。因此,不能理解为“龙渊宫”是因救河决而起。服虔注“龙渊宫”曰:“宫在长安西,作铜飞龙,故以冠名也。”北宋史学家刘攽更特别强调指出:“予谓救决河、起龙渊宫各自一事,非因河决且起宫也。”根据《史记·河渠书》的记载,元光年间河决瓠子之后,“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显见那次堵塞并未成功。建宫只会在堵塞成功之后,决不会建在决口发生之年。因此根本不可能在元光三年就于决口处建造这座“龙渊宫”。因此,濮阳“龙渊宫”应是误读的结果,是郦道元误将“龙渊宫”替代了“宣房宫”,即“武帝起宫于决河之傍,龙渊之侧,故曰龙渊宫也。”
2.《水经注》中的两处错误记载是“濮阳说”的重要来源
虽然郦道元的《水经注》价值很高,但是由于当时的局限,其记述并非都来自作者的亲身考察,难免有不准确、甚至以讹传讹之处。现就这两处文字一一加以分析:
其一,《水经注·河水》在“(河水)又东北过濮阳县北,瓠子河出焉”之后,注曰:“河南有龙渊宫。武帝元光中,河决濮阳,泛郡十六,发卒十万人塞决河,起龙渊宫。盖武帝起宫于决河之傍,龙渊之侧,故曰龙渊宫也。”“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堤宣房堰。粤在汉世,河决金堤,涿郡王尊自徐州刺史迁东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决坏。尊躬率民吏,投沈白马祈水神河伯,亲执圭璧,请身填堤。庐居其上,民吏皆走,尊立不动,而水波齐足而止,公私壮其勇节。”这段注文前面的话基本上是照抄《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的文字,本文前面已就这段文字做过分析,此处不再赘述。这里需要提出的另一个疑点是:郦道元既已认定“河决濮阳”就是“河决瓠子”,那么为何只记濮阳县有座“龙渊宫”,却没说还有座“宣房宫”呢?宣房宫在《史记·河渠书》中已有记载,名称也见于武帝自作的《瓠子歌》,如果濮阳真有座宣房宫,哪怕仅仅只有它的遗址在,郦道元也不会不写到它,而仅仅写到有个“宣房堰”。显然,这里本没有宣房宫。郦道元正是蹈袭了前人误解《汉书》文句的错误,认为堵塞瓠子后建有龙渊宫,故有此记载。
郦氏这段注文的错误还不止于此,接下来更是将汉代黄河又一次在白马县瓠子堤出险的事件,直接移置于濮阳。这一事件见于《汉书·王尊传》,原文是:“天子复以尊为徐州刺史,迁东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恐水大决为害。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马,祀水神河伯。尊亲执圭璧,使巫策祝,请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庐居堤上。吏民数千万人争叩头救止尊,尊终不肯去。及水盛堤坏,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动。而水波稍却回还。吏民嘉壮尊之勇节,白马三老朱英等奏其状。下有司考,皆如言。”这次事件发生于西汉成帝时,地点就在白马县的“瓠子金堤”,《汉书》记载替王尊请功的是“白马三老朱英等”,如果此事是发生在同属东郡的濮阳县,“白马三老”岂能越职言事?
《汉书·王尊传》的这段文字,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滑县在汉代确有一段黄河大堤名唤“瓠子堤”或曰“瓠子金堤”,它是黄河金堤的一段。二是郦道元把发生在滑县的“泛浸瓠子金堤”错安在濮阳瓠子河,不能不让人作这样的判断:他把元光中“河决瓠子”发生地放在濮阳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原因是他只知有濮阳的“瓠子河”,不知有白马县的“瓠子堤”,故而一见“瓠子”即认为是濮阳。三是王尊在河水“泛浸瓠子金堤”的紧急关头,“投沉白马”“亲执圭璧”祭祀水神河伯,显然是把白马县的“瓠子金堤”认作元光中“河决瓠子”的故地,于是有意效法当年汉武帝在瓠子“沉白马玉璧”祭祀河伯的故事。
其二,《水经注·瓠子河》在“瓠子河出东郡濮阳县北河”之后,注曰:“县北十里即瓠河口也。”“汉武帝元光三年,河水南泆,漂害民居。元封二年,上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于是上自万里沙还,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令群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于是卒塞瓠子口,筑宫于其上,名曰宣房宫。故亦谓瓠子堰为宣房堰,而水亦以瓠子受名焉。”“河水旧东决,径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相土又都之。故《春秋传》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卫成公自楚丘迁此。”本来这段注文前半段是照抄《史记·河渠书》的(《汉书·沟洫志》文字亦同),只是把“卒塞瓠子”改为“卒塞瓠子口”。“口”字一字之加,说明郦道元是有用意的,是为把“河决于瓠子”地点坐实为“瓠子河”。因为他在注文中两次说到濮阳城北有“瓠河口”,把“卒塞瓠子”改为“卒塞瓠子口”,自然就会让人认为堵塞的是濮阳县北的“瓠河口”了。接下来再看这段注文:“于是卒塞瓠子口,筑宫于其上,名曰宣房宫,故亦谓瓠子堰为宣房堰,而水亦以瓠子受名焉。”郦道元在这里才提到“宣房宫”,不过只是在抄录《史记》《汉书》的原文而已,并非自己见闻的记录。如果这次堵塞的,的确是濮阳瓠子河的河口,瓠子河又的确是那次决口后冲出来的一条河道,那么这条从元光三年到元封二年流淌了二十三年的河流便是一条没有名字的河流,或者有名字也不叫瓠子河,直到它被堵塞后,河道废弃了,这才“水亦以瓠子受名焉”,才被叫作了“瓠子河”,这合乎逻辑吗?那么“瓠子”之名又从何而来的呢?是先有“瓠子河”还是先有“瓠子堰”呢?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再看这段注文的后半段,郦道元又把“帝丘”与“商丘”混为一谈,再次犯了移花接木的毛病,说濮阳“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左传》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阏伯的封地为“商”,墓冢被称为“商丘”。而这些都被郦道元错误地移到了濮阳。对此,历代学者多已指出其错误,如杨守敬等所著的《水经注疏》中说:“颛顼、昆吾居帝丘在卫,阏伯、相土居商丘在宋,渺不相涉。”“以颛顼、昆吾与阏伯、相土所居为一地”是“舛误殊甚”。
通过对《水经注》两段注文的分析,可证明其所记是错误的。但由于《水经注》影响较大,故后世河决瓠子“濮阳说”流布甚广,“滑县说”竟为所掩。
三“滑县说”与“濮阳说”混淆原因辨析
对于“滑县说”与“濮阳说”这两个说法,笔者试图从源头上寻找其交集点,发现这个交集点是存在的,那就是:“濮阳”是大地名,“白马”是小地名,《汉书·武帝纪》所言汉元光三年“河水决濮阳”,是就大地名言之。汉代白马县属东郡,东郡治所在濮阳。晋初,分东郡置濮阳国,白马又为濮阳国属县。人们习惯言首府以概辖境,这也是史书记事之常例。白马作为东郡和濮阳国属县,当然可以“濮阳”代替。从这一点说,《汉书·武帝纪》把发生于东郡白马县的“河决于瓠子”记载为“河水决濮阳”是完全符合惯例的。史书中这种例子甚多,如汲黯的故里本在古白马县(今滑县留固镇尖冢村,“尖”即“汲黯”之合音,其墓尚存),而《史记》和《汉书》本传皆言:汲黯,“濮阳人也。”又,《汉书·翟方进传附翟义传》记东郡太守翟义起兵讨王莽兵败被杀后,王莽收其部众之尸筑为“武军”(武军即收敌尸封土而成的高垒,古代战胜者用以震慑敌军、炫耀武功):“聚之通路之旁,濮阳、无盐、圉、槐里、盩厔,凡五所。”其中濮阳的具体地点是东郡白马县境,即今滑县万古镇妹村,俗称“翟义台”。
如果这样的理解不错的话,《汉书·武帝纪》所言元光三年“河水决濮阳”与《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所言“河决于瓠子”就是一回事,其具体地点是“濮阳”辖内的白马县瓠子堤,而并非濮阳县的瓠子河。至于濮阳县的瓠子河,则完全有可能是黄河决口后所冲出的一条河道,其名就叫瓠子河,但是那和《史记》《汉书》所言“河决瓠子”无关;至于“龙渊宫”,那不过是因为后人对《汉书·武帝纪》文字的错误解读而生造的附会之作,真正的龙渊宫是在西汉都城长安之西的。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1409—1413、1409页。②⑧班固:《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9—1684、1675页。③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辞海》说:“瓠子河,古水名。自今河南濮阳南分黄河水东出,经山东鄄城、郓城南,折北经梁山西、阳谷东南,至阿城镇折东北经茌平南,东注济水。西汉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决入瓠子河,东南由巨野泽通于淮、泗,梁、楚一带连岁被灾。至元封二年(前109年)始发卒数万人筑塞;武帝自临,作《瓠子之歌》二首。工成,建宣房宫于堰上。”④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辞源》说:“瓠子,地名。在河南濮阳县南,亦称瓠子口。汉武帝元光三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漂害民居。元封二年,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帝自万里沙还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令群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并作《瓠子歌》。功成,于其上筑宫,名宣房宫,亦称瓠子堰。”⑤脱脱:《宋史》卷九十一,《河渠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2206、2256页。⑥班固:《汉书》卷六,中华书局,1962年,第193页。⑦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783页。⑨转引自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790页。⑩脱脱:《宋史》卷九十二,《河渠志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2285页。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六,中华书局,1965年,第2464—2465页。房玄龄等:《晋书》卷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419页。《新唐书》卷一百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4145页。唐沈亚之《魏滑分河录》亦载其事:“元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河南瓠子堤溢,将及城”“滑凿河北黎阳西南,役卒万人,间流二十里,复会于河。”见《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七。濮阳县地方史志办公室校注:光绪《开州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3页。河南省滑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重修滑县志》(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1、264、266页。班固:《汉书》卷六,中华书局,1962年,第163页。光绪《开州志》记载:“龙渊宫,在州(按即今濮阳)西南。”“《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起龙渊宫。”“旧志:‘在州南别驾里。”濮阳县地方史志办公室校注:光绪《开州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3页。顾廷龙著:《顾廷龙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83页。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卷五,中华书局,2007年,第140—141页。班固:《汉书》卷七十六,中华书局,1962年,第3236—3238页。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卷二十四,中华书局,2007年,第572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九年传,中华书局,1981年,第964页。郦道元著,杨守敬,熊会贞纂疏:《水经注疏》卷二十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031页。班固:《汉书》卷八十四,中华书局,1962年,第3439页。
责任编辑:王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