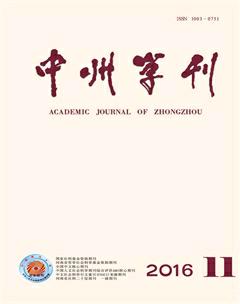老子的以屈求伸之身道及其体现
摘要:一种“彻底经验主义”的中国文化精神决定了老子的道与其说是一种思知的“有无之辨”的道,不如说是一种身体的“屈伸之间”的道,它使自身最终通向的并非是西方式的去伪存真的真理形上学,而是中国式的以屈求伸的生命辩证法。这种生命辩证法,不仅以一种“显微无间”的方式使诸如弓箭意象、水的意象、龙的意象以及势的意象这些中国文化中的“典型意象”成为可能;也以一种“体用一源”的方式,使以屈求伸的精神贯彻在从武术、军事、政治到文学艺术等中国古代的实践领域之中,从而以其身、道的完全合一使中国文化彻底实现了从原始的神秘主义向“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这一神的祛魅化的思想转型。
关键词:老子的身;以屈求伸;道的祛魅化;中国文化的典型意象;中国古代的实践精神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1-0097-10
一、老子的身与身的以屈求伸
1.“祛身”还是“尊身”?
老子被尊崇为道家的鼻祖和开山。但是,但凡涉及何为老子道家的道的问题,却以其“玄之又玄”而始终给人以雾里看花之感。然而,实际上,“大道坦坦,去身不远”。对于古人来说,一如“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的中国“下学而上达”的逻辑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愈是玄远之物则愈和我们自身的亲己之切的身有关。于是,为了为老子的道觅求真正的答案,一种之于老子“身道”的研究就势所难免。而事实上人们却看到,后者正是古往今来的老子解读者的一大理论盲点。
应该承认,身在老子研究者视野中的消失是事出有因而情有可原的。因为不正是老子为我们写下了“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①这样的“身体原罪说”的名言吗?不正是老子以其对人痴迷于“五色”“五音”“五味”“畋猎”“难得之货”的讨伐而揭中国“禁欲论”思想的首篇吗?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王弼的“唯理是从”“崇本息末”的不无形上的老子注解,也才有了宋明学人“释老并称”这一将《老子》极度唯心主义的妖魔化。但是,所有将老子祛身化的解读者与此同时都忘记了,正是老子,不仅提出了“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②这一生命究极的大诘问,而且还宣称“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③,“修之以身,其德乃真”④,以对“以身观身”⑤的自身之身而非“以我观身”的对象之身的肯定,把“贵身”“尊身”这一议题率先提到了中国哲学的议事日程,并为我们开出了后来庄子对人类“以身为殉”的异化现象批判的先声之鸣。
2.身体的以屈求伸
一旦把老子学说定位为一种“贵身”“尊身”的哲学,那么接下的问题就应转向对老子身的概念的讨论。《释名》谓:“身,伸也。”在这里,身伸同音又同义地被理解为身体的伸展。这种解读以其取象于身的“功能性”而与中国式的“即用显体”这一词义解释的原理相契合,并且也与西方之于身的“实质
同理,与《释名》的解读一致,在老子那里,身同样被理解为伸展之身。然而,比《释名》的解读更深入的是,中国“相关性”的元逻辑决定了老子不是就“伸”自身来谈伸,而是如“屈者,所以求申也”所云,在伸展与屈就之间来谈伸,故身被理解为“以屈求伸”之身。这样,正如你唯有收回自己的手臂才能使自己的手臂得以伸出那样,作为身体行动的“伸”不是来自外力的作用,而是体现在身体自身“伸展自如”之中、身体自身屈伸之间的张力和效力之中,并由此使吾身固有、非由外烁和生而不测的“生命力”“生命能”得以产生和成为真正的可能。这种“生命力”“生命能”也即古人所谓的“神”,所以才有了古人的“身”“伸”“神”三者同谓而异名,也才有了老子“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⑥这一对神的彻底祛魅化之论。
人们看到,在老子的学说里,这种身体的以屈求伸不仅体现在身体行为的屈伸之间,而且还有所引申,触类旁通地体现在一切身体行为的两极之间。如,翕张之间,老子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⑦;强弱之间,老子称“将欲弱之,必固强之”⑧;兴废之间,老子称“将欲废之,必固兴之”⑨;取予之间,老子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⑩。再如,进退之间,老子称“进道若退”;盈虚之间,老子称“大盈若冲”;明昧之间,老子称“明道若昧”;动静之间,老子称“静为躁君”;刚柔之间,老子称“柔弱胜刚强”;勇怯之间,老子称“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祸福之间,老子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除此之外,这种发端于以屈求伸的相反相成的思想,不仅“近取诸身”地体现在我们自身所从事的各种行为之间,而且还以一种中国式的“物即事也”的方式,“远取诸物”地推广延及到世界的万物之间。由此就有了老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之说的推出,并使自己当之无愧地成为后来庄子的思烁千古的“齐物论”这一中国式相对论思想的理论开山。
因此,虽同为人类文明的发轫期,当几乎与此同时期的希腊哲学家从思维出发,在其“真”与“伪”的非此即彼的知识之理上愈骛愈远之际,老子却反其道而行之,从身体出发,在“伸”与“屈”的亦此亦彼之中为我们发现了生命之道的归趣,以至于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老子的道,与其说是思辨性的“有无之辨”的道,不如说是一种行为性的“屈伸之间”的道。这不仅以“伸者阳而屈者阴”而使中国古老而神秘的“阴阳”的原型大白于世,而且以“以身体之”的彻底经验主义的方式使原儒不落两边、无过无不及的“从容中道”思想得以破译,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有别于西方真理之形而上学的中国生命辩证法的真正确定。
3.老子生命辩证法及其实质
第一,非我。正是基于这种生命辩证法,才使老子在人类自我空前膨胀之际极大地高扬了“他者”的反馈、参照的意义。所以,老子不谈我之“为主”而谈我之“为客”,不尚人之“自我”而尚天之“自然”,不主一马当先而主“万物并作”,从中不仅使老子以“企者不立,跨者不行”为喻,提出了“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这一“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的人生至极之理,还以“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的推出,标志着“有容乃大”这一人类伟大的宽容精神业已被中国古人视若神谕。
第二,消极。正是基于这种生命辩证法,才使老子在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时代独具慧眼地揭示了“物极必反”的规律。老子发现,正如“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那样,盛极而衰是万物发展的必然宿命。由是才使他提出了“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这些深旨宏论。出于对此的自觉,老子谆谆告诫我们,为了让生命真正做到“周行而不殆”,我们必须从穷奢极欲、急功近利走向持满戒盈、功遂身退。或换言之,从无所不用其极走向“莫知其极”。唯其如此,才能使我们在张弛有度、盈中有亏之中通向“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的万物之奥,并深契“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第三,回归。正是基于这种生命辩证法,才使老子在一个以“唯进步主义”为取的社会,却“吾以观复”地以复古为归。一方面,对社会文明的二律背反的深谙,使老子提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他比任何人都更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在文明之路疾奔中所带来的累累伤痕;另一方面,对疾进的人类文明的痛定思痛,又使老子得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的结论。这样,一种“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且“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的建立就成为老子的政治纲领。这一切,与其说是使老子成为中国“反文明”的乌托邦的思想先驱,不如说是在当时疾进的人类文明犹如强弩之末之际,老子为我们首揭出“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这一极其深刻的历史命题,并把“以退为进”的生命辩证法推而广之地落实到人类社会生活领域,为后来汉初的“我无为而民自化”的“黄老之治”埋下了深深的历史伏笔。
第四,不争。正是基于这种生命辩证法,才使老子面对势不可挡的弱肉强食的历史趋势,高高树起了“不争之德”的思想旗帜。老子的时代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业已打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滚滚而来的财富,而老子看到的却是“金玉满堂”的王侯一个个命不保夕的危机,看到的是“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这一人生真趣。也正是基于此,才使老子从人人趋之若鹜的之于物欲的“争”转向个个避之犹恐不及的“不争”,并对“不争之德”致以崇高礼敬。他写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尚贤,使民不争”,“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读到这些在《道德经》中几乎俯拾皆是的关于不争的讴歌,你才能理解老子何以提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以其对战争的极力声讨使自己成为中国古代反战主义的最早先导,并借以让高标尊王抑霸的儒家将自己引为同道。
第五,崇婴。正是基于这种生命辩证法,才使老子在人们之于人情练达的一片鼓吹声中发出了对人性天真的、由衷的赞美。于是,在老子笔下,不是精于世故的老者而是稚气未脱的婴儿成为“至德”的象征:“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讲,不仅由于婴儿以其混沌未开而代表了生命之德的原始状态,还由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婴儿以其极其“骨弱筋柔”而在生命的屈伸之间留下了巨大而无限的空白。这一切为我们指向了万生之滥觞的老子的“天下谿”,并从中使老子得出“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这一命题。如果说,在老子那里,这种向婴儿的复归打下了鲜明的道家印记的话,那么,在老子之后,这种向婴儿的复归则由于孟子之于“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李贽、罗近溪之于“童心说”的大力提撕,而超越了儒道派别对立,一跃成为中国古代名副其实的“常德不离”的普遍的道德真理。
第六,守雌。正是基于这种生命辩证法,才使老子在天下无不以“称雄”自炫的世纪却对甘拜下风的“守雌”极尽膜拜顶礼。老子承认,相对于刚强的雄性而言,“柔弱”是雌性自己的名称,是雌性所发出的无奈的呻吟。但是,人和草木的生命的实际情况却是“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脆弱,其死也枯槁”;水以其“无有入无间”“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一切表明,“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已成为天道的必然体现。随之而来的是对“雄尊雌卑”这一难以撼动的位序的根本扭转和革命性的改变。故针对天下的“英雄崇拜”,老子宣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谷”,“天门开阖,能为雌乎”,“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这些论述里不仅出现了以牝胜牡这一“攻守之易势”,而且由于把雌而非雄与“天下谷”“天门”“天下根”联系在一起,从而标志着在父系话语愈演愈烈之际,一种母系话语至上的哲学在人类思想中的异军突起。
如果从上述非我、消极、回归、不争、崇婴、守雌这些特性出发,把老子的思想望文生义地仅仅理解为一种不思进取的东西,那么,显然是与老子的思想大异其趣的。实际上,老子告诉我们的是一种“只有……才……”的假言逻辑,这种逻辑决定了正如“退一步海阔天高”那样,作为进的张、本的退,其最终是以进为目的的。同理,如果从老子的“正言若反”出发,把老子的思想仅仅理解为正话反说的语言的辩证逻辑,那么与老子的思想依然是离题千里。实际上,老子在这里与其说为我们推出的是一种语言的辩证法,不如说是一种梅洛-庞蒂的“肉身化的辩证法”。这种“肉身化的辩证法”服务于身体现象学而非服务于语言修辞学。后者表述的是语言的“正言”如何偷换为“反言”,而前者则表述的是生命行为的内隐的“潜能”如何转化为外显的“在场”。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就是“回到自身就是走出自身”,“因为我的身体能拒绝世界进入,所以我的身体也能使我向世界开放”,“主动性=被动性”。这些极高睿智的表述,恰恰可看作是对中国古老的身体的以屈求伸思想的现代反响和弘扬。
因此,身体的以屈求伸原则不啻是一把开启老子的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的锁匙。它以一种回到生命运动自身的方式,不仅让种种视老子为消极的、保守的、没落的老子之说者三缄其口,也使一切关于老子乃“帝王南面之术”和“阴谋”的发明家之论可以休矣。固然,老子在其著作中以帝王之师之姿大谈特谈统治权术,因此导致了司马迁“韩、老合说”在思想史上的推出。但深而究之,与其说老子更多讨论的是帝王的治术诀窍,不如说他以一种返本追源的方式,更多讨论的是但凡为人者都必须恪守的“修之以身,其德乃真”的修身之道。因此,较之儒家之“尚阳”,老子则以“尚阴”为人所称道。但细体其义,老子的“阴”,与其说是阴私诡秘的阴,不如说是负阴抱阳、阴阳相须的阴。其所通向的并非是作为“阴谋”的谋略之“术”,而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生命之道。职是之故,才使“儒道互补”从根本上成为真正的可能。而这种“儒道互补”并非仅仅是对儒家“阳盛阴衰”倾向的补充,而且是使中国文化重回充满活力的以屈求伸之身,正像归隐者陶渊明的诗“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我们感受到的除了一颗志在林泉的心之外,还有不甘于现实的勃勃生命的萌动、悸动。
二、以屈求伸与中国文化的种种典型意象
让我们先从老子的“执大象,天下往”这一名言谈起。何为老子的“大象”?成玄英在《道德经开题序决义疏》中说:“大象,犹大道之法象也。”那么,什么又是“大象之法象”呢?林希逸在《老子口义》中的注释无疑是一语中的的:“大象者,无象之象也。”这一解释不仅与老子“恍兮惚兮,其中有象”这一“道”的表述深深相契,也可以与梅洛-庞蒂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二者交织的“身”的定义互译。故进而可以推出的是,老子的“无象之象”的“大象”就是《易传》推出的因“言不尽意”,故“圣人立象以尽意”的“意象”。这里的“意象”的“意”,与其说是意识的“心意”的“意”,不如说是既为中国大易生命哲学又为梅洛-庞蒂所极其推崇的身体的“生意”(生命意向)的“意”。既然如前所述,以屈求伸被视为身体生命力、生命能的集中体现,那么,这也意味着,它实际上是与中国身体性文化的“典型意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并不是与西方意识性文化的罗蒂的“特许表象”有关。中国哲学之所以区别于西方哲学,恰恰在于其更多的是借助于有别于“特许表象”的“典型意象”使自身得以表现和阐述的。
我们不妨深入中国“象文化”里,看看与以屈求伸相关联的有哪些重要的典型意象。
1.“弓箭”的意象
老子谓“天之道,其犹张弓与”?在这里,老子将弓箭的所指提升到“天道”的高度,足见弓箭的意象在中国古人心目中地位之高,寓意之深。按照“易、老相通”论者的观点,既然老子的天道不外乎大易之道,那么,这种弓箭的顶礼亦成为《周易》学说中的应有之义。故在《周易》里,不仅有“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之说,有“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之论,还有“见豖负塗,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之辞,从中我们感受到了在古人心目中弓矢所特有的祛除妖魅的神奇。无独有偶的是,这一切恰与《周易》核心字的“吉”字的甲骨文取象于室内有矢这一字形暗通款曲。
除此之外,古代的“弓箭崇拜”还可见之于“羿射十日”这一古代神话的英雄叙事里以及中国古人对于“射礼”的备极顶礼里。《礼记》中“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子生,男子设弧于门”,讲述的是古人之于后裔之始其所事的是射礼;《淮南子·时则训》中“季冬之月,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射鱼,先荐寝庙”,《白虎通·田猎》中“王者祭宗庙,亲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也”,讲述的是古人之于祖先之终其所祭的是射礼;《国语·楚语》中“天子褅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其牛”,讲述的是古人无论祭天还是祭祖都始自射礼,都与射礼须臾不可离。这一切都说明了古人对射礼的膜拜之极,以至于“垂弧”(即“设弧”)一词已成为古人生日的代称;正如《诗经》中所说“发彼有的,以祈而爵”,能够成为神射手乃古人荣登爵位的必由之径;在古代社会最初的“大学”里,不是“诵经”而是“习射”被设为最重要的乃至唯一的必修课程。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弓箭崇拜”既明,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弓箭崇拜”如何成为可能?显然,一种中国式的“反身”而非“寻思”的哲学决定了问题的答案只能从我们自身的“身道”来探讨,而非来自对象“物理”的推理。也就是说,弓箭之为弓箭,恰恰是以身体的以屈求伸为其原型的:正如身体是以其屈求其伸那样,弓箭同样是以其弛求其张为特征的。所不同的只是,如果说前者屈伸之间的张力仅仅囿于身体的举手投足之间,那么,后者作为身体的延长却可以如《孙膑兵法·势备》中的“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使这种张力远远超越了我们自身的生理界限而得以极大地发扬。然而,即使二者力量如此难匹,实际上却难掩“弓道”与“身道”之间内在的一致。故而我们看到,也正是基于这一内在的一致,才使在中国古人那里,“身”字也即“躬”字,而“躬”字恰恰以其从“身”从“弓”,而将看似大相径庭的“弓道”与“身道”彻底归一。
2.“水”的意象
谈到中国文化中的“典型意象”,不能不涉及“大象无形”“无状之状”的水。在这方面,老子留下了关于“水”的千古绝唱。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于道”。在老子笔下,水成为“道”的别称:“江海之所以能为白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白谷王”,水被加上“王”的桂冕;“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水又被视为“强者”的象征。此外,有人统计,《老子》全书81章中,至少有17章与水的论述有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子之于水的情有独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水的讴歌在老子之后并没有音歇响绝,反而愈演愈烈。如《管子·水地》提出“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又如《淮南子·原道训》提出“水之为道也……万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在郭店楚简的《太一生水》篇中,又以其主张太一生成水又“藏于水”的观点,以及太一生水“成岁而止”的理论,以形上的意与形下的象高度统一的方式,标志着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意象”的水意象的最终奠定和成形。
这样,与之相应的是“水之崇拜”在中华大地的应运而生。在远古的陶器文明中,我们看到了陶器的盛水功能以及陶器上鱼的图形、水纹图形;在先民的神话传说中,我们看到了《史记·殷本纪》里所记载的契母简狄“浴水受孕”的水的创生论;在古人祭祀祖先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以大泽为祖地,乃至古汉语中有“祖泽”之称;在古代祭祀祈雨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古人视水为“万物弗得不生”的生命之本及对水的畏如天命、敬若神明;在《诗经》的爱情诗里,我们看到了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使男女邂逅相逢,从而才有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爱情千古之诵;在堪为中华文化“族徽”的“阴阳鱼”那里,我们看到了与其说是雌雄之间无入而不自得的“鱼水之欢”,不如说是由古代所推崇的水之生殖能力而形成的极富“大写意”的文化符号象征;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女人是水做的那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对柔弱的女性的歌颂,还在一个“水文化”业已走向式微的时代,把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水的推崇再次提到中国文化的议事日程。
中国文化之所以有水的崇拜,恰如中国文化之所以有身的崇拜。身有所谓“流体”之说,水的“流体”性质更是不言而喻的。身之性柔,水之性亦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水能圆能方,随器易形,因地制流,乃至其“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这样,身是以屈求伸的,水则是以亏求盈的。用老子的话说即“洼则盈”,用《太一生水》的话说即“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正如身在屈伸之间为其调动出了无限的潜能那样,水在亏与盈的落差之中使柔弱胜刚强成为可能。及其至也,其可以“激水漂石”,也可以“百川沸腾,山冢崒崩”。这一切表明,中国文化所崇拜的水既不是泰勒斯的还原论意义上的水,也不是中国五行说的系统论意义上的水,而实际上是生命辩证法意义上的水。无怪乎在《太一生水》的水的理论里,古人不仅强调水的“阴阳复相辅”的属性,还主张水是“四时之所生”“成岁而止”的,从而在看似无机物的水里赋予了极其鲜活的有机生命的特征。
3.“龙”的意象
尽管老子著作中并没有直接出现有关龙的意象,但是孔子“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这一对老子的极度赞赏,却在老子精神思想与龙的关系上为我们带来了无穷的联想,并使龙的意象依然不失为中华文化的典型意象,甚至更具代表性的典型意象。以至于可以说,如果说“弓箭意象”“水的意象”作为一种中华文化的典型意象在一些人心目中稍嫌牵强的话,那么,龙的意象则以其人所公认、万民顶礼而深孚众望。中华民族的远古图腾乃龙的图腾,而这种图腾者的后裔子孙被称为龙的传人。按神话传说,中华民族的祖先要么是人身龙首(如伏羲),要么是乘龙从天降至人间(如黄帝),要么是女“感神龙而生”(如炎帝),并且自秦汉始,沿此流风余韵,龙定型为帝王的化身,故有“真龙天子”之称。除此之外,以其“角似鹿,头似蛇,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龙集各种动物之大成,而成为鼎盛之极、无往不克的最高生命力的象征。缘乎此,才使作为“生经”的《易经》以“乾”为首卦,其又“时乘六龙”地取象于龙成为可能。缘乎此,才使中国文字以龙为生动之极的写照,从而就有了诸如生龙活虎、龙飞凤舞、龙腾虎跃、藏龙卧虎、龙凤呈祥、龙马精神等成语的诞生。
那么,到底什么是龙呢?虽然对此的答案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闻一多先生所给出的解读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他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龙图腾的原型是蛇图腾,蛇为龙的主体原型。尽管围绕这一观点依然有种种非议,但是它却有着坚定不移、难以驳斥的种种理据。如,在古汉语里,龙蛇连缀,由此就有了“龙蛇”这一合成之词,《论衡·龙虚》中“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即其一例。再如,在《易传》中,不仅同样有“龙蛇”一词,《系辞下》中还提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将“尺蠖”与“龙蛇”相提并论。按古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尺蠖”,乃“虫体细长,行动身体一屈一伸,如尺量物,故名”。这里所描述的正体现了作为“长虫”的蛇的形态和特征。
其实,在笔者看来,蛇为龙的主体原型的最主要也最根本的依据,恰恰在于蛇与以屈求伸的中华身道精神完全不谋而合。这一点可见之于《系辞下》“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的表述,也可见之于《说文》“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的解读,还可见之于《易经》乾卦关于龙如何与时消长地从“潜龙”到“飞龙”的爻辞。关于龙(蛇)这种身的以屈求伸,著名法国汉学家余莲对之的论述最为深刻、有力。他写道:“龙的身体蜷曲时,是它的力量最凝聚的时候;它身体蜷曲紧缩,为了前进得更快。龙的蜷曲意象因此代表一切的形状所蕴含的潜能,并且这潜能不断地变成现实。”他还接着谈到了观察高低起伏的山水地形中的“龙势”的风水师:“风水师在龙弯曲的身体内缩之处,观察出那是生命力最密集的地方”,其情况恰如一棵枝干曲尽极致的老松,它“蟠虬之势,欲附云汉”。在这里,作为龙的意象之解的点睛之笔,余莲的解读不仅可看作对长期隐秘的龙的生命密码的真正破译,同时也意味着将龙的精神与中国道的精神的内在联系第一次大白于世。
4.“势”的意象
《孙膑兵法·备势》宣称“羿作弓弩,以势象之”,《考工记·弓人》宣称“射远者用势”,《孙子兵法·势篇》宣称“势如彍弩”,它们都将弓箭与势联系在一起,表明和弓箭一样,势同样为中国文化中的典型意象。这一点与老子著作中“形生之,势成之”这一重势思想互为呼应、交相辉映。中国武术讲势,从而才有了《纪效新书·拳经捷要》中关于中国武术理论“势势相承,遇敌制胜,变化无穷,微妙莫测,窈焉冥焉,人不得而窥者,谓之神”这一论述。中国兵法亦讲势,由此才使《孙子兵法·势篇》中的兵法理论“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得以推出。中国政治讲势更是众所周知,从管子的“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势也”,到韩非子的“抱法处势”政治纲领,都使这一点表露无遗。无独有偶,这种尊势的思想同样也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里。在中国古代文论《文心雕龙·定势》里,它表现为“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这一“文之任势”说的兴起。在中国古代画论里,它表现为诸如顾恺之的“置陈布势”、荆浩的“气势相生”、米芾的“折落有势”这一“画之体势”说的发明。在中国古代书论里,它表现为蔡邕的“势欲凌云”、虞世南的“势逸不可止”、崔瑗的“绝笔收势”这一“书之写势”说的诞生。凡此种种,使中国文化的势已不仅仅囿于慎到笔下那种“腾云驾雾”的纯粹的自然之力,而是从自然到人事地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天下式”。
中国文化中作为典型意象的势的发现,再一次印证了中国文化的道乃是以屈求伸之道。《宋论》中有“屈而能伸者,唯其势也”。按王夫之的解释,势之所以为势,恰恰是以以屈求伸为其潜台词的。故而才有如前所述的以弓喻势,如《孙子兵法》“激水之疾,至于漂后者,势也”所说的以水喻势。此外,论及势的这种性质,还不能不提中国古代“势学”研究大家法国汉学家余莲的精辟分析。他对势“组合之中起作用的潜势状态,机能运作的两极性、交替作用的趋势”这些性质高度概括性的提取,可视为对身的以屈求伸内涵极其精准的描述。
固然余莲对中国古代势的分析别开生面且独树一帜,但是,与此同时也难掩其研究依然存在着一种致命的理论误区。这种理论误区就是他对势的“身体维度”的熟视无睹和付之阙如。他不明白,中国哲学之为哲学,中国哲学之所以区别于西方哲学,恰恰在于它是彻底现象学意义上的一种“近取诸身”的哲学。这决定了,势与其说是一种纯粹形而上的抽象概念,不如说实际乃为一种下学而上达的具体的身态。换言之,一如笔者一度指出的那样,寻本而追源,势也即作为男性生殖器的“阳势”之势,其作为势的身体性原型,乃是势之所以为势的真正脚注。职是之故,才有了《易传》中“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这一表述的推出。此处的“专”与“直”,与其说是抽象地作“专一”与“正直”解,不如说应从中国文化特有的具体象征出发,将之视为男子阳物在阴阳交接时的“抟聚”与“伸直”之象更为妥帖和准确。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以一种现象学的“回到事物本身”的方式,使势的以屈求伸性质得以真实的破揭,并使对其的解读重返一切中国文化现象都植根于此的那种极其始原和无比生动的“生活世界”。
三、以屈求伸在中国古代实践中的广泛运用
既然我们把身的以屈求伸理解为老子的道,那么,这种“万物之源”的道作为“身道”而非“思道”,就不仅以一种“显微无间”的方式,与种种殊相与共相高度统一的中国文化的“典型意象”有关;与之同时,它还以一种“体用一源”的方式,在各个性天合一的中国古代实践领域里得以体现,并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实践精神的集中表现。为了对此加以说明,让我们的考查首先以中国武术实践为其开端。
1.武术实践
武术实践作为最为切身、最为直接的身体实践,使身体的以屈求伸之道表现得最为直观,最为明显。案头上根据现代著名太极拳大师自身体会编撰而成的《随曲就伸——中国太极拳名家对话录》一书,以一种现身说法的方式说明了这一点。书中指出,太极拳最基本的精神要领就是《拳经》所说的“随曲就伸”:“太极拳要求你把胳膊伸直,但是并不像其他运动一样,把你的胳膊伸得很直很直,而是在曲当中求一个直的感觉”,它要求你“身体打开,在将展未展之时,直中还有曲。不能外表看是僵硬的”。此即《拳论》的“于紧凑处求开展”。在这里,“紧凑是指它的四肢外形,手、腿伸展出去的幅度不必太大,手、脚、躯干之间有一种呼应关系。合则‘紧凑嘛。否则即使手脚伸出去很小,彼此之间的关联性不强,那就叫‘局促了。‘开展是指你的神意要高远,以有限的身躯容纳无限的自然”。
对于该书的作者来说,这种“随曲就伸”就是“柔中有刚”。所谓“柔中有刚”,是指“周身无处不是拳,这就要协调,柔是协调的基础,你若周身不能协调、不能柔和到一定相随的程度,就不可能会达到周身每个部位都可以发力,也就不能形成完整的力。所以说要想练好发力,必须要去僵求柔”;所谓的“柔中有刚”,也指“刚和柔的变换,从神与气上来讲,是通过隐与显表现出来的,隐则为柔,显则为刚。从姿态上讲,是通过开与合表现出来的。合则为柔,开则为刚(即蓄则为柔,发则为刚)。在运动过程中表现为柔,在运动到落点时表现为刚”。“这样,不遇敌则已,若遇劲敌,则内劲猝发,如迅雷裂风,故外似处女,内似金刚,此为陈式太极拳的一大特点。”这一切,正应了拳谱的“运劲如百炼钢,何坚不摧”,“极柔软,然后极坚刚”,“外操柔软,内含坚刚,常求柔软之于外,久之自可得内之坚刚”。
正是基于这种柔中有刚的“随曲就伸”,才使太极拳运动既以其“身备五弓”而可视为一种“弓”的意象,又以其“蓄势待发”而可视为一种“势”的意象。关于前者,书中作者提出“练拳架子的时候要求一身备五弓,要有弹簧力。这时你要舒展,但不能直,不管你展多大,都是弧形,胸不能挺,一挺起来就不是弓了,两边看是两张弓,正面看也是弓,两腿也是弓。腿要不形成弓形,气到膝盖就会不足。在五弓基础上松彻底,气血身形都要松。要松到家,松到家以后才能产生弹簧力”,并且指出“所有劲里我看最主要的就是掤劲,万法不离掤。身体往那儿一站,手往那儿一放,意念没方向,浑圆的,拉不开,挤不动,产生八方的掤劲,也叫弹簧劲”。关于后者,书中作者则提出“首先要在收放中练出气势。收的时候,是虚的状态,气势上是蓄。‘蓄势,两掌张开,意念中把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全部通过两掌收于自己的腹部。往外放的时候,外形上一弓步,脚跟、腰间、两臂、双掌形成完整一体,劲力通过双掌放出去,形成排山倒海的气势,如此一收一放,形成流动的气势……静养山岳,动养江河,这就是对气势的描述。逐步如临渊,运动如张弓,发劲如放箭,做到这些,气势就出来了”。
2.军事实践
军事是武术的放大,与武术虽有形式上、规模上的差异,但并不能掩盖二者原则上的一致。这种一致表现为,中国武术上的“随曲就伸”实际上演变为中国军事上的“因势利导”。故中国军事最基本的原则与其说是科学式的因果论,不如说是慎到式的因循论。如果说因果论把军事的胜负看作是人为努力的结果,那么,因循论则把军事的胜负理解为无为而为的运动,战争的结局看作是余莲所说的“不得不如此”“自然而然产生”的。
因此,在中国古老的军事理论中,“因势”“借势”“任势”“审时度势”为其“第一原则”。一方面,这使古代的军事理论家们对“势”的威力极尽讴歌之能事,“势”被视为不可抗拒的无穷潜力之展示,从而就有了《孙子·势篇》中的“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势如彉弩”,如此等等之说的产生,以至于以其“计利以听,乃为之势”“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而成为“无往不利”的“利”的代称。另一方面,它使古代的军事理论家由此进而走向了“势”的决定论,“势”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般决定人类战争的命运。由此就有了《孙膑兵法·篡卒》中的作战“其巧在于势”,《孙子·势篇》中的“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孙子·虚实篇》中的势“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淮南子·兵略训》中的“势胜人”,如此等等结论的奠定,其结果使古代军事理论《孙子》认为,“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也即一种“优势”的存在使敌我双方在未战之前就胜负已定,甚至它可以使我们做到《孙子·谋攻》中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那么,这种无往不克的势能如何成为可能?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再次回到前述的王夫之的“屈而能伸者,惟其势也”的理论。也就是说,对于古人来说,势之所以为势,恰恰在于屈与伸之间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和相互转化的关系,以及随之产生的一种“引而不发”“蓄势待发”的势能。乃至可以说,二者之间的差异、对比愈明显,其内蕴的势能愈递增。其道理就如同在拳术中,我们的身体愈内敛、愈紧凑,也就愈外展、愈膨胀,随之而来的力量也就愈富有、愈无穷。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在军事实践中,这种屈与伸的关系可以触类旁通、引而申之为迂与直、弱与强、守与攻、久与速、害与利、隐与显、死与生等之间的关系。与之相应的,屈而能伸的原则使军事理论家孙子提出“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养则能避之”,“兵闻拙速,来睹巧之久也”,“形兵之极,至于无形”,等等。实际上,如果说上述的事实还让你对中国军事理论的屈而能伸的原则持有疑虑的话,那么,孙子军事上的死生处境辩证法则以其屈的最大化而将该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孙子·地篇》中写道:“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从而就有了中国军事史上“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穷寇勿迫”等战例一个个接踵而至。所有这一切,不仅与西方如克劳塞维茨辈所追求一味强攻、直接对抗的思想形成鲜明对比,也与东方古老的老子思想心有灵犀,并且同时也表明“孙老合说”的观点以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完全成立。
3.社会政治实践
正如以屈求伸的原则支配着中国的军事实践那样,以屈求伸的原则同样支配着中国的社会政治实践。这一点不仅可见之于《尸子》卷下的“汤复于汤丘,文王幽于羑里,武王羁于王门,越王栖于会稽,秦穆公败于崤塞,齐桓公遇贼,晋文公出走,故三王资于辱,而五霸得于困也”这一历史书写的史实;也可见之于韩非子的“勾践入宦于吴,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故能杀夫差于姑苏。文王见詈于王门,颜色不变,而武王擒纣王于牧野。故曰:‘守柔曰强”这一老子式的解读;还可见之于从周文王一直到曾国藩这些中国历代著名政治家基本上都以以屈求伸为其最为重要的修身功夫,才有了诸如“韬光养晦”“敛迹藏锋”“持满戒盈”“功成身退”等极富中国特色的政治智慧的推出。这样,“德者,得身也”,对于中国古人来说,道德的最高宗旨与其说是“兼济天下”,不如说是“修之以身,其德乃真”的“明哲保身”。也就是说,唯有看似消极地返归于身,守护于自身,我们才能“身,伸也”地实现从“己身”向“天下之身”的真正积极的延伸。
也正是由此切入才凸显出了中国古代“势”的政治学的合理性。尽管汉学家余莲基于中国古代“势”的政治学的哲学辩护,以其价值中立的色彩和作为专制主义的左右袒而备受非议,但是,一旦我们把他所强调的“势”更多地理解为并非“权重位尊”的势,而是“因势利导”“以屈求伸”的势,那么,人们对于余莲的“势”的政治学的种种非议就会随之冰释。因为在余莲的解读里,势实际上是《韩非子》中的“不亲佃民,不躬小事”“明君无为乎上,群臣悚惧乎下”之势,是“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无不克则莫知其极”之势。乃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韩非子的“术不欲见”的“术”,还是韩非子的“法莫如显”的“法”,以其“审合形名”、因循趋利避害的自然人性,其同样也从属于势。故就此而言,中国古代政治家的势既可视为孙子“不战而战”的兵法的重演,又可视为老子的“无为而为”的道法的再现。由此我们发现,正如司马迁所说“归本于黄老”“原于道德之意”,这样,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韩非子学说与老子学说之间也存在着内在关联。
此外,以屈求伸的原则不仅支配着中国社会政治实践的横向的现实层面,还在中国社会政治实践的纵向的历史向度上有所体现。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社会历史观之所以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社会历史观就在于,如果说西方传统的社会历史观(西方启蒙主义是其集中体现)从意识出发,坚持社会历史是循着理性进步而呈线性的发展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社会历史观则从身体出发,主张社会历史是循着屈伸运动而呈往复的态势。王夫之无疑是后者历史观的代表。王夫之在《宋论》中描述中国历史时说:“极重之势,其末必轻,轻则反之也易,此势之必然者也”,“否极而倾,天之所必动,无待人也”,“承大驰而势且求张之日”。或一言以蔽之,对于王夫之来说,物极必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由此才有了历史中治乱、盛衰、抑扬、离合之交替,也即古人常说的“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这一点,既可以整个中国历史作为其坚定的事实依据,又被两千年前老子提出的“物壮则老”所一语中的。同时也意味着,就其究古今之变的理论而言,被视为辟老的船山实际上正是以《老子》为自己思想的真正开山。
4.文学艺术实践
以屈求伸的原则也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领域中得以体现,并且是更富创意、无所不用其极的体现。如果你对这一点存有疑问的话,那么,建议你步入中国文学艺术作品的“大观园”巡视一番。从中国园林艺术中的曲径通幽,到中国建筑艺术中的势欲凌云的向上微翘的飞檐;从中国书法艺术中的笔走龙蛇,到中国绘画艺术中的隐显互见;从中国音乐中的抑扬顿挫,到中国诗歌中的对比衬托;从中国戏曲中的穿针引线,到中国小说中迭起的章回(迴)和悬念。在这里,你与其说看到的是艺术家直抒胸臆的一泄无余,不如说看到的是艺术家“引而不发,跃如也”的表达的含蓄,看到的是一种以迂为直、以屈求伸的直以迂显与伸以屈见。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往往都不是唾手可得的,而是曲折婉转,看似近在眼前而实际却远在天边。
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实践中,这种曲与伸的关系往往是通过诸如静与动、虚与实、白与黑、少与多、柔与刚、藏与露、起与伏、收与敛、内与外等关系范畴表现出来的。故与以屈求伸的辩证原则相应,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有苏轼的“静故了群动”之论,有笪重光的“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之论,有张式的“空白非空纸,空白即画也”之论,有古代命题官的“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古画院考试命题诗)之论,有刘熙载的“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之论,有唐志契的“善藏者未始不露,善露者未始不藏”之论,有董其昌的“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疏林或高或下则有情”之论,有王夫之的“才着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去”之论,有王国维的“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之论。凡此种种,其论虽异,其旨却同,它们都殊途同归地以身体的以屈求伸为理论原型。无怪乎诗人王维在论及“文意”时提出“身在意中”。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身在意中”观点的推出,既不失为对中国文艺理论之旨的高度总结,同时又可视为对梅洛-庞蒂的画家不是用“心”而是用“身”去绘画这一当代“身体美学”思想的先发之鸣。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梅洛-庞蒂的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又一次不期而遇。二者都把文学艺术形态理解为内在的“意”与外在的“象”的统一,也即“不可见的”与“可见的”的统一,从而最终把文学艺术形态与合内外的身体形态联系在一起。进而,在此基础上,二者都把文学艺术实践理解为身体的内的外化、外的内化的践履。在梅洛-庞蒂那里,这种践履表现为“回到自身就是走出自身”,而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那里,这种践履则表现为身体运动的屈中有伸、伸中有屈。我们看到,正如梅洛-庞蒂通过这种践履使身的无限的“我能”得以释放而通向“诗意的神秘”那样,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则通过这种践履使身的不息的“生生”得以彰显而直抵了艺术的“真力弥满”“造化已奇”的至胜境地。此即中国古人“有神自在身”的境地,也即老子基于身的以屈求伸的“不化而化”“无为而为”的道的境地。这种“文以载道”再次表明了老子的学说以其文、质兼摄,以其放之四海而皆准所具有的无穷魅力。
注释
①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13章,中华书局,1984年。以下引用此书内容的相关注释只标注章数。②44章。③13章。④54章。⑤54章。⑥60章。⑦36章。⑧36章。⑨36章。⑩36章。41章。45章。41章。26章。36章。73章。58章。2章。69章。22、24章。16章。23章。25章。30章。34章。59章。57章。19章。58章。80章。64章。14章。46章。19章。8章。22章。3章。73章。81章。30章。46章。55章。10章。28章。76章。78章。43章。78章。28章。10章。61章。6章。35章。77章。8章。66章。78章。51章。[法]莫里斯·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85、339页。[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商务印书馆,杨大春、张尧均译,2005年,第217页。参见张再林:《中国古代身道研究》中与“生命意象”有关的若干篇章,商务印书馆,2016年。参见张再林:《身体哲学范式与体育论旨间的互窥——以中国古代射艺为例》,《体育学刊》2016年第5期。参见《五行》帛文以及太极拳的“行云流水”说。中国气功则旨在使身“导气令和,引体令柔”。[法]弗朗索瓦·余莲编:《势——中国的效力观》,卓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8、128—129页,引言叁。参见张再林:《中国古代身道研究》中第二十章“中国古代‘势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及解构”的有关论述,商务印书馆,2016年。关于这种解释,可参看美国汉学家夏含夷与中国学者赵建伟对之的论述。余功保编:《随曲就伸——中国太极拳名家对话录》,人民体育出版社,2002年,第156、58、95、327、330、329、345、214、147、111—112页。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1册,岳麓书社,1982年,第177、179、157页。
责任编辑:思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