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教育背景——品怀特海的精神发展史
严中慧
怀特海的个人生平堪称一部精神发展史。怀特海在《自传》中谈到 “这些个人回忆的重点在说明我人生中有哪些有利的因素,帮助我发展潜在的能力。”如果我们能够学习与领会怀特海的精神发展史当中那些生机活泼的要素,我们对课程、对教育就会有更为宽广而深刻的理解,进而绵延为我们教育善好的种种可能。
美妙的英国古典家园
怀特海于1861年2月15日生于英国肯特郡。由于年幼时身体虚弱,由父亲为其教读。10岁起学拉丁文,12岁起学希腊文。除了兄长的陪伴之外,一位老园丁还常带他去户外活动,使他的生命富于活力。老女仆惠雪,为蜷缩在炉火旁的膝垫上的怀特海,朗读狄更斯的小说。他享受过家庭成员给予的爱,也享有好的家庭教育环境,那是一段欢乐温暖的日子。童年是人生宝贵的记忆,对比罗素不幸的童年、混乱的婚恋和时常涌动的要自杀的念头,怀特海始终保持着生命的热情,不难理解美好的童年对任何一个人的意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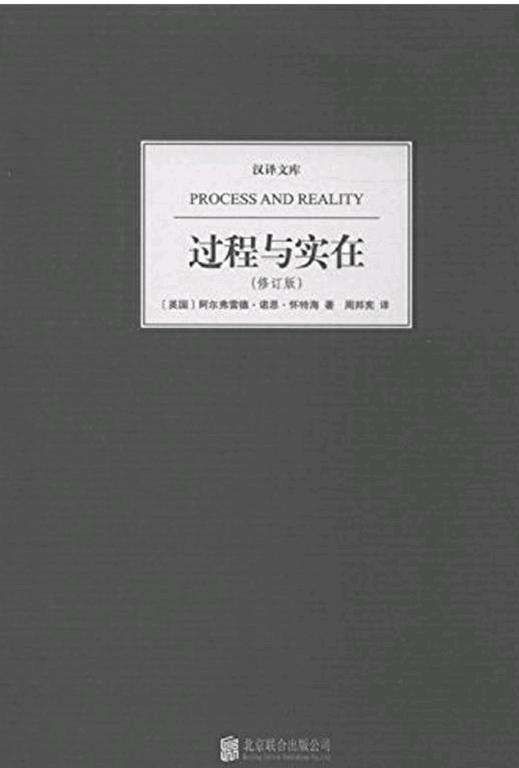
风景如画的肯特郡是怀特海童年生活的美的背景。此地滨海,是兵家征战的要道,留有许多古迹。幼年的怀特海就在随常可见古罗马城堡的断壁残垣、诺曼式的壮丽的建筑游玩,也会游历奥古斯丁首次讲道之处。3岁时的秋天(1864年),怀特海亲见了白金汉宫、荒疏政务的维多利亚女王以及她的卫队,以孩子的目光向历史盛大场面投去一瞥。深刻的历史感不需要寄赖后天的灌输,从小的耳濡目染如烙印一般驻留于怀特海的心。
他出生在一个从事教育、宗教和行政管理的家族,祖辈父辈在教育管理上卓有成就。其父与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泰特交往甚笃,并深受广大民众的爱戴。父亲在担任牧师后响彻教堂的传道声,体现父亲对宗教的虔诚,这对怀特海有很深的影响。怀特海深切地意识到,他不是因为他父亲有知识才敬重父亲,而是因为父亲关心当地事物的个性。若说怀特海日后追求的是一个万在有情的和谐世界,那么他第一次领略“和谐”一词的涵义也因为他的父亲。当旧约派的父亲去为洗礼会派牧师离世而诵经时,英格兰人在宗教上的强烈对立情绪和人际之间的亲密情感使怀特海深受震撼,这使怀特海对教育和历史产生了兴趣。
“一便士阅读”
19世纪中叶,受到民主运动的影响,英国的文化经历了大约50年的改革,其中一个现象就是“一便士阅读”。在坎特伯雷行政堂区的教室里,每天晚上都有“一便士阅读”的活动,人们只花一便士,就能阅读众多文学佳作中精选的读物,这一便士的收益用于支付煤气费和管理员工资。在那时的英国,教堂是培育进入人类生活中的深层的最高价值的全国性机构。作为阅读的休息,中间还会安排两三次带有钢琴伴奏的歌咏和独唱,以及小提琴独奏。行政堂区还会为参加“一便士阅读”的读者寻求解答文学问题的名家人物,比如受人尊敬的牧师、医生、律师,为大家做出释疑。怀特海的父亲就经常充当“一便士阅读”活动的释疑者或主持人。
这种教育面向一切人。怀特海在《回忆》中记录了一位傻老先生,他每晚花上一便士来堂区的教室读书。与这位傻老先生同等阶层的人也可以接受教育,而不仅局限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上层阶级。各个阶层的人都需要学习足够的知识,得到智识的启蒙,才能推进社会的文明。并且教育也不仅仅是学校的事,“一便士阅读”无声地招引着人们终身性地学习。怀特海说“我最宝贵的记忆之一是,在我有生之年,我已目睹英国的教育,以及它带给英国人生活所带来的变化。”
“狭窄而适合现代世界”的基础教育
十四岁(确切地说差四个月就要十五岁了),怀特海才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学校在多赛特郡的舍伯恩镇,这里的地理、历史与人文同样利于人的成长。来自南大西洋温暖而潮湿的风,使得多赛特郡土壤肥沃,富庶多产。若要种植灌木的话,随意哪一头插在地上都能够在一年内长到6英尺高。苹果园、林地、蕨类植物和草丘也自然很茂盛。这里民风淳朴,如果一个中学生在乡村路上要喝水就会得到免费的苹果汁。“人的性格大半归于地理”,这样的地理大半也归因一所学校的“性格”。
舍伯恩学校由圣阿尔德海姆所建,与杰出的学者阿尔佛列德王也颇有渊源。因为爱德华国王六世在16世纪改建了这所学校,学校里的学生又被称为“国王的学子”。新房屋也被修成古式的,用古老的石料建造。校钟是破旧的,它是亨利八世从金衣农场带来的,当钟声响起时,我们仿佛能听到若干个世纪的生命的声音,因而成为学校的一项传统。这里还有另一项传统,那就是“最大的老地主”为一切付钱,有钱人担任校董事会的董事长,投资教育慷慨大方。“支配着这个学校的与保守党为伍的最大的地主们都是有良知的人,他们知道如何培养有教养的人。”——这一切莫不体现出英格兰学校教育中浸润着优良的文化。
舍伯恩学校尽管处处闪耀着慈爱宽和的一面,却不会失之过柔。这里有着严格的班长制,对学生品德的管束可谓纪律森严。怀特海在舍伯恩上学时当过级长,是六位负责学校管理维持校规的高班生之一。作为学生领袖,他曾杖责一个偷窃的儿童。如果不在全校面前杖责,那个偷窃的儿童就会被开除。
怀特海所受的教育是古典式的,怀特海坦言“一种古典式的教育对这些英国儿童的未来生活产生了极其实际的影响”。怀特海认为他所受的基础教育是狭窄而适合现代教育的,因而也是幸福的。在那里,怀特海学习古典文学、历史、地理、数学和科学。舍伯恩学校给予学生运动和自修的时间,这时的怀特海已经是一个体育健将。在舍伯恩学校的最后两年,历任院长所住的房间成为怀特海的私人书房。闲暇时,他喜欢阅读华兹华斯和雪莱的诗篇。他凭直觉意识到罗马与英国人缺乏真正亲密的关系,而希腊人却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严格的古典博雅教育,奠定了怀特海日后的学术研究的基础。普莱士认为“多数科学家所学发生严重偏差的二十世纪,他(即怀特海)在科学家与人文学方面所具有的良好的平衡正是他的特征之一”,怀特海在舍伯恩学校的教育或许为其日后的发展打下平衡的基础。
大学教育——剑桥大学
1880年秋天,怀特海开始了他三十年未中断的剑桥大学生活。怀特海的大学时间是勤勉的,除了每天课堂学习之外,还要花两三个小时来学习数学。在剑桥大学,他先是当学生,后来当研究生,1885年获得研究生奖学金还获得了教学工作。
剑桥大学的正式教学由具有第一流能力的风趣的教师承担,怀特海对这些教师的教育很满意。尽管如此,怀特海仍直言:不能夸大受惠于剑桥大学在社会科学和智力方面的培训。怀特海所听的大课都是关于数学的,他从未进入过另一间大课教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欠。怀特海认为剑桥大学的习惯做法只适用于非常专门的环境,即只适合第一流的天才,却未提供适合一般大学生的课程。
剑桥毕竟英才济济,学风醇厚。怀特海在剑桥的晚饭时光常常与教授、同学高谈阔论,一般从下午六七点钟一直到晚上十点左右。政治、宗教、哲学、文学,无所不谈,也因此读了大量各类图书报刊。那时怀特海对康德十分着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些段落几能成诵。每周六晚,怀特海还与师友们进行“史徒会”(Apostles),以柏拉图式的对话来切磋交流。核心成员是年轻的学人,然而一些史学家、法学家、科学家和国会议员们也如长了翅膀的天使一般,成为这个活动的年长会员。怀特海曾说,他之得益于交谈并不亚于书本。
怀特海走的是一条漫长的成长路程,他的前半生都在扎实地积淀。他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个职位是高级讲师,那时他已经快50岁。剑桥大学期间,怀特海大量阅读,为建立自己庞大的哲学体系扎实准备,失眠曾严重困扰他。迁居伦敦后,有八年他居住在乔叟提过的老磨坊附近,那里有种古朴天然的美。或许因为这种美,怀特海的失眠渐渐消失了。在伦敦大学期间,怀特海担任多项教育行政职务,经常参与伦敦高等学校教育的视导。哈佛大学的年代是怀特海创作最为高产的年代,谱出了最具创造活力的乐章。有一次,有人问他如何能够在哈佛任教却能按照每周一章的进度写完 《科学与近代世界》,他回答说“书上的一切,在过去四十年里都谈论过了。”
来自妻子、学生的教育
妻子韦德有外交官家庭背景。妻子的审美趣味总是为其增添奇妙神秘非凡的魅力。怀特海常言道,妻子勃勃充溢的生命力刺激着他,使他懂得存在的目的就在于追求道德和审美方面的至善至美。
怀特海晚年著述不断,却从不觉得跟年轻人谈论是浪费时间。在哈佛,他每周至少三次演讲。他给学生讨论的时间不是二十分钟,而是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怀特海家的夜谈至少持续了十三年……巧克力饮料、饼干……彼此交谈。怀特海夫妇巧妙的鼓励,激发年轻人的思想火花。怀特海认为“从那里所得到的启发可以使人改变气质”。跟年轻的心灵接触,使自己的源泉长流不息。
1947年,怀特海在哈佛大学去世,享年86岁。
怀特海无论作为哲学家、数学家还是教育家,著述都丰富,而且那么饱有生命的热力。他作为一个整全的人,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类之师,作为一个集大成的有机哲学家,都让人倾慕和深思。与其思考我们如何去培养怀特海这样的人,不如去创建一种利于“怀特海”成长的外在环境,美的教育背景。正如怀特海所言,“这种美的背景使教育中的一个要素,正如解释惯性和潜在的理想主义。如果没有认识到教育阐明了我们下意识的生活中一个始终存在的梦想世界,就不可能理解什么是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