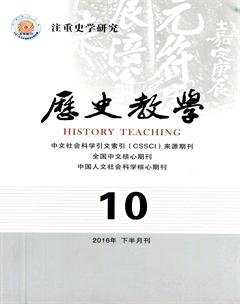“商性”相通:汉唐间河西走廊与丝绸之路贸易
高荣
丝绸之路被誉为“人类文明的运河”。因所经地区不同,又有绿洲道、草原道、西南道和海洋道等。但是,由中国内地经河西走廊、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和北非的经贸文化交流的陆上丝绸之路,则是古代中西方经贸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国际通道。地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塔里木盆地交汇地带的河西走廊,不仅对于古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也是中原王朝对外开放和涉外管理的重要窗口。
一、河西走廊是古代丝绸之路
商贸往来繁盛之区
早在先秦时期,由中原经河西走廊到西域各地的丝绸之路就已出现。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公元前5世纪前后,中国的丝绸已见于中亚、南亚和欧洲等地,而殷墟妇好墓中的玉器则主要来自新疆和田,“玉门”之名即源于其地为输入美玉的门户。张骞通西域后,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不仅汉朝“使者相望于道”,而且西域各国使者也“更来更去”,络绎不绝。河西汉简中有很多西域使者商人往来各地的记载,所涉及的国家有楼兰(鄯善)、于阗、康居、大月氏、罽宾、乌弋山离等30多个,其中还有不见于文献记载的祭越、折垣等国名。据永光五年(前39年)《康居王使者册》记载,“数为王奉献橐佗”的康居王使者杨佰刀等人每次从敦煌入关,都会得到沿途各县的饮食供应。这些西域各国的使团,多以政治使节之名,行商业贸易之实。因此规模很大,动辄数百人。汉简记载的一批从内地途经酒泉禄福(今酒泉市肃州区)、敦煌渊泉(在今瓜州县境内)回国的西域使团,自于阗王以下竟有1074人。由于过往人员众多,沿途食宿等均由当地郡县供应,以致河西各地疲于应付。汉成帝时西域都护郭舜在给朝廷的上书中就指出,敦煌、酒泉等郡“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到东汉时,更是“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魏晋十六国时期,虽然中原动荡不安,但河西则是相对“独安”之地,西域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等国仍然“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中就有很多与敦煌、酒泉、张掖等地贸易的记载,而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粟特文书则表明,即使在“永嘉之乱”前后,在河西走廊敦煌、酒泉以至姑臧(武威)、金城等地,仍有数以百计的粟特商人活动,他们对当地粮食等各种物资的市场行情非常了解。隋唐时期,通往西域的三条路线“总凑敦煌”,河西各地商业贸易空前繁荣。隋朝大力经营丝绸之路,西域胡商“多至张掖交市”,其中大业五年(609年)共有西域二十七国国王、使者聚集张掖进行互市贸易。唐代更有大批西域胡商云集河西,以致“商旅往来,无有停绝”。贞观初年玄奘西行至瓜州,胡人石槃陀为其介绍了一位往来伊吾30多次、非常熟悉沿线交通的胡翁做向导,而此胡翁则以一匹曾十多次往返伊吾的老马相赠,并最终经莫贺延碛到达伊吾。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石染典请过所文书,分别记载了开元二十年(732年)三月和次年正月西州商人石染典两次到瓜、沙等地贸易的情况;敦煌佛爷庙湾唐墓出土的胡人牵驼图,正是胡商往来贸易的写照。
二、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
胡商汇聚之地
汉代河西四郡的设立,为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后,东来西往的使者商旅日月相继,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更加活跃,定居河西的西域胡商也日渐增多。他们在长期的交往中已逐渐汉化,其中在姓氏上开始采用单音汉姓,形成了以所在国名为氏的习惯,如月氏(支)人氏支、安息人氏安、康居人氏康、米国人氏米、曹国人氏曹等。
敦煌是往来西域的门户,更是多民族聚居和多种文明汇流之地。西汉时已有西域胡商在此定居,南朝时的康绚,就是西汉时留居河西的康居后裔;东汉时,敦煌被称为“华戎所交一都会”。敦煌悬泉置出土的一枚“浮屠”简表明,佛教在1世纪末已传入敦煌并在民间流行;到2世纪末,敦煌已有一批胡汉高僧在此译经布道,其中竺法护就是世居敦煌的月支(氏)人。当时居住在敦煌的粟特人有百余家之多,唐代沙州西北的“兴胡泊”就因“胡商从玉门关道往还居止”而得名。唐代敦煌县所辖的从化乡,则是专门为定居当地的粟特人而设的。
除敦煌外,凉州也是粟特人的重要聚居地,而且势力相当强大。北魏灭北凉后,在武威俘虏了一批粟特商人。他们不仅经商,还屡屡干预当地政治。前凉奋节将军康妙、后凉西平太守康宁等,都是手握重兵的实力派人物;而世居武威的安氏家族,在唐初已是“民夷所附”的“奕代豪望”,安修仁及其子弟十多人,均为李轨的股肱近臣,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唐初能迅速平定李轨集团,正是得益于安氏家族及武威胡人的支持。到唐中叶时,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而胡居其五。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河西兵马使盖庭伦联合凉州九姓胡商安门物等,杀了节度使周泌,足见胡人势力之大。
河西走廊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不仅外来人口众多,而且各种文化和外来宗教(如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皆在此交融汇集。唐代禁止百姓信奉祆教,但在敦煌壁画和敦煌文书中却有很多“赛祆”活动的画面和记录,沙州、凉州等地还有祆祠,显然是在当地聚居的西域胡人所建,而敦煌文书和壁画中的“赛祆”礼仪与场景,也应是当地民众活动的反映,足见唐代定居河西的西域胡人绝非少数。
三、河西走廊是中原王朝
对外开放的窗口
汉唐时期,河西是丝绸之路长盛不衰的主干道,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中原王朝的对外交往特别是与西域各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其涉外管理也日臻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自成体系的管理机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负责涉外管理事务的机构主要是大鸿胪和尚书所属的主客曹。大鸿胪秩中二千石,其下有大行令及诸郎,是集民族、封国和外事管理于一身的中央大员;尚书所属的南、北主客曹,最初只是典掌文书,东汉魏晋时权位渐重,取代了大鸿胪的部分权力而直接管理外交事务。敦煌悬泉汉简中就有尚书所属的“使主客谏大夫”“使主客郎中”等中央吏员发出的文书。至于“使送康居校尉”等,则是因事而设的临时性加官,事毕则罢。隋唐时期,随着对外交往的频繁和三省六部制的确立,鸿胪寺和尚书省礼部主客司已成为专门管理对外事务的中央机构,而且分工逐渐明晰,其中鸿胪寺主要负责礼仪及具体事务,礼部主客司则主政令与管理,在整个涉外管理中居于主导地位。
但是,不论是官方使者还是商旅、僧人,举凡出入境文书的签发与查验登记、沿途交通食宿供应、市场价格的确定与交易管理等各项具体事务,都是由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具体承担和实施的。地处丝路交通核心区域的河西各级地方政府和边塞机构,在中原王朝的涉外管理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河西各地都设有相应的驿、置、传舍(馆驿)、关、市等机构和令、长、丞、尉、司马、啬夫、佐等吏员。东汉时的武威郡,在与北匈奴的联系交往中就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每当北匈奴诸王大人驱赶牛马到武威与汉朝商贾交易之时,往往由“所在郡县为设官邸,赏赐待遇之”。双方间的“合市”,也是在武威太守主导下进行的,武威郡治姑臧因此出现了“通货羌胡,市日四合”的繁荣景象。至于河西走廊最西边的敦煌郡,与西域间的交往联系更加密切,汉代很多时候西域事务都是在敦煌太守主持下进行的。悬泉汉简中就有汉宣帝甘露四年“敦煌伊循都尉”和元、成帝时期敦煌太守给伊循都尉的下行文书,而《后汉书》则记载了东汉在敦煌设立管理西域事务的中郎将、河西副校尉、西域副校尉等职官的情况;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仍然是“制御西域”的军政中心,敦煌太守则负有“统摄昆裔,辑宁殊方”之责。因此,敦煌(沙州)等河西郡县吏员之能否,对于人员往来和商贸关系的顺利进行都有着直接影响。一旦发生纠纷,可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记载了尚书所属的使主客谏大夫在得到西域使者与地方官员发生纠纷的消息后,责令敦煌太守按照有关律令查明原委,并在规定期限内上报朝廷;敦煌郡、县政府在接到上级文书后逐级转发,要求下属部门和相关吏员进行调查核实。
汉唐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完善的涉外管理制度。一是出入登记查验制度。凡是出入边境、津关,均需有相关传信(过所)文书,详细说明过往者姓名、身份、人员数量、携带物品、目的地等;非法越境者,将受到严厉处罚。二是接待过往使者商旅的制度。河西汉简中有很多当地官府接待过往使者官员的记载,因过往者身份地位不同,其所享受的车马和食宿标准也有区别。一些西域商人,为了获得中原王朝更多的赏赐或食宿、交通便利等,往往弄虚作假,甚至不惜冒充诸国侍子、贵人。魏文帝时的大鸿胪崔林就曾专门向敦煌太守府发文,令其参照以往“故事”和惯例,制定相应规格的接待标准,以使相关工作有规可循,有则可依。三是互市和通商制度。中央政府对边境互市的地点和交易物品等都有相应的政策规定,但能否严格执行,保证公平交易,则与地方政府吏员有着密切关系。如东汉末年,中原大乱,敦煌旷无太守20年,丝路贸易被当地“大姓”豪强所控制,来敦煌贸易的西域客商因经常遭遇欺诈和劫掠而心存怨怼,直到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3年)才扭转此种局面。时任敦煌太守仓慈通过打击当地不法豪强,安抚慰问西域胡商,重新整顿市场秩序,营造了良好的贸易环境。凡欲留驻敦煌者,由官府制定平价与之交易;欲往洛阳者,则由官府发给过所文书;对于从敦煌返回的西域商贾,由官府派吏民护送,以保证他们的安全,从而得到了西域商人的拥戴。
总之,汉唐时期的河西走廊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既是丝路交通咽喉要道,也是中外经贸文化交流的枢纽要区。不仅吸引了大量西域使者和商人,促进了本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而且对于保证中原王朝涉外管理的有效运转和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