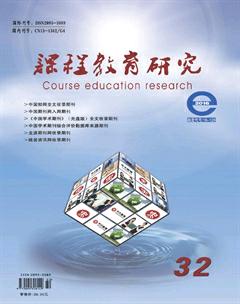浅议当代隶书创作的时代特征
吕升荣
【摘要】作为书法五大体别之一的隶书,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兴衰交迭,耐人寻味:战国古隶的天真烂漫,两汉分隶的异彩纷呈,晋、唐隶书的气格卑俗,宋、元、明三代隶书气息靡弱,清代隶书的张扬个性,无不承载着各个时期社会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与审美崇尚的各种气息,探究其发展历程,剖析其兴废成因,研讨其当代隶书的走向及隶书创作的时代特征,对于促进当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隶书向前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隶书 创作现状 时代特征
【中图分类号】J29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2-0193-02
隶书,从春秋战国始,到秦、汉、晋、唐、宋、元、明、清,数千年发展演变,直到当今,经历了重大的变革阶段,走过了极盛的发展时期,重又担起“进化先驱”的重任。
书法史昭示着我们,隶书创作的兴盛或者衰糜跟书法家创造力的强弱成正比,这似乎是一个充分而不必要的条件。在隶书没落的唐宋元明时期,书法的发展是波澜壮阔,大家迭出,重法尚意、崇姿尚态……书法的美被诠释得淋漓尽致。但最后却带来了“师帖者绝不见工”的颓败的局面,书法单行道上走的愈显寂寞,日益艰难。然而,书法是不能衰竭的。为了她的绵绵不绝,中国人绞尽脑汁,费尽心血,不断丰富她的审美内涵,不断提升她的审美意义。篆隶成了在中国的书法史上人们复兴书法生命力的重要工具。
一、首先来看看青川木牍。1980年在青川木县城的郝家坪战国墓葬中出土的两件木牍上的古隶已可见篆向隶演变的端倪。字的结体生动,显得率真自然,轻松活泼。并由繁趋简,许多字的笔画形态已现隶书雏形而开始了与篆书的分道扬鑣。是什么原因促使书写者对当时通行的大篆体做了如此大的改变?除趋急赴速的因素外,书者本人大胆变革和创造的勇气无疑是为直接的因素。正是这种可贵的创造精神,对中国的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初汉的《五风刻石》《莱子侯刻石》《霍巨猛刻石》《谷口鼎》《鲁孝王刻石》等,由于载体的多样性(石刻、墓砖、铜器、石阙、摩崖等),使书写者更充分地发挥出创造的天性,无拘无束,仪态各异,无雷同重复、矫揉造作。用笔结体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篆书,尤其是章法布局更体现出这时期的特点。没有程式化的束缚、没有规范的枝梧,书家的创造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至东汉,隶书日益成熟,其本体的生命力达到了辉煌、灿烂的巅峰,书家之众、作品之多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1]。
在书法艺术的各种书体之中,隶书具有中介的性质,即作为一种近体文字,隶书更接近作为近体的真书,而区别于作为古体的篆书。篆书的纵势,如曹衣带水;隶书的横势,左右舒展,如吴带当风。但它又直接从篆书演变而来,更多地保留了古体文字的信息。因此,就书法的字体而言,要写好今体书法(包括草书、行书和真书),必须有很好的学习隶书的背景:就书法的笔法而言,隶书的用笔介于古体和今体之间,既有篆籀用笔的沉静和深入转笔圆厚,又读真书、行书用笔的杀锋取势、形态变化及其神气和飞扬。写楷书参以隶书更古雅,“南北碑莫不合汉分意~汉分为真楷之源”。许多写北碑又写隶书的书家,常常将两者结合,难分彼此。于行草而论,单纯从帖学走出来的书家,与写汉碑、北碑的书家,所作的行草书风韵大异。前者易得其秀,往往笔画单薄;后者笔力苍厚、骨力坚劲,大字尤有气势。沈曾植章草根底汉隶,探求本源,出乎自然之妙。以中锋玉筋作秦篆是天经地义的方法,而邓玩伯一隶作篆,略参圆笔,让端庄平稳的小篆饰以隶书的翩翩风度,使篆书面貌一新[2]。
二、隶书经过了汉代的绚烂之极后归于沉寂。虽有唐代的殷仲荣、韩端木、史维则、李隆基;宋代的徐浩;明代的祝允明、文徵明、黄道周等偶尔作隶,但远逊汉人,全然没有隶书的风采灼灼、千姿百态。直至清代,隶书方得以复兴和发展。帖学的流败,阁体的盛行,加重了人们的求变心理。晚晴高压政策的逐渐减弱,理论的呼叫,唤醒了压抑许久的主体精神。
一旦艺术家的主体精神得以解放,其创作活力亦必然能冲破原来被视为不可逾越的清规戒律的束缚,其审美眼光,创作思维亦必然得以扩宽。清代隶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审美趋势的影响下,开始了向隶书本体之外无限空间的探索。
被称为清代碑学巨擘的邓石如,以其全面的造诣对清代中期书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隶书“遒丽淳厚,变化不可方物”。他以《怿山》《禅国山》之意藴与隶书,以篆籀之笔,兼取《曹全》的遒丽、《衡方》的浑厚、《石门颂》的纵肆而熔铸一炉,故而骨劲貌平、遒丽峭拔、虎虎有风,有着撼人心魄的感染力。反过来,他又以隶笔为篆为草为行,他的行书也有篆意、分韵,写得劲健开张,笔势磅礴,如屋漏如划沙。其书法风貌的极大艺术感染力,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归功与隶书。
吴昌硕在隶书领域也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另一块天地,他“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这正石吴氏隶书着床的母体。猎碣的笔法、意韵的介入,使他的隶书透出一股郁勃浑健、朴浊酣畅的撼人气势,同时他还广泛汲取《三公山》《嵩山台室》以及秦权量,《泰山》《琅琊》刻石,甚至秦玺、汉印、封泥、砖瓦文字等,笔力雄厚、气酣神畅。吴昌硕又以篆隶笔法作行书、作草书,笔势奔驰放纵,苍劲雄厚[3]。
能将隶书诠释得淋漓尽致的莫过于何绍基了。他广临汉隶诸家,铸以己意,我写我心,我写我意,我写我趣,创造了一派天机的新格局。同时他根据自己的审美眼光,对汉隶加以改造,笔画长者促之,短者纵之,瘦者肥之,实者虚之……遗其貌而取其神,师其意而不蹈其迹,熔铸汉碑之长,成一家之法。这是一片全新的艺术世界!唯其新,恰是艺术的生命所在。而且,更有书法史意义的是,何绍基晚年的行草书融入的隶书,篆书笔意,逐渐步入奇险之境,筋骨涌现,意态超然。的确,何氏行书如“天女散花”飞去的霓裳,透出一股仙气,美仑美奂。
三、清人隶书遥接汉人而能开出新境,推动隶书的又一次发展。隶书家门以借古开新的创新精神,以汉隶为基础,又不为其所囿,将审美的目光从隶书中扩展开来,向隶书本体外的无限空间作了大胆的探索,为隶书的创作赋予了新的内涵,并给她的书体以创新的营养。这给后人有益的启迪。徐生翁、来楚生、陆维钊、林散之的书法便是上述影响的产物。
鉴古方能知今。清人作隶,打破了隶书和其他书体之间的界限,无行中使各种书体通过隶书达到了一种内在的统一。这种内在的统一和联系,强调的是各门书体的一致性。那种同时“隶书求方笔……‘行书求秀润……楷书求圆笔”的方法是不利于风格的产生的。隶书有着动人的乐章,我们却不能组成优美欢畅的旋律。隶书艺术如苍穹中的五彩云霞,我们却不能鼓起双翅邀游其中,隶书的价值和魅力还远远没有被挖掘得很充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海隶书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为书坛所瞩目。隶书进化,从东汉始,至清代后期,到本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历代书家付出了艰辛努力,但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是没能突破汉碑局限,张海是代有着思想透析力的书家,他在长期学习古人、临池实践的基础上烛照先机,认为时代在变迁,社会在进化,如隶书超越不了前人,就意味着退化,那完全是与社会发展相悖的,他在反复思索、寻求中,认定汉隶是源远流长的隶书之本,要使有本之木长青,必须让他发出新枝茂叶,他找到了由基本形象生发出的扩展和延伸的真谛,他决意以汉隶为本,化裁汉简,用笔使转之间,糅进行草书笔法,最终破汉碑刻的忆限,以酣畅的笔墨表现求进化,破历化书家的历史局限,以崭新的时代感求进化,堪称当代隶书的一面旗帜。其特点有三:
(一)鲜明的、快节奏的时代感。现代社会是快节奏、高频率的旋律、理念,各种政治、经济活动无不显示出一种汹澎湃的气息、浪潮,张海草隶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读张海的草隶,仿佛有一股汹涌澎湃之势扑面而来,他用笔之快,仿佛迅雷不及掩耳,呼之而来,挥之欲去。
(二)浑然天成,自然流畅的表现。隶书的进化,说到底就是超越,进化之难也就是超越之难,难就难在自然。张海隶书之进化,隶书创作之走向恰恰就是自然而然,没有生般硬套,没有装腔作势,没有一点搔头弄姿和故弄玄虚,历代不少书家偏又淡漠汉简,而张海恰到好处地以化裁汉裁为突破口,突出隶书的“书写气”,突出隶书的“自然气”,在隶书创作中不局限于单纯对金石气的追求,而是努力表现出翰墨风采。因此张海写隶书是笔随手动,手随心动,自然天成。
(三)既具艺术价值,又具实用性的书体。隶书最早在春秋就被作为实用性书体。卫恒《四体书势》云:“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隶书发展到汉,取代秦篆,成为日常通用书体,然至隋唐以降,日常通用字体被楷书所代替,隶书成为一种装饰书体。以后直到宋、元、明、清,日常通用书体都是楷体和行草的天下,少数隶书大家的作品作为观赏性留存。
我们今天正处于大创新、大变革的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有极大的发展。我们的书风不可能不反映这一时代气息。我们的书法家要么就是思想上的侏儒,要么就是行动上的矮子。然而我们的创新不是面壁独创,不是空穴来风。要知“水之积也不厚,则其浮大舟也无力”,我们必须在传统中大力煎熬,摸爬滚打,才能求得凤凰莲磐的自由。历史在审视着我们,我们将不该负于历史。
参考文献:
[1]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2]郦道元.水经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550.
[3]山东书协.汉碑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