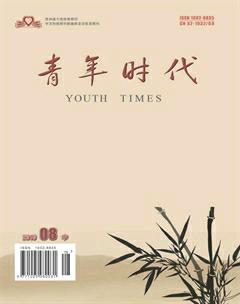俗世蛩音
赵宗梅
一、城市黄昏
今天我想写写黄昏。从乡村到城市,黄昏已经渐渐和我疏离。或许是日常生活的过于忙碌,对于城市的黄昏我真的了无印象,若仔细搜索,脑海里清晰浮现的还是小时候肆意燃烧的那一天晚霞。城市的黄昏早已退守到人们的视线之外,取而代之的是早早亮起的各色霓虹,光怪陆离,如一个个不真实的梦境。
我想或许我未留意,如果真的去寻找,城市的黄昏应该也自有它的意趣吧,但是每每坐在公交车上,或是在教室里,黄昏悄悄溜走,我却总是把它忘记。因为城市的喧嚣或是大脑的无意识业已把黄昏定格在生活之外,我已无法和它共同思想,这是我的悲哀。城市的黄昏毕竟不象乡村,会莽莽撞撞扑进我的视线,城市的黄昏是淡泊的隐者,只等待有诚心的人。就象清晨的第一缕霞光,在我的梦境尚未完结的时刻,她已经默默和我告别。
而我在黄昏做了些什么呢,大概还在教室里,抑或已在食堂吃饭,懊恼食堂的伙食低劣和服务态度的不友善,盘算晚上该上哪位老师的课或是自习时学些什么。黄昏的概念,只是词典里固定的词语,在我的心里实在没有位置。我不知道我每天为什么而忙碌,总是以为理想就在前方不远,可是翻过一座山,却看见山后面只是山。
生活是一尾五彩的鱼,她诱我同归大海,所以我永在跋涉。我在路上风餐露宿,遗弃梦想,学着不失望。我在清晨阳光普照的时刻,写着关于黄昏的文章,我想也许哪天我就能看见朝霞,也能亲近黄昏
也许生活永远如此,正如我在夜晚深陷诗的城池,蓦然望见孤独城市的夜晚总是盛开着绚烂的灯光,各式各样的光芒把天空的色彩完全掩藏,星星消隐在天幕的后面
闪都不闪!
二、俯仰天地间
似乎有一只蚊子在围着我的脸打转。但这并不是影响我心情的主要原因。其实也许只是阴天和偶尔想到的生活压力让我心生不快吧。
我,忧郁,直率,不工于心计,知道会有人喜欢我,当然更多的人不会喜欢。这个世界是倾向于热闹的,而我却不太懂得许多委曲的世故
单纯和傻其实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分。
在上海,每天坐地铁上下班,每天聆听列车沉重的呼啸,有一点点累,却也算不得什么。但还是憧憬偶尔能闲下来,到我喜欢的地方去转转看看。沉闷和无希望的生活总是让人觉得艰难,当然希望也许并不是没有
正如有人所说,我是一个喜欢生活在幻想中的人,舍此,似乎没有活下去的支撑。
早就懂得人和人是多么地不同,所以也并不苛求什么,一切就这么顺顺当当自自然然地向前流淌吧,我知道我没有任何能量去改变什么。北京的培训也没有能够把我变成女强人,骨子里还是原来的那个小女人呢,虽然并不指望去做一株寄生的植物。
我知道有许多人是和我相似的,满怀着一腔纯真,把美好的梦想装在心里,企图去温暖大地,得到的是冷漠的回应和令人心痛的嘲笑,以及现实无情的抛弃。只是有些人会懂得自救,有些人选择了沉沦。而沉沦的代价也许是从此湮灭,也许是名垂青史,至于我,当然是只会敬仰他们,无论成败。
我知道如今的上海一如既往是一座充满欲望的城市,繁华和败落在每日的阳光中浮浮沉沉,永无休止。令人窒息的空气把人挤压到最低。我行走在人来人往的长街上,想像张爱玲曾经在这里留下的脚印,想像有一天我能轻轻推开她家的那扇门,看见她曾经描述过的那棵开满了像纸手帕一样的令人讨厌的花朵的白玉兰。但我好像总是没有闲暇,我努力把被充塞得很满的时间加上一抹动人的颜色,希望在我回头眺望来路的时候,除了平淡和平淡,还有一些别的什么。
三、想起了当年的那些风沙
和朋友聊天,他向我说起昨天种花生的劳累,突然觉得这样的日子于我曾经是何等亲切。可是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淡忘了花生该如何播种,所以竟被人取笑。
小时候还住在老家,一个很小的村落,家里人很多。后来老奶奶和奶奶相继去世,两个姑姑也出嫁了。再后来有了弟弟,成了标准的四口之家。
总是忘不了小时候坐在板凳上啃地瓜的情形,所有家人都倾注对我的疼爱。那是一段黄金般完美的岁月,那种被呵护的感觉终生都在我的心头流淌,让我一生感念。老奶奶在我五岁的时候意识已经模糊,她经常分不清我们家里的人,可是却总是能清楚地喊出我的小名。一会儿看不到我,就会问:孩子呢?孩子在哪里?许多年过去,我还能清晰地在记忆的深处找到她衰弱却慈爱的身影。
那时候毗邻黄河的地带在春天经常会刮起漫天的风沙,村里人的脸也都透出原始而质朴的颜色。我在去小学的路上经常用红色的纱巾把脸全部蒙起,然后透过这薄薄的红色看太阳耀眼地亮在天边,心里便涌起一种安详而快乐的情绪。也许后来的我的乐观和坚持都是因为有了那时种种幸福感的积淀吧!尽管命运的流转也难免携来世态炎凉和阴差阳错,我却依然固执地相信远方,相信幸福总会在某个时刻从天而降。
许多年过去,有一天我再回到村里的时候发现了衰老和死亡,以及许多让人始料未及的成长。我想我在他们眼里应该也变了吧,因为岁月总是这样不容分说。可是我也只能作为一个匆匆的过客,和在这里已经不见的黄沙一样,很快就要飘落到他们看不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