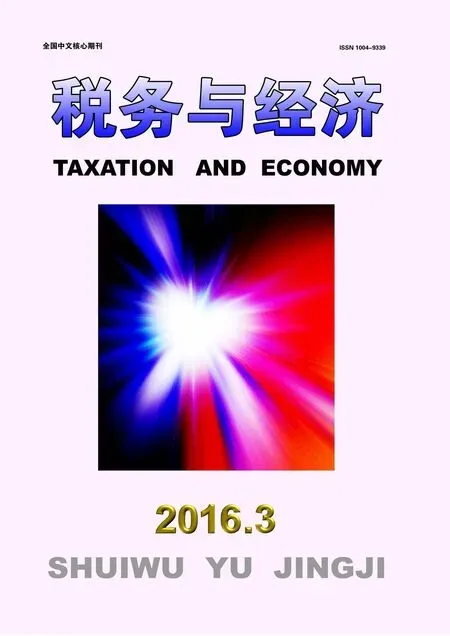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集约利用
刘 铮,金 鑫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20044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引致建设用地需求量显著增加。这一方面有力地支撑了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城镇周边大量优质耕地被占用,严重威胁粮食安全。据有关资料显示,“1997~2008年建设占用耕地3705.3万亩,同期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增加5110.9万亩”。[1]与此同时,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大量土地低效利用问题,“目前我国城镇低效用地占40%以上,处于低效利用状态的城镇工矿建设用地约5000平方公里,占全国城市建成区的11%”。[2]土地的低效利用严重威胁了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课题。
一、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关系的相关研究
关于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关系,学术界主要呈现出两个大的研究方向:第一,城镇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第二,土地利用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本文侧重于前一个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一)城镇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
关于城镇化对土地集约利用影响问题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1.城镇化不利于土地集约利用。由于城镇发展过程中以依赖土地增量的模式居多,而耕地是城镇建设增地的主要来源,增量土地的易获得性导致土地的利用效率低下,因此以耕地变化作为间接变量表明土地利用与城镇化的关系。史育龙(2000)通过对1986~1995年非农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的数据分析,得出10年间城镇建设用地占全国耕地减少量的比例大约为10%。在结合1995年全国各类建设占用耕地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推断出“城镇建设对于全国耕地建设的贡献率应在4% ~10%之间”。[3]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是土地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之一。朱莉芬(2007)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计量模型,分析了中国东部14省城镇化对耕地的影响。结果表明:尽管不同模式城镇化对耕地的变化影响不同,但两者都存在显著负向关系。[4]潘竟虎(2008)对甘肃省1997~2003年的城镇发展的研究得出: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建成区面积增加2 100.54hm2。小城镇遍地开花造成了区域用地结构不合理,城乡居民点出现的“双重占地”甚至“多重占地”现象严重,区域间土地利用不协调。[5]
2.城镇化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尽管城镇化进程中大量耕地被占用,出现了一系列的土地闲置和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但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城镇自身具有空间集约性,城镇化的发展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新增土地会不断减少,存量土地的利用效率会逐步增加。曹雪琴(2001)认为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土地粗放利用向集约利用转变,能够有效地解决我国土地资源短缺问题。经研究,我国“城市化水平从1957年的15.39%到1977年的17.5%,每年只增长0.10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减少耕地147万公顷。而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发展到1993年的28.14%,耕地年均减少58万公顷,仅为1957~1977年的40%。”[6]该数据表明城镇化发展不仅没有造成耕地的加速减少,反而缓解了耕地流失问题,间接地体现了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提高。李丹(2003)以人均占地简单地表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以城镇规模代表城镇化水平,得出城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7]彭冲(2014)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006~2011年中国大陆29个省区(市)的城镇化水平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了评价,研究表明两者总体上呈平稳上升态势,且存在一定的差距;就平均水平而言,城镇化水平始终高于土地集约利用。城镇化对土地集约利用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8]
3.城镇化对于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与前两种观点不同,有学者认为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城镇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存在动态性。宋戈(2006)认为当城镇化水平较低时,城镇数量扩张导致大量耕地被占用,出现“吃饭与建设”的矛盾。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容纳的人口更多,有利于节约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9]
有学者认为,定性分析只能粗略地表明城镇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并不能深入地反映两者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因而部分学者利用统计和计量等方法对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关系进行检验和探讨。梁书民(2005)通过人口——耕地模型对中国耕地的中长期变化进行了分析和预测,认为当前城镇化是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随着城镇化的发展速度逐渐减缓,耕地流失速度也会逐渐放慢,并在2050年城镇化基本实现时趋于稳定。[10]廖进中(2010)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长株潭地区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利用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情况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显示:长株潭地区的城镇化综合水平在1988~2007年间呈稳步上升趋势,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在1988~2002年间呈平稳状态,而在2003~2007年间出现倒“L”型的快速增长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动态计量模型,对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进行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研究表明:城镇化综合水平的变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变化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使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得到不断改善。城镇化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影响逐期增加;但在短期内,城镇化的推进对土地集约利用具有较大的负面作用。[11]郑华伟(2011)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和功能效用函数对全国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江苏省城镇化水平和江苏省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进而采用与廖进中(2010)相同的计量手段对全国及江苏省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利用两者关系进行了分析(全国城镇化水平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结果显示:在短期内,全国和江苏省城镇化水平都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但长期看,城镇化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两者具有一致性,城镇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不断增加。[12]
尽管现有研究中关于城镇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从时间维度上看,多数学者比较赞同最后一种观点,即早期城镇化是以土地面积扩张为主的发展模式,因而不利于土地集约利用,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镇本身具有的空间集聚优势逐渐凸显,土地集约利用程度逐渐增加。
(二)土地集约利用对城镇化的影响
在土地集约利用对城镇化的影响方面,“国内外许多学者普遍赞同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有利于城镇化推进的观点。”[11]张兆福(2002)认为城市土地的合理利用可以扩展城镇土地总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城镇土地利用结构,促进城镇化进程。[13]余方镇(2005)认为土地集约利用能够有效地解决各产业部门间的争地矛盾,提高城镇用地的综合效益,促进城镇化的不断发展。[14]但廖进中(2010)[11]和郑华伟(2011)[12]关于土地集约利用对城镇化水平的实证分析显示,土地集约利用对城镇化的冲击较小,就全国层面而言仅有3%。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而土地集约利用有利于城镇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因此土地集约利用能够对城镇化产生一定程度的有利影响。由于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评价指标是多维度的,因而,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程度在不同的研究中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三)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相互影响
与前述研究不同,在研究方法上,有的学者将物理学上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的耦合理论以及体现系统之间和谐一致关系的协调理论引入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利用关系的研究中。该方法并不是单独地探讨某一系统对另一系统的关系,而是同时探讨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两个系统间的关系。孙宇杰(2012)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综合评价了江苏省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并对两者的综合水平进行了协调度分析。结果显示,江苏省各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协调度总体上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在短期内不协调,稳定性不强;但长期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之间相互促进,向着越来越协调的方向发展。[15]张乐勤(2014)通过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方法对安徽省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利用进行了综合评价,测算了两者之间的协调度,并在此基础上采用GM(1,1)模型进行预测。结果显示,早期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均较低,城镇土地供给能够支撑城镇化建设,但两系统间协调度较低;中期城镇化快速发展,两者关系不稳定,耦合协调度波动明显;但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均有所提高,耦合协调度逐步改善,向着更加有序的方向发展。经预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将相互促进,两者关系将更加协调。[16]马德君(2014)以西北民族地区19个代表性城市为研究对象,研究显示,该地区城镇化水平远高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两者协调发展水平不高,存在明显的区域间差异。但整体上呈现系统间协调度逐步增强、区域差距不断缩小、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度趋同趋势。[17]
尽管耦合协调度分析较为直观地反映了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现状,但并未指出两者是如何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对于两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原因也尚未给予较为系统的解释。
二、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关系的机理分析
关于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关系的现有研究中,多数学者利用统计方法粗略地反映了城镇化水平变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部分学者利用计量手段和耦合协调度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二者之间的影响呈现动态变化过程。但是计量研究多局限于描述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关系的表象,从理论角度对两者相互作用的机制探讨尚有欠缺。本文认为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可以从集聚效应、外部性效应、市场价格效应和政策效应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集聚效应
集聚效应是城镇化过程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城镇空间范围内集聚的结果,同时又是决定城镇发展的重要动力。土地要素一方面能够为城镇发展和空间聚集提供空间场所;另一方面,可以为城镇发展带来经济效益。因而,集聚效应的产生和影响与土地集约利用的程度和变化是城镇发展过程中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
城镇化是由于生产力水平提升导致大量人口聚集的动态过程。作为集聚效应的主要来源,规模经济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的大量聚集。在生产领域,土地作为劳动和资本要素聚集的载体,为制造业产业聚集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而带来资本和人口聚集。“早在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佩第就发现世界各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差异,与其所形成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同。”“通过考察,佩第得出:比起农业来,工业的收入多;而商业的收入又比工业多;换言之,工业比农业、服务业比工业的附加价值高。”一、二、三产业间的收入比较,完全可以用作土地农用与工业用地的效益比较。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向城镇聚集、向工业聚集,有利于提高集约用地水平。在消费领域,由于劳动人口向城镇聚集,居民聚集地区的土地利用强度逐渐增大。同时,为居民聚集区域服务的相关产业,一方面为生产提供服务,一方面为居民生活提供服务,在“增长极”的带动下,都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从而带动土地集约利用。
规模经济以土地要素的聚集为前提,随着规模经济的产生与改善,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产出得以增加,区域内土地得到合理利用,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过度的集聚会导致规模不经济,在土地集约利用方面也是如此。当集聚程度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会导致城镇的过度拥挤;尽管在经济效益方面,土地集约利用依旧会有所提高,但同时造成的土地利用结构紊乱、土地规划失当,以及过度拥挤的“城市病”等问题不利于土地集约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二)外部性效应
城镇化的发展对城镇产业结构产生了外部性,促进了土地的集约利用。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的产生和扩大,促进了生产技术变革,推广了机器化大生产模式,减少了土地占用面积,改变了土地利用模式,有力地提高了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城镇建设需要的变化,产业结构出现了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被资本密集型产业所替代,以高投入、高产出为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服务型产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这些高密集性和高效益的产业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促进了土地集约利用。
城镇化加快了公共物品的投资,为土地集约利用带来了正外部性效应。城镇化进程中大量人口集聚在一定区域内,对完善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出客观要求。一方面,交通、照明和通讯等方面基础设施的投资加大了土地利用强度,同时能够为厂商生产与居民生活消费提供便利,带来了不需偿付的额外收益,提高了单位面积总产出。另一方面,由于城市聚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环境卫生等问题,相应的公共物品投资,能够有效地降低集聚不经济所产生的成本,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
(三)市场价格效应
城镇化过程伴随着土地要素集聚,而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必然受到价格因素的支配。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对土地资源进行统一的行政划拨。由于没有价格机制的引导,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无法体现,进而一定程度上导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低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价格机制日益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价格能够相对准确地反映出土地要素的供需现状。虽然土地资源比较稀缺,但是在早期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土地供给量相对充足,土地要素价格相对较低,因而,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中存在大量占用土地,且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对土地集约利用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城镇建设对土地的需求激增,远远大于土地供给。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价格杠杆对土地市场所起的作用逐步显现。获取增量土地的成本过高,将迫使各部门加大对存量土地的开发和利用。并且,随着土地稀缺性的凸显,与土地相关的产品价格相应增加,将促使经营者加大对现有土地的投入。市场价格机制作用于土地供求,必将促进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不断提高。
(四)政策效应
农业大国的特殊国情以及重工业优先战略,决定了中国建国初期的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近3亿农业过剩人口,迫切要求加快城镇化进程,进而对土地向城镇聚集产生了迫切要求。特别是在GDP崇拜导向下,各级政府一度把城镇化水平作为政绩考核的硬性指标,在短期内不能实现软件提升的条件下,最为便捷的方式就是城镇土地规模扩张带来的城镇水平提升,从而造成在一段时间里城镇建设用地激增,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城镇化带来土地资源浪费的诟病。经过几十年的城镇化发展,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城镇化的本质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各级政府反思城镇规模扩张带来的土地资源浪费弊端,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的相关政策,从法治和政策层面为土地的集约利用提供了坚实的保证。以此为转折点,在城镇化不断发展的同时,土地集约利用效应开始显现。
三、促进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集约利用的政策建议
土地聚集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城镇的不断发展加快了土地利用的空间转变。从时间维度上看,城镇化早期土地资源普遍存在粗放利用问题。随着城镇的快速扩张,集聚效应、市场价格效应、外部性效应以及政策效应等,促进了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既是城镇化进程的产物,又进一步对城镇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总体上说来,城镇化对土地集约利用存在一个先恶化后促进的关系变化。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监管,科学引导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我国作为一个资源非均衡的人口大国,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呈现较大差异。为了避免城镇化与土地利用“先恶化后促进”问题的再现,对于处在城镇化初期尚未形成“增长极”的地区,应通过政策引导等方式积极培育“增长极”、促进产业集聚,并对同时产生的土地扩张进行严格管理,从初始阶段就开始加强土地的集约利用。从法律、政策和监督层面尽可能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
第二,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有步骤地推进产业升级。应通过提高产业聚集区域基础设施共享率,加强产业间合作,有效扩展土地空间利用范围。加快高效益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第三,加快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价格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目前我国处于转型发展时期,政府需要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和规范,通过制定“协议出价最低标准”等干预措施对市场价格进行引导,推动存量土地的流转,严肃惩处土地交易中的违法行为。
第四,大力发展集约型城镇。集约型城镇具有土地利用强度大、效率高和结构合理等优点,能有效地避免城镇空心化问题,且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1]张迪,郭文华.城镇化对土地利用和耕地生态保护影响研究[J].国土资源情报,2010,(11).
[2]我国土地浪费惊人 开发区低效利用[EB/OL].http://finance.cnr.cn/txcj/201406/t20140629_515749309.shtml.
[3]史育龙.我国城市化进程对土地资源影响程度的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0,(4).
[4]朱莉芬,黄季焜.城镇化对耕地影响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7,(2).
[5]潘竟虎,等.甘肃省城市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4).
[6]曹雪琴.城市化与土地制约[J].经济经纬,2001,(2).
[7]李丹,刘友兆.我国城市化发展与耕地变动的关系研究[J].经济纵横,2003,(1).
[8]彭冲,等.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演变及关系[J].地理研究,2014,(11).
[9]宋戈,等.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关系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6,(1).
[10]梁书民.城镇化背景下我国耕地的中长期预测[J].农业经济问题,2005,(增).
[11]廖进中,等.长株潭地区城镇化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
[12]郑华伟,等.中国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1,(9).
[13]张兆福.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问题[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2,(1).
[14]余方镇.城镇化与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研究[J].开发研究,2005,(2).
[15]孙宇杰,陈志刚.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水平协调发展研究[J].资源科学,2012,(5).
[16]张乐勤,等.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协调度测度——以安徽省为例[J].城市问题,2014,(2).
[17]马德君,等.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度分析[J].财经科学,2014,(3).
[18]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