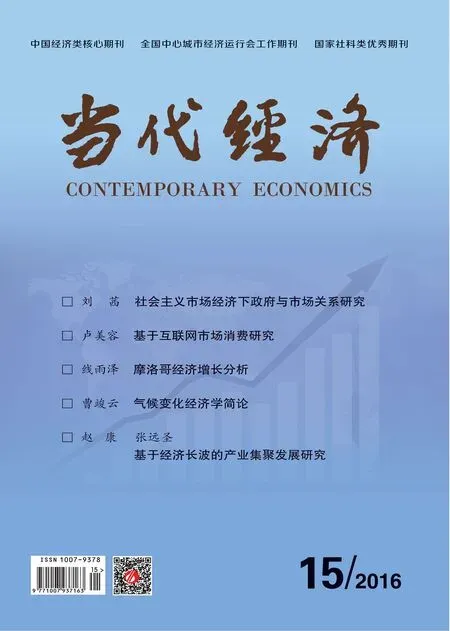“营改增”背景下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研究综述
易梦洁
(西南财经大学,四川 成都 611130)
“营改增”背景下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研究综述
易梦洁
(西南财经大学,四川 成都 611130)
“营改增”作为我国结构性减税的重大举措,经历了上海试点及全面扩围,即将迎来收官。根据“十二五”规划的整体思想,如何完善中央与地方增值税分配体制,已成为国内学者近两年研究的热点。本文对研究“营改增”后重构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的动因、意义以及数值测算的成果进行梳理总结,结合最新“营改增”政策,为改革实践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营改增 ;财政收入效应;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
一、“营改增”的财政收入效应
全面推行“营改增”是我国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关键所在,牵扯到我国两大税种,影响范围广,覆盖行业多,将会对国家及地区财政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近年来国内众多学者均在积极地关注“营改增”的财政收入效应,改革过程中积极地发现问题进而有效地解决问题是关乎到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重要课题。
1、短期效应
有关“营改增”的财政收入效应,众多学者均着眼于其短期影响。李方(2015)统计截至2013年6月,试点地区平均减税近30%,减税总规模超过900亿元。雷静(2014)认为“营改增”意味着地方主体税种缺失,大幅度减少地方财政收入;税务机构职责权限会减小。吴金光(2014)指出由于上海市“营改增”试点期间实行税收收入与改革前保持不变的过渡性政策,财政收入没有出现结构性波动,但是“营改增”全面推行之际,势必对地方财政造成减税影响,如何处理税收收入的划分,防止地方收入大的波动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张新(2013)将“营改增”的财政收入效应分为两点:一是总减税效应,体现在“营改增”全面推开给中央带来的减收规模大于地方,而收入的降幅会略低于地方。二是税收分成效应,他认为,除了减税效应给中央与地方带来的同步冲击,而营业税作为地方政府掌握的几乎惟一主体税的消失,形成了地方收入单方面缺损。王晓丹(2014)认为,“营改增”造成的地方财政收入锐减将使地方政府缺乏改革积极性,增加改革难度;且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不容忽视,经济增长受阻,进一步减少地方财政收入;由于增值税进项和销项税额的地域问题较复杂,更是增加了地区间的利益纷争,市场的统一性将会遭到破坏;地方财政风险增加。吴家红(2013)除了提到地方财政收入减少,还指出,在目前的财政分权框架下,地方本就承担着与其财权不相匹配的事权而导致收支失衡已久,而公共产品需求的增加将迫使地方财政支出日益增加。这“一增一减”的情形下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不言而喻。
2、长期效应
另外,也有不少学者针对“营改增”对财政收入的长短期影响进行了分阶段研究。胡怡建(2014)遵循“营改增”结构性减税的主导思想,推算出短期内全国2013年全面推行“营改增”将导致减税1600亿元,然而在长期过程中,参照一般均衡模型的原理,短期财政减收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将会使长期财政收入增长1.089%;崔丹等(2014)认为短期内由于市场信息不完全,供给和需求曲线不固定,导致财政减收;中期内分析供求弹性与1的大小关系,来分析收入格局能否得到改善;长期内,由于企业会扩大经营规模来抵销“营改增”导致的企业所得税的增长 ,市场的流通交易量增加,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将会持续性增长。田志伟(2013)提出在短期内,“营改增”的直接效应显著,结构性减税会使得国家税收较大幅度下降,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压力。从长期来看,“营改增”的间接效应更显著,不但能弥补“营改增”的短期结构性减税带来的财政损失,还将在降低宏观税负的同时刺激我国税收产生正增长效应。董俊杰(2014)提出“营改增”使地方财力在短期内大幅减少,将会改变原有的财力分配格局。从长期看,营改增将促使增值税的抵扣链条越来越完整,从而优化税制、减轻企业税负,为地方政府财力的提升提供了较大的空间。高培勇(2013)认为“营改增”的长期效应,不仅可以跨越税制改革领域而延伸至宏观经济运行层面,而且可以跨越宏观经济运行层面而延伸至财税体制改革领域。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看来,短期内“营改增”的结构性减税影响将不可避免的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而且各地区试点已经得到证实;还会降低地方政府改革积极性,加剧地区间利益纷争,财政风险增加,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将更加不平衡。而从长期来看,由于增值税的“税收中性”等自身税种的优越性,“营改增”的间接效应显著,优化税制结构,促进企业扩大规模,促使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持续增长。
二、“营改增”后重构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的重要性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目前营业税收入归地方所有的举措也是过渡政策,预计营改增全部完成后会有新的税制结构。“最具有操作可能性的就是对增值税的分享比例做调整,弥补地方税源。
董文信(2015)指出增值税扩围导致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出现严重的不对称,只有重构分享比例,才能符合“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的原则,稳定国家财政体系。耿变华(2013)提出三点意见,一是中央财政实力相对较强,增值税扩围后财政收入进一步向中央倾斜;二是地方政府改革动力不足,营业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高达30%,表明扩围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很大;三是维持现行分税体制不佳,试点地区试点期间改增的增值税仍归地方,影响税收制度的一致性,只能是作为改革初期的权宜之计。以故重构分享比例是极其重要的。潘罡(2014)认为,由于”营改增”的结构性减税影响,即使改革后税收收入仍返还地方,地方政府税收也将缩减,这将加剧地方政府事权、财权的不对称性,而且同一税种两种分享制度也将影响税收制度的统一性,这都要求必须对目前增值税分享比例进行政策性的调整。张启春(2014)也提出,试点地区试点期间的税收反还属于过渡性政策,随着”营改增”在全国和全行业内全面推行,其所带来的减税效应和改革成本仍然会落到地方政府的头上,必须从根本制度层面落手,重构中央和地方分享比例。
三、“营改增”后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的数值测算
国内众多学者对于重构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的测算,就测算样本来看有基于地方样本,或基于全国样本;就扩围进度来看有采取“一步式”也有基于“分步式”,另外,结构性减税是否考虑以及其他细节之处,众多学者均有自己的假定前提。
1、以地区收入为测算样本
国内不少学者以区域经济的财政收入数据作为测算依据。张启春(2014)基于“一步式”营改增和“不考虑减税效应”的前提假设,以75:25的比例模拟增值税扩围后湖北省、北京市、上海市这三个省市2013年的地方税收收入,测算出三个省市的地方财力损失占税改后增值税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4%,27%和26%;以维持地方财力基本不变为依据,测算出三个省市新的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分别为58.7%,51%和50%。松梅(2014)对云南省的8个样本城市在2012~2013年的营业税占所有税收的比重进行分析,在不减少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不考虑减税效应的前提假设下,测算出8个城市新的地方分享比例,依据众数来看应不低于60%。同时提出,该种分配调整方式应该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分配体制并没有进行调整的基础上进行。董其文(2010)通过对山西省相关数据的分析得出”营改增”后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应调整为69∶31。刘楚汉等(2014)基于”营改增”对湖北省各行各业的影响的分析基础,提出应提高增值税地方分享比例至40%,同时应进一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综合考察各地区的人口规模、消费能力、基本公共服务需要、经济发展状况、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等因素,尽量缩小增值税税源与税收背离所引致的区域间横向财力差距。董俊杰(2014)运用 2011 年的数据,在保持31个地区税收收入不变的基础上,假定当年增值税的纳税范围包含了营业税的全部应税项目,测算得到,除了陕西省的分享比例低于45%以外,其余的30个地区的新的分享比例均在45%以上。
2、以全国收入为测算样本
基于某一省市的数据计算得出的分享比例,并未很好的对于全国范围内的适应性问题加以详细的分析,故而众多学者直接以全国财政收入数据作为测算依据。耿变华(2013)基于三点假设:保持地方财力不变;全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收入共享;新的增值税收入地方的分享比例是地方增值税收入以及地方营业税收入占中央与地方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总和的比值,并依此将2001-2010年的重构增值税地方分享比例求算术平均值得46.29%,且检验合理。张秀莲等(2014)不考虑“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忽略归中央政府的营业税收入,认为改革后的“国内增值税收入”等于改革前的“国内增值税收入和营业税收入之和”,然后利用1994~2013年连续20年的面板数据对”营改增”后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进行了测算,得出新的地方分享比例为30%。董文信(2015)将2001年到2012年的地方营业税和全国增值税收入按照“营改增”的方式全部视作增值税收入,仍按75:25的比例分配,计算出地方财政相较原始值减少A%,他认为,为了保持地方财力不变,应将地方对增值税的分配比例调整到A%,来弥补地方财政损失。最后加权平均得到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为46.12%。刘明等(2013)考虑到改革过程的改革成本,以1994年到2012年的国内增值税为被解释变量,并以相应时间内“营改增”改革后增值税总收入、中央增值税收入为解释变量,构造线性回归模型,提出如果不考虑中央与地方事权的重新划分问题,则由Eviews软件求出“营改增”后增值税地方分享比例为52.18%。
3、多步式“营改增”假定
在今年7月2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应该会表决并宣布进一步将“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及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域,以全面完成“营改增”,这意味着新的“营改增”将会分成两个阶段出台。邢树东等(2013)当时全面地分析了“一步到位”式改革与“分步式”改革两种情况下历年增值税应在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基于改革前后地方财力基本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步到位改革适用性较小,他通过2001 年到 2010 年10 年的财政收入数据,预测未来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分配比例,以算数平均得出扩围后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为50.23%;而分步式“营改增”适用范围较大,第一阶段将不包括一些生活性服务业以及金融业在内的行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可得改革后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为 45.05%,第二阶段将所有现行征收营业税的行业纳入增值税范围,以第一步改革后的地方财力作为改革前地方财力,用同样的方法求得地方分享比例为46.85%。白彦锋等(2012)提出全面推行“营改增”之后,地方财力变化较小的可实行“一步式”改革,利用2000年到2009年全国财政数据进行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百分比的测算,加权平均后提出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为45.64%;对于地方财力变化较大的应实行“两步式”改革,第一步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提高到 37.74%,第二步是实行彻底的增值税“扩围”,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由 37.74%提高到45.61%。两种方式的分享比例差别甚微。
四、“营改增”的启发与思考
总的来说,测算扩围后重构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部分学者直接将税改之前的地方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总收入与税改之后的全国增值税的比值作为重构的地方财政分享比例;部分学者则沿用75:25的分享比例对增值税扩围之后的增值税收入进行分配,以测算出地方财政相较而言减少的百分比作为重构的地方财政分享比例;大部分学者则选择相信建立在自己严谨的假设条件之上的模型,用历年的全国财政数据进行模型的求解与预测,加之适当的时间序列分析,以得到增值税扩围之后重构的地方财政收入分享比例。虽然国内学者对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后重构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的必要性以及测算方法均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但均是各有侧重,在真正的改革过程中,如何兼顾各种细节因素对测算结果造成的冲击,是否应该考虑减税效应,如何协调省市财政结构与全国性税收数据之间的差距,一步式改革还是分步式改革,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分配等等,或许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模型对其进行求解。但同时又应该考虑到,全面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对于某一些变量该舍弃的则应该果断的舍弃。除此之外,应在总体上尊重原有的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利益分配格局,同时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布局、基本公共服务需要、人口数量及财力层次等综合因素,确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分享比例。全面”营改增”后重构地方政府财力保障机制,还要结合中央转移支付的手段进行利益分配,同时完善制度设计,着力于培养地方新的主体税种以完善地税体系,跳出“零和博弈”的误区,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共赢局面。在这种前提下,定能克服改革阻力,提高改革效率,那么增值税“扩围”改革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的重构,必将会为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新的契机,为活跃我国经济市场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1]白彦锋,胡涵.增值税“扩围”改革后中央与地方收入分享比例问题研究[J].税务研究,2012,11:38-41.
[2]董其文.加快推进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改革[J].税务研究,2010,11:25-28.
[3]高培勇. “营改增”的功能定位与前行脉络[J]. 税务研究,2013,07:3-9.
[4]“营改增”税收问题分析与对策——湖北省税务学会课题组[J].税务研究,2014, 05:18-21.
[5]胡怡建,田志伟. 我国“营改增”的财政经济效应[J].税务研究,2014,01:38-43.
[6]胡洪曙,丘辰.增值税“扩围”对地方财力的影响研究[J].税务研究,2012,07:42-45.
[7]刘明,王友梅.“营改增”后中央与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问题[J].税务研究,2013.12:18-20.
[8]王曙光、宋英华、宋佳.增值税“扩围”后的地方财力弥补对策[J].税务研究2014,11:44-47.
[9]吴金光.“营改增”的影响效应研究——以上海市的改革试点为例[J].财经问题研究,2014, 02:81-86.
(责任编辑: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