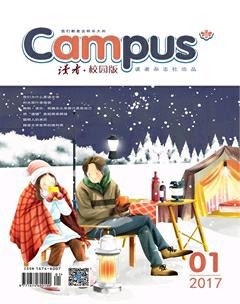念念不忘
闫晗
小学三年级的暑假,妈妈买回一袋白馒头,入口甜丝丝的。我家很少从外面买主食,我觉得新鲜,吃了一个,意犹未尽。那天姥姥和表哥也在我家,下午玩饿了,我回家打开橱柜,寻找中午剩下的馒头,可姥姥告诉我,让表哥吃掉了。我先是很意外,然后有点懊恼,那是一种期待落空后的沮丧。
其他人并不理解这种心情,这种不快原本过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可姥姥偏偏郑重其事地批评我小气。于是那点情绪迅速发酵变大,大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住那一天的心情。后来想想,那馒头其实并不好吃,比爸爸蒸的差远了,可是因为没吃到,味道便显得特别。
小时候的夏天,我最爱吃冰激凌,香蕉味儿的、巧克力脆皮的、紫米的、圆筒的,各有各的妙处。一年级时妈妈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她会买一些圆筒冰激凌寄存在学校小卖部卖冰棍的大叔那里,让他见到我就拿一个给我吃。那时我非常害羞,从不好意思主动去要,只是低着头从冰棍箱子那里悄悄走过,心里却又期望大叔能叫住我。
那时的圆筒冰激凌放在冰棍箱子里,冻得很硬,外面裹着一层淡蓝色的印花纸,揭下来时有一种流畅的快感,我们管它叫“大头”。有一天我拿着这样一个冰激凌,舍不得吃,想等到回家看动画片时,再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吃掉。到家一推门,意外地发现家里来了亲戚,舅舅家的表姐坐在那里。虽然心里并不情愿,我还是把冰激凌递了过去,客气地问她吃不吃。我妈最不能容忍我一个人吃东西,而不问问别人吃不吃,她说那是天底下最没有礼貌的事情。这让嘴馋的我常常过得很纠结。
那一天,二十几岁的表姐毫不犹豫地拿过冰激凌,大口地吃了起来。她吃得如此漫不经心,却没有注意到冰激凌其实只有一个,我一口也没有吃到。我看着她吃完,并没有抱怨,只在心里默默地觉得不喜欢她——她居然吃小孩子的东西。
度过许多个迷恋冰激凌的夏天后,我对一切冷饮突然产生了免疫力,而那种裹着淡蓝色印花纸的大头圆筒冰激凌也消失不见了。表姐结婚生了孩子,依旧是个情商不高的人,我觉得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
我从小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妈妈也并不给我零花钱。中学时,放学结伴回家的小姑娘们常常在校门口买各种吃食,铁板烧鸡排、油炸豆腐串、烤火腿肠……同桌家里条件比较好,会在附近的烘焙店买一种黄油曲奇,奶香味很足,隔着塑料袋都能闻到。有一次她分给我一片,圆圆的,精巧极了,口感绵软,入口即化。我之前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饼干,吃过之后也没有想到跟妈妈要钱去买,因为觉得这东西于我遥远而奢侈。我的金钱观过于朴素,莫名觉得这样的物质欲望是应该被压制的。长大后,我吃过很多曲奇,有烘焙店、西饼屋的,有盒装进口的,可我总觉得味道不及当年吃过的那一片,这里或那里总是差了一点点。慢慢地,曲奇也就褪去了光环,变成了很普通的一种食物。
日剧《大川端侦探社》里有一集,病重的黑社会老大想吃自己年轻时吃过的一种馄饨,手下买来市面上所有种类的馄饨,但都不是当年的味道。他吃过的那碗馄饨用料毫不讲究,特别之处只在于那味道恰恰符合了年轻时的境遇。也许这些求而不得的、存在着时空距离的东西,才是记忆里最美好的。
有个朋友在微博里说,小时候特别讨厌下雨天,因为不喜欢打那把旧伞,每次拿上那把伞都觉得很屈辱。可是,长大后的他没办法穿越回去,给从前的自己买一把新伞。小时候对物质的执念,也都只能由它们自行散去。有物件能让我们念念不忘,总好过无牵无挂,哪怕是再小的一点念想,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