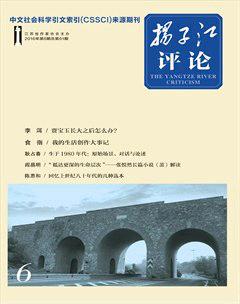“抵达更深的生命层次”
阎晶明
张悦然名下有一个很重的标签:“80后”。无论是从年龄、出道时间还是创作成绩上,她都是这个概念里打头阵的一位。我一向对十年为一代际的写作划分保持警惕,因为它非常短视且并不能说明多少文学问题,说到底是一种话题、姿态的说法而非美学意义上的标识。可是面对张悦然,这个概念好像挥之不去。2016年,张悦然以她的一部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茧》又一次刮起一股旋风,这一方面印证了她在小说创作上的实绩,另一方面更加加重了她作为一个年龄层次的代表性。“茧”不但是一个忽然跳到眼前的单字,而且没有任何依靠小说名字抓住读者眼球的刺激性。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张悦然是自信有力量挑动一个简单字词深邃含义的小说家,也是一位自信可以让小说人物故事证明一切的写作者。
《茧》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它在当下小说界有着怎样的暗示和意味?“茧,1.完全变态昆虫的囊形保护物。2.手脚掌因摩擦而生的硬皮。”(见《辞海》)作者或许借用了这样的比喻:“茧”是成长的代价,同时也是成长的呵护者。它制约着生命的自由生长,却也保证了其成长性。“茧”并没有在小说中成为直接隐喻,甚至没有对这个字词刻意引用,但“茧”的意味却成为笼罩整部小说的象征,没有完整读过小说,是无法体会到“茧”的外壳作用及其坚硬度的。
没有“茧”的《茧》却有一个更加坚硬的意象:一枚砸入人脑中的铁钉。这枚铁钉牢牢地、残忍地钉入到故事的核心,所有的人物躁动、挣脱、游走,都以这枚铁钉为圆心,在很小的半径范围内撕扯、挣扎。从故事层面上看,这枚铁钉是砸入一个人脑袋里、造成其终生植物人状态的刑事案件和残酷悲剧。在文革的混乱中,医科大学教授程守义遭批斗后,继而被人将一枚铁钉砸入脑袋,从此成为植物人。同一所大学的教授李冀生,隐约成为这一事件的“当事人”,虽然另一个叫汪良成的人自杀身亡而被“确定”为行凶者,李冀生却是逐渐浮出水面、不被惩处的“凶手”。
戏剧性在于,同在一所大学工作生活的程李两家,他们家人的生活、后代的成长都勾连在一起。植物人程守义,是横陈在所有人物和事件当中的一道沉重、深厚的壁障,令人窒息,令人厌恶,却又不可逃离,这个植物人打断了所有人通往未来的道路,同时又让历史在这种打断、阻隔中被奇异地贯通、串接、延续。
我们不妨先放下小说想要表达的主题,先来看看小说透过这枚“铁钉”,营造出的小说性、小说意味以及小说的现代性质感。
一是让“现在”与“历史”产生变异性、扭曲性的冲撞和勾连。程恭、李佳栖两个人的成长、情感,无不烙上自己未曾经历的祖辈、父辈历史,这种历史以强大的阴影投射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他们的关系一刻都不能脱离,又因此不可能产生相交。横陈在医院“317”病房的植物人程守义,既打断、阻隔他们的交往,又牢牢控制着他们不可剥离的“一体化”关系。他们未曾经历文革,依靠什么去写自己未曾经历的历史?历史如果完全远隔现实,作者当然可以写一部“历史小说”,而呈现在《茧》里的历史,恰恰是李佳栖、程恭刚好错过的昨天,是祖辈和父辈们人生中的一部分。于是,小说中的历史就是现实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于现实之外。在这个意义上讲,“80后”这个概念对认识张悦然的小说写作还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一代作家热衷于写“今天”,历史的沉重可以在自己的笔下不出现,因为他们未曾在其中生活过。但张悦然选择了面对一个同龄作家极少去面对的过往,回应了今天的现实与昨天的生活密不可分的联系。从小说叙述上,可以说作者找到了打通今天与昨天、当下与历史的通道,尽管这个通道是借助于一枚铁钉完成的。现代小说或艺术表现“现代”历史,总会找到某种契合点,使其成为“当代史”中的一部分,让人感受到历史的巨大存在,这样,作家艺术家就有了足够的“资格”去书写和表现自己未曾经历过的历史,就使得这种书写和表现不能简单地被划分到某种“历史题材”中去,而使其成为表达现实感受的必要组成部分。
二是因为一个特殊情节的刺目般楔入,使得严肃小说的主题隐喻与流行小说的传奇故事之间实现了有效拼接。这是当代西方严肃小说在美学上渐成趋势的新叙述策略。奥汗·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罗贝托·波拉尼奥的《2666》,都是化流行故事之腐朽为严肃小说之神奇的例证。那些小说里有深远的历史,精致的文化,有高深的专业和艺术,但也有谋杀、侦探,有世俗的爱情和紧张的情节。小说的美学抱负和可读性同时呈现,结出现代小说的“恶之花”。《茧》在这一点上有同构色彩,过去的历史以一枚铁钉为意象注入今天,今天的现实逃不脱与昨天的联系,不可能不受其沉重影响。
三是小说营造的情境、氛围,叙述方式的独特选择,体现了作者创作前的准备可谓深思熟虑。小说采取了李佳栖、程恭两个人交叉叙述、平行推进故事的叙述方法。但这种叙述却又不是当代小说流行一时的拆解补充法,即同一个故事由两个或以上(通常是两个以上)人物来叙述,他们是故事的不同程度的参与者或见证者,他们对同一故事的叙述,在使故事不断奔向完整的过程中又互相拆解,使故事本身产生分裂,含义发生分歧,题旨变得复杂暧昧。张悦然在《茧》里让李程二人交叉讲述,但并不对故事本身进行拆解,不发生理解上的直接“纠纷”。他们讲述的是各自看到的世界,实现的是共同向着一个沉重主题靠拢,表达的是同一代人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精神危机。从语气上,他们二人仿佛进行的是一场对话,虽然不是面对面,但都把对方想象成惟一的倾听者,第二人称“你”在小说里频繁出现,虽然不能说这是一部第二人称小说,却强化了叙述中的对话色彩。可以说,李佳栖、程恭是互为倾诉者和倾听者的关系,漫长的倾诉和耐心的倾听构成了小说的叙述格调。小说的第一章具有更强烈的对话色彩,这应该是小说从一开始立下的叙述基调,李佳栖、程恭共同讲述着见面时的故事,但两个人的叙述在情节上是“分工”进行的,并不对同一情节进行“各自”表述。当李佳栖讲述自己的堂姐李沛萱与之交往的故事时,与程恭的对话味道开始减弱,这也预示着,单纯的对话不可完成对复杂故事的叙述,尽管姐妹俩的故事并不需要全部细节化地让程恭倾听,但叙述必须按这样的方式进行。其后的大部分叙述在对话性上时强时弱,但通篇所制造的这种对话与倾听关系一直维系着。张悦然为自己的写作挑选了最具难度的方法,当然也独具效果。
戏剧性在于,所有人的活动都与植物人相关,难点在于,为他们的关联性寻找故事的粘合度,逻辑的必然性需要花更多心力。在小说里,所有人物间的关联呈扇面展开或合闭,而造成植物人的铁钉,正如扇子尾部的扇钉,起着控制、收拢的作用。在《茧》里,每个人物的命运、性格都与“铁钉+植物人”有关。程守义妻子性格的乖张是因丈夫成植物人引发的,在挽救无望后,她和一个普通工人有了往来并热切希望能够在一起生活,却被对方离弃,她在绝望中有过干脆将植物人丈夫置于死地的冲动,最终却不得不认命,过上了最不愿意又只能如此的不幸生活。程恭的父亲成为施虐式人物,性格的由来自然离不开程守义的遭遇。在李家,李冀生和程守义的命运正好相反,他成了“仁心仁术”的院士,成了新闻人物,成了学习典范。在程守义的植物人状态对比下,他的辉煌被添加了讽刺意味,更加上他实为“凶手”的身份,这一辉煌更具道德上的阴暗色彩。辉煌后面的黑幕才是故事的核心,尽管小说并没有深挖这一黑幕,因为小说要表达的是他们对后辈命运的影响。李佳栖的父亲李牧原,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却同时是一个父亲形象的背叛者和父命的反抗者。他以自己的婚姻为杀手锏,一次次打击这个在外面风光无限的父亲。他娶农村妻子,离婚后又与汪良成的女儿汪露寒共同生活,都是彻底反叛的举动。汪露寒作为汪良成的女儿,自幼背负着罪犯女儿的阴影,长期的压抑让她不得不逃离,她曾想过用呵护程守义来赎罪,却遭拒绝。和李佳栖的父亲李牧原共同生活也注定得不到应有的幸福,最终一无所得。
李佳栖和程恭,是所有人物中打开幅度最大的扇面。李佳栖的恋父而不得其爱,程恭性格中的复仇底色,这一切都为小说涂抹上了不可挥去的沉重阴霾。他们本来都有很好的家族背景、家庭教养,但他们的成长却不可抑止地被加上沉重的心理负担。小说故事的戏剧性、夸张度,全部因这段过往的历史造成。如此网织故事,爱与恨交织推进中,复仇、暧昧、隐秘、失控,欢乐与痛苦,出身骄傲与现实不堪相混合,营造出强烈的、混杂的、神秘的、诡异的小说氛围。故事足够复杂多变,情境足够阴晴不定,必然的命运结局与偶然的情节因素共存其中,将所有的人生推向不可预知的境地。
小说故事都由李佳栖和程恭的自述来完成,他们的“口述实录”,让故事在“局限”中散点式与渐进式地展开,而这种“局限”,是作者选择的结果,也产生了比全知视角更有魅惑性的效果。“倾诉”与“对话”的对位行进,让所有的故事先在地经过了情感过滤,色彩、色调也变幻不定。李佳栖与程恭,比之同在一个屋檐下的祖辈和父辈,经历的历史时间是最短的,小说却恰恰让他们来承担起叙述的职责。这是一种叙述策略,它使现实和历史之间,凡俗现实的比例远远大于“重大历史”,让历史成为影响和制约“成长”的巨大投影而非线性历史的一部分。“植物人”的沉重肉身,有气息但不发言的状态,残酷地干扰着现实。这就意味着,这是一部表现当下现实的小说,为了探究现实所从何来,紧挨着的过往必然成为不可绕开的一部分,历史既非现实也非背景,它是现实的闸门、包袱和刺目的聚光灯,也是现实的一面或平面或凸凹的镜子。作为新时期出生的作家,在小说里写祖父辈的昨天,这是一种有勇气的选择和探索,艺术上需要有独特的切入角度。《茧》里边的祖父辈们的恩怨情仇,有限地、谨慎地进入到今天的生活中。张悦然小心翼翼地处理了这个难题,确保其出现的艺术合理性及情节可信度。同时,小说也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历史只有同当下发生关联时,或直接影响,或间接启示,才具有追问、深究的必要。
当然,这毕竟是一个难题,探索还需要走很长的路。对张悦然以及她的同代作家而言,让小说记述更长的时代和生活,必须有此道义担当和美学抱负,同时还要在保证其创作的艺术品质的前提下进行。《茧》所呈现的历史场面相对有限,比例上显然明显少于“当下”,小说里提到的一些历史场景,也并无还原的要求,仿佛是过渡式交代。这似乎是作者防止情节失真的谨慎,生怕损伤小说品质的严谨所致。在我看来,或许还可以再大胆一些,更进一步,让历史本身有“说话”的机会而非主要靠“影响力”。这当然只是一种猜测,却也是阅读过程中积累而成的一点认识。作为一部细节绵密的小说,作者体现出对故事线索的清晰把握,对戏剧性的有效控制。不过,有的情节设制也或可以讨论。作为一部正剧色彩深厚的小说,人物的命运结局应更多体现在必然性上,有的情节表现如李牧原死于车祸,毕竟属于偶然性结局。与李牧原的命运相比,或可找到更具说服力、更能证明其悲剧结局必然性的情节。我的意思是说,对一部正剧来说,偶然性与小说故事之间,还是有重要程度区别的。李牧原是这部小说里除了两个叙述人之外被描写笔墨最多、最具故事性且影响了所有与之相关人物命运的角色,他的命运结局极具打击力度。“有人在死,有人在生,我们在生死的隔壁玩耍。床上躺着的那个人,不在生里,不在死里,他在生死之外望着我们。他的充满孩子气的目光犹如某种永恒之物,穿过生死无常照射过来。我们被他笼罩着,与人世隔绝起来,连最细小的时间也进不来。”小说如此透彻地描写了程守义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同样愿意看到其他人物具有相同的不可脱离性。
一个小说家,特别是年轻的小说家,一旦获得相应的名声后,往往会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而创作着渐趋简单化的小说。不要说怀着强烈的美学抱负去努力写出进入小说史的小说了,连稍微复杂一点的故事也疏于编织。张悦然的《茧》是一部认真之书,是一个不厌其烦做抽丝剥茧之繁复工作的漫长过程,是对历史、现实,成长、人生,亲情、爱情,道德、伦理的一次深刻探究之旅,是在艺术表达上力求寻找新意和独特性,为了“抵达更深的生命层次”(作者《后记》言)的一次全力冲击。去创造只有小说才能表现的世界,执着于只有文学才可以挖掘到的人生意义,这正是当代小说家特别需要表现出来的创作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