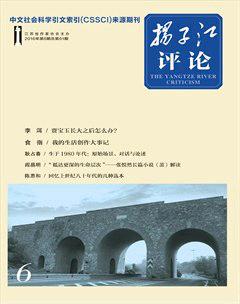交通意象转型与台北文化风格的变迁
林强
近二三十年来,乘坐地铁已渐成为中国一二线城市市民常态化出行方式。随着都市化步伐的快速推进,更多二三线城市也将进入拥有地铁的城市名单中。都市交通系统的快速更替升级,似乎是解决大中型城市交通瓶颈的大趋势。然而,日夜穿梭在地铁中,市民们感知城市景观、体验城市的方式与内容已悄然发生变化。都市新人类无法想象工业城市时期城市内部铁道旅行将是何种景象。唯有中老年人还能依稀辨识昔日的城市铁轨遗迹、沿途的城市意象以及彼时的诸种体验。在个人的怀想和文学的书写中,工业城市的乡愁氤氲生成。因此,我们有理由从纪实性的散文文本中梳理出从工业城市的铁路到后工业城市的地铁这一城市交通空间意象的变迁,提炼出世代居民感知体验的结构性变化,建构一种属于铁道与地铁的城市空间诗学。台北,作为东亚华文城市的先进者,城市交通系统的更替略早于北京、上海,其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现代—后现代都市景观也颇具典型性。本文即以台北的铁道—捷运空间转型为考察对象,意在勾勒台北居民城市体验与台北城市文化风格的转型,也想以此与东亚几大华文城市空间诗学研究展开对话。
一、中华路铁路:边界及其空间缝合
1949年年中,大陆来台民众渐增,街上摊贩明显增多,台北市政府为减少路上摊贩,委托台北市警民协会在中华路铁路东侧兴建两列用竹篾搭建每个约四公尺见方、没有墙壁的摊棚,全长约六百五十公尺,收容摊贩并由警民协会管理。1949年底,国民党撤退去台,大陆赴台民众激增,造成严重的居住问题,原来摊棚遂被加筑墙壁并向前后扩大作为居所。同时又在中华路铁路西侧增建第三列临时建筑,各列又向南延展,总长度达一千两百公尺。这些临时建筑都是不规则的、临时以木板和竹料陆续添搭的,区域内横巷交错,呈现十分强烈的暂时蜗居性质,它们围着铁道兴建,为50年代搭火车进城的旅客建构了独特意象。在短时间内繁衍起来的中华路棚屋成为台北都市中以货物低廉著称的地方,各类日用品至古董书画都有,而最著名的则是它的各省饭馆。中华路的吃食、逛店购物和西门町看电影,成了当时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消遣a。
以上文字虽呈现出50年代台北的都市状况,但作家的书写更能表达私人的记忆和体验;只有二者的参证,方能更立体而生动地还原特定时代中华路铁路的空间形态和感觉结构b。丘秀芷在《三线路》一文中就详细还原了中华路铁路及两旁摊棚的空间演变和个体体验。在她的童年记忆中,光复时期西门町没有中华路,也没有中华商场,只有三线路。起初,由于日本人大多被遣返,城中区空房子到处都是,谁先住进去,谁就有居住权。慢慢地,空房子没了,“三线路上铁道旁开始有人搭棚子住。竹子架子,上头搭些木板、铁皮、油纸、水泥纸,像办家家酒,十分‘有趣似的”;继而,铁道旁的竹棚屋愈来愈往小南门延伸,丘秀芷看到棚屋中“很多人家烧煤球、焦炭、生火很难,就把炉子端出屋外生。但下雨天又不能在屋外,只好又放在屋门口。我上学上得早,正好看他们家家户户在生火做饭,这些人好像没我妈妈那么会生火,常熏得一脸乌七抹黑的”c。由于时局不稳,绝望情绪弥漫,中华路铁道上惨剧不断:“日子不好过,有人熬不下去,干脆卧轨自杀,自杀有传染性,民国四十年前后,中华路铁道上常有这种事。夜里有班车,都在半夜自杀。……一两次,碰到那东一条腿,西一个头支离破碎的尸体之后,吓死了!”d丘秀芷以孩童的眼光来看光复初年中华路铁道的众生相,其中既有童趣的细致观察,也有突然直面死亡的恐怖。这些都展现了动荡时局中颠沛流离的底层民众与台北空间的内在关联。台湾光复至50年代,中华路两旁的错杂棚户既是当局的权宜之计,也是底层百姓暂时居所和谋生之地。这种临时性、错杂混乱的空间特征表征出底层民众的苟且偷安、焦虑乃至绝望情绪。
除了临时性的空间特征外,中华路铁道在当时具有很强的通道与边界功能。它是连接台北与中南部市镇的主要通道。中华路沿途的棚屋成为人们搭火车进台北城见到的主要城市意象。对于初次抵达台北的乘客而言,这种视觉景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过了淡水河,再看大到一片违章建筑,夹着西门町的铁路拖曳而来,台北就到了!那时还没建起商场,一片杂乱,一排排竹篱笆贴着铁道,家家烧着煤球,熟悉的煤烟味,混着蒸汽火车的煤烟味飘进窗来,后院晒得衣服似伸手都够得着,火车简直就是擦身而过。”e中华路上的铁轨连接着城里与城外,沟通着乡土与城市。这既是城乡之间通路的连接,也意味着空间的区隔。尽管中华路沿线的摊棚显得错乱逼仄,但这也呈现出城市所特有的繁忙杂乱景象。
城市空间的边界也意味着空间上的某种连接。“1950年代崛起的中华路摊棚以一种临时建筑的空间形式收纳了大量的外省政治移民,并发展成为都市中新兴的带状商业区,在空间区位上,它以一带状空间如拉链般将西门町与城中区接合起来,形成更具中心性的商业街区。”f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华路的这种缝合作用更加明显。
由于中华路两旁的违建越建越长,为了整顿市容,台北市政府拟定中华商场整建计划,于1960年春,将铁路两侧的棚屋全部拆除,在东侧建造全长1171公尺的钢筋水泥三层店铺八栋,自北向南以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命名,计有1644个铺面,中华商场成为台湾最大的百货总汇商场。1969年,中华商场各栋二楼以陆桥相连,1971年更与武昌、汉口和开封等街道的陆桥相连。从衡阳路至汉口街三栋的商场二楼已成为西门町游客必经之道,由是,西门町与城内中央行政区紧密连结在一起。“中华商场具体地连接城中与西门町而成为中心。”g可以说,中华商场的运营,也开启了西门町黄金时代。逯耀东便记录下中华商场兴的繁华景象:“中山堂后向中华路,中华路自中华商场建妥以后,八幢大楼一字排开,从北门到小南门,台北市又出现了一道发光的城墙,各种不同的小百货商店向这里辐辏,各种不同地方风味的餐厅向这里集中,尤其在新生大楼扩建后,楼下的新生大戏院开幕,入夜之后,这一带地方灯火辉煌,人声与过往火车声交织在一起,成为当时台北市最嘈杂也是最有活力的地方,逛罢衡阳街到中华路吃饭,成了台北或外地人到台北休闲的例牌。”h原本杂乱无章的摊棚变成颇具现代商业形态的百货商场,这无疑是台湾当局立足台湾发展经济的一部分计划,同时也表明相对稳定的两岸时局让一度处于不安、焦虑乃至绝望的底层民众重建起稳定的庶民日常生活世界。当时的中华商场甚至成为流行文化的集散地,“喇叭裤、AB裤、迷你裙、鸡窝头,都在这条走廊流动着,美国的嬉皮文化也随着唱片海报与电影流行过来”;新生戏院外的巨幅电影广告看板,就是绘画艺术,“从中华商场这边看过去,那个戏院就是现代文明的最高殿堂,那时的戏院好大,看电影是种文化仪式”i。来自美国的流行文化随着资本流动渗透进中华路的商业形态,无形中塑造了年轻世代追求时尚同时反抗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感觉结构。
中华商场的繁华并没维持多久。1972年,当丘秀芷再到台北时,中华商场又与1951时违建棚屋极为相似。王盛弘初抵台北时,看到的已是“几栋烂房子”的中华商场。中华商场最后的四年时光竟是如此景象:“一栋连着一栋踏着低低高高的阶梯逛去,集邮社、古玩社,公厕终年弥漫尿骚腥臭、地板永远泛潮,旧衣店、成衣店,点心世界旧桌椅上阳光斜斜射来,把锅贴、酸辣汤刚送上桌那一霎映显得云蒸霞蔚,唱片行、电器行,商场后方当当当铁路道口栅栏放下,火车硿咙硿咙驶过,建筑物好似也有了一阵轻颤。”j垂死之际的中华商场,一楼的生意竟然比以前还好,“尤其在它将要拆迁的前夕,挤满了抢着做最后拍卖的摊位,主要仍是衣服、皮鞋、皮包,又是人潮汹涌,好一幅回光返照的景象”k。残破、凋敝以及被拆除前最后的畸形繁华,在在宣告中华商场死亡的命运。出人意料的是,似乎只有当中华商场被彻底拆毁,人们才会重新记起它,甚至才会重新认识它的前世今生:“我才知道它原来是清代的台北城墙,日本人敲去建了铁路,所以两边才那么宽。”l邱秀芷、郭冠英等人的记述生动还原出中华商场的生与死,王盛弘也抓住了中华商场死亡前氤氲而出的怀旧氛围。这种文献式记录必将比建筑物更具生命力,也更能召唤出20世纪50-70年代台北市民隐微而繁复的感觉结构。甚至于,随着建筑物的死亡,早已堙没不闻的历史文献也会随着建筑物倒塌的声音浮出水面,隐隐约约回响着空间、权力和意识形态绾结、更迭的身世。
中华商场兴衰演变史,在见证者的记述中,既是空间的公共历史,也是个人的私密史。从三线道到中华路铁路沿线的摊棚,再到中华商场直至被拆除,个人的感知体验在空间中被塑造,也参与进空间历史演变进程中。世代的感知体验汇聚成特定时空中的感觉结构,表征着那个时代的精神结构和空间结构。在时间长河中,在城与人的磨合建构中,城与人最终涵容成空间—生命共同体。正如雷骧在回首过往时所意识到的:“我成了台北的一部分——而台北却是我生命的全部。”m
如果说,中华路铁轨、中华商场曾经作为城乡的通路、边界和地标,曾经起到区隔和缝合的作用,那么当纵贯线铁道地下化后,作为边界的城市意象已经不存在了。随着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中华路不再是城市地标,它成了城市空间的文化象征。
二、北淡线:梦想通道及失落的乡土世界
日据第二十年,年方十岁的郭雪湖跟随母亲,开始首次的滬尾(即淡水)旅行。他们从双连驿上车,搭乘筑好不久的北淡线铁道。在列车上,母亲提及淡水河口的小镇,特别会说到“大船”及“蛤蜊”。前者包括日本统治者的铁壳右炮艇以及来自“唐山”厦门、福州的大帆船,后者则是全岛知名的滬尾海产。如果说,在郭雪湖的童年世界中,北淡线还充满了国族迷思和乡土眷念;那么,时移世易之后,战后新生代对北淡线和淡水的感知包含更多的童年梦想、异国情调和未来的诗意想象。
一直居住在北淡线铁道旁,北淡线几乎成为林文义生命中不可磨灭的牢固记忆。曾经的北淡线,蓝色的车厢,绿色胶皮的坐椅,稀疏的乘客以及列车长质朴的声音,都在童年记忆中散发出乡愁般的温暖。对于林文义而言,淡水曾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陌生名词,几乎是另一个遥远的世界。十五岁时,他用零用钱买了去淡水的火车票,想象着一场梦幻般的、属于少年的初旅。“淡水很美,去的时候适逢向晚,淡水河口潮涨,许多鱼状的舢板在漫漫的潮水间奋力摇摆,晚霞在逐渐幽暗下来的远天,许多人等着渡轮过河,他们要回到对岸显得荒瘠的八里乡。……十五岁,开始拥有一个永远不渝的恋人,美丽而充满异国之美的淡水镇。一直到现在,这个年过卅的男子依然没有变节。”n到远方的铁路与青少年的梦想相连,淡水镇的异国情调恰恰具备梦幻的颜色。这让林文义产生近乎偏执的眷念和温暖的慰藉。由北淡线勾连起的现实和梦幻空间,竟包含林文义的两种生存姿态:一种是对冷酷现实的抗争与逃离,另一种则是对理想与温情的向往和坚守。因此,虽经过重重的世事变迁,林文义仍时时省思和追溯:“从十五岁到三十岁,荒谬、纯情、痛楚、伤感都已不再有任何的意义;至少,北淡线永远伴随着我期待黎明,黎明里有一个滨海的小镇,是我不渝的眷爱。”o其实,不止是北淡线,伸向远方的铁道永远给人无限的遐思,那是迈向梦想的通道,理想的未来将在铁道的远方展开。作为梦想的大都市台北,同样在铁道的终点处让少年雷骧产生无限遐想p,而彼时火车的缓慢和铁道的漫长均构成对梦想的考验。
然而,在工业化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北淡线的功能意象更为鲜明。作为交通运输线路,北淡线及其各站剥离了梦幻的色彩,大多数时候呈现为百无聊赖的都市交通节点和人群集散地。“北淡线一串六节的火车厢,在过平交道的转弯处缓慢下来,车列向离心的外角倾斜,然后煞停。人群从车门如倾倒出来一般,纷纷落在铁轨和碴石上。这是数十年来北投小站王家庙(现在捷运称‘唭哩岸站)的固定风景,把每日沿中央南路两侧厂家的职工们,运送到此。”q显然,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北淡线缺乏诗意和梦想。被都市生产束缚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往返中早已失去了梦想的能力。唯有游离在都市生产节奏之外的人才会对日常生活中的铁道寄予奇幻感。或者说,在工业化生产之中,铁道已被简化为单一的交通意象。而唯有铁道被淘汰时,它们才会凭借文字回光返照。雷骧对藏青色的柴油车厢、摆着空鱼篓打盹的小贩等旧景物的描写与其说是对工业时代柴油火车的怀旧,毋宁说是对乡土文明的宁静、和谐、温情以及诸氛围的伤悼和召唤。不仅如此,曾经因为火车行驶的缓慢而残存于铁道旁的乡野景致,也会勾起人们对乡土社会的无限留恋。在雷骧的观测中,北淡线的铁轨旁,在一块不及五码的砾石土地上,曾有一位从澎湖来的老人开垦种植天人菊。因为对泥土的不舍和对乡野生活的眷念,不为生计所困的老人固执地置身在想象的都市田野中。这位老人颇可作为城市中最后一名农夫的缩影。
毫无悬念,当1999年淡水线被废弛,那残存的花圃和老人也必然消失在高速运转、毫无人格特征的捷运系统中。“那套新的网路系统,正是要重叠在原来铁道线上的,那种植在窄窄的铁道腹地的天人菊消失了,整个被捷运工程局的钢片围篱包裹起来。照拂它们的那个老人,此刻也许就在对街某一幢公寓的窗口,遥望这些蓝色钢皮。为此,他失去了劳动的愉悦而怔忡罢。”r早在1990年代初,北淡线老站一律要被拆除时,雷骧就一回又一回地守在那儿,试着描绘老站里的空气和气氛。他无奈地看到:“在都会捷运系统的计划里,支线铁道成了重复和多余。事实上,除开列车到站的前后几分钟之外, 北投站早就想撤离废置也似,空寂已成为正常情状。”s乡土世界的气息已经远去,失去功能的北淡线以及旧站最终变成荒芜之地,有待被捷运系统改造。更令人不堪的是,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的竟然变成城市的流浪汉和拾荒者,他们流连于即将被拆除的旧车站里,丝丝缕缕地赓续着只有乡土社会中才会自然流露的温情。雷骧曾在空荡荡的候车室里观察到:“一个头戴斗笠的赤脚大汉,浓黑的眉目,四肢粗长。那样貌,理应在田间忙于农事,但他的褴褛说明了异地的流落,神色也显示与体貌不配称的失绪——正躬身拣拾刚刚离站而去的人抛落在地的烟头儿”t;此时,另外一名拾荒老人竟然慷慨赠烟,这让雷骧莫名感动。拾荒者和流浪汉之间惺惺相惜,正如涸辙之鲋,这是一个世代凋零的悲情。这也恰恰意味着,捷运系统的空间变革,必将催生新的世代及其感觉结构。
三、 捷运系统:后工业社会的都市奇观和心理时空
台北快速都市化,必然促使城市交通更加便捷化和网络化。捷运系统的出现呼应了台北城市国际化的节奏。台北人不得不经历捷运兴建过程中城市交通的堵塞,也受惠于捷运系统完善后生活的便利。而对于作家而言,日常交通的便利化、立体化、高速化,并不仅仅停留在实用层面,他们更在意捷运系统所引发的一系列生活变迁,比如由捷运线串联起来的商圈经济、辐辏的人流、多元文化群落及其内在的关系。他们更在意书写捷运车厢内外、商圈场所中人的感觉方式、行为方式乃至文化模式的嬗变。于是乎,敏锐如雷骧、张维中等便开始对捷运系统及其沿线的社会观察。他们穿梭于台北城的地下和地上,用文字和图画勾勒一个世代的社会风景和时代精神,或者更深入到书写者——旅者的心灵境地。
记录一座城市有多种方法,雷骧的捷运观测及其书写行为却有较清醒的自觉意识。他曾看过一部西方的图绘本,“画家用了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把一座德国城市,从二百年前一个人口稀疏的农业村聚,一步步形成都市的流变过程,写实的呈现出来——以固定的一个角度,同一个空间视野,描画它在不同时代下的样貌。读者从村集形式到目前的都市商业街之间,比较出时代演替的意义”u。也许是受此影响,雷骧“仿佛肩负这一类市街演化论的图鉴使命,我踟蹰游走,以一己的图录方法描记它们。”
(一)自动化、非人格化与新技术奇观:捷运系统景观特质
捷运成为台北市内交通的主要工具,这不仅意味着台北市内交通系统和交通景观体系的更新换代,也意味着市民在行走过程中感知内容和感知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此前的铁路,虽然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但它毕竟还具备鲜明的人的特质——诸如开火车的人、列车乘务员以及较慢的行驶速度;而到了捷运系统,除了将此前的铁轨拆除另建高架铁轨、开掘地下轨道之外,也将人的因素消除于无形。铁轨设备的更替必然引发都市人新的乡愁,即对工业时代遗迹的怀想;而电气化时代高科技的全面盘踞、人的因素被抹除无痕,也将产生新的疏离感和荒原感。此二者均在雷骧的观测中被精准捕捉。“我犹记支线废驶之后尚未拆除时,钢轨红锈厚结,灰绿色的劲草瞬间即从碴石缝中攀上钢轨,或有力的伸向四方,这一种停驶即变成废迹的景象,予人强烈毁杇的印象。”v工业时代的铁轨一遭荒弃便如遗迹。北淡线曾经是林文义通向未来、异域的梦想之旅,如今难觅踪影,这也意味着对工业时代的乡愁只有在物象和感知的双重消亡之时才会被召唤出来。而后工业社会的感觉结构也随之呼之欲出。可见,感知形式、感知内容的内在更迭,恰如生命形态的此起彼伏,代代相传以及变异,在不断怀想、遗忘乃至排除中生成、演绎出新的感觉结构。
捷运木栅线是台北市最早通车的一条线。这条线势必给刚开始体验捷运线的乘客带来新鲜感和刺激感。捷运木栅线的转弯设计便十分离奇,“自‘科技大楼站往前,几乎是一个九十度的大转弯,(车速此时‘自动降到5k/h),接着在‘六张犁停靠,起步后又是一个相反四十五度大转弯,然后等到直道时,又几近‘飞驰的速度轰然钻进往‘辛亥站的长长隧道里”w。速度的骤然变化、路线的大幅度转折以及高度的巨大落差,给初乘者的视觉和身心构成极大挑战。在自动化的技术控制之下,捷运木栅线展现出新时代的交通奇观。此外,捷运系统高度统一的空间美学设计,又构成新的交通景观体系,这最终会内化进市民新的审美评价标准和身体—空间感知模式中。而捷运站上,“不过三、五分钟,哗啦,哗啦的,长条银梭般的列车驶来煞停,旋即驶离,像似什么兽类,快速的舔吸一过,月台便空无人迹”x,这倏忽即来倏忽即去的捷运以及空荡荡的月台,又会产生新的陌生化、荒原化体验。这与林文义笔下充满温馨的童年记忆、充满理想化幻梦感的铁道旅行体验,有着明显差异。信息化时代高科技的物质文明已然实质性楔入世代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孕育着新型感觉结构。历史经验表明,新形态物质文明的出现在引起陌生感乃至恐惧感之时也将带来新鲜感和奇幻感;而当它变得司空见惯时,新技术文明又会制造出新的奇观。特别是进入现代—后现代文明之后,这种视觉—心理上的奇幻感更替得尤为快速。
通过文字与绘画,雷骧成为捷运系统这一景观美学的阐释者。可见,文学艺术乃至商业文化(如广告、影视等)、通俗文化共同塑造了新的美学原则和感觉结构。或者说,捷运系统只是后工业社会的通道形式,其他如消费空间(大型商场百货、酒店、展览会等)、网络空间等早已让消费社会的感觉结构粉墨登场。就捷运系统而言,非人格化的美学特质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已充分展示在雷骧描绘捷运月台的画作中。诸如人的消失或渺小化、星空和天际线的凸显以及高架铁轨流畅的线条,均缘于捷运月台被高大水泥柱高高擎起。这也意味着从高处观看到的世界,少了些人情味,多了些冷漠。“远远近近十分美丽”的捷运月台夜景最显著的特质就是无人化和非人化。
另外,捷运以及高度发达的都市工程也彻底改变了地方的景观与风格。比如,士林一带曾是雷骧年轻时熟悉的地方。那时的士林仍是“独立镇街性格”,闽式二楼连排的铺面和民居组成类似大陆闽南内地的村镇;而在都市规划、资本运作等诸种机制的合谋中,如今闻名遐迩的士林夜市,已然成一消费奇观,人潮摩肩接踵。可以说,捷运系统的开通与连接,在人潮、物资的输送和消费时尚信息交流方面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在快速流动中,都市人更易产生不确定性和疏离感。
(二)流动性、拼贴与分裂:捷运系统的心理时空
高速化的捷运系统将台北各商圈以及中途各站网络化,人们只要用比以往坐公交车甚至小车更短的时间就能到达城市各个角落。便捷化、高速化的捷运系统一方面固然拉近了市民之间的空间距离;但另一方面,空间障碍被消除之后,城市景观变成片段化或者点状化,捷运线路沿途的景观印象日益模糊不清或者支离破碎;更具意味的是,人潮加速流动后,人与人的关系愈加流动不居,人人变成孤岛,人群变成非人格化和类型化,个体心理深度逐渐消失或者愈加碎片化在快速运转的捷运线路和无数个相同形制的车厢分身中。以此来看雷骧的《捷运观测》,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由捷运带出来的城市景观和人物,多呈现出印象式的浮世绘,不仅人物个体心理深度消失或者碎片化,城市空间统一性的景深也消失了;流动性、临时性、碎片化、平面化乃至假象化变成雷骧笔下意象(人物、空间、景观)的主要特征;雷骧书写和摹画的策略也有意无意地表现为拼贴和蒙太奇。这不能不说是后现代都市风格审美特质的具体展现。
在《捷运观测》中,举凡盛极而衰的面线摊、带着重度灼伤面具假借“爱心艺人”名义的乞讨者、剪艺者、贩售泡泡枪的少年摊贩……都在雷骧的行旅书写和摹画中被快速勾勒。他们没有前世今生,有的只是暂时性地辐辏与展示。捷运车站里,人潮短暂的汇聚与流散,说明了都市中人与人关系的流动性、不稳定性和陌生化,而这种都市关系和情感状况无疑是建立在诸如捷运系统之类的都市基础设施之上。追求更快速、更高效的都市工程必然改变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和感觉结构。另一方面,流动着的都市人潮和在车厢中暂时定格的人群,面目也变得类型化而非人格化。当雷骧在捷运车站观察候车的人群时,他不是近距离地读出候车人的脸部表情,而是从整体上描摹候车人大体相同的肢体动作,并把他们诠释为“候车人们”或“群体的孤独”,这种整体观察的眼光正如“我们从不分辨此一批蚁,与若干年所见的另一批蚁有何不同;这一群雀,与别一群雀有何不同,总以等一距离观看而无从感触‘身受的体察”y。冷漠化或神性的观察视角恰恰说明偶然聚集的人群类型化和非人格化特征。
在现代—后现代都市中,人已成为一座座漂浮的孤岛,他们彼此之间似无连接,心理深度或者分裂状态似乎也消失在人潮汹涌的现实水平面之下。因此,雷骧用浮世绘的方法成功地捕捉到了台北人的精神—心理肖像。在诸如《穿越时空》 《足印》 《浮世》等篇中,雷骧勾绘出了捷运车厢内外并置而不无矛盾分歧的时空、荒诞的都市情境和分裂的心理时空与颠倒的精神世界……凡此种种,与林文义、雷骧笔下那曾经温情脉脉的北淡线人情世界相比,都表明了后现代都市感觉结构的典型特征。显然,后者以一种逆向的单线时间统一了北淡线的乡土特性和情感空间,而前者则采取多元并置、共时、分裂、颠倒的方式呈现出后现代都市精神状况。
在《穿越时空》一文中,雷骧观察并临摹了一张海报:“画面看到两巨列公众交通工具:蒸汽火车在左、捷运电联车在右,同时从背景的古城门洞穿前而来。”因要凸显的主题是“穿越时间100年”,故而海报将“百年前刘铭传时代购入的蒸汽火车,与前几年购入的捷运电车行驶,同一时从更古老的公共建物前贯穿”。雷骧意识到这张海报是由三张来源不一的图片——北门城、老火车、捷运列车——经由电脑绘图合而为一。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时间的穿越、空间的并置、电脑科技的拼贴诸种元素被整合进一张海报中,整张海报以不无违悖社会现实(蒸汽火车早已淘汰)和空间规制(北门城无法容纳捷运电车更遑论同时容纳电车和蒸汽机车)的奇幻方式被呈现出来。仅仅就这张普通的海报(甚至无需考虑它的经典性意义),我们就已把握住后现代状况下已然无处不在的都市拼贴审美特质。
正如捷运系统已经将台北城网络化一样,后现代状况已经悄然改变每一个都市人的心灵世界。在《足印》中,雷骧以近乎小说虚构的笔法描绘了这般场景:一位女子深夜在空荡荡的地下捷运月台候车,月台上的黄色警戒线以及警戒线内那一对用油漆涂画出来的小小足印子引起她的联想,她“总觉得那双小足印像某些凶案留下的血迹——尤其与那隔离效果的黄色带状在一起的时候,仿佛尸体倾间才被移去……”z由此,女子想起若干年前自己写给某男子的信:“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是杀死你!然后再杀死我自己。”这是出于彼时为恋情所苦无法自拔的绝望手笔。然而,时过境迁之后,那酷烈的心态竟有些荒谬。此时,“从遥远的黑洞里射出列车头的强烈光柱两条,接着轰隆的声音将她略有不悦的联想,彻底的掩盖过去”,门启处,正对着那双小小的血足印。雷骧对女子内心世界的想象一反此前浮世绘的无心理深度的肖像描摹与勾画。他通过深度的内心展示,勾连出女子内心深处存在过的杀人念头。杀人念头,只不过是一种象征化的表达,它代表深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最疯狂的想法和心理状态。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诸种疯狂念头虽然不断生成,但总会在倏忽之间被压抑到无意识深处直至被永久禁锢。因此,当捷运列车从黑暗中射出光柱奔腾而至且门启处正是那双血足印时,这就意味着那是一辆开往无意识深处内心罪证的列车,每个人皆可以对号入座。捷运月台上女子的浮想联翩,实际上是其内心世界分裂状态的展示,这种分裂普遍存在于都市中每一位乘客的心灵中。只不过,随着呼啸来去的捷运列车,这种不断被勾连起来、又不断被驱散或压抑下去的想法正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常态。
在《浮世》中,雷骧更是在捷运月台中揭示出颇具象征性的感觉结构类型。当雷骧站在电扶梯顶端勾头下望,他看见“逐级静立的男女老少的头顶,在画面的远近法中上升、变大”;由此,雷骧想象天堂司阍者与之近似的日常所见:“纯净质轻而羽化的形体,在人间获得歇息之后,灵魂浮升上来,它,正接待着哩。”@7死亡之后,灵魂脱离形体飞升到天堂,竟然与电扶梯不断向上输送人体的过程有些相似,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叹雷骧不无奇诡的想象力。而更令人震惊的是,雷骧由此想起自己曾从相反的角度描摹过医院电扶梯的场景:“一所巨型医院的门厅,宽阔的电扶梯分作并行的两行,把前来就诊的歪倒人形,缓缓提升到极高的顶端;而另外一列,则是毫无希望的、沉重的人们,又慢慢滑坠下来。这些抱病者的身形是欲望累积的罪躯,在死亡之门前,在浩大的医院门厅,构画出人间的‘地狱变图。”@8对医院电扶梯自下而上的观望与想象,勾画出的是欲望累积的病罪之躯坠落地狱的图景,这无疑是对捷运月台电扶梯天堂想象的颠覆;但这两种图景确然构成对电扶梯想象的两极。或者说,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刻都在两极的路途中上升或者坠落,只不过无法如雷骧般警觉而已。电扶梯隐藏着天堂—人世—地狱的两极世界,这是人类生活状态—精神状态的结构性描画。可以说,凭借着捷运月台上自动化的电扶梯这一物质构件,雷骧成功揭示了人类感觉结构的两极及其过程,即下坠与超升以及循环往复。
四、结语
从中华路铁路、北淡线再到捷运,我们见证了台北交通干线空间意象及其功能的结构性转换,那就是从工业城市交通动脉的通道、边界意象与空间缝合的功能到后工业城市网络化、自动化、非人格化空间奇观的呈现。随着城市交通空间的结构性转型,世代居民的感觉结构也由动荡时期的绝望、偏安一隅时的世俗化追求和以流行时尚的追逐反抗威权社会,一变为对日渐远去的工业时代铁道及其乡土温情的追怀,再变为碎片化、拼贴的、分裂的后现代心理时空。换句话说,每一个时代的城市空间结构与意识形态彼此涵容,它们共同孕育出类型清晰又彼此承续的感觉结构类型与城市文化风格。
【注释】
afg曾旭正:《战后台北的都市过程与都市意识形构之研究》,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199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1-143、141-143、152页。
b本文借用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感觉结构”概念。所谓“感觉结构”即指“一个时期的文化”,“整个生活方式”,一种生活的特殊感觉。它“不是与思想相对立的感觉,而是感觉过的思想和思想过的感觉,是一种当下的实际意识,处在鲜活的相互关联的连续体之中”。也就是说,感觉结构可以用来描述特定时期人们对生活的普遍感受,它包含时人共有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它还具有突出的潜意识特征,即人们认知世界常常是通过经验世界而不仅仅是理性意识,这些都鲜明地表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可见,感觉结构能够较有效地分析长时段中社会群体的感觉、心理、价值观和审美经验,也有利于分析人们从乡土到都市社会转型过程中获得的社会体验。参见Williams, Raymond, The Long Revolution, Greenwood Press, 1975, p.48.以及Williams, Raymond,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p.132.
cdehijl 人间副刊策划主编:《回到中山堂——延平南路98号和周遭生活圈的故事》,台北:台北市文化局2002年版,第128-130、131、122、64、124、124-126、123页。
mpqrstuvwxyz@7@8雷骧:《捷运观测》,二鱼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82、180-181、51、53、56、57、48、4-5、16、4-5、104、98、100、100页。
k王盛弘:《十三座城市》,龙门书局2011年版,第113页。
no林文义:《北淡线铁道》(原载《联副》1984年3月23日),《寂静的航道》,九歌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