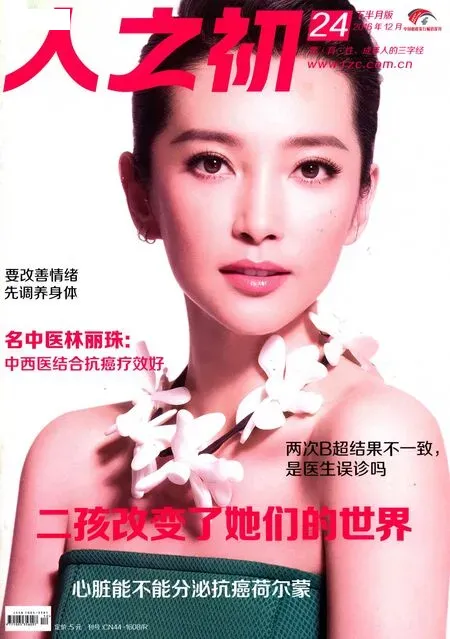促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能提升的财税政策研究
闫 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 北京 100072)于树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28)
促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能提升的财税政策研究
闫 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 北京 100072)
于树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28)
2016年第三季度,世界经济依旧低增长,通过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结构性改革进展的评估发现: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着结构性改革乏力问题,这是世界经济未能摆脱低增长困境的主要原因。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初见成效,但也遭遇较大瓶颈。要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能,需要在全面梳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含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找准“痛点”发力。“痛点”最终落在产业结构上,既要弥补服务业的先天不足,又要推动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在财政运行呈现若干结构性特征、财政资源相对不足的前提下,可着力打造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四新”,形成新动力推动经济增长。
世界经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财政政策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已过去八年,低增长的阴云始终伴随着世界经济缓慢前行,而且短期内丝毫看不到“拨云见日”的迹象。尽管各国仍是一片忙碌:政策不断放宽的同时,要不断处理短期政策长期化所带来的风险,但是市场反应依旧低迷,大宗商品价格依旧不振,贸易增长依旧缓慢甚至收缩,负债率依旧节节攀升,经济保持低速增长水平,权威机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屡次调低。从经济增长周期的角度难以解释本轮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增长的现实,基于此,我们尝试从结构性改革的角度进行解释,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做出全球经济结构性改革乏力的判断。
一、全球经济结构性改革乏力
(一)美国向实体经济回归的结构性改革未见实质性成效
美国的结构性改革走的是一条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之路,先后实施了“再工业化战略”、“出口倍增计划”、“新能源战略”、“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战略”等结构性改革,通过振兴制造业、出口、公共基础设施等行业来带动需求,通过发展新能源等渠道来改善供给,进而实现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时至今日,如果对其改革成效进行评估,结论是未见实质性成效。
从宏观经济数据看,在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2016年美国一季度GDP增速为1.4%,二季度跌至0.8%。三季度美国的制造业、服务业相关指标向好,失业率虽从8月的4.9%升至9月的5%,非农业就业数据连续三个月放缓,但失业率已达充分就业水平,且就业参与率正在提高。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初次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美国实际GDP按年率计算增长2.9%,较前一季度1.4%的增速有大幅提高。宏观经济较好的表现令加息预期进一步上升。
然而,在数据背后,还需要看到: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填补的,产业升级、创新较慢且与其匹配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缺乏,生产效率难以提升,尤其是在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下,企业盈利和市场活力仍然不足,致使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此外,美国的财政状况堪忧,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30日的2016财年内,美国预算赤字较上财年增长34%,占GDP的比例从2.5%上升至3.2%。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美国财政赤字将会长期持续增长,美国政府为此必须发行更多国债,预计2016年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升至76.6%,而到2026年这一比重将攀升至85.5%。未来如果财政状况持续变差,财政政策将会收紧,经济复苏的前景将更加不容乐观。如此,我们认为,美国的结构性改革收效甚微。
(二)欧元区基于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改革走偏
欧元区面临着较多的结构性问题,分散在生产要素、机构设立、成员构成、宏观政策等层面,但对经济复苏影响最大的结构性问题则是劳动力结构失衡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劳动力结构失衡与老龄化和高企的社会福利有关。老龄化的劳动力结构与新经济形态下的生产技术和组织形式不匹配,对经济复苏形成严重阻碍。据IMF测算,1987-2014年间,老龄化导致欧元区全要素生产率年均下降0.1个百分点,而在2015-2035年期间这一作用将倍增。由于欧元区的社会福利水平较高,企业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在经济低迷、企业利润难以保障的前提下,会减少劳动力雇佣,难以形成充分就业,进而影响经济复苏。
改革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取得理想的成效,可是欧元区的结构性改革并没有专门针对劳动力结构优化,而是寄希望于负利率、大规模举债等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出预期的结构调整效能。不可否认,如果这些扩张性货币政策退出,欧元区的经济复苏定将止步不前,但单纯的货币政策施力,效果如何呢?
2016年三季度欧元区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其经济景气指数上升,工业产出增速止跌回升,制造业扩张势头明显,服务业扩张虽然放缓带来综合PMI下降但仍处于扩张区间,物价回升,就业市场继续回暖,贸易状况改善,主要经济体数据均向好。但要看到,10月份欧元区CPI年率初值仅增长0.5%,这已是创下两年多来的高位,目前欧洲央行已动用逾1万亿美元购买债券,以提振通货膨胀率,但结果距2%的目标值还差距甚远。还要看到,8月失业率为2011年7月份以来的最低值,但仍高达10.1%,青年人失业率大幅下降,仍高达18.6%。而且,英国脱欧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速放缓还没有显现。然而,即便三季度多项指标向好,但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环比增速并没有提升,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同比增速与上季度持平,仅为1.6%,环比增速也与上季度持平,仅为0.3%,较一季度的0.6%进一步降低。欧洲央行执委默施认为,欧元区经济在第三季度失去部分动能,经济预期依旧面临下行的风险。可见,欧元区旨在发挥结构调整作用的货币政策几近失灵,其结构性改革彻底走偏。
(三)日本“安倍经济学”舍本逐末致结构性改革被忽视
日本以“安倍经济学”为基础射出的“三支利箭”,即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刺激计划和结构性改革,至今已实施近四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失业率一度下降,物价一度上涨,企业业绩一度好转,经济一度出现回暖迹象。但是由于“三支箭”存在着受重视程度的差别,其出场次序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可被概括为“量化宽松辅以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置于辅助地位的结构性改革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因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那么前两支箭射出的效果如何呢?
日本央行为了抑制通缩进一步恶化,于2016年1月首次实行“负利率”政策,这是在量化宽松的基础上通过利率工具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但结果是物价持续低迷,9月日本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5%,已连续7个月呈现负增长,且消费意愿降低,两人以上家庭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1%,与此同时,外贸再次出现逆差,民间投资有所下降,经济整体表现欠佳。导致这种状况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财政刺激计划衍生的巨额国债负担,政府为防止财政陷入危机而调高消费税率,打击了消费,进而打击了脆弱的经济复苏。目前,日本除了在促进企业重组、改革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有一定进展外,应对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能源领域的结构性改革措施等均没有出台。
(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经济结构优化为主题的结构性改革仍然“在路上”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结构普遍单一,在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经济高速增长必然无法支撑太久,已日渐进入经济下行区间。而减慢直至刹住下行势头的惟一方法就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采取行动。
从实践看,俄罗斯开启了结构性改革的新阶段,立足于实现进口替代的主要任务,重视科技发展,创立“超前发展区”。二季度数据显示,俄罗斯经济衰退形势有所好转,失业率始终保持较低水平,贸易形势和财政形势改观。印度经济仍显颓势,对外贸易虽出现了企稳迹象,但工业生产持续下滑,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其结构性问题表现在制造业产能过剩、银行惜贷、民营企业投资乏力。巴西经济继续衰退,但呈现触底回升的态势,目前工业生产不断改善,对外贸易呈现企稳迹象,通胀压力下降,货币政策放松,为走出经济衰退而努力。韩国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三季度仅因住宅投资增长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但汽车、钢铁、电子等制造业不景气,出口萎缩,失业增加,结构性矛盾突出。新加坡三季度经济显著放缓,制造业、服务业双萎缩,贸易下滑。马来西亚内需增长强劲,但出口大幅缩减,制造业萎缩、工业生产下降等因素影响经济复苏。泰国经济总体呈现逐渐复苏态势,旅游业持续增长,政府支出持续增长,但工业不振,出口疲弱。越南经济下行、出口增速放缓、财政不平衡加剧且面临呆账问题。
我国率先确立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题,并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项任务紧锣密鼓地展开行动,但是在经济新常态的总体环境中,改革能否真正发挥效力,让经济增长稳定在既定区间,以顺利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还需要把握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在长期战略和短期策略上做出更加明确、可行的安排。从目前来看,我国已经量身设计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问题主要表现在改革的任务重、阻力大、可动用的资源少,缺少统筹考虑之下重点突出的行动指南。
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显成效
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与前两个季度持平,虽然增速较2015年同期的6.9%回落0.2个百分点,但仍处于7%左右的合理区间。经济增速稳步回落体现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供给和需求结构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优化,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结构)也得到升级和优化。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实效,需求结构进一步改善
从供给侧看,“三去一降一补”的结构性改革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在去产能方面,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任务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三季度原煤产量同比下降10.5%,年底前有望完成压减粗钢产能4 5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2.5亿吨以上的全年目标。在去库存方面,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下降1.6%,自4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下降;商品房待售面积自3月份以来连续7个月减少。在去杠杆方面,8月末,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4%,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在降成本方面,1-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87元,比上年同期减少0.17元。在补短板方面,前三季度,节能降耗成效突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2%。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水利管理业、农林牧渔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3.4%、20.5%和20.1%,分别快于全部投资35.2个百分点、12.3个百分点和11.9个百分点。
从需求侧看,投资、消费、净出口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6.8%、71%、-7.8%,其中消费的贡献继续扩大,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3.3个百分点,表明需求结构进一步改善。在经济回暖和政府政策支持下,民间投资活力呈现企稳回升态势,2016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2.5%,比1-8月加快了0.4个百分点,其中9月增长4.5%,比上月提高2.2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季度环比回落0.3个百分点,比1-8月加快0.4个百分点,主要是部分一线和二线城市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对房地产过度投资有所抑制。
相对而言,房地产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大,2016年前三季度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6.9%,虽较上半年回落一个百分点,但仍然是支撑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据测算,三季度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8%,与房地产相关的消费持续上升。此外,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明显,前三季度文化、教育、养老、健康、保健等产品的消费持续上升;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为19.3%,比上年同期提高1.7个百分点;符合消费升级发展方向的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光纤、光缆、智能手机、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SUV、新能源汽车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了较高增速。
前三季度,外需形势有所改善,进口和出口同比降幅分别收窄2.4个百分点和1.1个百分点。从结构看,货物贸易继续保持顺差,服务贸易逆差,一般贸易进出口、机电产品出口、民营企业出口在出口总额中占据优势。
(二)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工业结构继续优化
前三季度,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分别为7.7%、39.5%、52.8%,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回落0.3个百分点、回落1.1个百分点、上升1.6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分别为3.5%、6.1%、7.6%,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回落0.3个百分点、上升0.1个百分点、回落0.8个百分点。可见,产业结构继续升级,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加速上升。
前三季度我国工业结构继续优化。其中,制造业增长最快,且加速向中高端迈进,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6%)高4.6个百分点和3.1个百分点,占比分别提高0.6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企业的利润也明显向好,1-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4%,其中,8月增长19.5%。
此外,新经济业态快速成长。前三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0.8%,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4.8个百分点。
(三)贷款结构优化,人民币国际化提升金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
一是贷款结构向实体经济倾斜。9月金融机构新增贷款总额1.22万亿元,同比多增1 700亿元,环比多增2 713亿元,而贷款结构优化体现在企业贷款达2016年4月以来最高值,几乎与居民贷款平分秋色,且企业新增中长期贷款创二季度以来新高,是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相应地,居民贷款的占比下降,主要体现在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占居民贷款主体的房贷显著下滑。9月新增社会融资总量达1.72万亿元,同比多增3 910亿元,环比多增2 503亿元,其中对实体贷款新增1.27万亿元,环比多增4 704亿元,是新增社会融资持续回升的主要原因。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步入新阶段。人民币在10月1日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SDR),但随后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上升和英镑暴跌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市场担忧度陡然增大。但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人民币供求关系的改善,汇率与我国经济基本面关系将进一步协调,进而有力推动内外均衡、需求和供给共同发展,并成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工具。
(四)物价涨势总体温和,就业形势良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还体现在稳定物价涨势方面。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0%,比上半年稍微回落了0.1个百分点,9月份同比上涨1.9%,环比上涨0.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9%,降幅比上半年收窄1.0个百分点,9月份同比上涨0.1%,结束了同比连续54个月下降的态势,环比上涨0.5%。物价形势的向好体现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出改善市场供求的作用,尤其是通过去产能改善了工业领域的供求关系,进而使得工业产品的价格上涨,企业效益明显好转,企业信心得到增强,制造业PMI指数连续两个月为50.4%,显示制造业正在扩张,其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增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稳定就业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通过去产能促成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流动而间接影响就业。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 067万人,提前完成了全年1 000万人的目标任务。三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4%,低于4.5%的年度调控目标。良好的就业形势带来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8.4%,实际增长6.3%;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5 626元,同比名义增长8.1%。城乡差距继续缩小,前三季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2.82,比上年同期缩小0.01。
三、我国财政运行呈现若干结构性特征
2016年1-9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 400亿元,同比增长5.9%;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9 777亿元,同比增长11.3%。两项合计的全国财政收入突破15万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5 956亿元,同比增长12.5%;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8 121亿元,同比增长7%。
前三季度我国财政运行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回落,政府性基金收入保持加速增长态势。
前三季度,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速出现了自2015年一季度以来的首次回落,稳定回暖趋势被迫终止,增速较上季度增速降低1.2个百分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累计增速仍保持了2016年一季度以来的跨越式增长趋势,跃升至11.3%,增速进一步加快,且超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速的幅度从二季度的0.4个百分点拉大到5.4个百分点。由于作为财政收入主体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下滑,财政收入增速与GDP增速的一致性发生了改变,说明我国经济平稳增长的背后存在隐忧。实现稳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的压力仍然很大。
第二, 央地收入格局调整,央地收入增速差距减小。
在前三季度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的占比分别为45%和55%,较上半年的43.5%和56.5%的格局有所调整,中央收入占比上升,地方收入占比下降,调整幅度为1.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共享税增长较快,而共享税中中央份额较大。从增速来看,前三季度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的同比增速分别为4.4%和7.2%,地方收入增速仍然快于中央收入增速,但相比上半年增速,中央收入增速提高1.1个百分点,地方收入增速回落2.9个百分点,回落幅度较大,二者之间的差距缩小。
前三季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中,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的占比分别为11%和89%,与上季度相比格局未变。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加速增长(同比增长14%)的带动下,地方收入虽仍然保持领跑态势,但中央收入增速与其的差距进一步减小。
第三, 营改增减税降负效应进一步显现,房地产交易活跃带来相关税收进一步增长。
受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的影响,原营业税的纳税人改缴纳增值税,国内增值税和营业税继续保持此消彼长的增长态势:前三季度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23.8%(如果排除营改增试点带来的增收部分,国内增值税仅增长2.7%),营业税同比下降20.4%。
除了增值税和营业税之间的结构性变动外,营改增改革试点的全面推开还带来整体的减税降负效应。将改征增值税与营业税合并计算后,体现出逐月、逐季下降的趋势:7、8、9月分别同比下降10.9%、17.6%、21.3%;1-9月累计增长11.4%,增幅较上半年降低12.8个百分点。而从税收收入总体来看,1-9月累计,税收收入100 881亿元,同比增长6.6%,增速较上季度回落2个百分点。其中,9月税收收入8 243亿元,同比下降0.7%,税收出现负增长,说明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的政策性减收效应进一步显现。
此外,前三季度税收增收因素还有房地产交易活跃带来相关税收进一步增长。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8.3%,主要受房地产企业所得税增长25.4%带动;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17%,主要受二手房交易活跃等带动;财产转让所得税增长27.2%,契税同比增长11.7%,土地增值税同比增长13.7%,均受部分地区商品房销售较快增长带动;国内消费税仅同比增长0.4%,主要受产销量下降影响,卷烟和成品油消费税减收较多;出口退税同比下降10.8%,主要是2015年同期退税进度较快,基数较高;城市维护建设税同比增长5.2%;房产税同比增长4.9%;城镇土地使用税同比增长3.4%;车船税、船舶吨税、烟叶税等税收收入同比增长9.3%。但与上半年相比,上述税收收入增速普遍下滑。
前三季度税收减收因素有:车辆购置税同比下降10.8%,主要受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政策性翘尾减收的影响;印花税同比下降35.7%,主要是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下降49.7%影响;资源税同比下降15.8%;耕地占用税同比下降0.2%。
第四,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逐季回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跨越式增长。
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分别增长15.4%、15.1%、12.5%,增速呈现逐季回落态势,且回落速度加快。前三季度支出进度为年初预算的75.2%,略超过序时进度(75%)0.2个百分点。
与上半年相比,教育、社保和城乡社区支出等重大民生支出仍位于支出规模的前列。但增长速度最快的仍然是债务付息支出,支出金额3 649亿元,仅第三季度即增长1 302亿元,同比增长41.1%,季度环比增长55.5%。其规模也已超过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直追科技支出。可见,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规模,债务付息支出带来的支出压力和风险日益增大。除此之外,大部分支出增速较上半年回落,且教育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回落幅度较大。
前三季度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走出了负增长的低谷,不但延续了自2015年二季度以来增速逐季增长的态势,并且同比增速跨越式增长至7%。这一结果仍主要是地方支出的贡献,1-9月中央支出同比下降15.6%,地方支出同比增长8.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同比增长8.2%。
四、促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能提升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难题
在去产能方面,僵尸企业成为阻碍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绊脚石。处理僵尸企业涉及大量的人员安置、巨额的债务负担、过于复杂的权责关系等,处理过程中可能会威胁地方经济、金融系统、社会稳定。因此,地方政府帮助僵尸企业在金融机构融资,令其僵而不死,将“崩盘”风险尽可能地后移。
在去库存方面,由于库存大的原因是供给远大于需求,在这一前提下,从销售力度和营销手段上做不出去库存的文章来,只有找到新的市场需求才能实现,这就是难点所在。以房地产业为例,其去库存的压力在三四线城市,而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需求早已饱和,新的市场需求实难以形成。
在去杠杆方面,我国面临着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资金大量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而虚拟经济恰是杠杆累积的温床。此外,2015年设立的专项建设基金在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是快速形成新杠杆的渠道。据测算,专项建设基金可撬动4倍以上的投资,而被撬动的投资多来自银行贷款,再加上专项建设基金的体量大、投放快,杠杆效应不容小觑。
在降成本方面,企业成本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9月份的CPI和PPI的走势很大程度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即企业成本提高使然。此外,劳动力成本是企业面临的刚性增加的成本,因为受到老龄化、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收窄等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和结构制约,难以降下来。再从税费成本来看,在撤除“保持宏观税负稳定”的前提条件后,我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政资金就可能不充足,有可能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减缓。
在补短板方面,需要真金白银,但在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收入不可能像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那样充足,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框架下,难以加大增收力度。因此,在财政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只能进行以资源配置为导向的结构性调整,结果很可能是这块短板补齐了,原来的长板变短了。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找准“痛点”发力
考虑到上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均面临难题,我们的财政资源又相对不足,那么,要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能,就要找准“痛点”发力,先治“最要命的病”。这样,问题就转化为寻找“痛点”。首先让我们再重新梳理一下其中的逻辑关系:
我们是为了在新常态下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这就需要保证既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进而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需要促进技术进步和提升生产效率。如何做到这两点?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从何处发力?宏观经济政策对于拉动需求已经几近失效,而我国面临的矛盾恰好在供给侧,即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商品有效供给不能满足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结构性改革只能从改善供给入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梳理清晰逻辑关系之后,几个关键词跃然眼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生产效率,通过它们就可以找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痛点”。我们发现这几个关键词无一不与产业结构有关,即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能还是要回到产业上,从产业结构入手。
产业结构的“痛点”又在哪里呢?从对我国GDP的贡献看,服务业已经超过制造业并处于上升发展时期,但服务业的资本边际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总体上低于制造业,服务业比重上升会降低经济增速。再看制造业,我国制造业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去产能要处理僵尸企业、要裁员,这就要损害消费,拖累经济增长。可见,服务业先天不足需要后天弥补,制造业亟待产业升级,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痛点”。从当前来看,解决的方式就是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的翅膀,打造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即“四新”,形成新动力推动经济增长。
(三)支持新动力形成的财税政策建议
无论是弥补服务业的先天不足,还是推动制造业的产业升级,都需要借助政策的外力作用,财税政策支持更应不遗余力。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出台统一的财税支持方案。首先要明确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产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简称“四新”)的范围,例如,生产性服务业、康养产业、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互联网+等,列出清单,在合理分类的前提下,提供统一的财税支持。这种集中发力的支持远远好于“撒芝麻盐”式的分散支持,能够提高财税支持政策的整体效能。
第二,出台更为细致、全面的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揽子财税政策。因为“双创”是“四新”产生之源,财税政策应该从源头就提供支持。这里需要对“四新”企业出台专门的财税支持方案,因为在“四新”企业的初创期和成长期更易遇到融资难问题,没有财税支持,难以发展壮大。
第三,处理好政府与“四新”之间的财税关系。“四新”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必须着力扶植,但同时,“四新”的打造也需要消耗很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府和“四新”之间存在着“予”与“取”的双重关系。在传统的财税体制下,“四新”大多没有被覆盖,既缺乏对其提供财政支持的考虑,也缺乏对其征收合理税款的考虑。在“四新”加速发展的当下,需要在财税体制的设计层面统筹兼顾,处理好对“四新”的“予”与“取”的关系,一方面将“四新”全力打造为稳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对发展成熟带来稳定收益的“四新”征收合理税款,让社会共享“四新”带来的红利。
第四,以“组合拳”的方式,综合运用具体的财税工具。选用怎样的财税政策工具对“四新”加以支持?可以出台政策“组合拳”,包括直接的财政投资和补贴、间接的税收优惠和优先政府采购,以及发挥财政对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引导和撬动作用,即给予“四新”全方位的财税支持。
在2016年9月的G20杭州峰会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达成了五项重要共识,其中,创新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赫然在目,并最终形成了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三大行动计划以及结构性改革共同文件。当下或不久的将来,世界各国都会在这些方面有更大的投入,下更大的力气,以推动结构性改革最终落到实处。我国要想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只有抢占先机,全力打造“四新”发展。
[1]美联储数据库:http://www.federalreserve.gov/econresdata/default. htm.
[2]美国财政部数据库: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Pages/index.aspx.
[3]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库:http://www.stat.go.jp/data/index.htm.
[4]日本财务省数据库:http://www.mof.go.jp/jgbs/.
[5]国家统计局数据库:http://data.stats.gov.cn/.
[6]财政部数据库: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shuju/.
[7]wind数据库.
责任编辑:赵薇薇
Hypodynamic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Fiscal Policy for Improving the Effciency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 China
Kun Yan &Shuyi Yu
For the third quarter of Year 2016, the global economy remained low growth. And through the review on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major economies worldwide, it is found that hypodynamic structural reform widely happens all over the world which is the primary reason why the world economy has not jumped out of the dilemma of low growth.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has achieved an initial success in China, but also been encountered with great bottleneck.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ffciency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e pain spots” have to be solved based on the fact all the logic relationship withi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have been well coordinated. And the “pain spots” eventually come from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reform will not only fix the deficiency of service industry, but also push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fscal operation has shown several new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suffcient fnancial resources, the reform shall focus on forging “New Four” for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y so as to form new dynamics for the economic growth.
World economy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Fiscal policy
F812.42
B
2095-6126(2016)12-002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