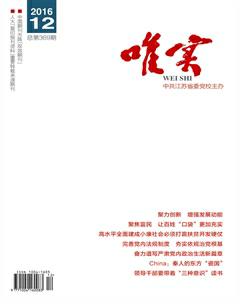中唐箴铭文折射文人情怀
周晓舟
箴铭文是古人用于警戒自身和告诫他人的一类文体,语言质朴,意义深远为其特色。在中唐社会动荡不已的背景下,除诗词歌赋外,文人以箴铭文为载体,将其作为抒发情感的工具,表达了对个人、仕途和社会的多样情怀。
一、中唐箴铭文及其社会背景
箴铭文其实是箴、铭两类文体。唐代以前,箴文绝大部分是针对帝王提出的劝诫,多用铺陈和用典的官箴为主,如杨雄模仿《虞箴》所作的《十二州二十五官箴》,从地域、职守等不同的角度对皇帝进行劝诫,37篇之多的数量,使箴体文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到唐代,箴文不仅用于劝诫皇帝,更多用于自我反省,检讨自己的言行并提出警示。于是,官箴渐疏,私箴逐渐占据主流,大批文人志士的箴文崭露头角,如柳宗元“所忧在道,不在乎货”的《忧箴》,即是作者对“忧”的理解,并提出了如何控制这种情感的告诫。而对于铭文,最初是“称美不称恶”,大多数刻在石头上的铭文都是赞颂型的,汉前刻于器物上的铭文对器物外形进行大量描写,警戒的意味相对较少,但自汉代开始,铭文逐渐脱离对器物的依赖,发展成一种用于自我警示的座右铭,慢慢地用于警示的铭文逐渐兴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曾效法东汉人崔瑗作《续座右铭》,座右铭也就成了相当流行的一种警诫性铭文。陆机在《文赋》中将箴、铭对举:“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虽说两者在风格上有差异,但人们论述时多将其归为一类,从南朝的刘勰到清朝的姚鼐都是如此。综上所述,到了中唐时期,箴文侧重于规劝人们改正缺点、过错,所谓亡羊而补牢;铭文侧重于警诫人们避免缺点、过错,所谓防患于未然,但两者均是用以劝诫人们正道直行。
箴铭文发生变化的根本因素源于每个朝代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中唐是极其动荡的一个时期,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使得朝廷元气大伤,吐蕃大举进攻,朝中皇帝和大臣不断逃亡,持久的割地讲和使得军事和财政收入产生巨大影响。直到公元805年,唐宪宗登基,收复失地,藩镇内部的世袭制结束,在其驾崩后,帝国才迎来了长达40年的太平。而这一时期的文人在仕途上更是几经波折,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古文运动在中唐时期的文学界更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不仅是关于散文文风、语言等的革新运动,更是一场改变思想、重建道德的文化运动。古文运动中的朝廷动荡不休,文人笔下的文章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二、中唐箴铭文体现的文人情怀
刘衍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中说道:“中唐之文,既是对前期古文运动先驱者的继承和发展,又是配合朝政改革,从文风到文体的一次彻底革命。”社会动荡,朝政全非,中唐士人学子的仕途和心态发生了很大转变,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生活多维度、多层面的感受,这一切激发出了文人们心中多样的情怀。文由心生,我们可以通过文章来了解文人在不同时期的经历、心态和情怀。
1.从自我警戒角度表现文以明道的现实情怀
自唐代伊始,将作者个人作为研究对象来阐述和剖析,并提出自我警诫的私箴越来越多,而其中较为优秀的私箴文可推韩愈的《五箴》。这是韩愈在古文运动前蛰居阳山时所作。通篇以自诫的手法表露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虽然称不上是严厉的说教,但却蕴含着自诫以外的一份不屈。在《序言》中韩愈写了自己因命运多舛而过早衰老的感叹,然后从“玩乐”、“言论”、“行动”、“交友”、“名气”这五个方面进行详述,表面看似批评自己饱食终日,无所作为,实则是警告自己如不改正就会沦入小人之列;看似是批评自己缺乏与当朝权贵对话的思维,太遵从道义而交友不慎,实则是表现自己“言多必失”后,当朝权贵的专横、昏庸和妒忌贤才;看似是批评自己太过自恃有才,锋芒毕露,提醒自己慎重处世,实则又已然表明“行也无邪,言也无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的态度,显示了对世俗针砭的愤激之情和刚正不屈的精神境界。通篇看似对自身问题的批判,实则以反讽的方式抒发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批判,表达他对自己怀才不遇,屡遭排挤打击的深沉感叹。此时的韩愈,因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而流贬阳山,而这篇箴文正是他流放期间所作,当政治理想和专制政体相冲突,重推孟子“仁政”思想、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拥有积极进取精神和保持对社会现实批评态度的韩愈自然不会屈服,他将“文”与“道”巧妙融合,从现实社会生活出发,明儒家之道,愤不平之事,“古道”既不能“行”于今,就只能以“文”来明道,而这里的“道”则源于现实又警诫于现实,是自身的一种不甘与反抗,也是警示自我和世人的标志。
“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重于后”的柳宗元对于“文以明道”的理解与韩愈的“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相同,其中有无奈但也确实符合当时政治功利性的需求。柳宗元的《忧箴》与韩愈的《五箴》有相似之处,都从自身角度出发。作者认为“子如不忧,忧日以生”,“忧”的存在是必然的;但又不可如小人一样,戚戚于忧愁,更重要的是,“所忧应道,不在乎祸”。这不仅是作者自身的一种理解,同时也提出了合理的控制建议。同样是取材于现实,同样是解决问题、抒发情感,还对世人有良好的影响力。
2.以借物抒情表现旷达乐观的博大情怀
箴铭文多阐述道理,因而要求行文精炼,能一语中的,切中要害。对于铭文而言更多是只提观点,不作过多的论证,但中唐时期借物借景表达情感的箴铭文不在少数,如陆龟蒙的《马当山铭》就是以太行、吕梁之险作为引子,烘托险中之险的马当山,再用夸张的手法描述马当山水的峻险,以及坐船经过马当山使人魂飞魄散的感觉,短短不到百字既是为了烘托“中如见芒”包藏祸心的小人,借景生发,讽刺尖锐。除了直观的讽刺意味,刘禹锡的一篇《陋室铭》则更为经典。通篇夹叙夹议,以陋室为物,以“德馨”之理作为骨架,加入富于形象感的描述文字,短短81个字将正反面对比、虚实相生、比拟法、用典等艺术表现手法囊括在内,不仅论证了“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观点,还简要而生动地描述了这间陋室内外情景。从立意上讲,文章不是以“君子”来进行自我标榜,而是以君子的进德修业律己,表现的是勉励自己砥砺操守,贫贱不移的勇气,也是对人生失意与仕途坎坷的超然豁达和乐观开朗的人生态度,将这篇“不陋”的散文,反转成为赞颂陋室主人淡泊高雅之生活情趣的抒情诗。刘禹锡一生的仕途也是几经波折,流贬不断,而《陋室铭》就写于他被贬为和州刺史期间,经历了八司马事件,一般壮志在怀的青年难免会悲观消沉,但刘禹锡反而更为坚强,他与韩愈和柳宗元又有不同,可以说他对儒学没有真正深入了解,他认为作者的官职越高,那么所写的优秀作品就会越多,因为较刘禹锡的文学地位而言,他还是一位政治家,其主要把握住了文章的实用性和功利性,为朝廷输送实际应用性的文章较多。由此不难看出,刘禹锡在多次贬谪后对朝廷还是抱有希望的,他的其他作品中会有对时局和政敌的不满,但他始终坚持理想,留下了一个改革家的坚强意志和乐观情怀。
唐代是文化大繁荣阶段,官僚中大多数人都普遍爱好文学。于是,文学之士较为顺利地走入仕途,而原本的官僚也会跟随文化潮流的影响去喜爱文学,最终文人在无形中接受了变为士人这一社会角色的转变。但真正的官场制度和文人的政治理想实则是两码事,一旦有了冲突,自然就会出现流贬现象。据统计,创作了占《全唐诗》总数近80%的231位诗人中,有192位当过官,其中75位诗人有贬官经历,比例占诗人总数的32.5%。在流贬的过程中,文人的身心受到双重压迫,但他们中有的人摧而不折,不但没有意志消沉,还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周边的人们,并渐渐地形成一种独特的人文思想。例如,写作《陋室铭》的刘禹锡;屡遭贬谪却一直坦然面对,佳作频出的苏轼;在贬谪中还能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贬到袁州、永州的韩愈和柳宗元,虽到蛮荒之地,却积极参加办学,指导后生,把文化内涵带到偏远地区,以此来提升这些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甚至在他们离开之后,还在他们曾生活过的地方薪火相传,成为一种生活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人生观,抑或是一种博大的情怀。
3.以箴文创新表现辞令褒贬的讽喻情怀
在古文运动之后,文学革新的失败没能阻止创新思想的传播,柳宗元的《三戒》就是最好的例证。虽说是箴文,但古代私箴也有以“戒”做篇名的,所以不足为奇。柳宗元自序:“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可见《三戒》是来讽刺世俗、针砭世人的,这与一般私箴用来自诫有些许出入,但这在作者的主旨思想上就是一种创新。《三戒》由《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组成,其题材均来源于民间传闻,是柳宗元跟客人所谈麋、驴、鼠的故事而编写的寓言,这完全打破了私箴只写人事的特点,还加入了讽喻的寓言特色。不仅如此,《三戒》纯用散文单句,和一般句式整饬、押韵的箴文也不同,这就是文法新,且寓言写物,语言活泼,文学色彩浓厚。它的出现,是柳宗元对传统箴文的变革。
柳宗元所写的文学寓言,使得这种文体在文学范围内获得了一席之地,也将讽喻情怀带到人们的视野中。从《三戒》的序不难看出,柳宗元是要警诫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的世人,从而来讽刺和批判当时社会不良的人情风尚。在《临江之麋》中柳宗元明显用麋鹿来比喻那些狐假虎威的人,告诫人们,一旦失去了主人的庇护,最终定会遭殃;在《黔之驴》中,柳宗元将驴子比喻为外强中干的人,一旦被识破“技穷”,总难逃厄运;在《永某氏之鼠》中,柳宗元借鼠托人,以老鼠映射那些仗势凌人的逞时作恶之人,说明这些人即便是一时侥幸,但日后必会遭殃。在柳宗元的寓言中,他喜以小动物为题材,抓住它们的某些生活习性类比人类,并突出特征,对时事风气进行评价,通过讽喻达到劝诫和改良社会风气的目的。讽喻,在日后被大多数文人所使用,白居易的讽喻诗堪称精品。这不仅仅是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更多的它代表着一种情怀,在文以明道的基础上对自己反省的追悔,也是对后世文人的劝诫。
箴铭文本身是一种劝诫和警示的文体,但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文人的笔下,它有了属于自己的内涵。而中唐的文人们在对社会生活多维度、多层面的感受下,有着对国家的满腔热情,有着对被贬的悲伤,有着对黑暗政权的控诉和讽刺,也有着那份勇往直前的乐观,许许多多的情怀在朝野的更替和时间的变化中闪烁着那份独特的光芒,而作为载体的箴铭文必将记录这一切,在承载过往的辉煌中,展现创新的魅力。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