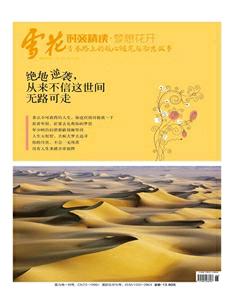被嘲笑的梦想,更有实现的价值
老杨
一
那年我读大三,住四人寝室。白天大家都在忙着为毕业后的日子做筹划,晚上熄灯后的一小段时间,就借着从走廊钻进门缝的稀疏灯光,分享各自的困惑和彷徨。
那时,我们的眼界很低,能够设想的未来不过是考研、工作、出国。A说:“我爸在家乡给我找了一份工作,虽然是稳定的国企,可是我不太想这么早就进入社会,不知道该不该考研……”B说:“我要去英国念书,但没决定到底是去斯旺西还是利物浦。”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挺想去工作的,但也想去留学……”轮到郑同学,短暂的安静后,她一本正经地说:“我想毕业之后先去工作,一边攒工作经验一边攒钱,计划两年攒出足够的银两,然后去法国生活……”
寝室顷刻间寂静无声,郑同学毫无察觉地继续讲,还带一点澎湃的情绪:“我想尽早地开始学法语,利用毕业前这一年时间,一边找工作一边争取考下法语四级证书,最好是能找到和法语相关的工作。每天坚持学习一个小时的法语,在去法国前至少要达到小学生的语言水平……”
这是一份多么周密翔实的计划,可是躺在硬板床上,望着天花板憧憬着法国生活的郑同学,和那个迷人的时尚之都相差的不止是一张机票的距离。这个来自乡下的姑娘,说不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经常头顶着贝雷帽,穿着皮夹克、七彩裤袜、圆头皮鞋,很顽皮地出现在校园里,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浑然不觉。她真的会到那个盛产文学和时尚,人人都吃奶酪尝鹅肝品红酒的地方去?
二
那一年,我们都在忙着为各自的前程奔波,谁也没看到郑同学五点钟起床去晨读的样子,也没理会她对着法国电影反复模仿对白的情形。
那时的郑同学,深夜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默读法语不小心发出声音的时候,会有寝室的姐妹不耐烦地抗议:“洗洗睡吧,又不是明天就要去巴黎!”她夏夜在水房外借着走廊的灯光热情朗读时,也会有同班的女生讽刺:“读的是什么啊?阴阳怪气的,还以为自己是苏菲·玛索呢。”
在一个庸碌的环境中,成为有梦想的异类,是一件十分需要勇气的事。我和郑同学接触不多,也不参与她的八卦,却在心底暗生佩服——我也有写作的梦想,却不如她那般大方磊落,只是偶尔在纸上涂涂写写,把那些文字置放在只有自己看得到的角落。我总是隐隐地觉得,那些深夜里从被子中透出的灯光,还有半夜去厕所撞到的读书身影,总有一天会有什么美好的东西,从那样的努力中孕育出来。
A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最终决定回到家乡成为国企的一名职员;B考取了利物浦大学,进修商科,市中心就有她爱的沙滩与海鸥;我经历一番挣扎,最后奔去远方,来到南半球的异国他乡为未来打拼;而郑同学,听说她去了深圳的一家公司,薪水不错,因为有四级法语证书,可以做一点零碎的翻译,日子过得踏实向上。
三
在出国的日子里,我经历了很多辛酸的时刻,奇怪的是,每当觉得自己苦到撑不下去的时候,总是会想起当年接触不多的郑同学。那束从被子里透出来的手电筒灯光,像是一个信念,照进我孤单的生活里。那一年,我努力写作,终于敢把一份梦想坦诚地铺满流水般的日子。我仿佛从未这样努力过,凌晨四五点钟起床,读书写作,白天上学夜晚打工,常常在油烟味道浓重的小餐馆里结束一天的辛劳,又在台灯下的被窝里读着严歌苓的文字取暖。我把文字当作最虔诚的信仰,把生命中发生着的故事写进时间的每一个缝隙里。
某一天,我突然收到那个成全了我梦想的邮件,上面的每个文字都在跳着舞,一个可爱的编辑问我有没有打算写一本书。我的生活从此更加匆忙,推掉很多没有意义的聚会,把每一秒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写作。因此我常常听见身边此起彼伏的声音:“你何必这么拼?”我有时只是微笑,有时忍不住说起“我在写一本书”。于是,我听到这样那样的回复,大多带着同样的语气——“啊?这个不好实现的吧!”“就你……”
我在那些有意无意的嘲笑中,开始理解,为什么人们说梦想是一件孤独的事。我继续着忙碌的日子,辛苦很多,朋友渐渐稀少。我一个人点亮凌晨的台灯,一个人写下满腹的心事,一个人抱着书本坐在图书馆里,一个人对梦想始终抱有虔诚的期待。
四
我把书稿整理完毕的时候,电视上正播放着第87届奥斯卡颁奖典礼,最佳改编剧本奖得主格拉汉姆·摩尔站在台上领奖,他手持小金人,感慨道:“我16岁时曾试图自杀,因为我觉得自己很怪、很另类,与其他人格格不入。而现在我站在这儿,此刻的我想告诉那些有同样感觉的孩子,‘我好古怪‘我好怪异‘我真是不合群,没错,你是这样,我肯定你就是这样,但请继续‘怪异,继续‘与众不同,当你成为下一个站在这里的人,请把这番话传递下去。”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有些人的面颊上挂着擦不干的眼泪。
经历了一年的挣扎,十万字的手稿终于到达编辑的手中,成为一本曾被许多人认为“不可以被实现”的软皮书。我感谢那个坚持凌晨四五点钟起床写字的自己,也感谢那些有意无意的嘲笑,就像九把刀曾经说过的:说出来会被嘲笑的梦想,才有实现的价值。即使跌倒了,姿势也会非常豪迈。
在我写作最艰难的时刻,偶然在脸书上发现了郑同学的踪迹。她真的去了法国,在埃菲尔铁塔下留了影,还把一堆世界各地的游客当背景,笑得没心没肺。照片里的她,依旧不好看,审美差到不行。
但是我想,这个从乡下跑到巴黎的姑娘,终于没有人再嘲笑她。
(摘自《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