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留心间的微笑
蓝菲
苔菲(1872—1952),俄罗斯著名的侨民女作家,俄国白银时代的“幽默王后”,原名娜杰日达·洛赫维茨卡娅,出身于贵族门第,家族艺术氛围深厚。她的父亲是一位律师兼演说家,幽默风趣之名远扬。苔菲文中之“笑”大概承袭自他。家中五姐妹也都与文学有着不解的缘分。比如苔菲之姐米娜·洛赫维茨卡娅是20世纪初俄国文坛的著名诗人,两次获得普希金大奖。其他姐妹也都擅长戏剧和诗歌创作。少年时的苔菲大多数时间都沉浸在书香诗海之中,当她回忆起自己的青葱岁月时,曾满怀诗意地说:“春天读屠格涅夫,夏天读托尔斯泰,冬天读狄更斯,秋天则是加姆森。”但无疑苔菲是家中文学才华最突出的一位,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在1910年一年内再版3次,她的《幽默小说集》7年内再版了十余次。后来其影响跨越了国界,在巴黎、布拉格、柏林、纽约、华沙甚至上海、哈尔滨等地的俄语读者中都享有极高的声誉,以至于当时的市场上还出现了“苔菲牌”香水和糖果。
苔菲塑造的世界是汇集了貌似最讲究风度的“绅士”、自认为最出类拔萃的“人精”、虚伪做作的文人、吹牛大王、溜须拍马的记者、傲慢自负的官吏、卖俏女郎、傻瓜蛋、失意者等各式人物的“人间喜剧”。然而它却不是一本令人恐惧的大部头,只是一个个短篇连缀而成的世间百态微缩浮雕。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抑或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列宁,都盛赞她的才华,是她忠实的读者。
轻描淡写的笑容
苔菲的幽默短篇小说中总是充斥着独具一格的气质,她的“笑”中蕴含着对所处时代的细密观察和人生思考。作为女性作家,苔菲有着天然的优势,尤其是在其创作早期,她以一颗女性敏感的心来感悟人生和世界,使其在对爱情、童真、少女的情怀等主题进行创作时更是游刃有余,动人心弦。评论家列尔涅尔甚至称她是那个时代短篇小说家和幽默作家中的魁首。

但苔菲的生活却是饱经沧桑的。对于其个体生命而言,她的婚姻生活是不幸的,离婚之后又丧失了抚养权,可以说夫妻缘和子女缘都是单薄的。而那又是一个酷烈的时代:两次国内革命将她推向了流亡的侨民行列,自此一路漂泊,辗转无定。她曾说:“我回想着我的奇怪旅程:从莫斯科出发一直向南,向南。全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其后她定居巴黎,终其一生未能再履故土。“二战”时期德军占领了巴黎,俄侨的生命和财产都受到极大威胁,再加上苔菲当时已是年老多病,以至于美国有传言她已经逝世。但这一切都没有打倒苔菲,她说:“活下去!充满朝气地活下去。对生活保持乐观的同时还要写作。”
常年背井离乡,孤独寂寞的生活,战争的威胁,这些都使得苔菲对于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对世情沧桑、人性莫测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知。但即便如此,苔菲依然为人乐观、真诚。因为乐观,她笔下的苦痛并不是撕心裂肺、鲜血淋漓的,希望之光依然照耀人间;因为真诚,即使深爱祖国,她对于民族劣根性也并没有躲躲闪闪,而是敢于刺破脓包,以便更好地去医治创口。
与其他短篇巨匠相比,苔菲的短篇小说有着明显的自身风格:不同于果戈里痛快淋漓地对俄国官僚阶级的丑态和封建农奴制的弊端进行深刻批判的“带泪的笑”;也不同于契诃夫的文短气长,简约犀利,清冷的笑;更不同于涉足宏阔社会领域,尤为关注国家民主、政治弊端,文笔老辣的马克·吐温豪迈又不失讥讽的笑;甚至与她的偶像——擅长使用凝练的语言,追求逼真自然,表现常态下一切的法国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相比,也有着微妙的差异。苔菲的幽默是在轻描淡写之中,寥寥数笔之间,笑意尽显。可是,笑过之后才是起点,当读者感受到与自身相似的无奈与纠结,从而体会到这背后更深的意蕴时,才会恍然,这才是苔菲创作的真正动人之处。比如《懒惰》中苔菲将“懒”变成了人类社会进步的伟大推动力,反证法式的黑色幽默令人印象深刻;《安慰者》中米莎的同学号称最擅长劝慰他人,却将原本开朗的母亲和姑姑“安慰”到了崩溃的边缘;《断头台》中描绘了一幅画面:人们边走边聊,向行刑台进发,其中还有人插队,有人要求监督,就像排队领取天堂入场券……由此可见,苔菲的“笑”就如其所言:“笑应该优雅而不低俗;深刻而不浅薄;笑应当尖锐而辛辣,应能触及什么人,应在其情调和音色中渗透进一滴滴的鲜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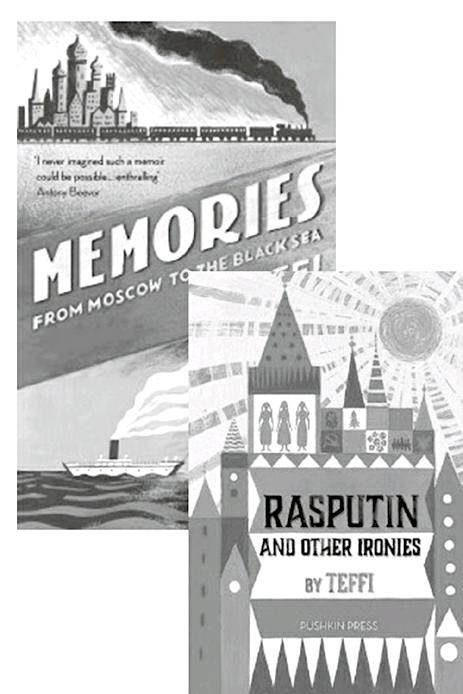
身不由己的命运
在读者的眼中,小说就是虚构的人生,但是在小说家的世界里,虚构亦是一种真实,她所经历的每一个孤独的日日夜夜,她与小说中的人同欢喜同悲伤同生共死的每一天,都是真实存在的,她在创造他们的生,也在催促着他们的死。苔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极为擅长细微地体察生活,表现最真实的人物内心和本性,同时敏感地体味读者的心理,极好地拿捏着分寸,对于人物创作的维度把握得炉火纯青。她的短篇小说不仅是情境的喜剧,更是性格的喜剧。现实生活中发生在各色小人物身上的种种琐事,仿佛就在身边出现的对话,无不充满生活气息。《关于温柔》描述了孩子、成人和动物之间的种种温馨,像一片片色彩斑斓的马卡龙,品读之后让人不免心甜意暖;《胸针》中厨娘一枚胸针引发“惨案”,一对夫妻因此分道扬镳,令人哭笑不得;《安泰》中伊万·彼得洛维奇面对妻子的琐碎唠叨表现出的可笑的大男子沙文主义,让人捧腹之后不免深思;《五月的虫》中流亡法国的俄侨科斯佳生活困顿,最终选择自杀,让人可叹可悲。这种接地气的创作饱含了“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如此直面芸芸众生使得苔菲的作品拥有了经久不衰的魅力。
此外,对于小人物的丑陋,苔菲并不是一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给予嘲讽,而是坦然地告诉读者她自己亦不能免俗。自嘲与嘲他在苔菲的文中都很常见,有时前者更甚。例如《回忆录》中,苔菲将自己和周围朋友称为“社会的鲜奶油”,嘲讽自己的不谙世事以及对周遭复杂社会的种种不适。这样的叙事特点和人物设计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代入感。随着他们穿越时空,却感悟超越时空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读苔菲的小说,阅读之初只觉平淡无奇,但细细回味之后却觉意趣盎然。因为她的恬淡怡人、抚慰心灵,令人犹如品味了一杯清新淡然的绿茶。即使苔菲笔下的小人物充满了为现实、为生活而不得已的种种无奈、难堪甚至悲哀,但这一切的背后始终有一抹笑意,这一缕会心之笑可以给人带来希望,愈合心灵的创伤,蕴含着勃勃的新生。在《瓦尼亚·谢戈廖克》一文中就展示了一名垂死的伤员对于生之希望的顽强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在生命的最后一夜,他以坚定的意志反复叨念:“我没时间死。我要回家,就让死神跟在我后面跑吧!我会甩开他的!我无论如何不会死的。”虽然他终究没有逃过死神的镰刀,但其强韧的意志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比如《宠物》讲述的是孩子对玩具温柔的守护。对于小主人公卡佳来说,毛茸茸的绵羊有一双人一样的眼睛,他将其当作自己的同伴。这个孤独的小男孩儿用他独有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善意和友好,展现出了一个冷寂却又纯粹的童年世界,告诉读者世上还有如许童真值得珍惜。成人的世界固然冷漠、残酷,但也不要忘记去寻找美好。《亚芙多哈》中的老太太由于不识字,始终无法弄清关于儿子的信件到底代表着生存还是死亡,虽然这是她人生的支柱,但她仍然坚强地活着,期盼着,为未来的人生努力着。激烈的爱总是想要征服、占有,苔菲书中淡淡的温柔的爱则是无尽的奉献、守护和照顾自己所爱的对象。
时光、幻梦、爱情及其他
除了贯穿于苔菲小说中的一脉清新温柔,还有一些意象和主题是她所钟爱并经常使用的。因为如此,才使得她的作品似一泓温柔的泉水,隽永并荡漾在每一位读者的心田。其一是时光。时间是苔菲舞台上一道最重要的幕布,春天和夏天是苔菲所偏爱的。每一个季节可能都是一种暗示,有时甚至是隐喻。如《春天》中曾有这样的描写:“夜是完全春天式的,有点闷,很平静。在这样的夜晚人们都忙着去什么地方,仿佛春天的喜悦就在某个地方等待着,只需要找到她。”“夜”是压抑的、哀伤的,春天却又让人萌生希望,这是期盼新爱情来临的象征。二是梦与幻想。这类意象的存在类似于宗教的救赎一般,它可以帮助人们自由徜徉在幻想的圣地,远离现实中的悲伤,缓解心灵的痛楚。《小船》中的护士韦列季耶娃在战地医院繁忙的救护工作之后,微作小憩,看到了初升的太阳照耀下的涓涓细流,上面有美丽的小舟,船中坐着两个可爱的孩子。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虚幻,事实却是满地狼烟,白骨累累,一派火与血的悲歌,又哪来的绿水、轻舟和幼童?但是其中反复提到的小舟这个意象在此语境下也就具有了独特的涵义:在充满不幸的世界,还是有救赎的,但那却只能在主人公的梦中或者幻想里才能体味到。最后是爱情。这是苔菲最擅长且热衷的部分。爱是一种充满着矛盾和张力的情感,在苔菲眼中它既包含快乐、温柔、欣喜、爱慕等积极的方面,也包含着暴烈的摧毁一切的力量。正如她的《爱如死一般强盛》,讲述一个迷恋威尼斯伯爵夫人的俄罗斯男人在求而不得后,又以其他花样繁多的猎爱方式来彰显他所获得的爱情真谛,可那还是真正的爱情吗?小说《春天》的女主人公深深怀念着自杀的勃比克,每每追忆曾经的花前月下,对比如今的形单影只都是黯然神伤。以上种种在苔菲的小说中是美好的也是令人心酸的,是激动人心的也是令人忧郁的,是值得同情的也是可悲可叹的。但是无论如何,它们都是苔菲笔下永恒温柔的变体与载体。

当今社会有太重的压力、太多的无奈、太少的温情,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性的丑恶、社会的悲哀。年深日久,我们的心越来越粗粝,再难鲜活,再难激动。仿佛便如出走离乡、渐感前路苍茫的旅人,隔着岁月的迷雾,始终望不见失落已久的故乡。久而久之,精神一片荒芜。这片清愁,不知究竟何时才能得以慰籍。或许苔菲的小说可以成为清凉之风,吹散障雾,带我们重温真正的人间喜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