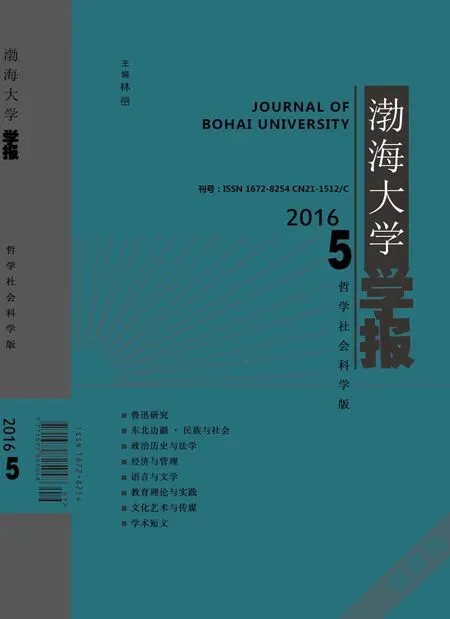科举制度与孔乙己的病态人
吴 波(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科举制度与孔乙己的病态人
吴波(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科举制度与孔乙己的病态人格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这本无异议,但如果追问科举制度通过何种方式、怎样的途径导致了孔乙己的病态人格特征,就会成为一个问题。科举本是中国古代社会为选拨管理人才产生的制度设计,其积极效应就是打破了社会身份、角色的世袭罔替陋习,促进了阶层的更替、交流。但考试结果往往决定了差异极大的社会地位和人生归宿,导致以求真、向善的学习行为异化为依附权贵、谋取利益的投机钻营。与鲁迅笔下的其他人物形象一样,孔乙己同样具有为求依附、认同而不能的紧张焦虑,也有因屡次落第而逐渐积累的愤懑怨恨,还有掩饰窘迫、维系尊严的绝望努力,更有以长衫显示差别的自恋、夸张行为,面对奚落、嘲讽,孔乙己更表现出强烈的复仇与翻身心态,以实现渴慕已久的敬畏与尊重。但是,科考语境决定了只有中第才能改变身份,否则只能承担失败的痛苦结果。制度性的心灵伤害、人格异化,具有伦理化特征的鲁镇环境,共同铸成了孔乙己的病态人格标本,并成为作家探索国民性的重要途径。
依附;焦虑;自恋;夸张;人格标本
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始终伴随着各种评论,但多倾向于文本描绘内容的复述,即“能指”层面的反复追索,缺乏“所指”层面的深入探讨,所以,关注、反思叙事内容背后的思考才更具价值。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一般皆具备特定时代中国人的人格标本特征,反映着人类不同阶段、不同阶层的典型属性。有“狂人”青春叛逆期的呐喊、怒吼,也有夏瑜慷慨赴难的舍生取义,更有涓生抗争礼教的爱情追求。至于阿Q则始终体现了平民中盗贼/英雄情怀,而祥林嫂却在“趋利避害”的祝福氛围中苦苦挣扎,生死不能自主,孔乙已则是科举时代病态人格标本,因科考失败而充满挫败感与伤害感。
孔乙己这个源于学童习字描红字帖的绰号,暗示了主人公本来的平庸资质,却非要追求智力性活动,科举追求治人者的地位,由此形成自身能力与目标追求的巨大错位。而科考失败又无法回归原来的生活状态,因为回归方向正是最初的否定目标,由此出现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的分裂特征,进而导致落魄现状与自尊追求呈现的巨大反差,使其成为许多人满足细微优越感的对象。这一结局的伤害效果大于断腿之类的私刑,因为断腿仅仅是针对特定的偷窃行为,孔乙己的称谓,则是对其所有能力以及人格品质的完全否定,真正的名字不被提及,其悲剧宿命已经蕴含其中。
一、制度性的心灵伤害
某种社会制度对于具体个人的影响,总表现为隐性、间接特征,只有那些直接关乎具体行为选择的制度设计,才对具体个人发生刻骨铭心的作用。受益者收获巨大利益而不觉,失去其他选择的受害者也同样浑浑噩噩。始于隋唐、明清达到极致的科举制度,曾为国家选人用材贡献巨大,也为消除等级阶梯提供了巨大动力。但随着时代发展,科举制度开始呈现异化特征。以秀才、举人、进士阶梯逐级晋升的形式,逐渐演化为目标单一、内容僵化的高淘汰率的竞争制度。所谓成功主要以大部分人的失败为基础,并形成一个人的学识能力只能由皇家判断的单一评价标准,并出现“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的局面。读书、学习成为追随、依附统治阶层的基本手段,威权意识、差序化心态更加强化。孔乙己这样的失败者则要承担挫折与伤害感,尤其要承担巨大的剥夺感与幻灭感。
曾经的投入、付出没有回报,只有作为反面教材面对嘲笑、讥讽,以至于起码的同情、怜悯也难以收获。面对的伤害越大,报复的欲望就越强烈。所以,失意落魄的孔乙己就以微薄收入,甚至是乞讨、行窃行为,终身以考试为业,努力争取翻身的可能性,改变差序化制度环境造成的伤害。因为“中国人是一个讲究差序格局的民族,他们常常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1],也会用不同方式对待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所以,唯有考试成功,才能变更身份,才能报复众人的嘲笑与蔑视。这种心态导致的最大后果就是科考成为人生的唯一支点与安慰,使其生存状态极度脆弱。而科考又是仰赖他人赏识才能成功的行为,故孔乙己生存状态的脆弱呈现为双重性,即人生满足来源的唯一性以及渴望恩赏的依附性,这一特征使孔乙己丧失了任何重新选择的可能性,科考既是人生追求的目标,也是自我封闭的牢狱,永无摆脱之日。
孔乙己执著于科考,主要是科举制度打破了社会身份、角色世袭罔替特征,使得阶层、代际更替成为可能,甚至可以实现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道路。这样,科考成为一种脱胎换骨、改换门庭的机会,甚至还具备一劳永逸之效。即先前的艰苦努力就是为今后的安逸享受付出的必要成本,付出越大,安逸享受就越心安理得。这对于世代耕作的农民而言,无疑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并产生疯狂模仿、追随行为。毕竟凭一次考试就可以改变个人乃至于整个家族的命运,自然就有时间、财富方面的巨大投入。
各种艺术形式的描绘,使否极泰来的科考、终成眷属的婚姻构成了令人向往的大团圆结局,由此不断放大了科考的理想色彩,却经常忽略科考对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与行为产生的负面效应。对多数平民而言,科考只是极少数人的运气,也是被缥缈的希望、憧憬放大的机会,更是由多数人的失败确定的机遇。如果说沙场征战的“一将成名万古枯”损害的是肉体生命,科考却使许多中国人形成心灵层面的受挫与伤害,产生一种血本无归的徒劳与幻灭感。这种制度性的心灵伤害,正是使孔乙己既是嘲笑对象也是泄愤对象的环境基础。嘲笑孔乙己的人也多为人生失意者,而更加落魄、潦倒的孔乙己则不幸成为别人的发泄对象,全然忽略了自己的遭遇。但孔乙己却因行为惯性迎难而上,将缥缈的希望视为奋斗目标,在充满羞辱、嘲笑的环境中等待翻身的机遇,等待着另眼相待的奇迹,这无疑导致了孔乙己的人格主体异化。
二、科举导致的人格异化
当科举考试直接异化为被皇家雇佣的目标追求时,向上、求学就会偏离终极真理追求,教育功能由最初的上行下效、化育人心的功能异变为单纯仰赖官家赏识而谋生的功利性行为。教育制度、教育手段、教育目标等均发生了质的变化。教育不再以培养人格、增长才干为目的,而是培养一种应试技能,使自己的所学获得皇家认证,成为治人的官吏。学习目的简单而直接,当官以谋取更大的物质利益,摆脱自食其力的劳动,依赖皇家俸禄生存。这一局面便产生了集体性的边缘型人格障碍,即“难以建立稳固的自我同一性,非常依赖与他人的关系来获得对自己的认同感”[2]。科考异化为求认同、寻攀附的行为,所有个性不复存在,受人仰慕成为人生最高目标,“面子”的畸形追求甚至可以扩散到阿Q那样的阶层。
科举考试教育制度单纯的目的,养成了大众的特殊心态及对考试的畸形期待。凡受教育者,就要成为治人者,却不允许成为普通劳动者,这样,受教育者就养成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极端心态,拒绝一切成为普通劳动者的可能,即学习的目的就是告别现在、摆脱过去,学子们由此承受着空前巨大的压力。接受教育就是拒绝平凡,也是摆脱苦难的精神支柱,更是督促学习的直接动力。至于先苦后甜的预期,既是辩证法的偏执运用,也是某种鞭策形式,更是中国教育至今还在延续的悲哀。因为考试一旦结束,学习活动就会终止,真理追求无从谈起。
科考使读书学习脱离了求知求真的终极目标,转向迎合官府的标准答案或要求,权力意识和权威意识就不断积蓄。因为标答终归体现着权威,甚至是世俗化的绝对,由此引来处心积虑的揣摩与推测,学子们就会提前进入皇家之彀。一旦入彀,人格品质养育则逐渐淡化,只有仰人鼻息或随波逐流。与此同时,个人学识能力评价标准丧失了客观性,只以榜上有名或入仕为官作为判断依据。仅仅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很难引来敬重,即学识不能换来高高在上的安逸享乐,不具备令大众驻足仰视的官家威仪,任何苦心孤诣皆为东流之水,更不能迎来基本尊重。孔乙己的悲哀在于科考落第还要证明自己具备学识能力,但却无人理睬。之乎者也之类的表达本是自证水平,但因无法实现沟通,却成为无能的标志,由此陷入越是渴望尊严,越是陷入困窘的局面。
读书、学习本是陶冶性情、修身致知的学习行为,最具个人性的感受、体悟,但是科考的功利性追求,使学习行为更多呈现为一种炫耀,一种远离平凡生活的宣誓,并通过高居众人之上或衣锦还乡来作为评价、验证。这样,读书学习不为致知、明理,只为他人尤其是官府的承认,只求令人敬畏、羡慕,功利性的考试结果,并成为光宗耀祖还是丢人现眼的分水岭。科举考试的刚性特征以及潜在的利益收获,决定了学子们的疯狂投入,舍本逐末地排除杂念与世隔绝,彻底放弃了人生的其他可能性。孔乙己的人格特征逐渐异化,封闭、孤立且紧张焦虑,毕竟科考结果总是具有诸多不确定性。
最令学子焦虑的是学习历程及归宿完全处在不自觉地监控、注视之中,生活几乎陷入完全透明状态,孔乙己之类要承受巨大的关注压力。这种关注的合理性源于投入产出的经济学法则。一个家族选择一个人学习,意味着在中举之前,无论是未成年还是成年,都由其他人提供生存保障。一旦中的,再以鸡犬升天之类的方式给予回报,从而加倍收回投入成本,封建制度下的腐败也就有了民间基础。所以,科考的这类特征就使学习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关涉一个家族的命运,为此,孔乙己在开蒙阶段就要承担巨大压力。落第、失败不仅是个人的耻辱,更是辱没家族的行为。参加科考就是努力证明自己有益于他人,能够造福于亲人和乡邻,否则就是罪过。孔乙己的落第无疑是一种罪过,无子无后更是罪加一等。这样,孔乙已只因个人的科考落第,就要承担一切后果,最终的落魄、潦倒就有大众的人格异化促成的根本因素。孔乙己始终被一系列的必须如此的应该所包围,而“应该总是产生一种强迫的情绪,一个人在实际行为中越是想实现这些应该,这种强迫感也就越大”[3]。这最终造成了孔乙己夸张性的穿长衫的行为,以此强调自己并非罪孽深重,相反还有为他人谋福利的资格与条件。
三、孔乙己的病态人格始于科举、终于落第
孔乙己的病态人格除一般性的依附、焦虑、紧张等因素外,还有一种无法克服的的自恋症。“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本质特征是过度的自我重要感,这种明显的自恋常常伴随着非常脆弱的自尊”[2](440)。这种病态人格主要源于超越实际能力的过度期望,由此导致了目标预期和实际结果的相悖,自视与评价的巨大反差,即主观意愿与现实认同的矛盾与冲突,落第结果生成的挫败感则因孔乙己想象中的关注而无限放大。
自恋症人格其内心深处往往有着强烈的对比、竞争意识,较之其他人更看重某一行为结果,并为此付出巨大投入,追求的目标就会逐渐成为唯一的精神满足来源,对其产生的依附也就更加强烈,承受失败的能力也就更加脆弱。所以孔乙己穿长衫站着喝酒的行为既是不甘失败的抗争,也是努力赢得尊严的悲壮。科考固然失败,毕竟还有读写能力,较之那些短衣帮同样还有高人一等的心理优势。但是,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与现实状态形成鲜明的反差,自我期许与大众嘲讽截然对立,结果是不但不能赢得尊重,反而强化了自己的失败与落魄。“在鲁迅小说中,人物有时是惩罚、示众的对象”[4],孔乙己无疑是充当了这类角色。
作为落第者,孔乙己既不能也不愿从事普通人的谋生方式,只想从事体面的劳动维持体面的生活,由此形成了愿望与能力、现实与可能之间的反差。本已沦为平民,却通过穿长衫、之乎者也的口语,处处否定自己混迹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孔乙己始终沉浸在理想愿望中不能自拔。无论是教小伙计识字,还是随口的“之乎者也”,均在引起他人的关注或尊敬,强调自己因受过教育而与众不同。而这等于把想象中的生活方式搬到了现实之中,即把理想中的生活方式搬进现实进行夸张式的表演,虽满足了自己,但却否定了他人的常态生活,讥笑、嘲讽便是夸张表演的收获。
孔乙己虽受过教育,但没有形成一个坚定的信仰,只是养成了顽强的等待赏识的翻身心理,在咸亨酒店的出现只具供人开心的价值却浑然不觉。在此,孔乙己的等待翻身的强烈心理具有重要作用,类似“苦其心智”的古训支撑着他忽略、忘却遭遇的种种屈辱。有朝一日中举,此时的遭遇就会成为韩信受胯下之辱式的传奇。可惜,孔乙己生不逢时,科考不再是人生的唯一抉择,他依赖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生存,翻身之日便遥遥无期,他就以近乎表演的方式体验已经无法实现的生活。
早年的孔乙己因具备读书求取功名的机会而具有一定的优越感,满怀妒忌、仇恨等复杂心理的关注就会如期而至。读书上进毕竟只能给予少数人,这种不公平就会导致多数人的嫉妒与仇恨。尤其是拥有特权和机遇的人不能表现出超越常人的人格品质时,人们的妒忌、仇恨尤其如此。但孔乙己不明就里,有意无意将自己与普通人相隔离,并在各种科举成功实例的刺激之下,俨然将自己视为各级官员的候补人员,蔑视周边为生存奔波劳碌的平民大众,这样,孔乙己就把自己人为地与生存环境孤立、隔绝,仿佛自己就是临时寄居此地,官府衙门才是自己的终身之所。这样,孔乙己就把自己置于没有退路的极端之地,所以,科考失败使他永远成为鲁镇人开心、欢乐之来源。
一个自我封闭、隔绝的人,必然要受到格外的关注,观察其未来可能的失败,以发泄自己受到蔑视的仇恨与愤怒,所以,孔乙己行为的心理动机就是拒绝承认失败,拒绝承认己不如人的事实,用一种几乎荒唐的方式维持着“唯有读书高”的虚幻情境,并体现了阿Q后来得以成名的“精神胜利法”特征。维护面子只是一种外在行为,内在的心理动机则是恐惧批评、指责。当自视与他人评价形成反差时,或预期评价与实际评价可能出现矛盾时,或是某种评价可能导致“揭短”时,恐惧实事求是评说的“面子”就会如期而至。说到底,这是一种扬虚长护实短的病态心理。所谓“长”不过存在于幻想或短暂的表演中,而“短”则是真实状态。适当的扬长护短是一种正常状态,某种幽默自嘲更是健康特征,但是扬长护短成为必须应该才是病态。
这种病态源于熟人社会,自觉不自觉的认定自己生活在一种关注之中,尽管这种注视只是一种想象或假定,但依然可以左右人的行为,故面子的本质就是“自卑”,由他人左右生活以及日常行为的状态。一旦行为举止不当,就会认为被人小觑,代表尊严体面的面子就会丧失,故孔乙己维护面子已经达到神经症或强迫症的程度。神经症意味着反应过度敏感,强迫症则表现为不断重复某种丧失意义的行为动作。所以,面子就是为赢得廉价赞美的行为。
孔乙己所有行为皆可概括为保全面子的努力,其目的无非是争取人们对求知学习者的尊重与敬畏,或是因自己读书学习渴望赞美性评价。但是,科举制度已经将求知求真的学习行为异化为偏执的谋利工具,故求知学习若不能因官府认可并与地位、财富相联系,任何努力都将遭遇蔑视,起码的尊重也就无从谈起。何况孔乙己连谋取温饱尚不可能,其学习经历更是一种学习失败的符号标志,并成为鲁镇人们证明自己的反面典型。至于亲近儿童的行为,固然可以称为良知犹在、童心未泯之类,其实是“孔乙己无法以他的‘文言’来与世人交流,更不能维系他的生计”[5]的标志。所以,孔乙己就是谋取起码尊严不可得的悲剧,自视预期与实际评价形成巨大反差的悲剧。
四、孔乙己悲剧的鲁镇因素
鲁迅善于描绘平庸之恶造成的个体悲剧,如祥林嫂周围的以趋利避害为动机的祝福氛围,九斤老太面对的动荡惶恐与紧张焦虑,孔乙己所面对的鲁镇则是通过嘲笑进行的惩罚,惩罚一个已经落魄却自绝于大众的不识时务者。
孔乙己不肯放弃虚幻优越感,以标志性的“穿长衫站着喝酒”表现区别,努力强调与众不同,这就是自绝于社会共同体。而未能进学就意味着他必须在已经拒绝的社会共同体之中生存,由此产生了意愿与现实的两级分裂。再加上个人的偷窃恶习、护短、争辩等,使其丧失了获得同情的条件,成为鲁镇人嘲笑、泄愤的主要对象。孔乙己的科举失利与系列劣行使其面临着双重缺陷,却强行要求众人对其给予尊重、谅解,这无疑是一种强人所难,更是一种对他人的深刻依赖。
孔乙己拼命维护的尊严仅仅是一种想象中的存在。偷窃本是罪恶行为,不能与知书达理的自诩相联系。但为某种目的从事偷窃行为,必须寻找说服自己的理由,否则难以实施。孔乙己选择了中国人常用的办法,以动机论自辩。窃书手段固然背德,但动机是为求学明理,故这一行为本身就有了高尚意味,由此形成了中国人成王败寇论的另一种表现。只要动机受到肯定,并获得相应结果,某种背德手段、途径皆成榜样。如匡衡的凿壁偷光,因其求学便赞美其破坏他人财物、偷窥他人隐私的行为;苏秦的悬梁刺股,因其悬挂六国相印,便赞美其自虐、自残行为。若孔乙己侥幸成功,恐怕又要出现一个新成语,窃书求知。所以“窃书不算偷”的争辩则是病入膏肓的标志,一种以科举结果论英雄的功利主义恶疾,以及道德评价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相对主义病患。
孔乙己窃书与书写工具的目的,可以解释为窃书卖赃换酒,只为口腹之欲;也可解释为参加科考,卖赃换得盘缠。这种可能性最大,因为一旦考中,偷窃这种恶行就会稀释甚至是原谅。何况异地为官的刚性要求,使中举者有很多机会重塑形象。为此,为科考而偷窃的罪恶感会最少,并导致后来的近乎理直气壮。但这样的人即使中举、入仕为官,也难以实现造福一方的预期,更无法承担探索真理之责。稻梁之徒如孔乙己之辈,只是汲取了消极的人生经验,将曾经的学海无涯、凿壁偷光之类的励志言论,转化成自己偷窃、犯错的理由,最终以断腿、残疾告终。至此,鲁镇人再无开心之日,毕竟只能爬行的孔乙己不宜作为嘲笑、戏谑的对象。
科举制度不仅扭曲了学习行为本身,使学习丧失了追求真理、完善人格的终极价值,也扭曲了学习者的人格品质,导致了一系列病态属性特征,自视过高、蔑视平民、攀附权贵等,同时也促成了平民大众成王败寇的心态。落第的孔乙己因一无所有,便极度渴望肯定、赞美,仿佛肯定、赞美可以化解自身的缺陷不足。假如孔乙己能够金榜题名,各种赞美就会随时而至,曾经的恶习就会变成传奇。如此没有恒定评价标准的环境,只能造就滥用私刑的丁举人,以及孔乙己式的喜剧性的悲剧人物。
在鲁迅笔下,中国人的人格特征有多种表现,但是具有巨大包容性的典型情境,使得具有多样性的中国人的人格特征具有高度的趋同性、一致性。无论是属于哪一阶层的人物,在寻求依附、争取认同、渴望尊严等方面极为相近。尽管,鲁迅的人物形象多以记忆最为深刻的农民为主,但是,面对挫折、苦难时的精神自慰特征,几乎是中国人在特定时代的典型标本。严苛的生存环境,俯首称臣、供人驱使几乎是唯一选项,更是决定着孔乙己之类的人很难获得公正评价。为此,夸张之类的行为方式就会不自觉的扩散、放大。“在夸张法中,个体主要是以夸大的自我来鉴定自己。在谈及自己时,指的是美化的自我。”[3](188)再加上极度缺乏宗教慰藉,使得孔乙己极度恐惧自己的失败成为他人的观赏内容,孤独、悲哀无从宣泄,依赖长衫之类的形式维护“面子”几乎成为一种准宗教。孔乙己没有子孙延续,没有亲朋故旧,自然无法通过扩大伦理关系抗拒社会关系的冷漠,或者更不能将某种社会关系转化为伦理关系庇护自己。所以,孔乙己频繁出现在自己曾经企图摆脱的场域,还要求公众的恭敬,这无疑是强人所难。
总之,科举制度与孔乙己的病态人格密切相关,也构建了典范的病态人格标本,同时也为某种行为判断标准留下了太多的争议。孔乙已的病态人格集中于偏执、极端,只因曾经接受过相应的教育,就将自己排除在凡人行列,以穿长衫站着喝酒的方式强调差别,努力摆脱被“看”的宿命。但是自身能力与目标追求的错位,主观愿望与现实状态的反差,内心的空虚迷惘与外在的夸张自恋,以及应该导致的强迫与对尊严的极度敏感,使自己在追求依附、恩赏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在紧张恐惧中体验着剥夺感与幻灭感,在故作姿态的各类行为中呈现着永恒的身份焦虑。尤其是在成王败寇的科考语境中,孔乙己拒绝承认失败的偏执以及行窃等恶行,终使其陷入不归之路,也为后人留下无尽的慨叹。
[1]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228.
[2]劳伦·阿洛伊,约翰·雷斯金德,玛格丽特·玛诺斯.变态心理学[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435.
[3]卡伦·荷妮.神经症与人的成长[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73.
[4]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75.
[5]吴康.书写沉默—鲁迅存在的意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31.
(责任编辑单丽娟)
东北边疆·民族与社会
主持人语:东北边疆历史文献和历史地理,历来为学人所关注。本期刊发两篇相关研究论文:邵恩库《“颛顼之墟”考略》一文,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推断义县敖家沟北平顶山遗址可能就是“颛顼之墟”。关于颛顼之墟,学界历来看法不一,各有所据,无有定论,本文可备一说。薛海波《谈〈呼伦贝尔志略〉及其史料价值》一文,分析、探讨了《呼伦贝尔志略》的编辑目的、背景、体例和内容。指出该书是在边疆危机背景下编纂的,目的在于“固我藩篱,保我土宇”,用事实说明呼伦贝尔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通过内容分析,充分肯定了《呼伦贝尔志略》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对于研究呼伦贝尔地区自清前期至民初的政治形势、边界位置、边防设置、经济发展、蒙汉关系、中俄外交纠纷、社会风俗演变等都有着重要价值。
本期栏目主持人:崔向东
I210.97
A
1672-8254(2016)05-0008-05
2016-03-18
辽宁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外悲剧型文学人物形象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W2015023)
吴波(1962—),男,渤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