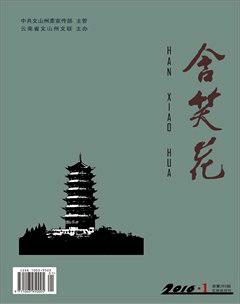极限
彭晓燕 渠培红
极限
彭晓燕渠培红

天开始放亮了,又是一个无眠之夜。
廖若辰从电脑前抬起头望望窗外,顺势伸展一下已近僵硬的脖颈和腰椎。初夏的清晨依然凉意颇浓,再加上一夜的雨水,空气中溢满了潮湿和冷气。他起身去卧室,从衣柜里胡乱拿了件较厚些的上衣披在身上,重新回到电脑桌前,点燃一支香烟。看着电脑桌面上刚刚完成的那份调研报告,廖若辰的心里感觉不到一丝丝的轻松。
自踏入某局的大门,为了按时完成领导布置的讲话稿、工作汇报、工作计划、工作总结以及名目繁多的调研课题,十余年来,他都记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次在通宵达旦地赶写材料了。长时间的写作,长时间的通宵加班,早已将年轻时的那份因完成一份工作而兴奋不已的朝气劲头打磨殆尽,剩下的只有小老头似的麻木和疲惫。
平时,通宵赶写完材料后,廖若辰总是连电脑都顾不上关,倒头便睡,因为他还要在上午8点钟上班时间赶到办公室上交完成的材料呢。也许是清晨湿冷的空气赶走了睡意,廖若辰吐一口烟圈,调整了一个较舒适点的坐姿,任凭自己的思绪在烟雾弥漫的空气中拉伸、蔓延。
想起当年初入某局时,自己是何等的兴奋和自豪。那时候的自己才二十岁出头,正是意气风发、充满幻想的年龄,在一岗难求的紧迫就业形势下,自己能考入某局这个被称作金饭碗的好单位,同学们羡慕不说,父母更是感到无上的荣耀和骄傲,逢人便说:他们的儿子成金领阶层了。那时候的廖若辰简直就是生活在鲜花和赞美声中,父母同事家的女孩排队等着和他约会,单位里那些大姐们争相去廖若辰的办公室给他介绍对象,那个被同学公认的校花柯蓝也向他投来了橄榄枝。
随后的日子,文笔不错的他被安排到办公室,给领导当秘书,负责撰写领导的各种讲话稿、发言稿、心得体会、甚至民主生活会上领导的剖析材料等,领导个人的调研文章当然也是由他来代笔。这是个人人羡慕的岗位,绝大多数人认为给领导当秘书是一件美差,与领导走得近,知道的事情多,又是笔杆子,肯定提拔得快。廖若辰的心里美滋滋的,感觉自己简直就是春风得意,前途无量。一段时间以后,他逐渐摸清了领导的工作思路,写起材料来得心应手。第一任领导发现他工作态度认真,又是熟人的子女,就顺手提拔他为办公室的副主任。领导的提拔无异于为廖若辰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他更是没日没夜地干呀写呀,几乎没有过过节假日,天天泡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老婆和孩子很少能得到与他一起吃饭的机会,这些年来,女儿都上到小学五年级了,孩子的家长会他却一次没参加过。爸妈家里遇到水管坏、下水道不通等情况,他都没时间去帮助修理。有一次老妈因脑血管阻塞住院,接到电话后,他匆匆来到医院,把医药费交到表弟的手里,又回单位忙他的材料去了。
就这样,一干就是十年,单位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而廖若辰的岗位却一直没有更换,因为要培养一个秘书不容易,像他这样能让领导用起来很顺手的人更是不好找。后来更换的领导越来越年轻,当然不会再是廖若辰父母的熟人,在干部提拔靠关系、不靠工作能力的当今,廖若辰的小主任,括弧副的,一干就是六七年。说白了,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是充满希望和干劲的,还不是都想着能有个好前程啥的。廖若辰之所以拼命工作,他想的就是可以得到领导的认可,可以让自己在更高一级的领导岗位上为革命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但当提拔的机会一次又一次与自己擦肩而过时,他的心里开始产生了波澜:我的青春能有几个六七年?我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根据历年来组织人事任用干部的惯例,三十五岁是任用提拔干部的一个年龄分水岭,自己的年龄已经走到分水岭的边缘,而我的希望在哪儿?
第一次参与竞聘时,廖若辰信心百倍,满心以为凭借自己三年如一日的勤奋付出和一大堆发表在系统内外省级以上报刊的调研文章,以明显高出竞争对手一大截的斐然成绩,必定胜出无疑。竞聘结果一公布,廖若辰却“意外”落选了。他一时很难接受这个失败的现实。为了能使他像往常一样勤奋工作,提拔工作结束后,单位领导干部就与廖若辰谈心,有的领导这样劝慰他:“小廖呵,你是个好同志,你的工作能力是大家伙公认的,要求进步是好事,但名额有限,某某同志比你年龄大些,你就权当友好相让好了。你以后有的是机会,好好干。”
第二次参与竞聘时,廖若辰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充满信心,但他有一种笃定的想法:这次该轮到我了吧。竞聘结果一公布,廖若辰依然落选。有了上次与廖若辰谈话的前提和经验,领导这样劝他:“其实呵,人就是那么回事,提拔又怎样,不提拔又怎样,反正我们是基层单位,芝麻大点的地方,芝麻大点的官儿,即便等到猴年马月也不会当上总局局长不是。关键呢,还是要把握好自己的心态,做好领导交办的工作,凡事别太较真儿就行了。”
第三次参与竞聘,廖若辰的心里开始有些麻木了,他几次询问自己:我还参与竞聘吗?这次若是再失败了怎么办?果不其然,第三次竞聘,廖若辰败在一名初中都没读完的酒鬼手里。这次领导这样对廖若辰解释:“我们这次提拔干部完全是依靠民主的力量,民主推荐是选拔干部的关键。小兄弟,和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以后要多长个心眼,不能只顾低头拉车,要学会抬头看路啊。再者说,就我们这样的基层单位,当了什么长又能多拿多少钱呀,还不如自己业余时间做个小买卖挣的多呢。”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廖若辰砰的一声把办公室的门带上,啪一下甩掉手中的材料,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生起闷气来。他奶奶的!我每天替龟儿子们写这些假、大、空的讲话稿、总结报告和根本没人理会的工作计划、工作制度。一年到头几乎没过过节假日不说,晚上加班开夜车更是家常便饭,再加上自己是个死要面子、傻不拉唧的家伙,领导给安排的工作都是力求尽善尽美。已经累得哼哧哼哧的,还在那里字斟句酌。没日没夜地写材料,辛勤工作回赠给他的礼物,除了腰肌劳损、肩周发炎、视觉模糊等“相伴终生”的职业病以外,就剩下希望渺茫了。
年复一年的枯燥、重复、又毫无意义的劳动,使得他身心憔悴、苦不堪言。随着单位工资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一降再降,曾经是时代宠儿的某局,如今变得门庭冷落。原来出去搞调研,人人都会骄傲的说自己是某局的干部,现在出门到一个陌生城市问路,请教路人当地的某局住址,路人竟一脸茫然地问:“没听说有这样一个单位啊。”廖若辰也曾多次动过辞职的念头,但每次都被掐死在萌芽状态。理由很简单:一是他还没达到需要破釜沉舟的境地。安逸的生活环境逐渐磨掉了他奋斗的棱角,虽然心里感觉很窝囊,但还是会忍气吞声。某局这个富有行政色彩的单位就有这本事,你再飞扬跋扈的一个小年轻,只要进得局里来,出不了三、五年,立马被驯服得乖乖得没脾气,没斗志。忍气吞声的功夫是廖若辰在某局大炼炉里磨练出来的收获之一。过去好多同仁都说自己是温水里被煮着的青蛙,现在的廖若辰深有感触。二是自己还是对潜心学习了四年的专业知识和从事了十年的业务恋恋不舍,感觉自己大有一种死皮赖脸、贴住不放的架势。虽然非常不满目前单位的体制,但是,这是他非常热爱的事业呵,每次动离开的念头时,心中就会产生一种生离死别的痛。在心里廖若辰咒骂自己无数遍了:死小样儿,没出息!三是拉家带口不容易。他的宝贝女儿马上要升初中了,全家人必须以她的学习为中心,紧紧围绕在孩子的周围。他,无可奈何。
每次竞聘失败后领导找他谈话,廖若辰的心里都很不是滋味,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像阴云一样弥漫开来。一直以来,在廖若辰的心目中,只有拼命做好工作才是人间正道,当领导的应当鼓励下属热爱本职工作,奉献自己的事业,应当拿工作成绩作为衡量员工职务晋升与否的主要标准。可踏入某局十年来的遭遇,让他对自己一向坚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疑惑,残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承认,只顾脚踏实地地埋头干工作,并不能为自己带来好的前程。最让廖若辰接受不了的事,就是眼睁睁看着那些从未接受过专业知识系统培训、连最起码的专业术语都不懂、有的甚至连十年义务教育都残缺不全的人,一个又一个的先后超越自己被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每当此时,廖若辰就百思不得其解,某局是事关地方发展的重要部门。需要的是懂业务、会操作、能参谋的高素质人才,一个又一个的门外汉把持着基层单位的重要位置,能行吗?出了差错怎么办?影响了行业的形象怎么办?每每苦思冥想到此,廖若辰就会突然变得气急败坏起来,妈的!关我鸟事!人家都不重用我,我还咸吃萝卜淡操心,“贱”就一个字。
廖若辰也知道,现在办重要的事不出点血是不行的。他曾几次邀请局长他们吃饭,效果却是不了了之。家里储存的几箱子五粮液已经被喝光了,软包中华和苏烟也没少送,但每次吃好喝好后,局长都会眯着眼睛笑呵呵地说:“小廖不错,年轻有能力,以后有的是机会。”
可机会呢?每次都是与自己失之交臂,廖若辰的心里呵,拔凉拔凉的,说不清是疲惫还是绝望,突然间廖若辰身子一歪,瘫软在自己的办公桌前。
廖若辰生病了,一直高烧不退,整整打了七天七夜的吊瓶。第七天夜里,高烧总算降了下来。七天不吃不喝,只靠葡萄糖液体维持身体的基本需求,廖若辰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出院后,医生嘱咐廖若辰在家静养一个月,但他只在家休息了一周,就被三番五次的电话给催促走了,因为局长的讲话稿急等用呢,其他人的文笔又一时不能迎合局长的心思,他只好拖着虚弱的身体上班了。
自从上次大病一场以后,廖若辰像变了一个人,虽然还是会经常加班加点地写材料,做到对得起自己那份工资,问心无愧,但从内心深处,他已经失去了往日那份对待工作的激情和创造力,不再意气风发,不再充满活力和向往。他变的开始顾家、顾孩子了,因为他突然发现,这些年来,自己最对不起的就是家里的老人、媳妇和孩子,以前的自己可以称得上是少不更事,现在的自己应该幡然醒悟了。痛定思痛,廖若辰决定痛改前非,所以只要家里老爸老妈有事找他,工作再忙他也会专门请假回家去打理;辅导孩子写作业成了他每天必修的功课;他推掉了几乎所有的饭局和应酬,一心一意回家陪老婆、孩子吃饭,帮助做家务;节假日期间,就带老人、孩子出去游玩。单位里有些依然把廖若辰当做自己竞争对手的同事很是不解,本来准备在下次竞聘时继续对廖若辰使绊子的那些个无耻之徒,为了求证真假,有人忍不住向廖若辰探探口风:“兄弟,听说你要放弃下个月将要举行的正科级竞聘,是真的吗?”言外之意,打死他都不信。而廖若辰的心里却是从未有过的平静,他非常清楚,自己已经在事业的道路上使出了浑身解数,既然这个社会不按常理出牌,那么他就不必再为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执迷不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