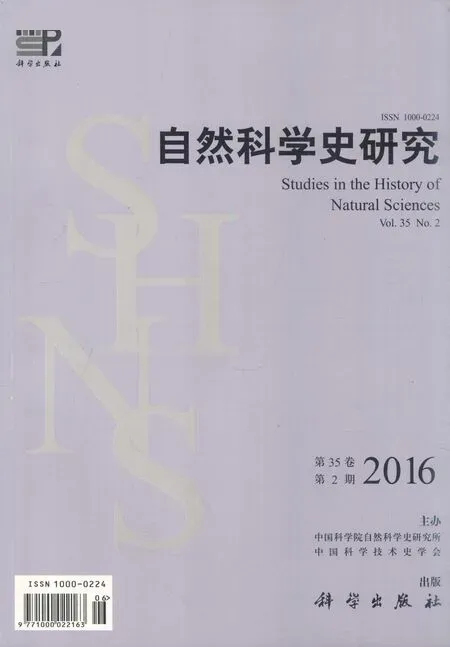维理士对中国地质的研究及其影响
陈 明 韩 琦
(1.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维理士对中国地质的研究及其影响
陈 明1,2韩 琦1
(1.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美国地质学家维理士1903年来华考察,进行地层、黄土、地文和构造地质学等研究,其成果发表在《在中国的研究》(ResearchinChina)中,对中国早期的地质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文章在梳理其考察经过和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早期地质学家对其工作的参考、补充和修正,分析其著作在中国的使用情况,以及他与中国地质学家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从而探索中国地质学的早期发展情况及其本土化过程。
维理士 《在中国的研究》 地质学 黄土 本土化

1 维理士生平
维理士(图1)1857年5月31日生于美国纽约州康沃尔镇(Cornwall),曾在德国接受中学教育,1874年返回纽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矿业学院接受五年采矿和土木工程的正式教育。毕业后被美国地质调查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所长克拉伦斯·金(Clarence Rivers King,1842~1901)引荐给庞佩利。庞佩利和克拉伦斯·金计划调查美国的铁矿资源,维理士的首个地质任务即为探查矿石沉积和采集样本,在庞佩利指导下的四年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1],3、5~6页)1884年,维理士加入美国地质调查所。他作为地质学家首次获得广泛认同是对东田纳西州和阿巴拉契亚山脉相邻部分的地质研究,成果发表在其首部专著《阿巴拉契亚山脉构造机理》(TheMechanicsofAppalachianStructure)中,引起了欧洲研究相似地质条件地质学家们的兴趣,这使他得以在1903年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地质大会上提交一篇关于逆掩断层的论文。[2]

图1 维理士(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1884~1892年,维理士负责地质调查所阿巴拉契亚山脉部门,1896~1902年,成为所长助理,主管地质学,1901~1902年,负责区域和地层地质学部门。其后,他从事编制北美地质图等研究,直至1916年。1895~1902年,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地质报告,1907年亦在芝加哥大学作报告。1915年,担任斯坦福大学地质系系主任,1922年退休,成为荣誉教授。[3]为了与世界各地的地质学家同行保持联系,他几乎全部参加了1891~1933年的国际地质大会和1926~1939年的太平洋科学大会;还经常出席美国地质学会(1929年任主席)、美国哲学学会和美国国家科学院(1920年当选为院士)的会议。[2]
维理士有“地震专家”的称号[2],获得的荣誉包括1910年柏林大学的荣誉哲学博士学位、1910年法国地质学会的金质奖章、1929年哥伦比亚大学的荣誉科学博士学位、1933年比利时利奥波德二世十字勋章(the cross of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Leopold II)、1936年比利时荣誉勋位勋章(Legion of Honor)和1944年美国地质学会的彭罗斯奖章(Penrose Medal)等。[3]他曾广泛游历和考察过英国、德国、法国、匈牙利、俄罗斯、阿根廷、智利、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新西兰和埃及等国家和地区。[2]1949年2月19日,维理士逝世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市(Palo Alto)。
2 考察经过
1903~1904年,应美国古生物学家沃尔科特(Charles Doolittle Walcott,1850~1927)要求和支持而发起、由当时新成立的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资助,维理士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沃尔科特提出该考察计划的最初设想是进行寒武纪动物群的研究,并在李希霍芬著作中指出的前寒武纪岩层区域寻找化石;[4]通过中国东部和西伯利亚的地层、构造和地文的观察以及化石采集(特别是与寒武纪动物群相关的),开展东亚和北美西部地质的比较研究。[5]维理士在《友好的中国:在中国人之间徒步两千英里》(FriendlyChina:TwoThousandMilesAfootamongtheChinese)*该书是维理士基于在中国考察过程中的信件所写的游记。另外,考察过程和结果也见于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的年鉴。参见文献[4]。中,则把考察最初的主要目的归结为寻找最古老的三叶虫——“亚当三叶虫”(Adam Trilobite)。([6],XIII、3~4页)
2.1 前期准备
在考察计划实施后,维理士携沃尔科特的信函拜访了中国驻华盛顿公使梁诚*梁诚出使美国的情况,参见梁碧莹的《梁诚与近代中国》(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梁诚以礼相待,并为其取了中文名,还询问了考察的精确路线以确保中方配合,同时建议他向驻华盛顿各国公使通报这次考察的目的以及到中国后去拜访袁世凯。([6],XIII、5~7页)除了官方的协助,梁诚还参与了考察所绘制的直隶、鲁、晋、川、陕等省的地理地质图*该图册名为《中国地舆地质图》(Research in China: Geographical and Geological Maps),其封面、开篇的说明文字、地理图都附有对照中文,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考察中所绘制的地图对中国重要区域的精度和地形表现在当时都是独一无二的,因而获得了1910年法国地质学会的康拉德·马尔特·布戎金质奖章(the gold medal prize of Conrad Malte-Brun)。参见文献[6],第xiv、107页。上中文的准备,并亲自书写图册所配的描述文字。([7],XIV页)该地理地质图在1907年经由梁诚函送中国外务部,并分发至以上各省。[8]
随后,维理士选择了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基础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白卫德*“白卫德”为Eliot Blackwelder的自选中文名。参见黄汲清:《我的回忆——黄汲清回忆录摘编》,北京:地质出版社,2004年,第146页。(Eliot Blackwelder,1880~1969)作为此行的助手。[5]1903年7月28日,两人离开波士顿,作为美国官方代表参加8月份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地质大会([6],9、12页),然后乘火车经由西伯利亚前往中国。其间,他们在柏林受到李希霍芬的接待,并商讨了在中国可能面临的问题。李希霍芬认为中国可能不存在亚当三叶虫([6],20~21页),还对维理士的考察提出建议并完善其方案,且于1905年3月参与考察结果的讨论([7],XI页)。除了给出适宜调查研究地点的建议,作为柏林大学地理研究所所长,李希霍芬还提供研究所的设施供维理士使用,并和他多次会谈,达成共识。[9]
在托木斯克(Tomsk),维理士和白卫德见到了托木斯克理工大学教授奥布鲁切夫,后者确保中国人会像他上次旅行时同样友好。在离开托木斯克途中,维理士顺便观察了贝加尔湖及其周边的地势及构造,思考中国山川的年代特征和地壳不稳定性的问题。([6],33~34页)此外,维理士在沿途拜访英、德、俄等国使馆,处理考察的外交事宜。
维理士一行乘火车到达大石桥(今辽宁省营口市境内),再经由天津前往北京,以办理外交事宜。([6],36~40页)在去总督衙门拜会袁世凯的途中,天津茂生洋行(American Trading Company)经理、美国人易孟士(Walter Scott Emens,1860~1919)推荐了李三(Li San)作为此次考察的翻译。李三曾经是易孟士任天津“都统衙门”发审(Prosecuting Attorney)时的探长。维理士随后拜会了袁世凯,后者更详细地询问了考察预期的路线以确保沿途地方官员配合。其后,津海关道唐绍仪为维理士一行提供了由大运河前往山东的私人船艇。1903年10月9日,考察之行正式开始。([6],49~56页)
2.2 路线选择
1903年,维理士一行首先考察了山东和辽东。*这两处区域也是李希霍芬向维理士提议的有震旦系典型特征的地区,参见Bailey Willis,Research in China:Systematic Geology,Washington, D.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07, p.37。行程大致如下:从济南到青岛,途中详细对张夏、新泰两个地区进行研究;由青岛乘船返回天津,白卫德在李三陪同下前往辽东半岛进行考察,*白卫德和李三是以游客和随从的身份前往辽东的,维理士一行把首次出行考察地定为山东而非辽东是为避免引起俄罗斯的疑心。参见文献[6],第106页。维理士则返回北京。1903年底,美国地质调查所地形测绘师撒尔真*“撒尔真”是Rufus Harvey Sargent考察时所使用拜帖上的中文名。参见Rufus H.Sargent, Jan C. Hartman,Mapping the Frontier: A Memoir of Discovery from Coastal Maine to the Alaskan Rim,Camden:Down East Books, 2015, p.105。该书第104~135页“The China Expedition(1903—1904)”的章节是撒尔真对1903~1904年中国考察的记述。(Rufus Harvey Sargent,1875~1951)加入考察队伍并开展地形测绘工作,维理士前往南口和明十三陵为公使馆调查自流水问题,*该次京郊地下水的调查是受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1843~1907)请求、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所长授权下进行的,调查报告提交予康格,后者转交予美国国务院并提议美国地质调查所开挖水井。参见文献[4]。白卫德和李三从辽东返京。([6],106~125页)维理士在此期间做了考察最后阶段的准备:阅读苏格兰东方学家玉尔爵士(Henry Yule,1820~1889)译注的《马可波罗游记》(TheBookofSerMarcoPolo),参考马可波罗和李希霍芬的旅行路线;与《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会谈,并在其图书馆中浏览书籍;在比利时公使姚士登(Maurice Joostens,1862~1910)的引荐下拜会比利时铁路总工程司沙多(Jean Jadot,1862~1932),索要保定附近的铁道线路和地形轮廓,以便撒尔真由该处开始地形测绘;阅读法国汉学家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的著作《两汉时期的中国石刻》(LasculpturesurpierreenChineautempsdesDeuxDynastiesHan),查找其中五台山的记录。([6],111~112、119~120页)
由于俄国势力等不安因素,无法选择由南口经张家口进入蒙古的西北路线。因经费限制,长江峡谷和当时未被考察的西南高原的路线也不合适。维理士的最终选择是向西到五台山,沿途寻找震旦纪石灰岩中可能存在的亚当三叶虫,继而由华中到上海,在途中研究地球内部力量和河流作用下山脉形成的历史。([6],126~127页)更具体的行程选择既要避免李希霍芬的长途路线,又要与其相关联,以便比较并核对观察结果。从西安府到长江的路线也是以前几乎没人考察过的。1904年,考察路线涉及直隶、山西、陕西、四川、湖北等省,途经保定府、五台山、太原府、西安府、盩厔县(现名“周至县”)、石泉县、兴安府、平利县、巫山县、宜昌府等地。([7],XII~XIII页)
3 考察的地质学成果
该次考察的科学成果集中体现在《在中国的研究》一书中,该书分为3卷和图册。第一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按照地区以及地质时期的详细叙述,白卫德主要负责地层,撒尔真主要负责地形测量,维理士则负责黄土和地文学;第二部分包括白卫德的系统岩石学和动物学记录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美籍德裔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所作的汉语字音表。第二卷汇总考察结果的详细描述,并结合其他人的工作论及亚洲东南部的地质。第三卷则是沃尔科特、古生物地质学家韦勒(Stuart Weller,1870~1927)和古生物学家格蒂(George Herbert Girty,1869~1939)对所采集化石的古生物学研究及讨论。([7],XIII页)
3.1 地层及化石
维理士在山东发现了连续的上、中、下寒武纪化石种属,建立了寒武纪连续地层,在寒武系剖面底部发现有早古生代小油栉虫属(Olenellus)化石。在比较山东和北美阿巴拉契亚中部地区的地质历史后,他认为两者相似之处在于底部都有非常古老变质岩的不整合、数千英尺厚的粘土和石灰沉积岩系,每个岩系上段主要是石灰岩。在李希霍芬指出可能存在前寒武纪动物群的辽东,找到了永宁砂岩(Yung-ning sandstone),虽然其中没有找到化石,但是维理士判断其地层年代应晚于山东的下寒武纪地层。[4]
维理士根据所获得的化石,认为直隶和山西位于北纬38度的寒武纪地层和山东相似,都存在上、中、下寒武纪地体。在陕南北纬31度30分发现有数千英尺厚、含有稀疏化石的石灰岩层,并根据河流中砾石包含的小油栉虫属化石,断定其中更老的地层为下寒武系。在北纬31度长江上,古生界底部附近发现了巨大的冰碛,根据所发现的小油栉虫属化石判断其地质年代为下寒武纪。该冰碛显示在早古生代极低纬度存在冰川,这是环境变化的重要证据。在北纬30~40度,观察到贯穿山东、直隶、山西和陕西至少三千英尺厚、与上寒武纪地层相衔接的石灰岩,李希霍芬曾经认定其属于石炭系,维理士根据所发现的化石将其归入奥陶系。由此,和美国东部一样,东亚在寒武纪和奥陶纪之间出现了连续的地层和动物群。在陕南大宁河,采集到大量辛辛那提期(Cincinnatian age)的化石。维理士认为遍及华北的奥陶系和煤系之间广泛存在不整合现象。[4]
根据李希霍芬和俄国探险家的工作,亚洲古老的结晶片岩和侵入火成岩产状(occurrence)构成了明显分层的岩系之下的基底杂岩。维理士详细观察了所含的几种片岩、片麻岩、花岗岩和基性侵入岩之间的关系,并在山东、直隶、山西和陕西等地采集样本,进行岩相学研究。五台山和毗邻山脉由从基底杂岩到煤系地质年代各异的岩石组成。在杂岩和寒武系的基底之间有两个由李希霍芬描述的岩系:较古老的“五台片岩”和较年轻的“下震旦系”。在考察上述山脉时,更详细地确定了这两个岩系与上下岩系的关系,并指明了每个岩系的组成。他发现五台片岩包含源自更古老沉积地层中的石英砾石,而在下震旦系和上震旦系(寒武系)之间发现明显而广泛的不整合面。因此,他将下震旦系与寒武系分离,但在该地层的石灰岩和页岩中没有发现化石。[4]
3.2 黄土研究
维理士一行观察研究了华北的黄土层。《在中国的研究》一书讨论了西北第四纪黄土层,着重讨论了忻州期中国黄土的早期理论、物质来源、搬运和物理特性等方面。([7],VI页)他认为,在地形发展时期的某一阶段,宽阔的河谷遍布冲积物,后来地表严重翘曲,河流改道,冲积物部分重新分布,而部分停留在泛滥平原翘曲所产生的小山上;更新世的气候状况促成了风和河流的交互作用,根据山脉历史,黄土积累年代应该在早更新世。途中的观察结果证实黄土的情况和所在地区的地文史相一致,与美国的类似沉积相符合;风的筛分(sifting)作用造成了其微细和统一的质地,其独特的结构或许是由于尘土层(dust bed)中水的毛细运动的物理效应,黄土可能是黄河等河流的沉积物积累而成。维理士对李希霍芬的观点进行了补充:李希霍芬所强调的风的因素在产生黄土独特质地和粉尘局部分布上最为重要,而风和流水都参与了黄土的搬运,流水在搬运上起的作用更大。[4]
李希霍芬用黄土(loess)一词描述以质地微细、垂直结构为特征的大范围厚层黄色土壤覆盖物,并根据其分布得出中亚沙漠的粉尘在风的搬运下形成黄土的理论。维理士则用取自黄土寨(Huang-t’u-chai。按:当为今山西太原市阳曲县黄寨镇)的“黄土”(Huang-t’u)描述广阔的黄色土壤沉积。他的黄土层以李希霍芬定义的黄土为主要成分,含有砂土和砾石、碳酸钙结核,以及大量从地下水中摄取的盐类、陆生贝类和骨骼;广泛分布于直隶、山西、陕西一带山谷以及某些毗邻的山上,构成中国东部大平原;时有分层,具有粘土沉积特有的垂直节理。([7],183~184页)
维理士认为黄土是由化学性质稳定的物质构成:石英、硅酸铝和氧化铁,伴生以可溶性碳酸盐、硫酸盐以及碱和碱土的氯化物;来源于地下水的盐类不断更新,使得黄土异常肥沃并使其中有大量的碳酸钙结核分布。李希霍芬以草根腐烂所留下的孔隙解释黄土垂直节理的成因,维理士认为这不足以解释不同环境下黄土沉积的结构。垂直节理不依赖于沉积的环境、地点和年代,质地和固结作用似乎是其发育的决定因素;将重力、毛细吸引和胶结作用通过湿润的介质和精细的土壤颗粒所引起的物理和化学活动过程纳入考虑,地下水中的盐类反复析出和溶解,产生了李希霍芬所认为造成黄土垂直裂理的垂直毛细管质地,形成了自我支撑的单元以维持陡峭的黄土墙结构。([7],249~254页)
维理士一行对中国东部大平原的冲积黄土层、山东半岛周边随风而来的产物以及从直隶保定府到灵山镇沿途进行观察。他在“北京湾”(Bay of Peking)*“北京湾”是维理士所描述的北京所在北纬40度中国东部大平原伸入群山之中所形成的类似海湾的部分。参见Bailey Willis, “Artesian Water Conditions at Peking, China”,Year Book (No. 4, 1905), Washington, D.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06, pp.215~220。进行了特别的考察,并在那里首次确认了河流在黄土层分布中占有主导地位,而黄土层沉积条件与华北及亚洲中部的地文关系密切,其起源和发育开始于忻州期之初。([7],186、196页)他还认为黄土的年代从晚上新世或者早更新世至今,沉积开始于第四纪或前第四纪;在干湿气候交替的亚洲中东部,风力在干燥季节和广阔的平原上更加有效,而水力在降水季节和河谷中更加有效,岩石崩解的产物被风力和水流交替反复搬运和分选,最终成为李希霍芬描述为黄土的细微粉尘,其间夹杂有一些洪水带入的粗砂土和砾石。([7],184~185页)
庞佩利把黄土层归为湖泊或阶地沉积,维理士将黄土层视为河谷沉积(valley deposit),认为河流是黄土层广泛分布的主要因素。与李希霍芬的观点——中国的山体增高是在黄土覆盖之前——不同,维理士得出黄土层之下的壮年地形外观只能在相对低的海拔发育,山脉特征应该是在黄土沉积后的地质时期形成的结论。([7],242~244页)在庞佩利和李希霍芬观察的基础上,他认为第三纪的北台期和唐县期亚洲气候温和潮湿,北部海平面上高度适中的区域经受侵蚀,地形和气候条件都有利于岩石风化产物的长期积累和广泛分布;接近第三纪尾声的亚洲内陆变得异常干冷贫瘠,赋予风以筛分的力量;旱季和雨季交替,风和河流交互作用,使风成产物的黄土和河流产物的砾石、砂土混成一体。([7],245~249页)
3.3 地文研究
维理士的考察开创了中国地文期的研究[10]。从保定府到西安府一带地文期被划分为:经历漫长侵蚀、形成以圆形的五台山顶峰为代表的近似准平原地形的北台期;与以前寒武纪片岩及古生代地层的壮年表面为代表的地形发育阶段相符合、以大量残丘相联系的宽阔谷地为特征的唐县期;以直隶、山西两省内加积作用为特征、黄土层早期沉积堆积为主的忻州期;涉及地表翘曲和正断层作用的山脉生长、以高山和深峡地形为特征的汾河期。([7],236~238、242、256~257页)从陕西南部渭河河谷、秦岭、汉水河谷、九龙山到扬子江一带地文期被划分为有显著地势壮年地形的秦岭期和以峡谷为特征形式的扬子期。([7],336页)
维理士一行在山东地文方面进行了翘曲以及正断层的影响的研究。([7],III页)对西北沿途黄土盆地进行了特征描述,并考察沿途的地势,以说明黄土层的分布和河流的排布。他认为忻州黄土盆地的特征主要是翘曲和断层的结果,而侵蚀作用则居于次要地位。([7],210~214页)忻州期以形成华北主要山岳形态特征(orographic features)的翘曲结束,其后开启了下一时期——汾河期。他还认为黄土期在时间上等同于忻州期和汾河期,而正确地诠释地文史可以为讨论黄土特性提供新的视角。([7],242页)
3.4 构造地质学研究
维理士观察了山东地区泰山杂岩的构造、震旦系的构造,以及新泰地区和鲁西的正断层;在直隶主要研究了灵山盆地的构造地质学;对山西的考察包括前寒武纪和古生代沉积的构造、正断层,以及变形幕(episode of deformation)的年代;长江中游地区的构造研究涉及宜昌到巫山县的扬子剖面以及九龙山剖面。([7],II、III、V、VII页)根据美国当时的地形研究和在中国的观察结果,维理士认为与北美的山脉历史相似,中国最古老的地形面(topographic surface)曾经部分是丘陵地区(hilly region)、部分是近乎水平的准平原,在第三纪前期或中期稍微升到海平面以上,后来地形面断断续续地翘曲,以山西霍山和陕西华山、长江大峡谷和向北延伸至黄河的山区为代表的东亚巨大山脉都是在现代地质时期发育的。[4]
考察队一行在五台山发现了逆掩断层,证实了洛齐和奥布鲁切夫的祁连山、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都有南或南东方向的逆掩断层构造的观点;维理士认为西伯利亚地台南移产生“水平挤压”,造成了我国向南突出的弧形大陆构造线分布格局;中元古代西伯利亚强烈地向南推进,古地中海在中生代闭合,喜马拉雅山和西藏高原在新生代隆起抬升。[11]维理士将兴安岭解释为上新世和第四纪(更新世)期间一系列现代地球运动所形成的巨大单斜褶皱的结果;他对地壳均衡说坚信不疑,认为因为海洋之下岩石圈更深层密度更大,重物质(heavy material)的“海底扩张”(suboceanic spread)挤压大陆基底,而外层相对延迟导致向海洋的明显运动,亚洲巨大的地壳运动是大陆之下地壳深层自南向北的侧向扩张(lateral spread)造成的效果。[12]
4 维理士对中国地质学的影响
由于合理的计划和分工,在李希霍芬等人所奠定的中国地质轮廓和地质学新的发展基础上,维理士相对短促*维理士一行在1904年6月20日乘船离开上海前往旧金山,在华逗留时间大约9个月,实际考察时间不到8个月。参见文献[4]。的考察也获得了相对精细和丰富的成果,对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汲清阅读了《在中国的研究》之后,称赞“真有令人‘五体投地’之感”,“不厌百回读”,该书第二卷抓住了中国乃至亚洲大陆构造的要点,第三卷的寒武纪动物群研究使“中国寒武纪地史由此打下基础”。[13]其考察成果屡为中国早期地质学家参考和引用,部分著作也被选作地质学教学参考书或被翻译成中文,而随着中国地质工作的开展,中国的地质学也在对其考察成果补充和纠正的基础上不断得到发展。除了地质研究对中国地质事业产生影响,维理士与中国地质学界也有一定的交流和互动。
4.1 中国地质学家对其研究的参考与借鉴
维理士在中国的考察成为中国地质研究的重要基础,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早期中国地质学术研究的实地考察记录、汇集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生地质工作成果的《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该书分别从地质系统、火成岩、构造、矿产等方面讨论和总结了实习期间的地质观察结果,参考了维理士在中国的考察成果,并在书中有广泛的引用。
通过地质考察,地质研究所师生继承并印证了维理士的部分成果。比如:在泰山及徂徕山一带的实习遵从他对泰山系的命名;对火成岩种类和时代的系统论述以他在各地发现和命名的火成岩作为参照和比较;在山东、山西和直隶的观察进一步印证了他对元古界的五台系和滹沱系的划分,以及对五台山地域不整合岩层的解释;地质研究所的实习观察结果认为他在五台山所见的太古界与元古界的不整合最为详尽,将五台系划分为不整合的三层褶皱是其首次发现。([14],3、24~30、32~33、37~39页)
维理士的工作对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地质学起到了示范作用,《在中国的研究》一书成为地质学发展初期的教学参考书,其中的内容也被纳入到一些教材之中。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图书存储表”中“地质学类”即写明“威烈士氏中国考察记,附图二册,英文,二部共八册”([15],29页);北京协和女书院校长麦美德(Luella Miner,1861~1935)所著的地质学教材《地质学》(TextBookofGeology)即基于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等的考察,书中使用了维理士考察的地质图,并引用他“泰山石系”和滹沱系的命名([16],19、20、23、24页);谢家荣在《地质学教学法》中将该书列为高等师范学校采矿科地质学的参考书以及地质旅行之前的参考报告[17]。
此外,维理士的部分文章也被翻译出版。孟昭彝的《地球内部之构成》译自其《地质构造》(GeologicStructures)*该书1934年的版本中可以找到与译文中前四部分对应的章节,第五部分没有找到对应部分,该文章尚不清楚翻译自哪一版本。参见Bailey Willis,Robin Willis,Geologic Structures,New York:McGraw-Hill, 1934, pp.401~408。的章节“Constitution of the Earth”[18]。周晓和的《亚洲之皱摺:山脉之研究——康藏高原及四川盆地之成因》译自其文章“Wrinkles of Asia”*Bailey Willis,“Wrinkles of Asia,”The Scientific Monthly, 1939, 49(5): 431~451.,并称《在中国的研究》“是为地质及古生物学界重要之文献”,“此文研究亚洲大陆之变化及山脉之成形甚属精确”[19,20]。另外,维理士著作中有关中国矿产的研究也成为引用对象,如王宠佑《中国的矿藏》(The Mineral Resources of China)曾引用其同名文章*Bailey Willis,“Mineral Resources of China,”Economic Geology, 1908, 3: 1~36, 118~133.中对中国矿藏的描述[21],而严庄编译的《矿物鉴定法絜要》在“编者识”中也引用其对中国矿产储量丰富的描述[22]。
4.2 中国地质学家对其成果的补充与纠正
虽然维理士在中国的地质工作对中国早期地质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成为参考和引用的对象,但是,由于考察时间、范围有限,所得出的某些结论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笼统甚至错误。随着地质研究的开展,这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相应的工作成果也被不断补充和纠正。
对维理士考察结果的补充和纠正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中有所体现。比如:地质研究所师生在直隶和山东等地发现的纺锤虫石灰岩层以及直隶、河南、山东和山西等地发现的燧石石灰岩都与南方海相石炭纪十分相似,他们认为南北岩石并非不相关,维理士分石炭纪沉积北为陆相、南为海相也并非绝对;在北方的观察印证了他的北方石炭纪岩层厚度较南方大为减少的观点,并进一步认为石炭纪岩层自长江越往北越薄,自北京往西北直至大同一带,则中生界岩层直接与寒武纪接触,石炭纪岩层几乎不可见;维理士将李希霍芬的南口系从震旦系中分离而归于新元古界,但是尚未提及东冶灰岩(原文为“东峪灰岩”)与豆村板岩(原文为“窦村板岩”)之间有无间断,而在获鹿县的实习则发现了处于两者之间、洛齐所谓的南山系。([14],9、14、38、44页)另外,后来中国地质学家的工作也在地层、黄土和构造等方面对维理士的研究有不同程度的补充和纠正。
4.2.1 地层划分
由于维理士的考察行程比较急促,无法进行广泛而细致的研究,考察又偏重前寒武纪和古生代地层,有些地层又缺乏古生物化石证据,所以难免存在地层划分笼统甚至错误的问题,这在维理士对震旦系和五台山地区的地层划分上表现尤为明显。
在李希霍芬的建议和其考察成果的基础上,维理士对其震旦系做出了修改,形成了自己对震旦系新的定义,这个笼统的定义突出表现为寒武系和奥陶系的界限不清。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在《震旦系》(The Sinian System)中总结了李希霍芬和维理士的震旦系、中国地质学会重新定义的震旦系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震旦系,认为维理士的震旦系包括了华北寒武纪和奥陶纪岩系,如果“寒武—奥陶系”与震旦系含义相同,则必然会被再度划分而遭到废止。[23]李四光讨论了“寒武—奥陶系”石灰岩中的地层间断的性质和范围后,认为维理士将李希霍芬描述的“Kohlenkalk”对应的石灰岩层整合于华北震旦系的最上层,这与他在安徽北部山区观察的事实不符,建议引入国际通用的术语“寒武系”和“奥陶系”取代中国的“寒武—奥陶系”。[24]
维理士对五台山地区的研究成果虽然一度成为地层分类的重要依据,但是同样存在划分错误。孙健初研究山西太古界地层后,没有观察到维理士描述的晋南的最古老岩石。在许多地方的古生代地层下,他认为维理士观察并描述的泰山杂岩的某些部分可能属于寒武纪。在观察的基础上,他证明维理士观察的五台山东南斜坡的结构并不复杂,而其有关年代可能有误。[25]杨杰将在五台山西北坡观察到的绿片岩定为台怀层(Série de Taihuai)对应于维理士的Aw层(zone “Aw”)和西台层(Sitai Series),将在五台山中部大范围的石英岩和片岩定为南台层(Série de Nantai),以对应维理士的南台层(Nantai Series)和豆村板岩(Totsun Slates),并以白头庵层(Série de Paitouan)取代维理士的An层(zone “An”)和东冶灰岩(Tungyü Limestone)。[26]王曰伦所带领的五台队的集体调查则对维理士所定的五台纪予以否定,重新划分了五台山的地层系统,并分析了其地质工作错误的根源。[27]
4.2.2 黄土及构造
在黄土研究方面,后来的研究也对维理士的考察结果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叶良辅在提及中国北部黄土问题时,指出李希霍芬和维理士认为黄土层厚度极大,实则只是小部分的黄土填充在上新统粘土沟壑中,再经历侵蚀而成的沟谷所呈现的厚层黄土现象。[28]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在对李希霍芬和维理士所描述的几个华北黄土剖面进行观察研究后,认为其下部并非真正的黄土,而是第三纪三趾马红粘土沉积。[29]巴尔博(George Brown Barbour, 1890~1977)比较了维理士和李希霍芬的黄土,认为维理士所命名的黄土包括红粘土、真正的黄土和带有再积黄土的砾石,即更广泛意义上的黄土,而其沉积时间间隔跨度过长,且在其范围内存在气候变化反差强烈的间隔和分期。[30]
与地层划分类似,维理士对中国地质构造的某些观察和结论也存在问题。翁文灏称他的科学理解可作为山脉研究的参考,但因考察范围有限,其推论不免有缺误,如漏略贺兰山、阴山、兴安岭等山脉,而长江流域山脉则相对简略。[31]王竹泉通过对太华山、汾河和阴山等地断层的观察研究,对他关于黄河发育的学说提出异议,认为其有关山陕之间地盘因太华山断层全部南倾的假定是错误的。[32]李春昱在渭北调查煤田时,对他在秦岭和平原之间落差很大的正断层的描述抱有疑问,认为他在华山潼关以西至华县观察到的很陡的正断层有待商讨,而其所判断的渭河断层发生时间则应该提前。[33]
5 维理士与中国地质学界的交流
1926年10月30日,第三次泛太平洋学术会议(The Third Pan-Pacific Scientific Congress)在日本东京举行,为维理士与中国地质学界的交流提供了机会。维理士作为美方代表参会,并担任11月2日“成矿时代及太平洋区域之地质统一”分会后半段的主席。其参会论文涉及“客利福尼亚及智利地震区之异同”(“成矿时代及太平洋区域之地质统一”分会)和“太平洋地质构造论”(11月3日“太平洋区域之地质构造,地盘升降,地震重力及地形测量”分会)。[34]
翁文灏作为中方代表参会*中方与会人员共12人,包括翁文灏、秦汾、胡敦复、任鸿隽、薛德焴、竺可桢、胡先骕、陈焕镛、王一林、厉家福、沈宗瀚、魏嵒寿。,认为维理士“为研究中国地质最有成绩之人”,并表示“与此耆年宿学共论一堂,深以为欣幸焉”。翁文灏在“成矿时代及太平洋区域之地质统一”分会,提交有《中国东部地壳运动》一文。该分会的结论为侏罗纪末沿太平洋各地均有造山作用,这与维理士等欧洲学者从前对中国的研究结果不符,却和翁文灏等在中国比较细致观察的结果以及加拿大、美国西部、新西兰的情况相符合。另外,在11月2日“太平洋区域石炭及石油之地质”分会,李四光提交了论题“中国北部古生代含炭层之时代及其分布”(翁文灏代为宣读),其纺锤虫化石研究认为维理士在山东和山西取得的化石不应单纯地归为上石炭纪。[34]
会后,维理士再次来到中国*维理士还有其他的来华记录。1937年,他曾为菲律宾政府考察矿产,7月份到过我国台湾岛,在工作结束时在我国与其妻团聚。参见“Willis Makes Investigation of Minerals”,The Stanford Daily(Stanford, May 25,1937);“Geologist to Talk on Foreign Tour”,The Stanford Daily(Stanford, November 08, 1937)。维理士在台湾由合欢山横跨中央山脉作全岛观察,其工作也涉及宜兰一带地区,不过并未发表报告。参见何春荪:《过去五十年内台湾地质之研究》,《地质论评》,1947年,第12卷第5期,397~424页。。12月6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大讲堂做了“中国与日本地质之比较”的演讲[35]。12月中国地质学会*作为对中国地质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地质学家,维理士和沃尔科特在1924年中国地质学会第二次年会上当选为通信会员,并多年担任此职;1933年白卫德亦当选为通信会员,并多年任职。参见1924年中国地质学会“第二次年会记事”以及1926、1932~35、1942、1947等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的“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录”。第二次常会上,他做了同样题目的报告[36]。会上李四光宣读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Evolution of the Earth’s Surface Features),维理士和荷兰地质古生物学家布劳沃(Hendrik Albertus Brouwer,1886~1973)参与了该论文的讨论[37]。在京期间,维理士曾在巴尔博陪同下考察北京周边[38]。12月13日,随美方泛太平洋学术会议参会代表由天津乘船至上海,受到中国科学社的招待[39],并访问了沪江大学[40]。
另外,维理士与一些赴美留学和访问的中国地质学家也有直接或间接的交流。张伯声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经受到维理士学术报告中有关中国考察内容的吸引,1929年转学至斯坦福大学地质系。[41]1940年,阮维周曾经会晤维理士和白卫德*维理士提议阮维周在芝加哥大学开学前到美国南部访问大规模开发的油田,并为他联络好了石油公司。参见杨翠华:《阮维周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19~20页。,并在他们以及古生物学家钱耐(Ralph Works Chaney,1890~1971)的介绍下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石油地质。[42]
6 结 语
对于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的中国地质学研究来说,维理士的考察成果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参考材料,其研究工作也对中国地质学的早期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无论是实地考察还是教学参考书,早期的中国地质学都存在对其研究成果的广泛的引证和借鉴。但同时因为其考察的时间短促、范围有限,考察所得到的结论难免有错,这些问题也被后来的地质工作不断地补充和纠正。中国的早期地质研究正是在以他为代表的外国地质学家的工作基础上,才逐渐发展完善的。
从1903年来华考察到1949年逝世,维理士几乎一直和中国的地质学发展保持联系:1903~1904年在华考察地质、1907年《在中国的研究》出版、1924年担任中国地质学会通信会员、1926年参加第三届泛太平洋学术会议及会后再度来华,以及其间对赴美访问的学者和留学生的影响,中国地质学在这近半个世纪中经历着本土化的过程,维理士的中国地质研究及其影响正是中国地质学过渡和发展阶段一个侧面的反映。
致 谢 潘云唐教授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九辰研究员审阅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1 Willis B.AYanquiinPatagonia:ABitofAutobiography[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2 Blackwelder E. Bailey Willis, May 31, 1857-February 19, 1949 [M]//BiographicalMemoir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61, 35: 333~350.
3 Willis, Bailey [M]//TheNationalCyclopaediaofAmericanBiography.New York: James T. White, 1951, XXXVII: 53~54.
4 Willis B. Geological Research in Eastern Asia [M]//YearBook(No. 3, 1904).Washington, D.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05. 275~291.
5 Report of Executive Committee on the Work of the Year [M]//YearBook(No. 2, 1903). Washington, D.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04. xv~lii.
6 Willis B.FriendlyChina:TwoThousandMilesAfootamongtheChines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7 Willis B, Blackwelder E, Sargent R H.ResearchinChina:DescriptionTopographyandGeology[M]. Washington, D.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07.
8 学术新报[J]. 理学杂志. 1907, (4): 71~78.
9 Willis B. Studies in Europe [M]//YearBook(No. 4, 1905). Washington, D.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06. 194~203.
10 黄汲清. 中国地质科学的主要成就[J]. 中国科技史料, 1983, 4(3): 1~11.
11 吴凤鸣. 1840至1911年外国地质学家在华调查与研究工作[J]. 中国科技史料, 1992, 13(1): 37~51.
12 Gregory J W. The Carnegie Expedition to China [J].TheGeographicalJournal, 1909, 34(1): 73~74.
13 黄汲清. 民国纪元以前外国地质学者在中国之工作[J]. 思想与时代, 1947, (49): 34~36.
14 章鸿钊, 翁文灏.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M]. 北京:京华印书局, 1916.
15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M]. 北京:京华印书局, 1916.
16 麦美德. 地质学[M]. 北京:北京协和女书院, 1911.
17 谢家荣. 地质学教学法[J]. 科学, 1922, 7(11): 1204~1213.
18 维理士. 地球内部之构成[J]. 孟昭彝,译. 河南省地质调查所汇刊, 1937, (5): 33~38.
19 维理士. 亚洲之皱摺(上):山脉之研究——康藏高原及四川盆地之成因[J]. 周晓和,译. 康导月刊, 1941, 3(8/9): 1~6.
20 维理士. 亚洲之皱摺(下):山脉之研究——康藏高原及四川盆地之成因[J]. 周晓和,译. 康导月刊, 1942, 3(10/11): 50~59.
21 Wang C Y.The Mineral Resources of China [N].TheWeeklyReviewoftheFarEast, 1921- 12- 24: 150.
22 严庄. 矿物鉴定法絜要[J]. 科学, 1916, 2(3): 301~309.
23 Grabau A W. The Sinian System [J].BulletinoftheGeologicalSocietyofChina, 1922, 1(1~4): 44~88.
24 Lee J S.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a Stratigraphical Break in the Cambro-Ordovician Limestones of Northern Anhui, and Its Bearing upon the Systematic Classification of the Cambro-Ordovician Strata [J].BulletinoftheGeologicalSocietyofChina, 1922, 1(1~4): 89~96.
25 孙健初. 山西太古界地层之研究[C]//孙健初. 孙健初地质论文选集.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1998. 1~22.
26 Yang K. Note Préliminairesur la géologie du Woutaichan (Chanhsi) [J].BulletinofGeologicalSocietyofChina, 1936, 15(2): 261~268, 286.
27 五台队集体调查. 五台山五台纪地层的新见[J]. 地质学报, 1952, 32(4): 325~353, 374~384.
28 叶良辅. 北京西山地质志[J]. 地质专报, 1920,甲种第1号: 1~92.
29 Andersson J G. Essays on the Cenozoic of Northern China [J].MemoiroftheGeologicalSurveyofChina, 1923, A(3): 1~152.
30 Barbour G B. The Loess of China [J].TheChinaJournalofScienceandArts, 1925, 3(9): 509~519.
31 翁文灏. 中国山脉考[J]. 科学, 1925, 9(10): 1179~1214.
32 王竹泉. 黄河河道成因考[J]. 科学, 1925, 10(2): 165~173.
33 李春昱.对于“渭河地堑”的质疑[J].地质学报,1956, 36(4): 405~416.
34 翁文灏.第三次泛太平洋学术会议中地质学会议述要[J]. 科学, 1927, 12(4): 496~506.
35 本校布告[N]. 北京大学日刊, 1926- 12- 04: 1.
36 Proceedings of General Meetings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Held on October, November and December 1926 [J].BulletinoftheGeologicalSocietyofChina, 1926, 5(3/4): 197~200.
37 Lee J 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Evolution of the Earth’s Surface Features [J].BulletinoftheGeologicalSocietyofChina, 1926, 5(3/4): 209~262.
38 张雷. 巴尔博与中国地质学(1921~1935年)[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5, 36(3): 316~324.
39 中国科学社招待美国学术界[N].申报, 1926- 12- 18: 10.
40 Famous Professors Speak to Shanghai College Men [N].TheChinaPress, 1926- 12- 22: 3.
41 王战. 大地构造学家、地质教育学家张伯声[M]//黄汲清, 何绍勋.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1: 245~259.
42 地质界消息[J]. 地质论评, 1941, 6(5/6): 439~461.
Bailey Willis’ Geological Research and His Influence in China
CHEN Ming1,2, HAN Qi1
(1.InstitutefortheHistoryofNaturalSciences,CAS,Beijing100190,China;2.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49,China)
Bailey Willis, an American geologist, who came to China on an expedition in 1903, carried out geological research on stratigraphy, loess, physiography, tectonics, etc. The results of this expedition were published inResearchinChina, which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geology in China. In addition to the depiction of the proces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expedition,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citation, addition and correction of his research by early Chinese geologists, illustrating the utilization of his works in China,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him and Chinese geologists, and thus renders a reflection of the early development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geology in China.
Bailey Willis,ResearchinChina, geology, loess, localization
2016- 03- 18;
2016- 06- 25
陈明,1986年生,辽宁西丰人,硕士研究生;韩琦,1963年生,浙江嵊州市人,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地质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项目编号:KZZD-EW-TZ-01)
N092∶P5-092
A
1000- 0224(2016)02- 0213-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