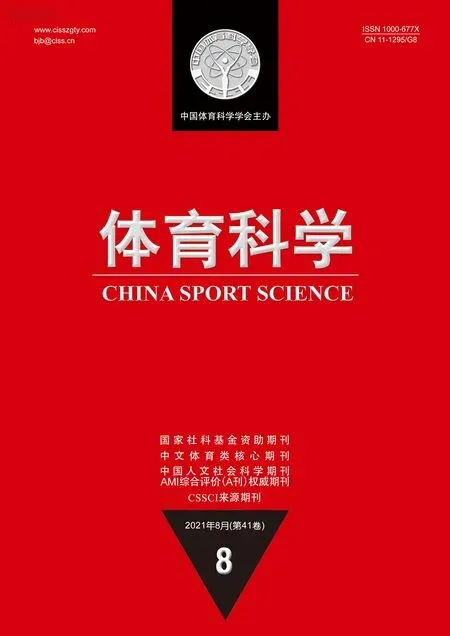民族救亡与体育转型:对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体育发展的历史审视
张爱红
民族救亡与体育转型:对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体育发展的历史审视
张爱红1,2
运用文献资料调研等方法,以整体历史观的视角,纵向从局部抗战时期和全面抗战时期两个阶段,横向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3个区域,全面地梳理出该时期我国体育发展的历史脉络,发现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体育呈现出参与规模大、形式多样,军事色彩浓厚和注重体育发展的理论探索等特征。在研究分析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体育发展的基础上,厘清这一时期体育发展在我国体育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历史定位及其为新中国体育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思想理论基础。
体育史;抗日战争;民族救亡;体育转型
1 抗日战争期限界定
抗日战争,国际上称之为“第二次中日战争”。关于抗日战争的起止期限,史学界主要有两种说法:1)“八年抗战”说,即抗日战争开始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结束于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举行日本投降仪式[8]; 2)“十四年抗战说”, 即始于 1931年“九一八事变”,结束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12]。
本文从体育参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角度出发,采取“十四年抗战说”,并分两个阶段对该时期我国体育的发展进行论述,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局部抗战时期和“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全面抗战时期。
2 抗战时期体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2.1 民族危机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随着国力的增强而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甲午战争”后更坚定了其“大陆经略政策”,中国成为其对外扩张的主要目标。20世纪20年代,经济危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而中国却因为农业经济和白银货币制而躲过了那场全球性经济萧条[8],国民革命也发展迅速。在英、法、美等国“绥靖政策”的纵容下,德国、意大利、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日益嚣张。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出台《对华政策纲领》,炮制了先占领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然后侵占整个中国的扩张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出兵中国东北,标志着《对华政策纲领》和《田中奏折》战略开始实施[17],也标志着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开始。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2.2 中西体育冲突
鸦片战争后,我国开始引进西方现代体育。洋务运动中引进了西式兵操,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规定从蒙养院到高等学堂“各学堂一体练习兵操,以肆武事”;1912-191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壬子癸丑学制”,规定从初小到大学各级各类学校开设体操科,推行军国民体育;1922年,教育部又颁布“壬戌学制”,改“体操科”为“体育科”,学校里废除兵操,代之以田径、球类、游戏、体操等主要内容,确立了新的体育课程体系,西方现代体育在学校中得以推广。
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引起国人对中国传统体育——武术的重新审视,主张以武术为学校体操课内容,以取代西式兵操[40]。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四分五裂的状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惨败更使中国人对军国民体育丧失信心,加之大众对西方“选手”体育的不满,体育界也出现了两次用近代科学理论来解释和改造中国武术以抵制西方体育的思潮[46]。
纵观20世纪30年代之前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可以看出,虽然有政府的支持、基督教青年会和留学生的推广,但是在实践中,受中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与西方现代体育对场地设备的要求所限,西方现代体育活动主要局限在东南沿海和一些大城市,内地和农村依然沿袭传统的发展逻辑在演进。
2.3 国民体质羸弱
至20世纪30年代,尽管西方的健康观念已经被部分中国人所接受,西方体育也在中国学校得以传播,但是,由于中国“君子无戏”的传统和抽大烟、赌博等陋习根深蒂固,加之社会动荡,所以国民体质极端低下。郝更生在1927年《体育》杂志发表的《十年来我国之体育》一文提到“大多数群众,皆沉没于昏天黑地之中。以言气概,则萎靡不振,懒态横生。以言体质,则心跳气促,迎风欲舞”[14]。对在校学生的体质测试则以确凿的数据印证了当时国民体质羸弱的事实:“1930年,浙江省教育厅对全省中小学生进行健康测试,抽查学生4 804人,结果只有26人算得上真正健康,健康比例只有千分之五”[2]。能够接受体育教育的中小学生体质尚且如此,社会上老弱妇幼、贪官赌徒的健康状况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航空学校招考记录中体育及格的人数不足1%[5],各地征兵中身体及格者不足30%[36]。
自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现代体育传入中国并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社会活动家的推动。但是,由于西方现代体育对体育场馆器械要求较高,只能为经济较发达的大城市中上层社会所接受;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中主“静”的观念根深蒂固,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广大地区的体育依然沿着传统养生的脉络在发展,国民体质羸弱。
3 抗战时期中国体育的发展
3.1 局部抗战时期体育的发展(1931-1937)
3.1.1 中国体育界的民族自觉
“九一八”日本侵华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尚武意识,学界开始对体育的发展问题和体育的功能进行深入的讨论。1932年,吴蕴瑞在《天津体育周刊》上发表了《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对当时认为刘长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为耗费钱财的谬论进行反击;1933年10月,《勤奋体育月报》创刊词疾声呐喊:“强邻压境,国难当头……积极的注重国民体育训练,准备疆场强劲的战士,养成耻雪保国的健儿……这是今后全国体育界的动向,也是全国体育界的责任”[39];1934年,董守义呼吁体育“不要忽略所应负有的使命,务使体育运动能够推及到广大的群众中去……整个民族的前途,将亦踏上强盛的地位”[6];同年,陈敦正在《国术周刊》撰文《复兴民族与提倡国术之意义》,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1936或1939年爆发,提出“奋兴武术,提倡国术,以锻炼全国的同胞,强健全民的体力,唯其如是,才可以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国民族,应付世界危机”[1];1935年,刘慎旃在《勤奋体育月报》上直接以“体育救国论”为文章标题发表体育救国的见解[22]。邵汝干则呼吁“树立国家强盛的根基,负起时代的新使命,来建设新中华的自我本位的体育”[31];程登科也提出“利用军警权力辅助民众体育使全民体育化”[3]的议题;程登科在1936年《勤奋体育月报》上发表了《我们应否提倡中国的民族体育》一文后,王健吾于1937年也在《勤奋体育月报》撰文《复兴民族与提倡民族体育》与程登科进行商榷,提出体育的民族自尊问题。妇女体育界领袖高梓则在《中国女子体育问题》一文中驳斥了社会上流行的“体育不适于女子”的说法,号召通过体育来塑造“奋发图强的妇女,能尽天职的妇女,能工作能耐劳的妇女,勇敢有为的妇女,能为国家奋斗为民族牺牲的妇女”[9]。
在民族危机面前,体育界人士自觉担当起抗日救亡的责任,他们从国家民族的高度探讨体育发展路径问题,体现了高度的民族自觉。通过长达6年的大讨论,虽然体育界对于采取何种手段发展中国体育仍然存在分歧,但是体育对于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具有重大意义方面取得了共识。这次大讨论客观上推动了国人对于中西方体育的深入审视和对于体育发展本身的反思,排除了西方现代体育在中国传播的障碍,也开启了中国传统体育趋向科学化发展的思路,有利于中国传统体育的现代化转型。
3.1.2 体育教育的发展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结束了国内军阀混战的局面,从客观上来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10年,国民党统治区的体育教育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1928—1937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学校体育的法令、法规,1929年的《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1932年的《小学法》《中学法》《中等学校特种教育纲要》《师范学校法》和《职业学校法》。根据国民政府的教育法令,教育部制订公布了相应的法规,如1929年的《大学规程》;1931年的《专科学校规程》;1933年的《小学公民训练标准》《职业补习学校规程》;1935年的《师范学校规程》;1936年的《修正小学规程》、1937年的《小学普遍课外运动试行办法》《初级中学童子军管理办法》《中等学校强迫课外运动试行办法》等[32],以保证体育课程在各级学校的开设。1929年《国民体育法》第6条规定,高中及以上学校“体育为必修科”,无体育课成绩不得毕业。1932年公布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规定,专科以上学校体育课“每星期两小时,不及格者不得升级或毕业”。在体育师资培养方面,体育专科学校在1931—1937年由12所增加到29所[13]。
中国共产党于1934年建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后设置文教委员会,监管边区学校体育、儿童团体育的开展。在体育人才培养方面,陕甘宁边区通过开办体育系、举办脱产体育培训班和不脱产体育短训班3种途径来满足体育人才的需求。
3.1.3 社会体育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比较完备的体育立法来推动社会体育的发展。1929年,《国民体育法》第1、2、3、4、5、7条对社会体育发展的目的、主管机构、场地设施、体育社团组织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1932年2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规定各级民教馆设立健康部,主管体育卫生事务。同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规定,各省、市体育场的面积不少于80亩,县体育场面积不少于30亩,儿童乐园应有满足儿童兴趣的设施设备[11]。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计,全国体育场由1931年的1 412所增加到1936年的2 863所[13]。各地体育场除对民众的足、篮、排、网、乒乓等球类活动进行指导,每年还举办各种球类比赛、田径运动会、游泳比赛等。对于体育比赛,1931年颁布了《民众业余运动会办法大纲》予以规范,这些政策措施对于推进社会体育活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把体育工作纳入社会革命当中,把体育活动作为争取群众、发动群众的重要手段。通过俱乐部、列宁室等半军事化组织开展以军事技能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体育活动,以巩固苏维埃政权。1933年6月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发第2号《关于建立和健全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训令,明确指出,俱乐部的任务是向一切乡村、城市、机关、部队进行广泛的包括体育在内的社会教育。1934年4月和6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先后颁发《俱乐部纲要》和《俱乐部组织与工作》等训令,规定由俱乐部的基层单位“列宁室”来领导基层群众的文娱、体育、卫生活动。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的局部抗战时期是中国体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体育界自觉承担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发出“体育救国”的呼声;国民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都颁布了一系列体育法令,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学校体育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制度化;体育竞赛空前活跃;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也开始克服盲目排外思想。观念的转变、制度的建立和实践活动的开展加快了中国体育现代化转型的步伐。
3.2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体育的发展(1937-1945)
3.2.1 抗日根据地的体育活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共产党对体育工作的指导方针开始向新民主主义方向转变。抗日根据地遵循着为抗战服务的政治要求,开始着手探索体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体育理论。
1937-1940年,抗日根据地的体育继承了中共苏区的经验,把发展体育运动作为团结、发动群众的重要手段。1937年成立的“陕甘宁边区体育运动委员会”和1940年成立的“延安体育会”是抗日根据地体育的领导机构。除继续沿用局部抗战时期中央苏区公布的《各种赤色体育规则》(1933)、《少队游戏》(1934)、《全苏区八月运动会举行规程》(1937年5月)[38]等体育法规外,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教育厅于1938年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小学应加强军事化的通知》,1939年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初级中学课程标准》《晋察冀文化教育会议文化教育决议案》《晋察冀边区中学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馆组织规程》《农村俱乐部组织法及工作大纲》[44],1941年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修正稿)和《延安九月运动会举行规程》,抗日根据地的体育法规还有1944年的《关于开展工长文教工作决议》、《陕甘宁边区抗日先锋队组织条件》、《部队游戏》等,以指导根据地各类体育的开展[38]。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在于他们没有以改造者的姿态向当地农民大谈理论和主义,而是切切实实地从当地群众的需求和利益出发,在边区普及人人可以参加的教育,并在幼儿学校、初高级小学、师范学校、中专学校和高等学校中均设置体育课。边区经常性的体育活动是军队中的体育训练,而对于乡镇、农村的工农大众,边区政府采取改造传统体育活动的方式吸引群众参加。比如当地的打社火、踩高跷、跑旱船、扭秧歌、拔河、赛马、打腰鼓等活动深受当地群众喜欢。边区体育干事们剔除这些项目中的封建迷信内容,每逢传统节日便组织男女老幼群众参与。在深得民心的情况下,再向群众普及现代体育项目和军事体育训练。开展运动竞赛也是根据地宣传、推广、检阅体育的重要形式。全面抗战刚开始,苏区就开展了“八一”运动会,进行抗战动员。这一时期,适应抗战需要,根据地因地制宜、因陋就简,采取各种方式在军民中普及以军事化为主的体育。边区政府教育厅于193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小学应加强军事化的通知》,要求在儿童中推行国防教育。边区小学自制木枪和木质手榴弹,体育老师指导儿童练习瞄准、刺杀、投掷手榴弹等军事技能,也通过军事游戏练习站岗放哨、防空急救等军事知识[29]。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军民生活面临极大困难,保障军民生活和提高军民体质成为党和边区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边区政府通过大生产解决粮食问题,通过体育活动解决健康问题。1942年,朱德在《祝九月运动大会》一文中提出“改善军民生活”和“普及体育运动和卫生保健知识”两大任务。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中国共产党于1941年9月创办延安大学,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体育训练班”为基础创办延安大学体育系,培养体育骨干,指导群众性体育活动。1942年1月在延安成立体育科学研究机构——“新体育学会”,编译体育刊物,探索体育发展方向。叶剑英、冯文彬、童大林、张远等相继撰文探讨体育运动的大众化、普遍化以及对体育活动进行分类指导的原则。这一时期,抗日根据地体育活动在保持军事化的同时,增添了民族化、专业化的色彩。针对部队、工厂、机关、学校、农村等不同的参与人群采取分类指导的原则,在机关干部中开展“十分钟运动”,在村镇开展下棋、武术、新秧歌等传统体育项目,还利用“三八”、“五四”、“八一”、“九一”、春节等节假日进行各种运动竞赛,激发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改善群众体质,提高军队战斗力。
全面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在体育工作方面,不仅提出了为抗战服务的政治要求,而且找到了在工农大众中普及体育的现实途径,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体育运动的方向和内容,探索体育规律,着手建设新民主主义体育理论。根据地的体育实践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体育政策和方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3.2.2 国民党统治区的体育活动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我国体育界就存在着关于“体育军事化与教育化”、“普及体育与选手体育”、“西式体育与国术”的论争。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抗战时期。1938年3月,国民党通过《抗战救国纲领》宣布中国进入抗战救国阶段,体育的军事化、普及化已成为无可置疑的方向。
由于中国近代社会首先是在学校引进了西方现代体育,所以为了抗战需要,国民政府首先把发展体育的重任压到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的肩上,责令其管理全国体育工作。1942年,国民政府把体育委员会改组为“国民体育委员会”,其下设学校体育组、社会体育组及研究组,负责指导督促全国体育之职[10]。所以,这一时期体育教育担负起为抗战服务的使命,呈现出军事化特色。1938年颁行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规定,各校切实推行军事训练、童子军训练和强迫课外运动,以强健其体力。《纲要》第八条规定:“中等以上学校一律采取军事管理方法”[15]。1939年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的《体育教育改进案》明确提出,学校体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自卫、卫国之能力”。1941年颁布《修正国民体育实施计划大纲》后,建立了一批培养体育专门人才的体育专科学校:国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体育童子军科、中央干部学校童子军科、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体育科、四川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艺术体育组、湖北省立教育学院体育专修科、四川体育专科学校、私立径南体育专修科等[33]。这些体育专科学校绝大部分分布在内地,其中四川省多达7所,虽然办学条件艰难,但是使我国的体育教育专业得以延续,尤其是大量体育人才进入到西南、西北等落后地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内地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
与“体育军事化”相伴随的是军事体育化。全面抗战前国统区军队的体育活动没有统一指导。为了贯彻“战时体育”方针,国民政府于1938年在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立体育科,由留学德国并力主“体育军事化”的肖忠国任科长,主管军队中的体育事务。在中央训练团特设军事体育干部训练班,培训军队体育干部。训练班每期1年,前后3期共1 000多名学员,毕业后大多数任军校体育教官。1939年,军委会政治部又决定以第18军为军队体育实验区,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推进军队体育的发展,一些体育人才得以在国民政府军队中施展才华。曾参加第5届远东运动会为国争光的孙立人训练出财政部税警总团,1938年更名为缉私总队,正式设立体育处,下设总务、教练、竞赛3个组,由留美体育博士张咏任处长兼总教官,以推进官兵体育训练并举行运动会检查训练效果,为国民党训练出一支精锐之师。1942年,孙立人部改组为中国远征军新38师入缅甸作战,共歼灭日军33 000余人,成为消灭日寇最多的国民党军级单位。
在社会体育方面,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法律、条例鼓励国民参与体育运动。1939年,颁布《体育场工作大纲》、《体育场规程》和《体育场辅导各地社会体育大纲》,鼓励体育设施场馆建设;1941年,公布了《奖励民众体育团体实施要项》对体育社团的组织做出规定。1942年,颁布《分期设置国民体育场办法要点》责令各省、市从该年度起,限期完成每一乡镇设置一个简易体育场的规定。1944年,制定并施行的《体育场工作实施办法》对于指导民众体育运动、举办体育竞赛、协助壮丁训练都做出详细规定[35]。该时期详尽的民众体育立法推动了民众体育的规范发展,尽管处于战争状态,我国体育场馆数量仍然由1937年的1 786所增加到1945年的2 029所[15]。除督促建设场馆、建立体育社团外,国民政府还采纳程登科“强迫运动”的建议,动用军警督促全体民众参与体育锻炼,以强身健体服务抗战。
除大力推行西方现代体育外,国民政府对于中国传统体育也予以重视。以梁漱溟、钱穆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理论家们认为,自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对中国“固有文化之厌弃反抗”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21],中国欲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应该回过头来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之真价值[27]。以张之江、褚民谊为代表的“国粹派”体育家和中央国术馆力倡国术救国论,在国民中推广太极操。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国民政府也聘请民间武术家在军队中担任教练,向士兵传授武术格斗技能。“无极刀”创始人李尧臣为国民政府训练出了抗日战争中以“肉搏战”而著名的二十九军大刀队。
在大后方,国民政府也通过体育节和体育竞赛活动增强民众体育观念。1942年,颁布《体育节举行办法要点》把每年9月9日定为体育节,体育节前1周为宣传周,规定体育活动项目无论中西,因时因地因人定举,“贵能深入民间”[4]。关于运动竞赛,国民政府于1940年颁布《各省市县运动会举行办法大纲》,在1940-1945年的陪都重庆,光是有详细赛事记载的国术比赛和大型运动会就有27次之多[20]。除正式的体育竞赛,大后方也籍由体育节而举行了很多大规模的群众体育活动,如爬山、划船、滑翔伞塔跳伞等。这些运动竞赛和体育活动,不但激发了民众的体育兴趣,而且普及了运动员的规则观念和观众的秩序观念,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中国体育的规范化。
3.2.3 敌占区的体育活动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蚕食鲸吞,我国大片国土沦陷。日本实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侵略手段,在沦陷区建立起日伪政权,并仿效日本体协模式成立伪“华北体育协会”、伪“中国体育协会”等组织,开展体育竞赛活动和各种民众体育活动,麻痹中国民众。在学校,体育课“不仅内容上参照日本,就连列队、口令也全部使用日语[25]”推行奴化教育。
尽管日本帝国主义把体育运动当作殖民统治的工具,但是,体育精神本身所包含的民族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和凝聚力。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结构、心理特征和价值体系在民族苦难面前成为中国民众文化认同的“粘合剂”。沦陷区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也把体育活动视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途径和表达民族情感、捍卫民族尊严的场域。
沦陷区的人民主要通过3种方式进行反日抗日的斗争:1)进行消极抵制。在伪“国民政府”统治区,汪伪政权强制学校体育完全仿照日本,以体育、军事训练和少年团“三位一体”的方式,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奴化训练。许多体育教师平时仍按学生喜欢的教学方式上课,只有在伪政府要员进行检查时,才按“规定”上课,搪塞敷衍检查,使得日伪规定变成一纸空文[36]。2)通过体育活动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认同。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中华武术会联合精武体育会、国术会、益友会、慕尔堂国术团、忠义拳术会等民族传统体育团体联合成立“上海市国术协进会”进行抗战救亡活动。1939年秋,协进会举办“上海市国术运动会”,开幕式上,在场人员“热血沸腾,情绪激昂”[33],国仇家恨把中国人的心紧紧地连接在一起。3)组成抗日团体进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1938年1月山东省沦陷后,青岛市武术组织组成“国术救国团”,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后又改成爆破大队,“游击青岛外围,牵制敌人重兵”[34]。
在沦陷区,日本人因体育的规训功能和仪式特征而把它当作推行奴化教育和标榜“大东亚共荣”的工具,所以,从伪政权颁布的学校体育课程设置和运动竞赛宗旨来看,沦陷区的体育具有浓厚的殖民色彩。但是,由于体育所具有的强身健体功能和民族凝聚力,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却把体育当作健身强兵、凝聚民族精神、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途径和场域,故而,沦陷区的体育活动实际上担当起了团结民众进行反殖民、反奴役和反控制的历史责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国大地上形成了3种不同性质的政权,也出现了3种不同特色的体育。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的体育发展总趋势是立足于体育普及选择发展道路,在推广西方现代体育的同时对中国传统体育进行改造,尤其是国统区的“强迫运动”和抗日根据地的“十分钟运动”,都凸显了体育的普及化取向。在沦陷区,对于日本人用以粉饰太平的体育比赛,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或者消极抵抗,或者在体育比赛中通过取胜来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从在民族危机中加强了民族认同的中国人民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国统区、抗日根据地,还是沦陷区,体育都成为争取民族独立,打击侵略者的有力武器。体育成为抗日救亡的符号,运动竞赛成为展示民族精神的神圣仪式。
4 抗战时期中国体育的特征
4.1 体育参与规模大,形式多样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大地便燃烧起体育抗日的烽火。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更使体育抗日的规模从北国传到南疆,从沦陷区传到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
在组织机构方面,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有成立于1932年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和1941年成立的“国民体育委员会”主管全国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工作,成立于1938年的“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体育科” 掌权军队的体育训练,成立于1933年的“中央党部民训部体育课”和“党政军学体育促进会”负责体育的宣传促进工作[13]。革命根据地有成立于1933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成立于1934年的“俱乐部”和“列宁室”等体育管理机构。
随着体育社团组织的大量涌现,国民政府于1932年10月颁布《修正民众团体组织方案》,以法规的形式规定各种社团成立的程序与原则,强调民间团体组织绝对服从国民政府和中央的统一管理[14]。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奖励民众体育团体实施要项》,鼓励民间体育社团组织的建立。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与社会部联合公布《体育会组织办法》,将 “普及体育,增进健康,发扬民族精神及研究体育学术” 定为体育会的宗旨[45]。抗日战争期间,影响比较大的全国性体育社团组织有“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全国青年体育协会”、“中央国术馆”和抗日根据地的“陕甘宁边区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于1937年)、“延安体育会”(成立于1940年)、“延安新体育学会”(成立于1942年)等。各省地方也成立各种体育组织,领导民众通过体育进行救国活动。
在体育内容方面,为适应抗战需要,国统区通过体育立法、体育场馆建设、设立体育节、建立国术馆等方式倡导国民体育,使爬山、划船、武术、航模、跳伞、球类运动等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在学校体育方面,通过建立和完善体育管理和督学机构、增加体育课时数等措施使体育教育步入正规且凸显战时特点;在竞技体育方面,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抗战结束,中国除了举办省级运动会、大区运动会,还举办了第5届和第6届全运会,参加了第10届远东运动会、第10届和第11届奥运会,带动了民众体育活动和竞赛活动的开展。
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锻炼身体,好打日本”思想的指导下,体育活动盛况空前。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作战之余进行各种体育锻炼活动,如徒手体操、器械体操、球类运动及跳高、跳远、推铁饼、投手榴弹、爬山与赛跑等,当时贺龙领导的120师“战斗篮球队”和刘伯承领导的129师“棒球队”惠誉根据地;当地群众也积极参与各种体育活动,溜冰、游泳、跳集体舞、爬山、打球、扭秧歌、敲腰鼓、耍狮子、舞龙灯、跑旱船、踩高跷等不一而足[25]。
总的来看,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高涨,为抗击日本侵略而锻炼身体、参与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这一时期在战时特殊背景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全民健身的新现象。
4.2 服务于民族救亡,军事色彩浓厚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岁月中形成了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只是在西方列强入侵之后,沉睡于中国人意识深处的民族认同才被唤醒。法国历史学家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在《民族是什么》中说,“共同的苦难比起欢愉更能团结人民,对民族记忆来说,悲愤比胜利更有价值,因为它带来的是责任感,能调动万众一心的努力”[47]。“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魔爪日益深入,中华民族的厄运日益深重,中国人民悲愤的民族心理益愈强烈,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把体育当成民族救亡的武器,掀起“锻炼身体,好打日本”的民族主义体育浪潮。
除了国统区、陕甘宁边区、沦陷区游击队等武装力量把体育当作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学校体育教育也实现了军事化。体育教育家程登科极力宣传“体育军事化”教育,他认为“非常时期之体育,若不能做军事之准备,不得谓之合时代之体育”[28]。当然,体育军事化不是以战争中的专门战术代替体育课,而是在不改变体育内容的基础上,以军事精神进行管理、训练,以使学生养成坚实的身体和勇敢、坚强、牺牲、忠实、绝对服从等军事精神,“通过训练,使自己准确而敏捷地行动,竭尽全力,将自己从一个普通人转变为一个称职的军人”[19]。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提出,学校体育的目标是“平时为自强,战时为卫国”,同时规定各级各类学校推行军事训练、童子军训练,强迫进行课外运动[18]。体育教材大纲规定,学校体育课程内容应包括划船、救生、骑射、露营、驾驶、滑翔、跳伞等军事技能以及拳术、击剑、劈刺、角力等自卫活动[36]。抗日根据地边区学校体育教育也与抗战需要相联系,把军事训练作为中小学体育课的主要内容。1938年,抗日根据地边区政府也制订了“为适应战时环境的需要,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军事训练,小学实行军事化组织,使学生在必要时直接参加抗战”的教育方针[30]。
抗日战争时期的体育凝聚着中国国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情感,举国上下,把通过体育锻造“钢铁般的身体”、打击侵略者、保卫国防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4.3 注重对体育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
1931-1945年抗战时期是我国在思想认识上对体育发展道路探索选择的重要时期。19世纪后半期,西方体育引入中国。之后一个多世纪,体育发展道路问题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主题之一。20世纪初期,在封建统治者、维新派人士和民主革命者的大力提倡下,中国开始实行以“兵式体操”为主的军国民体育;20世纪20年代左右,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美国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传入,中国体育界引发了一场以“兵操存废”和“中西体育之争”为焦点的大讨论,最终导致1922年“壬戌学制”的制定,中国体育走上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新体育道路;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的爆发又赋予体育新的历史使命,从而引发人们对于“体育发展道路”的思考与论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社会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体育救亡”的呼声日渐高涨。1932年,刘长春独自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初赛即遭淘汰的消息传入国内,舆论哗然,《体育周报》《世界日报》《大公报》等多家报刊呼吁体育改革。中国体育界掀起了“土、洋体育之争”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断断续续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主要围绕“洋体育与土体育”、 “军国民体育与自然体育”、“普及体育与选手体育”、“体育之军事化、医学化与教育化”、“体育与两性差异”、“单轨体育与双规体育”、“体育训练的迁移”、“体育训练与身体发达问题”等主题展开。从形式上看,这次讨论不过是20世纪20年代体育“土洋之争”的延续,但是二者在性质上却有着根本的区别。20世纪20年代的论争是在“何为体育”的层面上解决对体育自身的认识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讨论则超越了体育本身的范畴,在更广泛的文化层面上探讨体育的发展问题。20世纪30年代体育之争的重点是选择何种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是想解决民族危机日深的条件下如何发展中国体育的问题,这与整个民族文化的构建紧密连接在一起[41]。
这次体育之争反映了国人开始理性地思考中西方体育的矛盾与统一之处,解决了中国体育的“西化”和“化西”的问题。体育的“土洋之争”实质上是西方体育文化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两种异质文化类型交汇、碰撞的结果。最初引进西方现代体育本是中国落后挨打的无奈之举,加上西方殖民者的文化标签,很多中国人在接受西方体育文化的过程中产生抵制情绪。但经过两种文化的接触与融合,西方体育中那些完全不能被中国文化接受的异质被剔除之后,中国在接受西方体育的“西化”过程中,也进行了对西方体育的改造,即“化西”的过程,从而使西方体育成为中国民族“救亡图存”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对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也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对民族传统体育特别是武术进行整理,主动走上现代化之路。所以,20世纪30年代的体育论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土洋体育的矛盾,走上现代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共同发展的道路,使二者共同担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5 抗日战争对中国体育发展的影响
5.1 强化了体育为国家民族服务的意识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痛斥晚清帝国的中国人缺乏民族观念、国家主权观念。中日甲午之役也被国民视作“日本与李鸿章之战”。但是,经过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的洗礼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掀起了一场真正的民族自卫之战。在这场战争中,体育因其强身健体、磨练意志、锻造团结奋进精神的独特作用而成为中国儿女救亡图存的武器。蒋介石在抗战舆论压力之下,也扛起体育救国的旗帜,“我们要积极自强,要不为人家所轻视,首先就是要注重体育,提倡体育,体育如果不能进步,则整个国家各部门的工作都不能进步!”
体育为国家民族服务的意识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屡犯中华、称中国为“东方病夫”[23]的背景之下,在这种意识支配下,晚清政府在军队和学校中推行欧洲大陆的体操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军国主义思潮衰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留美学生的影响之下,国民政府于1922年颁布“壬戌学制”中以“体育课”代替“体操科”,教学内容中增加英美的竞技运动和游戏,注重学生人格修养和身心协调发展,从此学校体育和军事体育区分开来。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为国家而体育,为民族而体育”的意识逐渐升华为国家政策,体育军事化、军事体育化、全民体育化成为抗战时期体育发展的总趋势。无论是抗日根据地、国统区,还是沦陷区,中华儿女都把练兵健体、打击日本侵略者作为动力,在艰难危险的境况中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和竞赛,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维护国格的民族精神和团结抗日的民族情感。体育竞赛成为振奋民族精神,打击日帝嚣张气焰的舞台。“九一八”事变后,北京通县潞河中学学生臂戴“誓死保国”的黑纱,自动组织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抗击日本侵略者。1932年,日本企图通过让“伪满洲国”参加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的途径使其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之下,东北籍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在天津《体育周报》发表 “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岂能叛国,做人牛马[24]”的声明后,毅然代表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在世界体育舞台彰显了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维护了国家主权。1934年第18届华北运动会上,天津南开学校的学生打出黑白两色的巨幅标语,“勿忘九一八”、“勿忘东北”、“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大会主持人张伯苓俨然拒绝日本驻天津领事撤销标语的抗议,使运动场变成了控诉日本侵略罪行和号召抗日救亡的会场。
抗战时期的体育成为民族复兴和保国卫疆的斗争武器,起到了唤醒民众、鼓舞士气、激发民族情感的作用。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体育成为锻造国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的特殊战场,中国各族、各地、各阶层的人民和海外侨胞团结一心,共赴国难,参与到体育救国的洪流之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投身于神圣的民族正义之战。
5.2 促进了我国体育的现代化转型
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限制,中国的传统体育未能像西方体育一样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所以,中国体育的现代化转型是在西方现代体育传入的背景下被动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在中国体育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19世纪中期西方现代体育传入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从军事领域扩展到学校,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体育只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大城市和苏区革命根据地比较普及。
正是基于民族救亡的需要,在国民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抗日战争期间的体育活动深入到西南、西北、东北等边远地区,参加体育活动的人群扩展到社会各阶层,撼动了中国“主静”的传统观念,激发出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尤其是在鼓舞广大妇女参与体育活动方面,真正起到了移风易俗、解放妇女的作用。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逐步完善了具有现代化意义的体育组织和机构,制订了相对完备的体育法规和条例,初步实现了我国体育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全国各地体育组织的建立、体育活动的普及、学校与社会的各种体育比赛,都促进了中国现代体育的进一步发展。
在西方体育加速传播的同时,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也开始走上现代化转型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体育“土洋之争”的大讨论加深了体育界对于西方现代体育和中国传统体育的特点和价值等方面的认识,使得国民政府在大力推进西方现代体育的同时,也将国术列为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的重要内容。提倡中国传统体育的武术家们也开始以西方现代科学等知识来整理和诠释中国武术文化,推动中国传统体育向着科学化方向发展。中国国术馆馆长张之江不但创办了“中央国术馆国术体育传习所”、“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而且率领武术代表团赴香港、日本、欧洲进行武术表演和体育考察,主持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武术代表队的选拔和集训。抗战期间,中国武术家们本着“提倡武术、研究武术、铸造强毅之国民”的宗旨,进行武术的整理、教学、交流,建立和完善了武术竞赛制度,推动着武术在科学化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型。
从体育观念的转变、体育法规的颁布、体育组织机构的建立、体育教育的进行、体育活动的推广、体育比赛的举办、现代体育与国术并重等方面来看,抗战期间我国体育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迈了一大步。
5.3 为新中国体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通过法律推动体育场馆建设和体育教育的发展,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国统区共有体育场馆2 029个,学校数268 909所[7]。加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体育场馆和培养的体育人才,这一时期的战时体育发展客观上为新中国体育提供了场地和人才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共有大、中、小学校35万余所,学生2 577万余人,专任教师93.5万人[43]。从管理制度来看,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都设置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颁布了关于推动体育发展的法令、法规,开展了丰富多样的以服务军事战争为主的体育实践活动,完善了体育竞赛制度。这些都成为新中国体育发展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体育思想则成为新中国体育思想理论的直接来源:1)体育大众化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把改善工农群众健康状况,争取工农大众的体育、卫生权利写进党的决议之中。局部抗战时期,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于1932年规定“体育运动应在工农群众中开展,发动群众经常做各种运动……如跳高、跳远、游泳、赛跑等,强身健体,锻炼革命斗争中需要的技能”[42];俱乐部、列宁室成为苏区发动群众体育运动的主要组织机构。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纲领,为新民主主义体育提供了理论依据。1942年起,边区推广“十分钟运动”,军民一起参加各种体育活动;2)“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体育思想。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在1940年签署的《体育训令》中指出:“体育运动应在全师内广泛开展起来,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同时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普及”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方针,延安体育界将这一方针贯彻在体育发展中;朱德总司令在1942年《祝九月运动大会》中提出“普及体育运动和卫生保健知识”的要求。这样,以“大众化”、“经常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为特征的群众性体育锻炼热潮在抗日根据地兴起。“体育大众化”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体育发展方针不但指导了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体育实践,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体育的宝贵经验,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体育为人民服务”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思想的理论来源。
抗日战争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对于体育发展道路的探索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时代需求和中国体育在外力促动下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规律。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体育在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理论建设方面的积极探索和广泛开展的体育实践活动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新体育”发展的宝贵遗产。
6 结束语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体育在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下围绕着强身健体、提高战斗力而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全国民众在不甘做亡国奴的民族抗争精神下积极参与体育活动,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在运动场上扬眉吐气。这一时期的体育虽然属于战争时期的“非常态”体育,但是,在民族救亡的外因促动下,我国体育在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理论建设方面的成就,不但使西方现代体育在我国得到普遍、深入的传播,而且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也摈弃了封建迷信的色彩,依据西方身体理论进行改造,提升了国人对于体育的认知,从而推进了我国体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
抗日战争期间体育的发展锻造了中华儿女的强健体魄和抗争精神,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改变鸦片战争以来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历史命运打下了基础。同时,在抗击日本侵略期间,中国以独立的民族姿态登上国际体育舞台,参加第10届和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0届远东运动会,展示了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榜样。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中国,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方面的卓越贡献使得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26]。
虽然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昔日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雄踞于世界东方,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体育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民族复兴”大业中的贡献不能被历史淹没,抗战精神和体育的认同意识应该世代流传,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增添新的内涵。
[1]陈敦正.复兴民族与提倡国术之意义[J].国术周刊,1934,(127):1;1934,(128):2;1934,(129):2-3.
[2]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27.
[3]程登科.怎样利用军警权力辅助民众体育使全民体育化[J].体育季刊,1935,(2):179-187.
[4]重庆市体育运动委员会,重庆市志总编室.抗战时期陪都体育史料[C].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39-240.
[5]道志.体育漫谈[N].新华日报,1942-09-09(4).
[6]董守义.提倡体育的原动力[J].勤奋体育月报,1934,(1):26-27.
[7][日]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民国篇·下)[M].台湾:文海出版社,1976:151.
[8][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M].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491,516.
[9]高梓.中国女子体育问题[J].教与学,1937,2(7):237-243.
[10]谷世权.中国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7:259.
[11]谷世权.中国体育史(下册)[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173.
[12]郭德宏.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J].历史教学,2005,(1):5-15.
[13]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史学会.中国近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211,244,306.
[14]郝更生.十年来我国之体育[J].体育,1927,(2):1-18.
[15]何启君,胡晓风.中国近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206,244.
[16]黄华文.抗日战争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38-48.
[17]黄亚玲.中国体育社团的发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155.
[18]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698.
[19][德]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M].孙志新,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144.
[20]李重华.抗战时期陪都体育赛事[J].抗战文化研究,2008:196-204.
[2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201.
[22]刘慎旃.体育救国论[J].勤奋体育月报,1935,2(5):519-522;1935,(8):713-719.
[23]刘鹏.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大国——新中国体育60年[J].求是,2009,(16):25-27.
[24]刘长春.刘长春自述[N].体育周报(天津)第20期,1932-06-18(20).
[26]聂家华,刘洪森.中国近代史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245-246.
[27]钱穆.民族与文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20-23.
[28]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文选[C].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279.
[29]陕甘宁边区体育史编审委员会.西安:陕甘宁边区体育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51-70.
[30]陕西省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陕甘宁边区体育史料1935—1948[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5.
[31]邵汝干.建设民族本位的体育[J].体育杂志,1935,(1):5-6.
[32]宋恩荣,章咸.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38-258,263-273,325,326,331-344,385-397,443-445,466-483,496-497,500-503.
[33]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97.
[34]体育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体育史料第3辑[C].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7:226.
[35]体育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体育史料第14辑[C].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7:51.
[36]体育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体育史料第16辑[C].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210.
[37]王增明.中国近代体育法规[M].中国体育史学会河北分会,1988:156-159,424.
[38]王增明,曾飙.中国红色体育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140,141.
[39]马崇淦. 本报旨趣[J].勤奋体育月报,1933,1(1):1-2.
[40]熊晓正.从“土洋对立”到“建设民族本位体育”[J].体育文史,1997,(4):13-17.
[41]熊晓正.中国体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57.
[42]曾飙.苏区体育资料选编[C].合肥:安徽体育史志编辑室,1985:25.
[43]张健.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79.
[44]张援,章咸.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429.
[45]赵卓.中国近代体育制度发展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1:47.
[46]浙江体育学会体育史专业委员会,浙江文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近代体育史文集[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50-52.
[47]RENAN,BRÉAL,MEILLET.Langue Franéaise et Identité Nationale, Textes d’Ernest Renan(1882), Mickel Bréal(1891), et Antonie Meillet(1915)[M].Lambert-Lucas Limoges,2009:33.
National Salvation and Sports’ Transformation:A Historical Survey o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ZHANG Ai-hong1,2
Using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overall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is paper combed the historical clue of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ly from the vertical view of two-stages of regional and general Anti-Japanese War,the horizontal view of three parts of the Guo-Min-Dang area,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rea and the enemy-occupied area.This paper found out that Chinese sports had four characteristics,such as the participation in a large scale,the various forms,the strong military feature and the focus on the exploration of sports theory.On the basis of objective discussion on sports development in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this paper clarified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sports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sports modernization this period and the basis of material,regulation,concept and theory for new China sport.
sporthistory;Anti-JapaneseWar;nationalsalvation;sports’transformation
1000-677X(2016)08-0079-09
10.16469/j.css.201608007
2016-06-12;
2016-07-14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91S-S1507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课题(2016YB008)。
张爱红(1973-),女,山东高唐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历史与文化,Tel:(010)62989376,E-mail:waitforu_2014@126.com。
1.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2.北京体育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1.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2.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G812.9
A
——评《休闲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