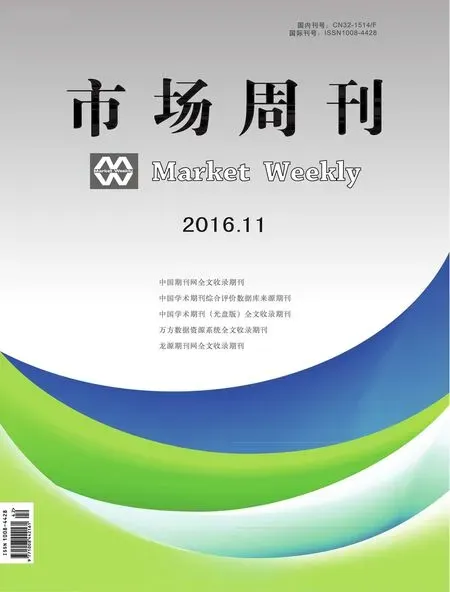公共产品:一个概念的再审视
梅锦萍
公共产品:一个概念的再审视
梅锦萍
公共产品无疑是公共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但是目前对于这个概念的认识仍然存在一些混乱和误区,文章对公共产品的概念重新梳理,并重点区分了公共产品与公共资源、俱乐部产品等之间的歧异,在此基础上对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加以了探讨。
公共产品;公有产品;公共资源;免费产品
一、从公共事物到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这个概念最早由学者林达尔于1919年在《公平税收》一文中提出,后被萨缪尔森于1954年在《公共支出纯理论》一文中发扬光大,公共产品现已成为一个被频频使用的概念,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引用或者运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仅仅关注和强调公共产品的“消费非排他性”以及“非竞争性”的表面特征,而没有关注到这个概念的实质性内涵。需要指出的是,不仅这两个特征本身尚存很多争议,而且在一些有关公共产品的外延性的理解上还存在很多误区,本文希望通过对公共产品这一概念的再审视,消弭其中的误区,以便进一步澄清这个概念。
公共产品概念以及公共产品理论的形成与公共事物的客观存在有关。很多学者早已关注到公共事物及其带来的一些困扰。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公共事物是有别于私人事物的,并且“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①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而后来的大卫·休谟则在其《人性论》中进一步提出公共事物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而且认为,由于公共事务是一种超越私人利益的“集体消费品”,如果仅仅从个人利益出发,往往无法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相反,人们只有先制定一种普遍主义的规则,遵循一定的公共理性,保障公共事务的供给,这样最终才能确保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正和博弈。②大卫·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应该说学者们很早就意识到公共物品的存在。
可以看出,公共物品正是满足公共需要的重要资源。相比于公共事务的宽泛指向,公共产品有着更加明确的学科界限和特定意涵。应该说,公共产品主要用来讨论公共财政如何在公共部门以及公共领域进行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概念,因而也是公共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主流公共经济学的各种教科书中,有一个重要的假定,那就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生产和提供不同,类似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以及如何做出决策这些基本的选择问题,私人产品往往是私人根据市场信息做出个人的选择,而对于公共产品而言,却往往成为“公共部门内部的选择、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影响私人部门决策的方式。”③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那么,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或者说公共产品的特性到底是什么?公共产品如何提供?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
二、公共产品:何种产品?
按照萨缪尔森的经典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或服务指的是这样的物品或服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服务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种物品或服务消费的减少,为了进一步说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区别,萨缪尔森借用了数学等式来借以说明。他认为公共产品和私人物品分别可以表示为:

公式(1)表示对于任何一个消费者i来说,他为了消费而实际可以支配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数量就是该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总量Xn+j,区别于公式(2)所表示的物品或者服务Xj的总量等于每一个消费者i所拥有或消费的该物品或服务数Xij的总和。④高培勇编著:《公共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我们可以借助于上述这两个公式进一步说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区别何在。首先,是否具备消费的非竞争性是区别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一个重要标准。所谓消费的非竞争性指一种公共物品一旦被提供,一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减少其他任何人对同一物品的消费机会和消费数量。对于私人产品而言,如果它被某人使用,其他人就不能使用该产品,“如果林恩喝掉一瓶苹果汁,弗兰就不可能喝同一瓶苹果汁,”①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但是,公共产品却和私人产品有明显的不同,它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non-rival consumption),即“一个人消费不会减少或阻止他人消费的情形。”②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国防就是纯碎的公共物品,因为国防建设以及军事装备实际上是供每一个公民“消费”(保护所有公民),而且每一个人在“消费”的时候,并不像消费苹果汁那样具有竞争性,一般情境下,所有公民在对国防这样公共产品的消费上并不存在相互竞争的情形,即使多追加一些消费者,往往也不需要增加额外成本,仍然具有一种非竞争性。这是公共产品区别于私人产品的第一个重要特征。
是否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或者排他的成本是否很高是公共物品区别于私人产品的另一个特征。私人产品往往是私人通过市场中的价格体系进行购买,对于个人而言,正是因为私人购买的物品或者服务可以排他性地为个人所用,所以才会受到“支付的激励”③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但是并不是任何一种商品和服务都能够通过市场出售或者购买,有些商品和服务就存在受益的非排他性问题。例如学者们经常讨论的灯塔问题,若想不让经过灯塔的任何船只从中受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技术上也难以实施,也就是说,灯塔无法像其他的私人产品那样通过市场价格体系进行收费,因为存在着非排他性或者排他的成本太高,导致了消费者的搭便车行为,适用于私人产品的价格体系显然会失灵。
效用上的非分割性(non-divisibility)也是公共产品区别于私人产品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对于私人产品而言,可以按照谁付款、谁受益的原则,因而私人产品可以按照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范围的大小加以区分,根据购买人付费的多少加以提供,所谓的“按质论价”,因而这种产品或者服务是可以分割的,但是在效用意义上,并不是任何产品和服务都是可以分割的并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正如我们上述举过的国防以及灯塔的例子,对于国防而言,无法在效用上(居民所受到的国防保护)进行分割,只要该居民具有一定的公民权,都享受等值服务,公民无法也因为其属性(例如财富的多寡、地位的高低)的不同按照市场规则来购买不同的国防服务,这一点显然不同于私人产品。④高培勇编著:《公共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三、公共产品:公共资源抑或俱乐部产品
公共产品确实是个客观存在,公共产品概念的提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现实中,纯粹的公共产品少之又少,如果按照排他性/非排他性以及竞争性/非竞争性两个维度区分的话,我们可以将社会物品分为四类,即私人物品、俱乐部型准公共产品、拥挤型公共产品以及纯公共产品(参图1)。在现实中,除了私人产品之外,我们所讨论的大部分公共产品其实都是俱乐部型准公共产品以及拥挤型公共产品,它们并不完全符合纯粹公共产品的定义,厘清它们和纯粹公共产品的区别对于现实公共事务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1 社会物品的类别
(一)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拥挤型准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都属于社会产品,但又有着细微的区别。首先,从概念的界定上区分。作为人类的稀缺经济资源的一种,公共资源是指这样一种产品,它的消费一方面是公共的、不受限制的,一方面它的最优供给量是给定的,在达到这个供给量之后,新增的消费又会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公共资源被看做是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的产品。从具体类型上分,它包括可再生资源,如林地、牧场等;可持续利用产品,如公路、计算机网络等;以及短期内不可耗竭资源,如大型油田、矿藏等。由此我们可以把公共资源看做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它不完全符合公共产品的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它无法有效的排他,但是却具有竞争性。
其次,两者的产权特征的区别。一方面公共资源性产品的产权等同于公共产品的产权,是一种具有受益非排他性特征的公共产权。每个消费者都是该产品的产权主体,在没有发生拥挤的条件下,都享有平等的产权。另一方面公共资源性产品又是一个有限度的公共产权,并且在多数情况下它类似于存在消费的私人产权。由于公共资源类产品是给定最优供给量的,随着消费者消费量的不断增长,它的实际供给量将会超过给定的最优供给量,从而出现边际效益下降的状况,任何新的消费将会导致其他消费者效用的减少,这个时候它就不再是消费者可以同等的享用的公共产权,而是被消费者竞争性使用的有一定私人产权性质的产权。⑤袁义才:《公共经济学新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二)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俱乐部型准公共产品)
首先,从概念的界定上来区分。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M.Buchanan)在他的《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中提出,介于市场提供的私人产品和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之间的一部分混合产品,可以通过组成各种各样的俱乐部的方式来提供,以这种方式提供的产品就是俱乐部产品。从根本上来说,俱乐部产品就是关于一种产品提供方式的某种系统性制度安排。由于它具有较大的排他性成本但又存在有条件的排他的途径,所以,可以在以公共产品方式提供之外,采取一种俱乐部式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它的有效供给,如此说,俱乐部产品就是一种可以俱乐部这种特定方式提供的混合产品。我们可以从布坎南的界定中得知,俱乐部产品是一种具有“排他性和非对抗性”为特征的产品,即指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可以轻易做到排他性特点的产品或服务。这与我们前文所提及的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个重要特征的公共产品是不完全相同的。
其次,从产权特征上区分。相对于公共产品的公共产权特征,俱乐部产品既具有和其相似的消费权的非竞争性的产权特征,即每个俱乐部成员都享有同等的消费权,每个成员对俱乐部产品的消费不影响或减少其他成员对俱乐部产品的消费。这时它是限于俱乐部范围内的公共产品。但同时又有与公共产品不同的产权特征:一是俱乐部产品的产权具有分步排他性。俱乐部成员与非俱乐部成员之间存在排他性,只有俱乐部成员才拥有对俱乐部产品的使用权,也就是说俱乐部成员享有相对于非俱乐部成员的完全的排他性产权,或者说是一种私人产权,而在俱乐部内部,各成员关于俱乐部产品的产权又是非排他的,各成员共同分享公共产权,一个成员不能把另一个成员排除在任何俱乐部产品的使用权之外。二是产权规模的有限性。俱乐部产品的产权不能无限扩大,也就是说俱乐部产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存在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临界点,消费的非竞争性就会发生变化,产权就会有所不同。
四、公共产品:市场提供抑或政府提供
对公共产品概念的探讨实际上最终还是服务于现实中的制度设计。毋庸置疑,亚当?斯密对于如何才能更有效率地提供私人产品提出了一套经典方案,那就是依靠“看不见的手”(市场中的价格机制)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率配置私人产品的一种方案,但是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机制,并没有达成共识。首先,从其字面意义来说,“公共”二字容易引起误会,会使人认为只要是政府提供的产品就是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也必须由政府提供。其次,人们会认为准公共产品都等同于理想型的“公共产品”。正如上文分析的,公共产品概念只是定义了所有产品中的两极,一极是纯公共产品,另一极是纯私人产品,而在两极中间的大量产品被忽略了,也留下了很多争论的空间。
对公共产品究竟应该由政府还是市场来提供仍然是当今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需要面对的问题。传统的理论认为,公共产品必须由公共部门提供,私人部门不能提供公共产品。原因在于:传统理论认为,由于“搭便车”问题,决定了由私人部门来生产公共产品是不合适的,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这种观点显然遇到了挑战。
首先,从理论上看,从词义上理解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部门来提供。这是由于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中,由于免费搭车问题的存在,“个人不具备任何手段去截留那些利益,以阻止其流向他人,也难以收取费用以弥补其发起人。”这就使私人通过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将无利可图,或所得收益不足以弥补成本,从而私人不愿提供公共产品,或提供的数量达不到有效率的数量,公共产品的提供就需要政府介入,但是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公共产品都具有纯粹公共物品性质。实际上,许多公共产品更多地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它们具有私人产品的一些特征,因此对于这类产品,如完全让政府来提供也将是缺乏效率的,因而需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介入该类产品的提供。
其次,从实践上看,对于具有非纯粹公共物品性质的公共设施与服务,让市场发挥作用效率更高。世界银行在以“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为主题的发展报告中,对不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的普遍缺乏并且在这方面投资效率低下的状况提出研究建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商业化经营和引入竞争机制。
可见,一般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市场机制没有根本冲突。换言之,对于一些市场性强的公共产品,国家可以进行特殊管理,但不一定只采取单一的国家财产方式,实行政府独家投资包办的做法,市场资本完全有可能介入一些公共产品的投资领域。
梅锦萍,南京晓庄学院商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商学院在职博士生。
C93
A
1008-4428(2016)11-151-03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批准号12CGL07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