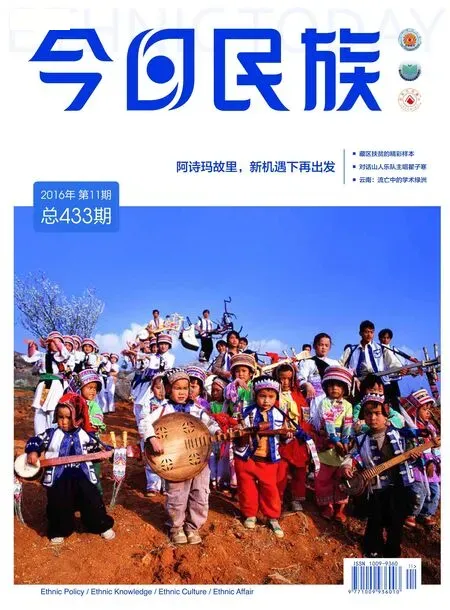“我们只是传播者”—对话山人乐队主唱瞿子寒
“我们只是传播者”—对话山人乐队主唱瞿子寒
文化遗产需要“传承者”,但同样需要山人乐队这样的“传播者”。他们为传统音乐呐喊,其影响更远,更深入人心。

几个月前,《中国好歌曲》节目中山人乐队夺得冠军。
山人乐队成立于1999年,起初是一个摇滚乐队。早期在昆明,后来活跃于贵阳,2007年,去北京后和公司签约,从此稳步发展。山人乐队是一支独特的乐队,带有浓郁的地域和民族风格。乐队成员起初都是摇滚乐的爱好者,想用摇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生活体验。但随着与外界交流的增加,乐队渐渐意识到云南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要性。2003年后,乐队开始学习民族民间乐器,并尝试把这类民间乐器与其他西洋乐器结合。
山人乐队的集体探索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中国好歌曲》上的成功是一例,另外,山人乐队还被文化部选中,派往一些国家做文化交流。
这样的成功给山人乐队带来一个改变,他们更加意识到民族民间音乐的价值。乐队主唱瞿子寒说:“最近几年,我们在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下,去云南各地采风,渴望进一步了解云南,了解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越了解,越发现民间音乐是一个宝库。”
另一方面,瞿子寒和他的山人乐队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角色。瞿子寒在不同场合,以及在本次访谈中,都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播者,为现代人了解这些音乐,开了一个窗口。我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承者。”瞿子寒说,传承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云南的民族民间音乐,无论它的根基如何,发展程度怎样,在今天都不得不应对现代化的问题。文化遗产需要“传承者”,但同样需要山人乐队这样的“传播者”。他们为传统音乐呐喊,其影响更远,更深入人心。
乐队是多民族的组合
今日民族: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乐队的成员。
瞿子寒:现在乐队有5个成员:主唱瞿子寒、鼓手小欧、贝斯手斯告·阿腊、鼓手打击乐Sam、民乐手小不点。
今日民族:听说你们的成员,有好几个民族。
瞿子寒:Sam是英国人,斯告·阿腊是石林的彝族撒尼人,小不点是贵州的布依族,我和小欧是昆明的汉族。
今日民族:每个成员各自有什么专长?
瞿子寒:每个人都有优势的部分。我负责乐队的词、曲创作,还有乐队的凝聚力。斯告·阿腊掌握了石林地区彝族的所有乐器,西方的贝司他也练了很多年。小欧算是半科班出身,受过正规的训练,在乐队中起到稳定剂的作用。小不点会很多不同的乐器,只要能发声的东西,他基本都能做出有意思的音乐段落,他自己还经常能发明一些“乐器”。Sam在古巴学习打击乐很多年,很小就接触西洋乐器,比如长号之类的。每个人都掌握了不同的技能,在一起可以发挥各自不同的优势。
今日民族:乐队成员不同的成长和文化背景,会为乐队带来哪些好处?
瞿子寒:最重要的就是给乐队音乐上带来更多的可能性。音乐是没有地域和文化障碍的,世界各地的音乐,都有很多的相似性,所以,我们既可以融合成一个整体,又有更多的色彩。
今日民族:你们的乐队吸纳了很多云贵高原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那你们是怎么定位自己的?是民族音乐的传承者,还是现代音乐人?
瞿子寒:我们乐队,相对准确的定义,是一个传播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承者。传承者需要自己特殊的文化背景,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我觉得山人(乐队)起到的是一个推动作用,在外界开了一个窗口,让更多的人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今日民族:那可以说你们是一群带有独特地域或民族风格的现代音乐人吗?
瞿子寒:可以这么说。关于音乐发展的问题我有一个想法。我认为音乐如果没有创新和演变的过程的话,比较难生存下去。有些音乐会慢慢变成一个文物。我认为我们的一些传统音乐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在变化中生存发展。我觉得新音乐和传统音乐的界限应该慢慢突破,不要局限。
今日民族: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学术界讨论音乐文化传承时,经常追问:要不要对当下做回应?你们是做出了回应,用包含了传统音乐的技巧,表达了你们对当下生活的看法。
瞿子寒:对。

从左至右分别是:Sam、斯告·阿腊、瞿子寒、小欧、小不点
故乡、城市、边缘人
今日民族:你们的音乐和你们的成长有关系,这个成长里头,乡村看上去十分重要。
瞿子寒:我小时候是在村寨里长大。我是军工家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和我父亲都住在滇西的寨子里。我是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故乡的人,总是一个阶段在这里,另一个阶段在那里,总处在一个流动的状态。在寨子里住,但又不属于寨子里的人,所以身份比较边缘。
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环境都不同。斯告·阿腊从小在寨里长大,基本没离开过。小不点,是十多岁才到了大城市。所以我们乐队处于一种不停地走动的状态。我们看事物的视角,会有不同的面。
今日民族:故乡可能是一种更加宽泛的意义,在媒体眼中,比如北京的媒体,就把云南当做你们的故乡,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故乡。
瞿子寒:我们也经常去国外,在国外我们的标签就是中国,就是一个更大的范畴。所以这个定义一直在变化。可能在云南,人们会认为我们是一群在北京的云南人。
今日民族:听你们早期的作品《山人》,从乡下人进城这样的角度讲述城市生活体验。在城市这么多年,你们对城市的感觉有什么变化吗?
瞿子寒:心理上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一直有边缘人的感觉。因为你始终不属于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是无法改变的,因为自己会给自己下一个定义。对城市和乡村,我们都是一个边缘的状态。
今日民族:作为生活经历,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城市和乡村的文化冲突?
瞿子寒:是1990年代到了昆明之后。虽然我向往去到这个城市,但一直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城市。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离开乡村来到城市的人会有的感觉。
今日民族:一些都市人听你们的音乐,可能会想象云南的乡野自然,好像你们是在寻归自然。其实他们可能忽略了你们表现在作品中的都市体验,这种体验主要是对城市的美好想象。而且,城市也是你们前进的动力。
瞿子寒:对,是这样的。我觉得城市化进程中有很多好的方面,但也有不好的一面,取决于你怎么看待。
今日民族:你刚才提到“边缘人”的身份,你们徘徊在两个边缘之间。对城市和乡村来说都是边缘人。
瞿子寒:对,我一直是一个“旁观者”,观察城市和乡村。童年是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我的童年是一种边缘的状态,我不属于这个寨子,我是个外来人,只是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
从摇滚乐出发
今日民族: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学音乐的经历。
瞿子寒:我很早就喜欢音乐,11岁开始学吉他,最早是学古典吉他,后来喜欢民谣,到昆明后,我开始尝试和别人合作进行集体创作,也就是乐队。我大概经历了这三种状态。我还是更喜欢这种团队的形式,在一个团队会有种归属感。我也分析过自己,因为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群体,所以后面我喜欢“乐队化的音乐”。现在我们就属于“乐队化的音乐”的状态。
今日民族:你们的创始团队,今天还有哪几个在呢?
瞿子寒:最早的人就是我和小欧还在。其实这个乐队算是成员变化相对较少的。中间还加入了几个成员。
今日民族:你们在什么时候开始从爱好到慢慢得到认可,开始真正有了做乐队的信心呢?
瞿子寒:是第一次迷笛音乐节。2002年我们第一次参加国内的户外音乐活动,就是迷笛。它也是中国现在音乐节文化最早的启蒙。我们也算是最早一批参与者。
今日民族:在这个音乐节上别人是怎么看你们的?
瞿子寒:别人觉得我们演奏的是不一样的音乐。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不管是参加的学生还是同行,对我们还是比较肯定的。因为当时我们的音乐手法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更多是重金属,而我们和重金属关系不大。
今日民族:那你们是哪种风格?当时你们唱的是哪些作品?
瞿子寒:我们的框架还是摇滚,但编曲方式不一样,是有一些民族元素在里面。《山人》这首歌是有的,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其他有些可能大家不熟悉,因为有一些我们没有发表。
今日民族:那个时代在昆明的乐队是什么状态?
瞿子寒:上世纪90年代,在云南独立音乐这个圈子里,大家受影响最多的是摇滚乐,摇滚是那个时代大家寻找自己音乐身份的最好的音乐形式。但大部分是金属,和整个国内摇滚乐队的风格区别不大。当时最多的就是流行、金属和朋克这三大类。
今日民族:你们当时不属于这三种?
瞿子寒:是的,但是会带有一些痕迹。早期我有段时间也喜欢金属,受过影响。而对我们做音乐的人来说,风格只是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还没有提升到一种文化,比如朋克文化,什么文化的。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手段,也可以说是技巧——这种形式的音乐适合表达怎样的情绪。但是,我们跟这种文化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它们是从西方过来的。
向民族民间音乐靠拢

拜访南美安第斯山脉印第安人
今日民族: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对民族的东西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往民族方面靠?
瞿子寒:其实一开始就有了,只是开始可能没有后面那么高的比率。有了“山人”这个乐队的名字,我们就是想做一些和云南有关系、跟中国音乐有关系、跟我们的传统和根有关系的音乐,不管是语言还是音色。
从表象上来看,最大的改变是从我们开始直接使用民族的乐器开始。这其实是别人给我们一个身份认同的重要阶段。因为更多人是看外在的东西,从我们加大民族乐器的使用频率上开始,大家觉得我们在转向民族音乐。但从我们的音乐理念上,我们一开始就是。像《山人》这首歌里,有一个段落,我是用吉他模仿白族的三弦,因为吉他是我更擅长的,吉他也比较包容,可以更快地找到这种音乐的感觉。后面我觉得它还是没法取代民间乐器和民间的节奏。所以,就想办法引进民族乐器。这种想法是迷笛音乐节以后就有了。就想去找一些不同的音色或者演奏方法,就想去学一些民间乐器,融合在电声里。现在看可能很简单,但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难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这么做。
今日民族:你们一开始的成员都不是特别擅长民间乐器,是后面慢慢学习的?
瞿子寒:是的。2002年至2003年我们一直在北京。“非典”时期我们回到了昆明。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加入的民间乐器比较多了。
今日民族:第一个学的乐器是什么?
瞿子寒:我学的是弦子,楚雄牟定的弦子。在这个之前,我自发做过一些昆明周边的采风。我当时拿一个小的录音机(用磁带的那种),去周边的一些对歌会。在那个年代,昆明已经有一些民间艺人会有自己的一个小群体,在昆明的某个角落自娱自乐,我经常去这些地方,我很喜欢。
今日民族:这期间,有没有什么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乐器或者人?
瞿子寒:早期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时,我就看到了一些乐器,比较多的就是楚雄的弦子。那时候还没有广场舞,他们都是自己弹自己开心,我就拿着录音机去录。我还跑了周边汉族的一些对歌会。当时跑马山有个对歌会我也去,各种节日,民间会有一些自发的歌会,我都去听,但是唱歌的形式多一些。
今日民族:我看到你后来用四弦直接代替了吉他,这个转变是很大的。四弦声音是很小的,你们怎么解决声音问题,还有四弦如何与其他乐器合奏等问题?
瞿子寒:这确实是很大的问题,把四弦搬上舞台其实用了很多年。对于现在来看可能很简单,但当时我们意识不到怎样发挥它的功能。一开始我们就是直接用话筒对着它弹,演出了很多场效果不好,后来我们就直接改成插电。定音也是个问题,以前我每一次演出,那些弦子我用水泡,就为了让那个弦钮不跑音。这是个民间的办法,调音的时候用点水来定弦,但我发现还是不行。后来就改用了金属旋钮,这样就稳定一点了。其实这个过程很长,是慢慢逼出来的。
今日民族:民间乐器确实有粗糙的一面,有各种问题,所以民间音乐怎样走到现代音乐中,你们有很深的体会吧!
瞿子寒:我觉得必须改革。其实像西方的流行音乐,就是白人的教堂音乐和非洲的民族音乐结合出来的。现在经常使用的非洲鼓,以前的状态和云南的象脚鼓、太阳鼓等调音方式都很接近,只是被一些音乐人改善了,才变成现在这样的。之所以它变成了主流乐器,就是因为这些改革。
今日民族:你们的探索,很有意义,不仅让城里人看到一种新的音乐,也会让一群更年轻的人从你们的经验中得到启示,节省了云南民族民间音乐向现代音乐转型的时间。
瞿子寒:谢谢!我们那时候真的很头疼,有一段时间的演出真的没法看,的确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
今日民族:民间乐器加入后,和声的问题怎么解决?
瞿子寒:比如说音阶的问题,我们仔细研究过。拿彝族的乐器来说,它不是十二平均律的概念,是七律,是七个等分音,所以它听起来不是那么准。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你把它弄准了之后就不对了,不好听了。后来我就想到,布鲁斯音乐也是同样的问题,它有很多的四分之一音,比如“咪”和“发”之间还有一个音,它要的是“咪”和“发”之间的那个音。所以后来我就释怀了,觉得这并不重要。十二音阶的概念是古典音乐中定的。我发现只要它在某几个音上是一致的就够了。我们现在的方式就是:只要在某几个重要的定音上基本是一致的,就问题不大,其他就是它的特色。
今日民族:你们的乐队就是求大同存小异。
瞿子寒:是的。如果要纠结音阶的话就没法弄,尤其是节奏。例如,我们学过的最复杂的节奏是怒族音乐的节奏。我们向怒族的老艺人学了一段时间,光是学那个琴就用了好几天时间,虽然我已经弹了那么多年琴。它的演奏方法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很复杂,不容易掌握。越深入,越了解,越发现民间音乐是一个宝库。

在怒江采风
(责任编辑 赵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