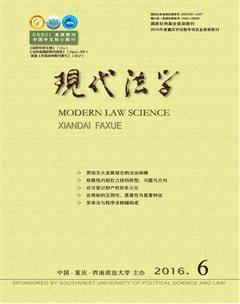论我国邻避风险规制的模式及制度框架
摘 要:
邻避风险规制所涉主体有行政机关、项目建设方、受项目影响的民众与技术专家等,他们在邻避风险议题形成、安全标准制定、风险评估、风险交流与风险管理中具有不同的角色与功能。基于风险知识的专业与信息的异化,不同主体在科学知识与社会价值方面会形成不同的判断与体认,这已使我国当前的邻避风险规制陷入恶性循环。打破恶性循环,需要重塑我国邻避风险规制的合法性。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邻避风险规制模式基于当代政治法律理论的支持,能够平衡风险规制中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符合我国社会现实需要,其制度框架由基本制度和操作性制度构成。
关键词:邻避风险规制;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环境协商;风险交流
中图分类号:DF468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6.06.10
一、邻避及邻避群相勾勒
自2007年厦门反对PX项目事件以来,“邻避”
“邻避”指的是一地居民希望保护自身生活领域,避免受到对居住地域具有负面效应的公共或工业设施的干扰,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恶行从身边驱逐出去,对于可能对自己生活造成影响的环境问题或风险,表达强硬的拒斥态度,并为此付诸行动等。(参见:杜健勋.邻避运动中的法权配置与风险治理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4):107-120.)已为我国公众所熟知。这种被视为个人或社区反对某种设施或排斥土地某种使用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乃至形成的邻避症候群(NIMBY Syndrome)已构成对社会秩序的严重挑战,正在侵蚀社会管理的基础。愈演愈烈的邻避冲突
近年来,我国的邻避冲突呈量级增长,本文仅列举10起有代表性、引起国内社会甚至国外极度关注的大型事件,参见文中表格。凸显我国的环境风险规制已经陷入某种意义上的合法性危机。频频发生的邻避事件,是对我国社会信任体系的沉重打击,而且威胁到政府行政的权威与效率。对制度的信任是我们服从该制度的心理基础,也是制度具有生命力的动力机制。缺乏社会信任的邻避设施修建,以及因之而形成的环境风险规制当然得不到受该设施影响之群体的支持,得不到社会支持的风险规制又削弱了政府进行环境风险规制的能力,如此往返,恶性循环,除了地点和时间不一样之外,我国各地的邻避冲突都以相似的模式展开。
2007年5月20日开始,反对PX项目的信息便通过各种现代通讯渠道传播,6月1日和2日,上万名厦门市民佩戴黄丝带上街游行,要求停建项目。
5月30日,厦门市常务副市长丁国炎正式宣布缓建“海沧PX项目”的决定。
11月6日,《厦门日报》报道称厦门市人民政府已决定复建PX项目。12月16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决定将该项目迁往漳州市漳浦县的古雷半岛兴建。
广州番禺区反对垃圾焚烧厂事件
2009年2月-2013年6月
2009年2月,广州市人民政府通告决定在番禺区大石街会江村与钟村镇谢村交界处建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于2010年建成并投入运营。2009年
10月,番禺大石数百名业主发起签名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抗议活动。
12月10日,番禺区表示,暂缓“垃圾发电厂”项目选址及建设工作,并启动选址全民讨论。
2011年4月12日,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召开“番禺垃圾综合处理(焚烧发电厂)”新闻发布会,项目再次启动征集,2013年6月26日上午,在南沙区大岗镇举行了第四热电厂的奠基仪式。
大连市反对PX项目事件
2011年8月
2011年8月8日,受台风影响,位于金州开发区福佳大化PX工厂的500-600米堤坝中的两段垮塌,经媒体报道,引起公众恐慌。
8月14日,约12000名市民到市政府驻地进行示威集会,随后展开游行,要求政府下令让这家化工厂搬出大连。
大连市委市政府14日下午作出决定,福佳大化PX项目立即停产并正式决定该项目将尽快搬迁。
路透社得到消息称,该工厂在示威当天仍在正常运行,《新京报》2012年12月24日报道,大连福佳集团一高管证实,该公司PX项目已复产,没有搬迁消息,并称“生产就从没停过”。
什邡市反对钼铜项目事件
2012年6-7月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7亿美元建设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
6月29日,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为钼铜冶炼厂奠基。7月1-3日,大量学生和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大楼前抗议和游行,要求暂停冶炼厂项目。
当地政府于7月3日宣布取消钼铜冶炼厂的建设。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高管于7月9日告诉《财经》杂志记者称,未来钼铜冶炼厂是否会继续建设以及是否会坐落在四川省这两点都还不明确。
启东市反对排污项目事件
2012年
7月
南通市人民政府批准日本王子制纸的制纸排海工程项目。
7月28日清晨,数万启东市民在市政府门前广场及附近道路集会示威,要求工程停建。
7月28日,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授权发布:南通市人民政府决定,永远取消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
市长在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一个名为“启东市发布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的视频,这个视频声明了政府的态度,即应市民的要求,这个项目暂时不会启动。
宁波市镇海区反对PX项目事件
2012年10月
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镇海炼化公司在原有的生产规模基础上扩建,总投资558.73亿元人民币,其中包含PX装置。
2012年10月初,镇海区的居民陆续到区政府上访,10月26-28日,镇海区居民聚集在公路上游行示威,要求项目停建。
宁波市政府承诺不再建设PX项目,并停止推进整个炼化一体化项目。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网站公布了宁波市经与项目投资方研究后的决定:(1)坚决不上PX项目;(2)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停止推进,再做科学论证。
昆明市反对PX项目事件
2013年5月
中石油云南石化安宁市草铺工业园区兴建1000万吨炼油项目,计划年产100万吨对苯二甲酸和65万吨对二甲苯。
5月4日,众多民众戴着写有黑色PX、红色叉的口罩,走上昆明市街头进行抗议。5月16日,群众于市中心老省政府的五华山聚集,再次游行。
昆明市市长李文荣承诺:“大多数群众说不上,市人民政府就决定不上。”
茂名市反对PX项目事件
2014年2-4月
2014年2月,茂名市人民政府高调宣传PX项目,官方媒体多次刊文介绍PX,举办了多场学习会,计划兴建PX项目。
3月30日-4月3日,大量市民聚集市政府与周边道路抗议,4月27日9时,民众再次聚集高新区七经镇米粮路口抗议。4月1日,有市民在广州中山纪念堂附近进行了反PX游行。4月3日,有市民在深圳大剧院门前聚集以表达对PX化工项目的不满。
3月31日,茂名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表示:“如绝大多数群众反对,茂名政府部门决不会违背民意进行决策。”4月1日,政府再向公众重申:该项目仍在科普阶段,在社会没有达成充分共识前不会启动。
杭州余杭区反对中泰垃圾焚烧厂事件
2014年5月
杭州市3月底公示2014年重点规划工程项目,其中包括即将在城市西部的余杭区中泰乡建造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4月24日,杭州城区居民及周边村民向杭州市规划局提交了一份2万多人反对建设九峰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联名信。5月7-10日,大量民众在拟设垃圾焚烧厂的地点聚集。
5月11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表示,项目在没有履行完法定程序和征得大家理解支持的情况下,一定不开工。
9月12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九峰环境能源项目相关情况进行说明,并发布规划选址公告和环评第一次公示,介绍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工作内容并征求公众意见。
上海金山区反对PX项目事件
2015年6月
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石化签订搬迁协议,将高桥石化迁往上海工业区即金山地区。
6月22日-27日,金山数万市民聚集区政府门口静坐并游行示威。
6月22日,金山区人民政府发布《告市民书》称:上海化工区规划环评不涉及PX项目,上海化工区将来也不会有PX项目。
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经研究要求上海化工区管委会终止本次规划(修编)环评工作。28日,金山区人民政府就规划环评发布《告市民书》(二)。
根据西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环境抗争的研究常被置于社会运动与集体行动的理论体系之中,认为环境抗争源于社会结构不公正,处于社会不同层级的群体未能公平一致地享受环境权利,是环境不正义的结果
环境正义关注环境保护中基本人权的保障,关注人类社会内部环境利益与负担的公平分配等。(参见:杜健勋.环境正义:环境法学的范式转移[J].北方法学,2012(6):115-126;张金俊.国外环境抗争研究述评[J].学术界,2011(9):223-231;王全权,陈相雨.网络赋权与环境抗争[J].学海,2013(4):101-107.)。通过上表中我国近年典型性的邻避冲突可以看出,其一般的发展轨迹为:政府规划某邻避设施——公众从某种管道知晓项目——借助现代传媒宣传其危害——要求政府公开信息或接受质询——政府态度暧昧——组织到城市广场或政府驻地——形成规模、示威游行——政府维稳、冲突发生——迫于压力,政府宣布项目缓建或停建。这似乎说明民意获得了重视,民众的环境维权抗争取得了胜利。但是置于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结构的大背景之下,我们会发现,西方学术界所运用的“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环境运动”甚至“环境正义”都不能准确概括发生在中国的邻避冲突[1]。Jean-Jacques Laffont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常缺失发达国家政府所具有的两个典型特征:对政府的“宪政制约”和一定程度的签订长期契约的能力;运行良好的民主社会所具有的制衡机制(最高法院、政府审计体系、分权、独立媒体)等,这使得政府更容易成为利益集团和赞助商的猎物[2]。对处于社会转型与利益分化时期
的中国而言,权威治理情形可能比这还要糟糕
参见: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J].社会学研究,2011(1):1-40.这种权威治理是“以中央权威为核心,以地方政府的逐级任务分包和灵活变通为运行机制的权威型社会治理体制”。(参见: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J].开放时代,2011(10):67-85;渠敬东,等.从总体性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104-127.)。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治理生态中,基于维稳的惯性思维,地方政府首先是动用强力压制环境抗争,如果事态发展并未按其设定的方向发展,超出其预期,则进行所谓的“按民意行事”,为一时计,在压力下宣布暂缓或停建项目。这很显然不能用“侵权—维权”的结构来解释,在“弱社会”的治理生态中,环境非政府组织(ENGOs)也不能起到西方实践中环境抗争的中坚作用,“中国的环保组织一旦和‘环境运动沾边,命运就多舛了”[3]。摒弃权利的迷思与“抗争—维权”的理论框架,我们回到中国邻避冲突的现场,从所涉主体的角色来研究邻避风险规制的模式转换,因为“人们的社会角色会对他们的决策产生特定的影响”[4]。邻避冲突所涉主体一般有行政机关、项目建设方、受项目影响的民众和技术专家等。
(一)行政机关的角色
第一,作为邻避风险公共利益的判断者和代表者。经过法律授权,行政机关可以判断与邻避风险有关的公共利益,行政机关可以判断邻避设施所带来的风险是否能够为社会所接受,邻避风险信息通过何种方式在何时向社会公开,以及采取何种措施来管理邻避风险等。第二,作为邻避风险规制的领导者和监督者。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规定评估邻避风险,制定邻避设施的技术标准,对邻避设施运行的全过程有监督管理的权力,并且可以依法对违法行为作出处罚等。第三,拥有权力当然就意味着承担责任。行政机关是邻避风险规制中责任的集中承担者,如果在风险规制中滥用职权,违反环境保护与治理规范,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立法对行政机关的角色规定得很明确,《环境保护法》第6条第2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制定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第16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行政机关也是循此展开邻避风险规制实践的,几乎所有的邻避冲突都是由政府主导下的产业规划引起,到冲突失控时,政府马上宣布缓建或停建以平息冲突,这充分说明了行政机关在邻避风险规制中的权力运用。
(二)项目建设方的角色
从当前邻避风险规制的实践来看,项目建设方作为行政相对人,遵守相关环境法律法规,服从行政机关的安排。政府招商引资,吸引企业前来投资建厂,而一旦发生邻避冲突,事态不可控时,政府宣布缓建停建,企业也得服从政府的这种安排,其前期投资可能“打水漂”。这也是在所有的邻避冲突中,我们看不到企业的身影的原因,似乎都是政府和民众的对峙。社会大众会天然地认为企业是具有“原罪”的,正是公众预见到基于“管制规则”,在法律的允许和保护之下,企业在管制红线之外必然会创造游离于法律之外的市场,或者偷排,或者超标排放,或者违规利用资源等,因此在项目立项之初就提出反对意见,这便是邻避冲突的源头[5]。但是,企业不承担邻避冲突的责任,这和西方的邻避冲突有很大差别:在西方社会,一般民众会把矛头直接指向企业,要求企业遵守法律,履行承诺;政府是管理者、监督者,更重要的是,政府是居间协调者。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企业虽不承担责任,但企业基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社经地位,始终影响着政策与法律的制定,影响着政府的决策。这就出现一个悖论,企业参与决策的源头,而不对决策的结果负责。
(三)受项目影响之民众的角色
对于受邻避设施影响的周边民众来说,由于其较弱的社会经济地位,没有能力影响政策与法律,政府环境决策可能会忽略他们的利益与诉求,附之以信息的渠道不畅、邻避专业知识鸿沟等,当他们通过其他管道得知邻避设施可能修建在自家后院时,便开始抗争。有人认为这就是所谓的“邻避情结”,即居民想要保护自身生活领域,维护生活品质所产生的抗拒心理和行动策略
一般来说,邻避情结是一种全面地拒绝被认为有害生存权与环境权的公共设施的态度,基本上是一种环保主义的主张,它强调以环境价值作为衡量是否兴建公共设施的标准,邻避情结的发展不许有任何技术面的、经济面的或行政面的理性知识,它是一种情绪性反应。(参见:M.E.Vittes, P.H. Pollock, S.A. Lili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NIMBY Attitudes[J].Waste Management,1993,13(2):125-129.)。公众对于政府、专家缺乏信任,更不会相信企业会守法运营,其结果就是政府与专家的话语失去舆论控制力,从而激发更多的人参与抗争[6]。公众运用价值测量来衡量自身的风险,以有用的标准,采取实用主义的策略进行抗争[7],因为“缺乏制度化纠纷解决方式的激励,从而转向非规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8]。价值具有多元化和相对性,价值是一种主观感受,这与科学的理性判断当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民主国家中,普通人的直觉更具规范性,公众的观念应当作为环境风险规制的主要标准。”[9]为了维稳,为了向上级交差,政府便作出妥协,民众的邻避抗争似乎取得了胜利,其权利与诉求似乎得到了保障,但这不是程序性的制度保障。厦门PX项目最终迁往漳州,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也择址建设,大连PX厂从未停产,这些足以说明政府的承诺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行为选择。
(四)技术专家的角色
为了科学决策,邻避风险规制通常要依赖相关领域的技术专家,所以,技术专家也是邻避风险规制中非常重要的主体。与普通公众不同,专家通常在特定领域内有过专门的系统知识训练和长期的经验积累[10]。因此,专家在其知识路径上作出的判断往往被认为是科学的、权威的、可靠的。纵观当前的邻避冲突,技术专家提供邻避风险知识,并且为行政机关决策的合法性进行论证。政府的说辞中经常包含“根据专家意见”、“专家认为”等用语,其包含的意思就是,专家是客观的、中立的、有权威的,专家的意见是正确和确定的,有专家辅助的决策是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是正当的。我国《环境保护法》第14条对专家意见作出了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经济、技术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听取有关方面和专家的意见。”殊不知,邻避风险规制中科学与价值的不同认知模式导致专家和公众对风险的知识形成不同的判断。专家一般会认为公众是无知的,会夸大风险,其对风险的认识是非理性的,甚至是错误的[11]。因此,技术专家认为将风险规制交由民主决策将是无效率与不科学的,主张在邻避风险规制中实施完全的“专家统治”,但这极可能导致权力的恣意。
二、我国当前邻避风险规制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规范的意义上,邻避风险规制应当是由议题形成、安全标准制定、风险评估、风险交流和风险管理等要素构成的制度状态。基于西方社会邻避风险规制的经验,在“国家—社会”的理论体系与“侵权—维权”的权利话语背景下,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司法救济是其基本的制度结构。我国《环境保护法》也是循此思路进行修订的,第5条确立了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基本法律原则,并在第5章中规定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也加强了司法救济的力度。有学者认为,新法“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对于环境行政管制的依赖性,并在确立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等宏观国家环境战略与法律价值导向的前提下,初步建立了社会化、综合化的环境公共治理的多元法律机制”[12]。但是从法律的社会效果来看,《环境保护法》的实施并没有根本改变我国邻避冲突的严峻现状,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规制邻避风险的能力依然不信任。总体而言,当前我国邻避风险规制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一)在邻避风险议题形成方面
所谓邻避风险议题,就是确定那些规划和设施是邻避风险,并据此进行风险规制。议题形成是行政机关分配资源进行风险评估、制定安全标准并进行风险管理的基础与前提。邻避风险议题的形成充满价值冲突。例如,对于PX项目,行政机关和项目建设方,在专家的辅助下,多认为是“低毒”、“无害”、“安全”,而民众则认为是“剧毒”、“相当于原子弹”、“高度致癌”、“和白血病、畸形儿相联系”
在网络上搜索PX关键词,结果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不同主体的态度与所持的基本观点。具体请见维基百科中关于“对二甲苯”(PX)的词条解释,以及在维基百科中搜索中国各地反对PX项目的事件。(资料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B9%E4%BA%8C%E7%94%B2%E8%8B%AF.)。在邻避风险议题上,科学和价值对立,专家通过科学计算与理性分析,得出自认为客观的、确定无疑的结论,并为行政机关所采纳。民众的价值认识则是多元的、充满争议的,民众认为专家的结论是在为政府背书。在实践中,行政机关通常没能充分考虑利益可能受损的群体,特别是邻避设施周边的民众的权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误区是,政府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想当然地认为小部分群体应该牺牲和付出……封闭决策、简单通告,当老百姓开始有意见时,又采取回避的办法,于是越闹越大。”[13]有论者认为,这是因为“政府行为的企业化和市场化,使得社会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的种种努力,在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冲动面前显得软弱无力”[14]。
在厦门反对PX项目事件中,政府决策中完全看不到市民的身影,大多数市民对建PX厂并不知情,2007年5月20日左右,有人通过手机短信传播该PX项目信息,社会公众方才知晓。事件发生后,相关的媒体报道也一再被屏蔽。第256期的《凤凰周刊》由于刊登了《厦门:一座岛城的化工阴影》一文,被厦门有关部门禁止销售。讨论该事件较为集中的厦门小鱼论坛于5月28日被关闭,网络上各大网站(如网易等)曾有报道PX项目的新闻,但迫于政府压力都相继删除。在茂名PX项目事件中,政府决策“先斩后奏”,议题形成中完全看不到民众的身影。自2014年2月起,茂名市人民政府开始高调宣传PX项目,官方媒体多次刊文介绍PX,举办了多场学习会。《茂名日报》2月27日刊登了《茂名石化绿色高端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一文,详尽介绍了茂名石化公司的优点与品质
参见:周清树.茂名事件:反PX诉求如何“跑偏”[EB/OL].(2014-04-11) [2015-11-18].http://www.bjnews.com.cn/note/2014/04/11/312650.ht.。3月17日,茂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华章向当地主要网站、三大通信运营商负责人就相关舆论、信息管理方面的工作进行具体部署,要求他们守住底线、服从管理,当地还加强了网络舆情监控和引导。与此同时,要求石化系统、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学校的学生签署《支持芳烃项目承诺书》[15]。政府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宣传其优点与品质,另一方面,逼迫民众签署《承诺书》,从来没有和民众进行过良好的沟通,民众完全处于议题之外。
(二)在邻避风险安全标准制定方面
邻避风险的安全标准是进行风险规制的依据,也是项目建设者进行作业的基本依据,科学的标准能够消解反对者的疑虑。邻避风险安全标准有诸多方面,包括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检测方法标准、样品标准等。这些标准大多是确定的,但这些标准一般是经过严格科学计算得出的图形、数据、符号与代码,对于没有受到科学训练的大众来说,显然超出其知识范围与认知能力。大众只要清楚简单地知道,该项目离我有多远,其排出的有毒废弃物能否到达我的住地,会不会影响我的健康与安全等。即使这么一个简单的安全距离标准,我国也没有相关的规定。如在大连反对PX项目事件中,民众普遍信任“国际组织规定PX项目至少应该离城市100公里才安全”的说法,而政府引用某权威专家的说法,认为“纯粹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并且举例美国休斯敦PX装置距城区1.2公里;新加坡裕廊岛埃克森美孚炼厂PX装置距居民区0.9公里;日本横滨NPRC炼厂PX装置与居民区仅隔一条高速公路
参见:吴睿鸫.别利用PX项目选址远近转移公众视线[EB/OL].(2011-09-16)[2015-11-18].http://focus.cnhubei.com/columns/columns4/201109/t1830576.sht.。没有一个客观权威的、具有说服力的标准,加之民众对政府和企业的极度不信任,恐慌情绪的蔓延就属正常。这种情绪性的反应,就是通常被认为的“邻避情结”,并因此引致邻避冲突。
(三)在邻避风险评估方面
风险评估是邻避设施修建的前提性与基础性工作,环境影响评价担负着邻避风险评估的重任。《环境保护法》将环境影响评价作为基础性的制度进行规定,根据第19条的规定,“编制有关开发利用规划,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且规定“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环境影响评价法》则作出了更具体与细化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要求客观中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新建设的项目,对可能会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和需要采取的措施,预先进行评估,并且征求项目所在地居民的意见,根据评估结果对原项目内容进行修改,直到取得一致意见再开始建设。要求运用科学知识,正确、客观、公开、公正地反映邻避设施安全风险的严重性
参见:《环境影响评价法》第4条。。这就要求至少满足以下两项条件:(1)价值合理性,即行政机关设定的风险规制目标能够为民众所接受,从而具有正当性;(2)工具合理性,即行政机关规制风险的手段或措施基于精确的计算和预测,具有科学性[16]。然而,我国邻避设施建设中符合立法规范的环境影响评价不容乐观。
在四川什邡反对钼铜项目事件、江苏启东反对排污项目事件以及其他反对PX项目事件中,在立项时都没有把环评作为决定项目是否建设的根据,而环评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公众参与的程度。什邡事件信息公示:“本次公众参与的范围主要为四川宏达钼铜有限公司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所在地的和本项目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有媒体报道:“除了当地居民反对之外,一些在当地投资建厂的企业,比如蓝剑集团以及长城雪茄卷烟厂对此也很有意见,甚至政府内部对此也有不同的声音。”[17]秦皇岛西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虽然没有酿成邻避冲突,但环评造假却触目惊心,环评报告中写到:“通过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告、发放调查表、公众参与等形式,调查结果表明,100%公众支持本项目的建设和选址。”报告后还附上了100份公众意见调查表,这些调查表的“填写者”全都表达了赞同的意见。但维权村民核实发现,100名被调查者中,有15人“查无此人”;有1人在填写调查表时已死亡;有14人常年在外;有1人因故意伤害他人已潜逃8年;有1人重复填写两份调查表;有1人在镇政府工作;1人未找到;有2人未核实。其他65份调查表虽然与村民名字相符,但均表示:“此前未见过该调查表,调查表不是本人所写,且不同意在该地建设垃圾焚烧项目。”[18]在众多的反对PX项目事件中,以下问题比较突出:环评程序推延,公众参与环节推迟,直至邻避冲突发生。
我国当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存在很多问题,包括环评目标设计不明确、环评操作难实现、环评管理设计复杂等。按照现行的制度设计,环评的管理简单终止于项目的前期,企业污染的责任追究并不和环评相关。其结果就是:“环评手续合法,但项目运行中环保却不合格的情况,给社会和公众造成环评无用的直观印象。”[19]从立法精神与制度目的来说,环评以解决选址与公众关心的环境问题为旨归,但现实的情形却是通过环评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经过多方论证与公众意见表达,环评报告成了“承诺书”,企业承诺要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增加多少环保投资减少污染,政府承诺进行何种监管,配套多少工程来满足项目理论上的“环境可行性”。残酷的现实一再证明,政府与企业的承诺往往不能兑现,因为这些选址本身就“不合适”,公众意见也未能得到适当的表达,邻避冲突终不能避免。“环评造假,环评公关成了行业的潜规则,先把环评报告编圆了,拿到批文再说,环评终究沦为过场。”[20]
(四)在邻避风险交流方面
风险交流是风险规制中极为重要的环节,观察现实中各地发生的邻避冲突,我们可以看到,延迟或片面地传播邻避风险信息是行政机关的惯常策略,采用单向而非双向互动的方式进行风险交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和第10条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履行邻避风险交流的职责。《环境保护法》第5章设专章规定“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法》也有相当多的条文规定了风险信息共享与公开。《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也明确规定:“环保部门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环境信息,通过政府网站、公报、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一方面,就立法来看,仍然“体现为发布——接受的单向公开模式,没有确立政府的回应义务,不足以确保政府的公信力”
虽然新《环境保护法》在信息公开方面有了诸多进步,如明确了公民的环境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具体化,设置了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定义务,环评报告书公开等。但单向公开模式,无政府回应的问题依然存在。(参见:陈海嵩.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溯源与展开[J].法学研究,2014(3):62-81.)。另一方面,实践中有效的风险信息交流并不多。“在初期以目的正当而忽略手段与方法的合理性,忽略平等的沟通与解释,激起民粹行动,危及社会稳定后又开始妥协或敷衍,放弃应有担当,置政府与法治公信力于不顾。”[21]以四川什邡反对钼铜项目事件为例,铜的冶炼和提炼过程会产生多种有毒的副产品,包括水银、二氧化硫和砷等,居民们担心这些污染物会渗入城市的空气和供水系统[22],但是,政府“只发布了工厂环境报告的简短版本,该报告没有提供固体废物和废水的信息”[23]。在项目开工前,附近村民收到了村委会发放的“环境影响评价意见表”,该表列出了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项目对当地的好处,却没有把民众最为关心的项目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列出[24]。邻避冲突发生的模式几乎一致,政府在项目立项时,有效的风险交流与沟通几乎不存在,缺乏必要的环境信息支持,致使参与不能。首先,信息公开的方式单一,只是简单地公布于政府网站或是张贴告示,能够有效接收到信息的民众不多;其次,信息公开的时间较晚,一般是主管部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阶段才公开相关信息,这时项目已开始了前期大量的投资,民众认为被欺骗;再次,环评信息公示的时间非常短,且只公示简本,甚至很多项目连简本也未公示;最后,公示的内容简单模糊,或者以专业化的名词进行描述,公众无从知晓[25]。按照社会学的解释,在“问题知晓”环节,行政机关信息释放的关键词是“科学、安全、高效、合法”,而民众对之的理解是“风险、暗箱、利益、违法”;在“问题解释”的环节,问题认知扩大化——由邻避设施选址的科学性与合法性问题转变为权益保障问题,而行政机关的“决定—宣布—辩护”的决策思维对扩大化起到了激化的作用;在“问题评估”环节,进一步确认了问题认知,强硬的发布方式、民众不能置评、沟通不足使得民众从“利益受损者、受害者”的角度进行“问题解码”[26]。没有相应的反馈机制将公众的意见带回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再对之作出回应,其结果就是由对邻避设施选址的科学性与合法性质疑转变为邻避抗争的集体行动。
(五)在邻避风险管理方面
风险管理是邻避风险规制的核心环节,它是负有邻避风险规制职能的行政机关选择相应的行政执法措施用以排除、减少、缓解、转移和防备邻避风险的行政活动[27]。《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都明确和详细地规定了行政机关对邻避风险的执法与监督职能。但在实践中,行政机关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缺失,救火队员式的管理尤为明显。
在江苏启东反对排污工程事件中,在事件发生的前夜,也就是2012年7月27日晚,就有部分市民聚集在游行出发地,并通过多种途径放出游行的规划线路图,但政府几乎什么也没有做,好像就等着28日一早游行开始。颇为吊诡的是,政府于前几日挨家挨户派发“告市民的一封信”,这样使得原本乡下不知此事的人也知道了,更增加了游行的人数。在中午政府宣布排污工程永不建设后,现场人群渐渐散去,但这时吕四的民众来了,他们因为政府交通封锁、前夜步行了数个小时,心情极度糟糕,而政府方面也无人出面沟通,只是通过一个扩音器来解释所谓的工程项目,导致群情激愤
参见:Carlos Barria.China Cancels Waste Project after Protests Turn Violent[N].Reuters,2012-07-28;江苏启东万人集会迫市府叫停排污工程[N].RFI,2012-07-28;法新社.江苏启东抗议造纸厂污染民众与警方冲突[N].ABC Radio Australia,2012-07-28.。梳理一下,我们发现,游行信息在事前广泛传播,政府派发告示让更多人知晓,事件发生后,政府官员四处逃离,无所作为,组织混乱,对于一个现代政府来说,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上海金山反对PX项目事件中,事件从2015年6月22日持续到27日,长达6天。6月22日发布《告市民书》:“上海化工区上炼化一体化项目主要是为园区现有企业的原料配套,这次化工区规划(修编)环评不涉及PX项目,上海化工区规划环评不涉及PX项目,将来上海化工区也不会有PX项目”,民众对政府没有任何信任,6月23日,民众要求市长出面表态,而政府方面未有任何作为,导致事件持续发酵,至27日达到高峰,政府所做的只是出动警察设卡,阻止市民外出,乘公交车被要求出示身份证,地铁22号线亦停运,人民公园临时关闭。将人民广场聚集的民众送返至金山吕巷中学,要抗议的民众签保证书,要求不再进行示威活动,才能释放
参见:2015年上海市金山区反对PX项目事件[EB/OL].[2015-11-18].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5%E5%B9%B4%E4%B8%8A%E6%B5%B7%E5%B8%82%E9%87%91%E5%B1%B1%E5%8C%BA%E5%8F%8D%E5%AF%B9PX%E9%A1%B9%E7%9B%AE%E4%BA%8B%E4%BB%B6.。观察一下上文列出的所有典型邻避冲突,基本上政府的应对都非常被动,这也是由于邻避风险规制前所有环节失策导致的。
三、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邻避风险规制基础
基于以上分析,我国当前邻避风险规制模式正遭遇挑战,在邻避冲突多发的当下,应当重构邻避风险规制模式。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治理运动的勃兴给邻避风险规制提供了新思路——扬弃传统的自上而下科层式的、以命令与控制为主的权威规制模式,推动公共事务治理方式的变革与转型。一种公私合作的环境治理模式或许对于当下的邻避风险规制具有革新的意义,其“试图改变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一中心的、以政府行政管制为单一手段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模式”,“主张通过上下互动的参与、交流和沟通,以及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对环境与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实施社会公共治理”[12]。
(一)政治与法律理论基础
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邻避风险规制是以信息共享、平等协商、理性沟通、相互信任与责任共担为特征的新型规制模式,是政府、厂商、普通公众、技术专家乃至环保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合作型的治理模式。这种规制模式对于邻避风险规制具有伦理与法理上的正当性。在政治哲学思想中,受哈贝马斯话语理论的影响,协商民主观念为公私合作风险规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只有在所受影响的主体同意之下,政府决策才具有合法性,因此,合法的政府决策就被概念化为不同主体参与决策,提出各自论据并进行相互论理的过程。”[29]“这是一种程序主义的进路,通过建立一个程序框架,使各种观点能够理性交换、相互理解、充分论证,进而使决策考虑足够广泛,最大化运用现有知识形成洞见,并因此获得合法性。”[30]在当代公法思想中,合作治理和参与式治理的观念也强劲地支持邻避风险规制的公私合作环境治理模式。“合作治理的基本观点就是超越传统行政关系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对于管理事项公私的严格界线,强调公私合作,共同决策,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1]费雪教授认为:“通过公共理性引导利益冲突,缓和科学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商谈过程,风险和知识的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的程序性机制,容纳风险评估中‘事实和规范混合的复杂性,保证规制者高效‘行使实质性的、持续解决问题的裁量权。”[32]还有新公民参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新公民参与被认为是邻避风险规制的必要工具
新公民参与较之于传统的公民参与有两大特点:一是新公民参与更加强调对政策执行的参与;二是新公民参与扩展了参与公民的范围,囊括了低收入阶层民众以及一些新型社会组织等。(参见:魏娜,韩芳.邻避冲突中的新公民参与:基于框架建构的过程[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157-173.)。这些理论基础对于邻避风险规制的公私合作环境治理模式的正当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邻避风险规制的现实基础
1.公私合作环境治理邻避风险规制中各主体的角色转变
就行政机关来说,行政机关是邻避风险公共利益的判断者和代表者,但是这种判断是在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协商与沟通的过程中形成的,最终由行政机关以代表的形式向社会公开邻避议题的形成。行政机关当然也是邻避风险规制的领导者和监督者,但行政机关不是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行政机关要依赖邻避议题的社会背景、与该邻避风险相关的信息判断以及考虑各利益团体的关切行使权力。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更谨慎,对于生态环境危害不确定的邻避风险的规制,应当与项目方、受邻避设施影响的民众、技术专家还有环保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共同商讨邻避风险规制的措施与目标。针对PX项目、垃圾焚烧厂等这类科学与价值具有不同认识与判断的邻避议题,行政机关应当担任召集、协调与能力建设者的角色,让持不同意见的各方充分表达意见,对弱势群体的关切予以特别重视,促成一致意见与共识的达成。由于邻避议题的形成、邻避决策的作出并不是行政机关独自所为,所有有关切的主体都表达了意见,所以,责任也是有分担的,超越公私的界线,决策参与者都将承担相应的责任。正如“国家权威正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和责任日益变得模糊不清。”[33]
就项目建设方来说,服从自己参与行政过程所作出的邻避决策,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化的参与者与建设者。作为利益相关者,项目建设者要参与邻避风险规制的全过程,从邻避风险议题的形成开始到邻避风险决策的作出,都应该有项目建设方的角色,这是一种通过法律和政策保证的全面和广泛的参与[34]。这完全不同于当前权威式的邻避风险规制模式,几乎在所有的邻避冲突中,我们看不到项目建设方的出现,好似躲在行政机关身后的影子。项目建设方修建邻避设施,运营设施,维护设施,承担具体的环保责任,不应当也不能缺席邻避风险规制的过程。全面的参与一方面可以保证项目的投资有回报,不至于前期的投资因为冲突而“打水漂”,另一方面,既然作为参与者、决策者,也应当承担邻避风险规制的责任。
就受项目影响的民众来说,在公私合作环境治理模式中,其地位则与行政机关、项目建设方、技术专家等完全平等。他们不是邻避风险规制的局外人,更不是行政机关认为的敌对者、异议者,他们是和行政机关等一道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建设者。从制度的层面,应该调动民众参与的热情并保证民众参与的效果,这不是收集民意、召开座谈会等简单的形式化参与,而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协商、说理、论证、反思与回应。行政机关基于权力行使的判断,项目建设方基于经济利益的盘算,技术专家基于科学知识的可行与普通公众基于社会价值的考量,各方秉持解决问题与寻求共识的态度在一个可欲的平台上,经过多轮的方案辩论与反思,最终达成共识,作出行动决策,这不再是策略性的行动,各方“凭借一定方式探讨共同关心的环境事务,通过表达、论辩、沟通、互信、互助、协商,在利益碰撞中寻求妥协平衡,进而形成价值和利益共识”[35],这是一种“提升公共决策认可度的有效机制”[36]。当然,所有主体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承担由自己参与作出决策的责任。
就技术专家来说,在公私合作环境治理邻避风险规制模式中,专家不再只是行政机关的知识垄断者。受项目影响的民众也可以聘请专家,不同的专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供知识支撑,因此,此时的专家知识不再是独断的、确定的与唯一的。专家应当对自己所提供的知识进行清楚的解释,经过同行的审查并接受公众的质疑,不同知识视野的专家应当在尊重与科学的基础上进行辩论,从而去伪存真。专家虽然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与知识进行工作,但也不应忽略社会价值的关切。“虽然知识的争议是科学不确定性的源头,但通常很快会转变成社会价值的争议。”[37]因此,专家的知识必须和社会相连接,必须将科学知识置于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中,专家也应当有人文情怀,不光是以冷冰冰的数字与符号来演算,应当将知识转化为大众易于理解的形象化语言,从而增强民众的理解与沟通效果。
2.邻避风险规制应当在科学理性与社会价值之间达到平衡
邻避风险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一种客观真实的存在,这是不能回避的;另一方面,这种风险也是一种社会的建构,是通过心理与文化,并经由“环境主张的集成——环境主张的表达——竞争环境主张”的社会建构过程[38]。在客观意义上,PX项目、垃圾焚烧厂、核电厂、核废料存储等设施必然会产生环境污染的后果,主要包括邻避设施建造地区空气污染、水质污浊、生态破坏、景观影响、噪音污染、交通堵塞等,与之相伴随的是健康问题、房价下跌与社区品质降低等[39]。在社会建构的意义上,应当从风险感知者的角度来认知风险,它是一种心里的感受与文化的认同。“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并不取决于现实中具体发生了什么,它与人们的记忆、情感等潜意识相关,反映的是现实事件的个人主观印象。”[40]“人们除了想被告知实情之外,还想得到尊重。”[41]从2007年厦门反对PX事件开始,PX致癌的社会效应被不断放大,此后,各地一有PX项目,便逃不出冲突的宿命,引起民众的恐慌与民意的强烈反弹。在江苏启东反对排污工程事件中,政府已经承诺工程不再修建,但民众执意要求市长出面解释,由此引发了更大范围与更大规模的冲突,因此,邻避风险的社会建构不容忽视。
客观真实的邻避风险奉科学与理性为圭臬,以技术专家的知识为支撑,由于现代社会分工与知识的精细化掌握,公众对这些专业的科学知识很难解码,这就容易形成专家的垄断统治。但在现代民主国家里,忽略民众的社会价值与选择是不正当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决定了公共决策过程不可能是公共决策者在单纯的知识分析的基础上理性选择的过程”[42]。邻避风险规制不是一种与价值无涉的活动,技术专家负责描述与解释风险,而社会大众则通过邻避风险发生的社会背景来理解与风险有关的文化意义与社会知识。因此,邻避风险规制的制度安排就应当考虑双重属性,并在客观理性和民主价值之间寻找平衡。当前的邻避风险规制模式基本上建立在客观与科学的评估基础之上,忽略了社会民众的诉求,科学与社会分裂,专家的观点不被社会审查。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邻避风险规制模式则是努力寻求科学与民主的平衡,行政机关、项目建设方、受项目影响的民众以及技术专家等主体从不同的知识视野与社会经验出发,进行理性的对话与交流,各方在制度保证下的平等地位则为这种交流提供了可能性,这样就可以确保邻避风险规制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3.公私合作环境治理能够解决我国邻避风险规制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在我国当前的邻避风险规制模式中,行政机关主要采取“产生问题——掩盖/逃避问题——试图压制”的路径进行,这从大连PX项目事件中可以得到最为明显的反映,政府告知民众工厂停产,可是两年后,民众发现项目还在运营,通过工厂得知,该项目从未停产。这样的策略性行为导致民众的邻避抗争升级,并且在政治、法律与道义中遭受挫败。深究其原因,行政机关拥有无限的规制职能但其规制资源却有限,这与邻避风险规制的复杂性产生了矛盾,这正是我国邻避风险规制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当前的邻避风险规制模式之下,行政机关是风险规制的领导者与监督者,也是责任的集中承担者。在行政主导之下,“成本与收益的非对称性结构凸显出传统决策模式已经落后于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的客观需要”[21]。邻避风险具有复杂性、多样性、极强的科学技术性,行政机关并不能完全了解邻避的属性。在行政机关与其他相关主体之间,邻避风险信息也存在不对称性,行政机关由于种种原因也不能完全掌握这些信息,在这样的矛盾之下,可能会造成规制失效。
因厦门居民反对而迁到漳州修建的PX项目,于2009年3月获得发改委核准,同年5月动工,该项目在2013年初因环评违规被环保部处罚
参见:彭利国,方芳.三年等待,发改委终核准;半年欣喜,环保部再棒喝——最敏感PX项目环评违规始末[EB/OL].(2013-02-01)[2015-11-20].http://www.infzm.com/content/86048.,同年7月30日,其一条未投用的加氢裂化管线发生爆炸事件
参见:彭利国.中国PX,再经不起爆炸声[EB/OL].(2013-08-02)[2015-11-20].http://www.infzm.com/content/93050.,2014年5月,环保部官方网站曾公示漳州古雷石化基地规划环评未完成,建议发改委撤销该基地总体发展规划
参见:汪韬,何海宁,王亮.11个月前消失的公函:环保部建议发改委撤销古雷石化规划批复[EB/OL].(2015-04-07)[2015-11-20].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724.;2015年4月6日,PX项目厂区发生爆炸,造成12人轻伤、两人重伤的后果
参见:福建漳州古雷PX工厂爆炸[EB/OL].(2015-04-06)[2015-11-20].http://www.qzwb.com/gb/content/2015-04/06/content_5079557.htm;http://www.taihainet.com/news/fujian/yghx/2015-04-06/1389287.ht#g1389287=1.。这是一个典型的邻避风险规制失败的案例,项目从厦门移址漳州,几经波折,环保部一次处罚,一次警示,结果还是发生了两次爆炸,造成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邻避风险规制模式就是让项目建设方、受项目影响的民众以及相应的技术专家参与整个风险规制过程,这些主体与行政机关一起在邻避风险规制中作出决策,并承担相应的责任,通过信息的交流与相互的协商达成风险规制的目标,从而解决风险规制的复杂性难题。
四、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制度框架
制度化的保证是解决我国当前邻避风险规制所遭遇挑战的恰当途径,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邻避风险规制应当由基本制度与操作性制度构成。
(一)基本制度
基本制度是规范或调整邻避风险规制主体在风险规制中行为的规则体系。
1.环境协商制度
环境协商是在协商民主理念的引导下,受环境资源因素决策结果影响的各相关社会行动主体参与环境资源决策过程,经过公开阐明立场,审慎地权衡各方利益诉求,采取讨论、辩论、协商的方式达到统合意见,作出环境资源决策[43]。首先,有促进决策民主化与强化民众参与行政决策的能力,因为“商谈过程是多方主体合意交流和对抗交流的过程,与过度回应特定政治利益的传统政治过程相隔离”[31]40,“公众期待通过个体行动或者组织化的方式参与治理或形成一定范围内的社会自治”[44]。其次,可以促进利益团体的成熟,就邻避议题而言,我国各利益团体、公益或弱势团体之间仍处于极端对立、相互猜疑的恶质状态,难以针对各方的利益达成良性的共识。通过协商,可使利益团体的活动空间加大,促其成熟发展。最后,通过环境协商,可以促进信息收集与交流,“每一位参与者均愿意根据讨论修正自己的偏好,愿意回应性地提供新的信息或者主张”[45]。在协商式规则下,不论行政机关或各利益关系人,都较不会隐匿信息,而较能开诚布公地将有关信息贡献到协商会议中。具体来说,环境协商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1)预告。将所拟邻避设施规划与建设信息登载于行政机关公报、媒体及网站等,内容须包括规划的目的、选址的依据、相关程序的时间以及项目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等,使利害关系人与公众充分了解相关信息。
(2)选定召集人,成立协商委员会。一般来说,召集人应为中立的第三人,根据我国情况,召集人宜由行政机关具有良好声誉的工作人员担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项目建设方代表、受项目影响的民众、技术专家、行业协会、环保非政府组织、媒体代表等组成协商委员会。Boyer教授以政府对水污染的管制为例,指出利害关系人的选择应当考虑:工厂所有人及工厂股票持有人的利益、附近民众的健康与就业率、附近的生态环境、下游民众对干净河水的使用权、中下层民众低价货品的需求利益、其他同类竞争之货品业主的利益甚至国民生产总值等[46]。从实际来看,利害关系人将受邻避设施的重要影响,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利害关系人须有诚意,对采用协商方式有强烈的诱因与一定的共识;部分利害关系人就某些方面已有共同的立场;利害关系人须认清其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3)协商会议的召开。在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应该将协商会议的议题、参与人员、日期、日程、协商规则等内容进行公告。同时,行政机关应当安排适当的训练课程,帮助把握议题的主要争议、协商目的并熟悉协商规则,有利于将来协商之达成。协商会议一般应当公开进行,协商委员会的成员地位平等,通过说理和沟通,对于邻避设施的规划与修建达成一致协议。这里的一致协议可以理解为一般协议,即虽有人不同意,但其所不同意的事项并非那么重要,也不致因此破坏决议或提起诉讼,就算是成功的协商。对非重要事项持反对意见之利害关系人,可以发表声明,以示对其所代表之利益负责[47]。
(4)评论。协商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后,行政机关应当对于协商的内容与结论进行公告,接受公众评论。利害关系人及社会公众可以一定期间内,以书面或口头陈述的方式,对协商的任何事项提出资料、意见或辩论。一般来说,经过协商达成的意见,在协商中提出意见者都希望推动协议执行,会对协议进行支持[48]。
(5)形成正式的议题并公布。评论期间过后,行政机关将公众评论的意见进行整理,并反馈于协商委员会,协商委员会再据此对协商会议形成的结论进行修正,行政机关最终确定结论。行政机关负有说理的义务,对所有的评论意见采纳与否都应当作出清楚的说明,并依行政程序要求公布。
2.邻避风险交流制度
风险交流制度的关键词是全过程、双向、反思与开放,这完全不同于当前邻避风险规制中的自上而下、单向与封闭[49]。当前学界讨论风险交流的文献也较多,但多集中于管理学领域。对作为“外行”的大众与技术专家之间、大众与行政机关之间的风险交流则探讨得不多,对于大众因为专业知识不足而交流能力短缺提出的因应对策则是宣传和教育。通过风险交流可以进行知识启蒙与理念传递,并使公众的态度改变,风险交流制度的目的在于“政策利害关系人之间能够相互了解彼此的立场,及时解决公害纷争,公正制定彼此都能接受的管制标准”[50]。在邻避风险议题形成、安全标准制定、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方面,风险交流都应当扮演重要角色,而处于风险交流中的行政机关、邻避设施建设方、受项目影响的民众与技术专家等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以开放的态度提供有关邻避风险的信息,进行相互补充与讨论。“提供适当的规则、制度或原则,为公众和专家运用不同的风险知识创造平台,既能够促进专家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工具,又能够为公众的参与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从而促使这两种知识的融合与统一。”[51]风险交流制度希望邻避风险规制中的不同主体就相关的议题展开对话,增强对于邻避风险议题的理解,以推动邻避风险规制共识的达成,从而重塑行政机关与公众之间的信任,维系社会秩序。“风险交流的关键不在于‘教育外行公众理解专业技术问题,而在于建立和维持对专家的‘信任。”[52]邻避风险交流包括相关邻避信息的获取和对邻避信息的反馈与回应。
(1)相关邻避信息的获取。“获取相关信息既是风险交流的内容之一,也是公众有效参与的前提。”[53]我国2007年颁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专章对于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进行了规定。环境保护部于2014年12月19日发布了《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但最为公众所关心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却鲜有提及,“不便提供”、“不易公开,容易引起媒体炒作”等都是环保部门的拒绝理由
参见:孟斯.环境信息公开,有法难执行[EB/OL].(2011-05-13)[2015-11-20].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290-Access-still-barred.。环境信息公开不仅是立法问题,更是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问题。企业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诚实准确地公开有关邻避信息,虽然我国法律尚无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具体规定,但是政府也应当基于法律规范的精神公开相应的邻避信息,因为规范不止包括法律规则,还包括了原则和法理[54]。
(2)对于邻避信息的反馈与回应。对于公开的信息,有效的反馈与回应是风险交流的核心,真正的交流不应是单向的灌输或教育,而应是双向的互动[55],是跨越邻避风险专业门槛的知识流动与信息共享。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保护法》关于信息公开的规定,即“发布—接受”式的单向模式显然不足以收获更大的掌声与政府公信力的确保[56]。这一点也可以从《环境保护法》实施后的状况看出,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于2015年1月1日实施,2015年6月发生了上海金山区反对PX项目事件,时间持续长达6天,政府发布了两份《告市民书》,但内容简单,关于市民对《告市民市》的质疑,没有作出有效回应,事件迟迟得不到解决,这其实仍然是将民众排除在邻避决策之外的一种表现。让民众不进入邻避风险决策程序的核心部分,即在传统上认为民众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真正参与科学技术争议。成功的风险交流能够消除民众对于邻避风险的担忧,重建技术专家所进行的科学评估并基于此形成行政决策的信任。通过风险交流,最终会打消民众的疑问,以开放的心态来接受邻避设施,行政机关会以此证明其决策的正当与合法,项目建设方也能够让项目顺利进行,技术专家则捍卫了其专业知识的权威。
3.动议制度
所谓动议制度是指申请人向特定的邻避风险监管机关提出建议,要求其依法启动邻避风险议题形成、制定风险标准、实施风险评估与风险交流、开展风险管理等,特定行政机关对申请人提出的建议予以审查,并作出相应处理的制度[57]。如果申请人对邻避风险规制机关的处理决定不服,可以依法请求法律救济。申请人包括受邻避设施影响的民众、与邻避风险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普通公众、环保非政府组织以及新闻媒体等对邻避风险监管感兴趣的主体等。动议制度体现民主与自治的价值,还可以制约行政机关履行责任。动议制度的基本结构包括:
(1)提出动议申请。申请人就邻避风险议题形成、邻避风险相应标准、风险评估、风险交流以及风险管理等过程以书面形式向邻避风险规制行政主体提出建议,要求其履行邻避风险规制职责,申请书中应当列明建议的内容、理由、法律依据以及相应的佐证材料等。
(2)动议申请书的审查与受理。邻避风险规制机关对动议申请书进行审查,材料齐全、内容清楚、符合法定要件的,予以正式受理。为体现动议的价值,应当设立专门的机构收集动议材料,对审查与受理的期限进行规定,受理与否应当及时告知。在这个过程中,受理机关应当与申请人保持沟通,将受理的进程及时告知申请人,其实这也是环境协商与风险交流所要求的。
(3)审核与作出决定。经过正式受理的动议,邻避风险规制机关应当对申请的内容进行实质调查和核实。如果申请人动议的内容属实,属于规制机关的法定职责,规制机关应当接受申请人的建议,作出相应的决定,明确规制程序启动的时间等;如果认为动议内容缺乏依据,或不属于其法定职责范围,则驳回动议并说明理由。
(4)申请救济。救济也是动议制度的基本内容,邻避风险规制机关拒绝受理动议,或超出规定时间没有作出决定,或申请人对邻避风险规制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都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二)操作性制度
操作性制度是指为推进基本制度的顺利进行而需要的工具与方法。
1.技术专家研讨会
专家研讨会是环境协商与风险交流的基础操作性制度,邻避风险涉及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与争议性,借助专家研讨针对风险在技术上形成一定的共识,并以此作为风险规制的基础。专家研讨会的组织者是风险规制行政机关,邀请相关领域的技术专家就风险规制议题中的专业技术问题进行研讨与辩论,让科学与技术事实问题在辩论中得到明晰化。会议中形成的所有材料,包括专家对邻避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科学评估,以及专家对风险的解释和判断都应该如实记录并进行整理归档,这些会议记录连同会议过程都应当向社会公开。
2.共识会议
共识会议被称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新模式[58]。基于认知模式的差异,公众倾向于不相信技术专家,这已经对风险规制措施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59],因此,凝聚公众与专家之间的风险共识就成为风险规制的重要任务。共识会议可以作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尝试,“专家对邻避风险的科学和理性判断在得到容易理解的解释时通常能够有力地校正公众的认知错误,同时,公众对邻避风险的社会学视野分析则可以矫正专家因为社会分工而可能形成的偏狭。”[60]共识会议的流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组建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监督会议的组织与运行,一般包括规制机关工作人员、技术专家、项目建设方代表、公众代表各一名;规制机关工作人员则扮演会议过程中的调解者角色。
(2)确定会议代表。风险规制行政机关根据志愿报名,选择参加共识会议的普通公众代表,应当注意代表的广泛性。根据共识会议起源地丹麦的经验,共识会议中公众小组的成员以15人左右为宜。
(3)召开第一次预备会。召开第一次预备会的目的是让公众小组对邻避风险议题进行深入了解与学习,以掌握相应的知识与能力。在预备会中,规制机关扮演调解者的工作人员帮助公众小组成员学习与讨论邻避风险的专业文献资料,公众小组提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4)召开第二次预备会。在第一次预备会议的基础上,公众小组可以再次深入学习相关知识并提出问题。同时,指导委员会指定专家研讨会的专家小组对公众小组的问题进行回应与答复,回应与答复不应使用晦涩难懂的科学术语与表达,应当跨越专业的门槛,以普遍公众能理解的话语进行说明。
(5)共识会议正式召开。指导委员会召集专家小组和公众小组,营造良好的会议氛围。在会议的第一阶段,由专家发言,阐释邻避风险的相关知识,并对公众小组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应。会议第二阶段,公众小组与专家小组进行交互式询问与对质,进一步澄清事实与观点,对一些理解方面的歧义进行辩论。会议第三阶段,公众小组形成书面报告,即已经形成共识的结论或建议,对于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专家小组可以再次提供信息并进行指导,公众小组根据情形变化修改结论或建议。会议第四阶段,对于报告的实质内容不作改变,专家小组更正报告中的表述性错误,公众小组通过新闻发布会发布报告。
共识会议所形成的报告在邻避风险规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支持环境协商与风险交流制度的顺利推进,邻避风险规制机关应当认真考虑共识会议报告,作为风险决策的基础性资料支撑。
参考文献:
[1]肖唐镖.当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概念、类型与性质辨析[J].人文杂志,2012(4):147-155.
[2]让-雅克·拉丰.规制与发展[M].聂辉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
[3]霍伟亚.回望:这半年,环保组织都在忙些什么[J].青年环境评论,2012(3):6-9.
[4]凯斯·R·孙斯坦.风险与理性——安全、法律与环境[M].师帅,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45.
[5]凌斌.规则选择的效率比较:以环保制度为例[J].法学研究,2013(3):17-36.
[6]何艳玲,陈晓运.从“不怕”到“我怕”:“一般人群”在邻避冲突中如何形成抗争动机[J].学术研究,2012(5):55-63.
[7]Elizabeth J.Perry,Merle Goldman.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254.
[8]孟甜.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检视[J].法学评论,2015(2):171-180.
[9]戚建刚.风险交流对专家与公众认知的弥合[G]//沈岿.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新发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201.
[10]王锡锌.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一个理念和制度分析的框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295.
[11]Dan M. Kahan,Pail Slovic,Donald Braman, John Gastil.Fear of Democracy:A Cultural Evaluation of Sunstein on Risk[J].Harvard Law Review,2006,119:1074-1076.
[12]柯坚.我国“环境保护法”修订的法治时空观[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3):17-28.
[13]崔筝.中国城市“邻避运动”渐起[EB/OL].(2011-08-12) [2016-03-09].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676-Rise-of-the-Chinese-nimby.
[14]董正爱,王璐璐.迈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的变革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15(4):95-101.
[15]沈彬.面对“PX 恐慌”为何总无良策[N].东方早报,2014-04-01(A04).
[16]戚建刚.风险规制过程合法性之证成——以公众和专家的风险知识运用为视角[J].法商研究,2009(5):49-59.
[17]崔文官.什邡:百亿钼铜项目夭折真相[N].中国经营报,2012-07-09(A09).
[18]杨柳.秦皇岛西部垃圾焚烧厂项目环评失实——环评机构竟这样造假[N].人民日报,2013-01-29(04).
[19]王亚男.中国环评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展望[J].中国环境管理,2015(2):12-16.
[20]刘伊曼.中石油云南项目未批先改扩建:赌环保部不会叫停[N].南方都市报,2015-03-24(10).
[21]冯辉.公共治理中的民粹倾向及其法治出路——以PX项目争议为样本[J].法学家,2015(2):104-119.
[22]Ben Blanchard.China Pollution Protest Ends, but Suspicion of Government High[N].Reuters, 2012-07-08.
[23]Tania Branigan.AntiPollution Protesters Halt Construction of Copper Plant in China[N].The Guardian,2012-07-03.
[24]朱德米,平辉艳.环境风险转变社会风险的演化机制及其应对[J].南京社会科学,2013(7):57-63.
[25]杜辉.挫折与修正:风险预防之下环境规制改革的进路选择[J].现代法学,2015(1):90-101.
[26]魏娜,韩芳.邻避冲突中的新公民参与:基于框架建构的过程[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157-173.
[27]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M].王成,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40.
[28]P. Corrigan,Joyce.Five Arguments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J].Political Studies,1997,48(5):947-969.
[29]赵鹏.知识与合法性[G]//沈岿.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新发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72.
[30]Jody Freeman.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Administrative State[J].UCLA Law.Review,1997,45(1):1-98.
[31]伊丽莎白·费雪.风险规制与行政宪政主义[M].沈岿,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9.
[32]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01(9):40-44.
[33]郑少华,齐萌.生态文明社会调节机制:立法评估与制度重塑[J].法律科学,2012(1):84-94.
[34]秦鹏,李奇伟.协调各方利益冲突,规范环境立法途径[J].环境保护,2013(4):34-36.
[35]邓海峰.生态法治的整体主义自新进路[J].清华法学,2014(4):169-176.
[36]M. Schwarz,M. Thompson. Divided We Stand.Redefining Politics,Technology and Social Choice[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0.
[37]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M].洪大用,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7.
[38]何艳玲.对别在我家后院的制度化回应探析[J].学术前沿,2014(3):56-61.
[39]Claret Twigger-Ross,Glynis M.Brea Kwell.Relating Risk Experience,Venture Some Ness and Risk Perception[J].Journal of Risk Research,1999(1):73-83.
[40]Fischhoff,B.Risk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Unplugged:Twenty Years of Process[J].Risk Analysis,1995(2):137-145.
[41]汪劲.中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比较研究——环境与开发决策的正当法律程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99.
[42]杜健勋.环境利益分配法理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3:260.
[43]杜辉.论制度逻辑框架下环境治理模式之转换[J].法商研究,2013(1):69-76.
[44]Simone Chambers. Deliberative Democratic Theory[J].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03(6):307,309.
[45]Boyer. Alternatives to Administrative Trial Type Hearings for Resolving Complex Scientific,Economic and Social Issues[J].Michigan Law Review,1972,71:111.
[46]Henry Perritt,Jr. Negotiated Rulemaking and Administrative Law[J].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1986,475:90-101.
[47]叶俊荣.环境理性与制度抉择[M].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259.
[48]杜健勋.交流与协商:邻避风险治理的规范性选择[J].法学评论,2016(1):141-150.
[49]丘昌泰.公害社区风险沟通之问题与对策[J].法商学报,1999(34):17-58.
[50]戚建刚.风险规制过程的合法性[G]//沈岿.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新发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80.
[51]P.M.Sandman. Responding to Community Outrage: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Risk Communication[M].Americu Industrial Hyyzene Associatiom,1993.
[52]金自宁.跨越专业门槛的风险交流与公众参与[J].中外法学,2014(1):7-27.
[53]Ronald Dworkin. Thc Model of Rules[J].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eiw, 1967,35(14):22.
[54]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Improving Risk Communication[M].National Academy Press,1989:21.
[55]陈海嵩.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溯源与展开[J].法学研究,2014(3):62-81.
[56]戚建刚,郑理.论公共风险监管法中动议权制度之建构[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5):142-153.
[57]刘锦春.公众理解科学的新模式:欧洲共识会议的起源及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2):84-88.
[58]戚建刚.风险认知模式及其行政法制之意蕴[J].法学研究,2009(5):100-110.
[59]金自宁.作为风险规制工具的信息交流[J].中外法学,2010(3):380-393.
本文责任编辑:邵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