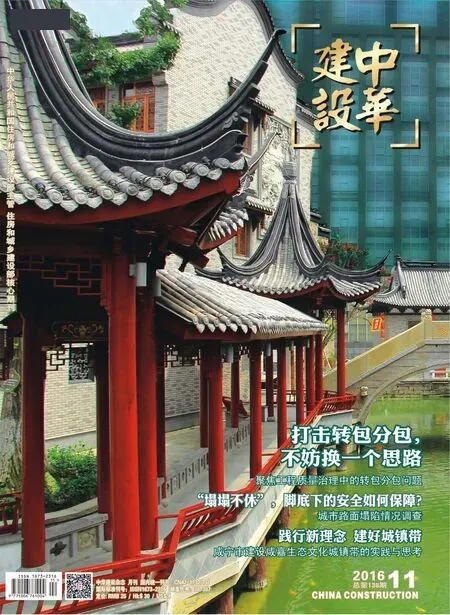“三线建设”回眸
云远
“三线建设”回眸
云远
前几年,有位学者为新出版的书《彭德怀在三线》写了篇书评,寄给北京某报,责任编辑提笔就把文中的“彭德怀在三线”改为了“彭德怀在三八线”。或许,在这位编辑的记忆库存中,搜索不到“三线”这个主题词,觉得是作者出现了笔误。
“三线”这个词,如今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然而,时光倒回半个世纪,“三线”却是一个实实在在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主题词,是一件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直到今天,三线建设的得失,对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也不乏借鉴意义。

起因
1956年,中苏关系恶化。
1962年,美国在台湾海峡多次组织军事演习。
1964年,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更是个吊诡的年份。在北方边境,中苏关系完全破裂;在南方,随着越南战争的加剧以及美国向台湾海峡增兵,中美两国的关系也更加紧张。
中央高层针对这种国际形势,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我国处于各国敌人的包围之中,随时会发生侵略战争。
现代战争的胜利与否,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特别是军工生产。当时,中国的军工产业普遍分布于东三省及东部沿海地区,一旦开战,敌方可以在战争初期就瘫痪中国的军工生产线。
因此“三线建设”被提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
所谓三线,是指远离可能的战争区域,即“国土防御第三线”。这些地区普遍集中于中国的中西部深山中。
中央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将所有的军工制造、机械制造、化工、电子、精密仪器行业的生产资源,逐步迁入大陆腹地的四川、湖南、贵州等地,而且为了保密,涉及军工类的工厂几乎全部设在了山区。
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这些内陆不易被战争涉及到的省份,被归类为“三线地区”,而这些当时肩负国家兴衰重任的工厂,被内部简称为“三线厂”。
在当时为了保密,所有当时涉及军工的厂都没有名字,只有一个邮箱号,一个四位数的数字简称。这个项目,从1964年开始,到1980年结束,用时15年,耗资2052亿,占全国支出的三分之一(那个年代城市人均工资才30块钱左右)。为此新修合计超过8000公里的铁路线,完成1100多个建设项目,2000多个工厂、研究所、冶炼厂。45个产业基地和30多个新兴工业城市平地而起。大批沿海地区的科研人才、高级工程师、大学学者、年轻干部和熟练工人被迁移到了这些地方。
基地
绝大多数的“三线厂”都被建设成一个基地,厂区和生活区连成一片,围墙高建,与世隔绝,内部除了工厂和职工宿舍,所有设施一应俱全。从幼儿园到高中、技校、大中专,甚至研究所,各种学校无所不有。
论医院,“三线厂”的医院的治疗能力、医生整体能力甚至超过地方医院。银行、食堂、内部菜场、电影院、工会俱乐部、商店、粮油店、游乐场、汽车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基本不用出厂区,人的一生就可以在里面度过。
三线子弟的前半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厂里的孩子仿佛是在“世外桃源”里长大的,他们有专属的童年回忆。清晨6点厂里无处不在的大喇叭就开始播音,伴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人们开始吃早饭,骑着自行车奔向车间与学校。这样的场景每天随着喇叭早中晚要重复三遍。
每个小朋友胸口都挂着把家门钥匙,因为家里除了上班的父母就是小孩自己了,学校不会像现在这样天天补课,下课就自己回家,或者和小伙伴们满厂地乱跑,反正厂区也没多大,父母从不担心跑丢。
在周末的晚上或者节假日里,露天剧场的电影是小孩子们的最爱,每次都拖着板凳早早地去抢占好位子,每次播放的基本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题材电影。

学校里老师讲的绝对是标准的普通话,所以厂里的子弟普通话都说得很好,讲普通话其实是因为在厂
里可以听到天南海北的语言,东北话,山西话,上海话,没办法统一,那大家都说普通话吧。
在很长时间里,三线厂都是以相对隐秘的方式存在的,就像是一个个独立的王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转折
20世纪 8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三线建设的战备意义自然下降,大部分三线企业随即进入调整改造时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三线企业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对此,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 1983年 12月 27日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提出,三线企业可以继续调整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改变三线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三线建设的企业本来就有“剑”有“犁”,既有军工企业,也有基础工业,更不用说大量能源交通企业了。
在调整改造中,三线企业“化剑为犁”,实现军民融合或军转民的转型发展,虽然历经痛苦,但对西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来说,毕竟是有了相应的积累,奠定了物质、管理、技术和人才基础。
1984年,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开展全面调查,认为在所有 1945个三线企业和科研院所中,建设成功的占48%,基本成功的占 45%,没有发展前途的仅占 7%。这大体表明,三线建设这根“扁担”,确实挑起了两个战略要求的重担。
重估
时光飞逝五十年。当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虽然没有包含促进西部大开发的设想,但我们今天评价三线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大局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线建设实现了生产力向西部地区的布局。三线建设的实施,使内地的一些省市发展成为各具特点的新的工业基地,改变了工业布局,1978年内地和边疆地区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达到36.7%,比1952年的29.2%提高了7.5个百分点。1965年至1978年,四川省工业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由12.25亿元增加到59.4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加了3.9倍(高于全国的3.4倍);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份额(按当年价格计算),由2.24%增加到3.7%,即增加了1.46个百分点。三线建设所形成的一大批优秀企业,成为西部大开发的生力军。
三线建设以前,虽然也讲要支援西部,但没有具体抓手,三线地区生产能力有限,靠自己发展始终较慢。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过去比较落后和闭塞的西南、西北及湘鄂豫三省西部地区,初步形成了能源、钢铁、机械、电子、化工、汽车、军工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建起了一批具有高度文化和科技含量的科研院所,造就了攀枝花、六盘水、德阳、十堰、金昌、酒泉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成都、重庆、昆明、西安、太原、银川等西部的中心城市,经济和科技能力也因三线建设而显著增强。从 1965年起,陆续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交通干线,基本上打通了西部发展的脉络。这些成就,极大地改变了西部经济社会发展面貌。
现今的“两点一线”区域,铁路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企业和科研机构星罗棋布,当年的点线分布,已经扩展为生机勃勃的新经济区。三线建设时开始兴建的内(江)昆(明)铁路,以及2010年开通的
“渝—新—欧”国际铁路,成为连接东南亚经济圈的重要国际通道,这凸显了当年实施“两点一线”战略构想的重大意义。
西昌、攀枝花属于大凉山彝族地区,费孝通1991年到那里考察后,感慨地说: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 50年。
教训
不过,三线建设项目实施条件差、投资大、周期长而导致当期效率低,也是不争的事实。
1966至1978年,三线地区每1元基本建设投资提供的国民收入为4.98元,比全国的6.87元低27.6%,比一线地区的9.34元低46.7%;三线地区每1元基本建设投资提供的国民收入增加额为0.309元,比全国的0.406元低23.9%,比一线地区的0.655元低29%。单以1978年重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比较,三线地区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总产值只相当全国的68.7%、一线地区的49%,每百元全部资金实现利税只相当于全国的53.7%、一线地区的38.4%,每百元总产值实现利税只相当于全国的77.8%、一线地区的76.7%。
三线建设项目在不发达地区的穷乡僻壤,按照“靠山,分散,进洞”方针选择三线企业落户地址。正因为如此,攀枝花市、广安市、南川区等地被选为三线企业落户地。例如,南川区三面环山,一面靠江,三线建设时期交通十分不便,距离重庆市区虽然只有150多公里,但有一部分是山路,在当时的交通状况下,汽车运输需要1天多时间。这样的闭塞条件,有利于战备隐蔽,却导致了企业原材料、产品运输困难且成本高,这对企业的发展不利。
同时,三线建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缺乏科学论证、摊子铺得过大、进度要求过快、盲目突出政治、不讲经济效益的现象,造成了较大浪费,部分企业产生了难以继续生存发展的问题。
对今天的人来说,三线建设的政企不分是更有现实感的教训。三线建设项目实施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嵌入式发展,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以中央投资为主,在穷困的山区建设工业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项目实施所需原材料的供给与所生产产品的分配都由国家计划配置,企业还独立办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这种各自独立运行,使中央与地方、三线企业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脱节。
由于以军工项目为主,产品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嵌入的三线企业与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太紧密的关系。加之嵌入的三线企业均为当时的高端技术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能形成产业集聚和企业集群。不仅如此,即便是与嵌入的三线企业配套的生产企业也难以发育壮大。后来广安市、南川区境内三线企业逐步搬迁,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即便是被废弃的三线企业厂房设施等,也有不少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其原因,主要是受产权约束。当年中央实施的三线建设项目由中央直接投资,产权属于各部委特别是国防工业部门,地方无权使用。由此可以看出,当年三线企业难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除生产生活条件差外,还由于缺少与地方经济的融合。即使在三线企业调整改造过程中,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与广安市、南川区境内三线企业搬迁不同的是,一些三线企业逐步与当地经济融合,向内生发展转变。例如,国家在实施攀枝花钢铁项目的同时,将其与攀枝花市建设同时实施,特别是近年来与地方经济融合,发挥中央企业辐射、拉动地方经济的作用,实现了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与攀枝花市的共同发展。再如,在重庆市北碚区集中发展仪器仪表企业,以及与之配套的科研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向内生式转变,使该区科研及门类齐全的仪器仪表产业实现集聚和形成企业集群。相反,同样是仪表企业,南川区境内的天兴仪表厂,除了生活条件艰辛外,还由于在市场经济下没有实现向内生型转变而导致迁移。
嵌入式发展还导致嵌入的工业与当地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形成巨大差距。当地人民对三线建设给予巨大支援乃至付出了牺牲,没有得到足够的反哺回报,有的甚至还给当地带来污染和环境破坏。
这些,都是那个铿锵岁月留给我们的不得不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