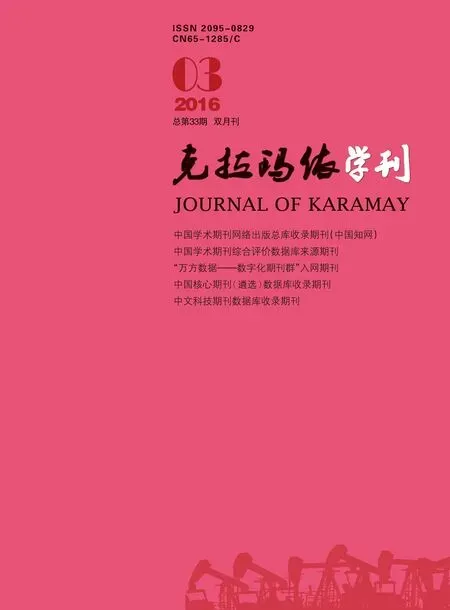变迁与重塑: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地制度演变视域下的乡村社会变迁*
徐建飞
(1.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扬州225009;2.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变迁与重塑: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地制度演变视域下的乡村社会变迁*
徐建飞1,2
(1.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扬州225009;2.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地制度经历了“私有私用→私有共用→公有共用”的演变过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时间之短、转变之大、程度之深、影响之广在农地制度演变史上堪称奇观。农地制度的演变并非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紧密关联。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地制度的急剧调整对乡村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格局、社会意识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地制度;经济;政治;社会意识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徐建飞.变迁与重塑: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地制度演变视域下的乡村社会变迁[J].克拉玛依学刊,2016 (3)54-59.
近代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与重塑始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也是社会各界一直致力于解决但又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历史实践已经证明,谁解决了乡村社会的土地问题,谁就能广泛赢得民心,谁就能掌握和控制乡村社会治理权。近代中国不同的政治力量和团体为寻求乡村社会的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概言之,主要有如下三种理论与实践:一是南京国民政府倡导推行农村复兴计划和农村合作运动;二是以梁漱溟、晏阳初、彭禹廷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民间力量提出的以“政、教、富、卫”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运动;三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的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开展的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乡村社会改造。无论是国民政府推行农村复兴运动还是民间力量的乡村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终究因为没有根本改变乡村社会的土地问题,乡村社会建设与政策预期相去甚远。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环境下,通过调整土地政策,解放农村生产力,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赢得民众的支持与拥护,最终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由此可见,乡村社会的变迁以及社会历史的深刻变革都与农地制度的变动密不可分,研究乡村社会的建设与改造就必须要关切农地制度的演变与调整。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地制度的演变是以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互变动为核心而展开的。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虽然农民将土地等生产资料入股合作社,其使用权归集体所有,但仍拥有土地所有权;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农民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都归集体所有。因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地制度经历了“私有私用→私有共用→公有共用”的演变轨迹。
可以说,制度变迁并非是孤立的,它必然会产生联动效应,即具体体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层面上,深刻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意识等诸多领域。当然,农地制度演变也不例外。正如杜润生所言,农地制度演变“当然要分配土地,但又不是单纯地分配土地,还要着眼于根本改变农村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亦即不仅要夺取国家政权,而且还要改造基层政权,要建立起一种有利于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新的、民主的、自由的社会关系”[1]4。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地制度的急剧调整对乡村经济、政治、社会意识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地制度的流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推行土地改革运动,废除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下简称《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以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为总的原则,详细规定了土地的没收或征收、土地的分配、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和执行方法等内容。
随着个体小农经济弊端的日益暴露,中国共产党逐步尝试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必须采取三个相互衔接的步骤和形式。首先,在农村实行由几户或者十几户自愿成立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然后,在互助组的基础上,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将农民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实行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在半社会主义合作社的基础上,同样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建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2]434以此实现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向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形式,弱化农民的土地产权,将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等产权归于合作社。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地制度演变视域下乡村社会的经济变迁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地制度的演变对乡村社会生产资料的变革、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农民生产生活的改善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随着土地改革的推进,地主的土地、农具、牲畜、房屋等生产资料被没收,广大贫雇农分得土地等生产资料。土改完成后,各阶级土地占有状况发生了明显改变,原先无地、少地的农民按照人口平均分得土地,贫农、中农占有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90%以上,原来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8%左右。[3]29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没收地主土地的同时,应没收地主的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乡村中多余的房屋。”[4]295因此,土地改革不仅使农民拥有了土地,且其农具、耕畜等生产资料也有明显改善。据(中南区)河南、湖南、广西、江西及武汉市的统计显示,农民群众在土地改革中一共取得了房屋11 362 339间、耕畜5 142 340头、农具10 605 810件、粮食4 579 380 012斤,这些原本由地主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通过土改被没收,再分配给农民。[5]404随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得土地等生产资料逐步归集体所有。
农地制度的演变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相比民主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总值显著增长。1949年农业生产总值为325.9亿元,土改后,农业生产总值增长明显,1950年增长为383.6亿元,增长17.7%;1951、1952年农业生产总值分别为419.7亿元、483.9亿元,与1949年相比,分别增长了28.8%、48.5%。土改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农业生产资料产权归属进一步变更转化,农业生产总值快速增长,1953年农业生产总值为499.1亿元,1954年农业生产总值为515.7亿元,1955年农业生产总值为555.4亿元,1956年农业生产总值为582.9亿元,1957年农业生产总值为603.5亿元。[3]14、1041957年的农业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了119.6亿元,增长了24.7%;与1949年相比,1957年的农业生产总值增长了277.6亿元,增长了85.1%。另外,主要农产品产量也逐年递增,耕地及播种面积渐进扩大,主要农家牲畜快速猛增。
此外,农地制度演变下农民生活状况也大为改观。土改后,农民因分得土地等生产资料,生产积极性高涨。“原先整年在地里忙来忙去,干死干活弄到年底还是两手落空,挨冻受饿,哪有心计划咋种地,该锄三遍锄一遍,庄稼咋能长得好,现在出力是自家的,谁能不下劲干!”[6]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也使得农民的购买能力进一步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1951年其购买力比1950年增加25%左右。据对苏南18县的18个典型村调查统计,1951年农民购买力比1950年增加了30.66%,其中1951年农民购买生产资料比1950年增加了45.76%,购买生活资料增加了23.82%。①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地制度演变视域下乡村社会的政治变迁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地制度演变对乡村社会的基层政权变革、阶级结构的变动以及乡村权势理论的转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秦统一中国到清朝,国家政权只延伸到县域。新中国成立后,乡村基层实行区乡制,政权向基层下沉。1950年12月8日,政务院第62次政务会议通过了《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视乡和行政村同为乡村社会基层行政区划。此后,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中国乡村基层政权为乡、民族乡、镇,从而使得基层乡政权体制有了法律的保障,乡村基层政权建设进入了法制化轨道。
土改缩小了乡的规模和范围,将行政村建制改为乡建制。1951年4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谢觉哉部长在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的报告发布了《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要求:“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应酌量调整区、乡(行政村)行政区划,缩小区、乡行政范围,以便利人民管理政权,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挥人民政权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并提高行政效率”。[7]根据中央政府对基层政权建设的指示要求,全国各省各地对乡政权区划做出调整,缩小乡的规模和范围,主要是将沿袭民国时期的大乡划小,并在县与乡之间设立县辖区公所。随后,为了避免小乡制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的扩大产生负面影响,为了能够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的发展并加强对乡村基层政权的领导,中央决定适度扩大乡镇的行政区划,于是,乡村基层政权再次调整和重建。“到1955年底全国220 000个乡并为110 000,几乎减去一半,乡所辖范围随之扩大一倍。”[8]45
农地制度的变动对乡村社会的阶级结构调整与划分也发挥了作用。土改前乡村社会贫农、雇农占据绝对的比例,而地主和富农所占比例较小,其阶级结构呈现上边小下边大金字塔式特征。据统计,土改前,贫雇农、中农、富农、地主户数分别为6 062万户、3 081万户、325万户、400万户,分别占总户数的57.44%、29.20%、3.08%、3.79%;贫雇农、中农、富农、地主总人口分别为24 123万人、15 260万人、2 144万人、2 188万人,分别占总人口的52.37%、33.13%、4.66%、4.75%。[5]410然而,随着农地制度的运行、阶级成分的重新划分,地主、富农日渐衰微并逐渐废止,而贫农、雇农上升为新中农,乡村社会中农化趋势凸显,其阶级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纺锤式特征。从21个省份农户土改后的阶级构成来看,土改结束时到1954年末,贫雇农、富农、地主分别由土改结束时的57.1%、3.6%、2.6%,下降到1954年末的29.0%、2.1%、2.5%,降幅分别为28.1%、1.5%、0.1%;而中农则由土改结束时的35.8%,增长为62.2%,增幅为26.4%。[9]31同时,随着基层政权的下移、阶级结构的变换,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被削弱,国家政治权力逐步渗透到乡村社会,贫下中农一跃成为乡村社会权力的主权阶层。“农村古老的社会权力结构,经过这场变动被全部颠倒了过来,没有人再可以凭借土地财富和对文化典籍的熟悉获得威权,原来的乡村精英几乎全部瓦解,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从前所有的文化、能力、财富以及宗族等资源统统不算数了。”[10]230-231随后,农民协会、基层党组织等组织机构逐步健全和发展,使农民政治权利得到了保障。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地制度演变视域下乡村社会意识变迁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地制度演变对乡村社会心理及意识形态变迁有重要意义。当然,作为社会意识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在农地制度发生改变的作用下,也做出主观能动反映。
(一)不同阶层对农地制度演变的心理反应
乡村社会心理变迁主要是指乡村社会各阶层对待农地制度调整的心理反应及其具体表现的演变过程。当农地制度的调整能够符合利益诉求时,农民则表现出支持拥护的心理。旧社会,农民饱受地主的欺凌与剥削,当得知土地改革将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其他农民时,农民无不拍手叫好,绝对支持和拥护土改。据载,1949年下半年,浙江农民柴仁德听说要实行土地改革了,非常开心,兴高采烈地说:“土地改革,自己有了田,不用给地主缴租,就凭我的老劲也能养活了全家”。[11]相反,农地制度的变动损害既得利益时,被剥夺方则表现出抗拒的心理。地主和富农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土地政策百般阻挠。他们通过出卖或转让土地、粮食、房屋及农具,破坏农业生产资料,挑唆本地的乡村干部,散布谣言,扰乱民心等方式破坏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时期,富农到处造谣,迷惑农民,损害农民利益;在农民中间挑拨离间,破坏团结;想方设法阻挠农民入社。此外,还有一部分人对农地制度持怀疑、观望态度。土改时期,一些农民意识不到阶级剥削和压迫,对党和政府存在不信任,而对地主阶级感恩戴德。如“丹阳县永福乡一些思想觉悟不高的群众抱着观望的态度,对共产党能否真正实行土改信心不足,存在疑惑。”[12]18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民对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也保持观望迟疑的态度,担心将土地等生产资料入股后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如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新入社的中农加马力在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后,还存在顾虑,担心入社以后少分粮食。[13]
伴随着农地制度的变革、国家政治权力的介入、意识形态的宣传、自我意识的觉醒等,社会心理都会被动服从或主动融入制度革命的浪潮中。土改时期,为了惩治不法地主对土改破坏的行径,国家先后颁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等辅助制度。同时,各地建立人民法庭,对破坏土地法令、损害农民利益者,一律法办。农业合作化时期,针对不法地主和富农对农地制度的破坏,党和政府一方面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加以引导规约,另一方面则通过法律途径予以惩治。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法地主和富农意识到宗族的光彩早已褪色,昔日的权势已不复存在,如果继续顶风作对,只能自食其果,即便心中有再多不甘,也只能低头称降。这样,不少地主主动把隐藏的土地交出,把非法占有农民的生产资料退还给农民。
(二)农地制度演变下主流意识形态植入乡村社会
农地制度的演变也使得政治意识、国家观念、集体主义、阶级意识等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植入了乡村社会。通过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彻底翻身解放,对党和革命领袖毛泽东充满感激。因为他们深知“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们从苦海火炕中救了出来。我们这辈子和下辈子的子孙后代,都永世不忘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12]236-237农业合作化时期,广东各地农民知道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和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都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决定。[14]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民族国家观念逐步觉醒和生成。1951年1月,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到苏南农村观察土地改革情况后说:“土地改革开了两朵花:一朵是缴粮,一朵是参军!”[15]121翻身解放后的农民都不忘中国共产党的恩情,积极主动缴纳公粮,并将公粮称为“翻身粮”“抗美援朝粮”“子孙万代平安粮”。京郊翻身后的农民和妇女保证带头早交粮、交好粮,掀起了交粮热潮。[16]正当土改时,美帝国主义对朝鲜悍然发动侵略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妄图扼杀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全国人民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各地涌现出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兄弟姐妹争先恐后入伍的感人场景。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民也积极响应统购统销政策,努力增产粮食,主动把粮食卖给国家,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基础原料,尽可能地支持国家工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农地政策的贯彻落实,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也逐渐培育起来。《新湖南报》描绘了湖南零陵株山乡土改后农民团结互助的和谐场景:“农民们团结得紧紧的,根本听不到哪里有打架、生气的事情发生,夫妻亲亲爱爱,邻舍和和睦睦,有困难时,大家互助互济。”[17]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也有意识地对农民宣传集体主义观念,在乡村社会中营造了人人爱集体的良好风尚。四川温江县万春人民公社社员田汉清在接受思想教育后,集体主义思想有了明显提高,他看到公共食堂没有柴火煮饭,就把自家两千多斤柴送到食堂。[18]
旧社会,农民的阶级意识淡薄,对地主阶级剥削与压迫认识肤浅。更有甚者,不但不仇恨地主,反而对地主感恩戴德。在土改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诉苦教育,通过“引苦”“诉苦”“论苦”激发农民的阶级意识,农民也渐渐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农民的阶级意识觉醒后,不再对地主有畏惧之心,而是将地主视为敌人、作为消灭的对象。苏南吴县太湖区某次斗争会上,一位农民说:“我伲农民一人吐一口痰,就把地主沉杀(淹死)哉!”[15]113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就不法地主、富农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破坏活动和倒算行为以及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抬头倾向,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强化农民的阶级意识,受教育后的农民主动投入与不法地主、富农的斗争中,坚决回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福建省的广大农民团结一致,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合作社,决不让右派分子有可乘之机。[19]
五、结语
农地制度的演变与乡村社会的变迁既是作用者又是受作用者,农地制度的演变和乡村社会的变迁既可以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或是人类演变的进程,又可以被看成是这个整体和这一进程的部分。[20]111农地制度的演变一方面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原因,另一方面又是乡村社会变迁的结果形式或表现形态。农地制度得以演变的内在动力来自于乡村社会经济、政治、社会意识等要素的变动,农地制度的变动又必然会引发乡村经济、政治、社会意识的变迁。乡村社会变迁后新的组成元素又会推动农地制度新一轮的变革。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中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制的苏南区18个县的18个典型村购买力比较表,江苏省档案馆藏档,全宗号3006,永久,案卷号158.
参考文献:
[1]杜润生.中国土地改革(导言)[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2]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4]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5]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村经济体制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6]张革非.一个农民家庭的变化[N].河南日报,1950-9-9(3).
[7]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N].人民日报.1951-5-5(1).
[8]李立志.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9]莫日达.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57.
[10]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11]王克方.浙江农民渴望土改——佃农柴仁德访问记[N].人民日报.1950-7-9(4).
[12]中共丹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丹阳土改专辑.内部发行,1997.
[13]新入社的中农消除了顾虑[N].人民日报.1955-9-18(2).
[14]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提高了广大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N].人民日报.1955-10-22(1).
[15]潘光旦,全慰天.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M].上海:三联书店,1952.
[16]苏予.京郊夏征工作大部完成,翻身农民带头早交粮交好粮[N].人民日报.1950-9-12(2).
[17]龙先礼,王守仁等.一切都变了样——记土地改革后的零陵株山乡[N].新湖南报.1951-9-28(2).
[18]万春社事事讲共产主义,人人热爱集体,个个关心生产[N].人民日报.1958-11-6(3).
[19]以反右派斗争为主要内容,福建农村广泛进行阶级教育[N].人民日报.1957-7-23(1).
[20]张志丹.无伦理的道德与无道德的伦理——解码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悖论[J].哲学研究,2014(10).
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6.03.1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2016学年度“清华农村研究博士论文奖学金”项目“建国初期农地制度演变与乡村社会变迁(1949—195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6-01-06
作者简介:徐建飞,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党史党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