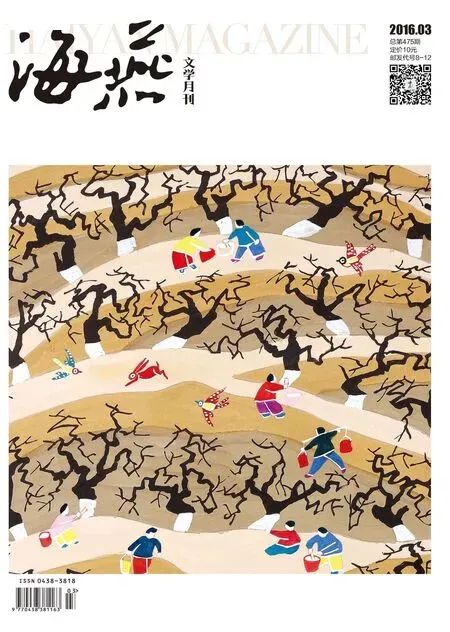两个人以及我的乡村时代
□杨献平
两个人以及我的乡村时代
□杨献平
这肯定是一生的梦魇。多年以来,它和他们在我内心甚至灵魂当中沉渣泛起,隐忍而又凶猛。它——略等于仇恨、惊悚、恐惧、毒药。他们,既是实指,又非常具体。它和他们所笼罩和贯穿的,大致是我一个人,也可能还有很多,生发于某一个地域,而又超越了一时一地的范畴。似乎从记事起,我就对她——爷爷的亲嫂子有一种恐惧,乃至挥之不去的惊悚。六岁那年,我拽着母亲衣角,背着碎花布书包,正式成为小学生那一天,母亲压低声音,神情凝重又神秘地叮嘱我说:“我和你爹不在家时候,不管大奶奶给你啥吃的,啥玩儿的,你都不能要!记住没有?”人生第一次上学,满心都是花花绿绿的新课本,哪儿还有心思听母亲的话?
母亲见我心不在焉,还在翻看课本上的北京天安门和巍峨的长城,忽然恼怒地用手拧着我的耳朵说:“俺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到底记住了没有?”我哎呀一声,急忙说记住了。
此外还有一个人,他叫杨战斗,和我属于一辈人,但和我父亲年龄差不多。他的家原先住在村子中间,后来娶了老婆,把房子修在了我们家对面。对于杨战斗,一开始我就知道他是队上的民兵连长,而且家里还常年存放着一支五四式步枪。某一个夏日傍晚,黑夜以匀称的方式覆盖了南太行村庄,村人大都端着饭碗在院子里吃饭,忽然有人惊叫说:“看!那一绺鬼火!”众人惊,纷纷挤在一起,朝村后的坡上张望。
茂密的橡栎树之间,果真流动着一团火。又有人说,老村长就是厉害!死了还要出来显示威风!那年代,人们还相信万物有灵,也相信人是有灵魂的,即使死去,还有另一种存在方式,并且与生者同在。我夹在其中,被父亲紧紧抱着,睁着一双懵懂的小眼睛随着众人看。
有人大喝说:“拿枪来,不信它不怕子弹!”说这话的人正是杨战斗。说做就做,他快步蹿回家里,拿出五四式步枪,对着后坡扣下扳机,只听当的一声轰响,子弹带着微小的弧光,向着那绺火焰冲去。霎时间,那绺火焰似乎真害怕了,先是慢慢游弋,好似闲庭信步,悠哉游哉,好不惬意;枪响后,急速如流星,仓惶似奔马,在橡栎树林子里迅猛流窜一圈后,瞬间消失在埋它的坟地里。
再一年深秋,村庄到处都是粮食味道,山上浆果腐烂的气息在山间流窜。放学后,我和几个同学小马驹一样嬉闹狂奔,到村口,正上气不接下气,忽然听到一阵阵暴烈的争吵声。我站住,竖着耳朵倾听,从印象深处检索那是谁的声音。
南太行乡村深处大山,矿产资源匮乏,人们大都纯粹以田地和山坡为生。尽管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期了,可中国的农耕文明仍旧在这里得以顽强而麻木的保存和传承。但由于资源少,人口多,人和人之间的争夺愈发激烈,并且充满原始性。从小到大,我们莲花谷村基本上三天、最多五天就会爆发一场“战斗”,不是杨二和张三,就是李四和王五。
但摩擦次数最多的,是各家妇女。
老人们说,女人是人当中最奇怪的,当闺女时候把自己包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可一旦成了妇女,就啥也不管了,坐在街门上露着白花花的乳房奶孩子,甚至裤腰带都在外面耷拉着。更奇怪的是,女人和女人,甚至和男人吵架骂仗,满嘴的自己和男人的生殖器不算,还把驴子、狗、猪、马,包括温驯的羊和咯咯打鸣下蛋的鸡,也未能幸免。
诸如此类的脏话,从俩三个妇女口中飞溅而出,其出口之顺溜儿,编排之韵律,简直就像是层出不穷的流水及其好看的漩涡怒波,由房顶或者院子里越过梧桐树和大槐树庞大的树冠,比缭绕的炊烟还具有扩张性。骂到激烈处,地面上会腾起尘土,周边的小树和墙缝里的草会忽然剧烈而又整齐地摆动起来,即使那些公鸡母鸡,似乎也忘了啄食,一只只地举起脑袋,躲在墙角左顾右看。
一般情况下,女人都是嘴上的功夫,实在不行,才会冲过去相互厮打,薅头发、扯衣裳、抓脸、咬胳膊等等是她们的强项。口水战斗一旦发展到肢体暴力,各家男人都会大吼一声,毫不犹豫地加入进去。
只见一个穿粗布衣服的妇女一跃而起,一边大骂一边冲下自家门前台阶,旋风一样奔到另一个妇女跟前,一把抓住对方衣襟,伸手在她脸上就是一招“九阴白骨爪”。那个妇女哎呀一声,继而发出凄厉的长嚎,动用全身力量反击。此时,另外两个妇女也加入到战团之中,眨眼工夫,又来一个妇女。四个妇女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庞大螺旋,嘶叫、喝骂、痛斥、叫疼、发狠、受伤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起初,我怕是谁又欺负我娘。
我娘尽管有三个姐妹两个哥哥,可都不在同一个村子里,想帮忙也够不到。我爹也是独生子,虽然有一个妹妹,也嫁到了外村。在村里我们家最孤单,势力最小,战斗力最弱。在暴力乡村,我们就像是落后的旧中国,挨打受气早已是特殊专利。
幸好这一次挨打的不是我娘。我定神一看,那个妇女是朱先妮,另外一个是她的大女儿,再一个是她的大儿媳妇和她的大孙女。我既惊诧又开心。原来,是她们自家人内讧,这是旷古不遇的大好事。我松了一口气,看了几分钟后,转身回家。母亲在家里烧火做饭,柴烟好像烟雾弹,在矮小的房子里乱挤一通,觉得无路可逃,才又转到门口,贴着早就熏黑了的门楣,成群的仙女一样逃逸而出。
“她们那是咋了?”
我的话刚出口,母亲就瞪了我一眼,惊恐说:“别管别人的事儿!”我“哦”了一声,柴烟不失时机窜入咽喉。
战斗戛然而止。
朱先妮被她大闺女搀扶着,披头散发,一边趔趄着上台阶,一边嚎哭和痛骂。她大女儿一脸血道子,肯定是被她嫂子或者侄女儿抓的。她本来脸长,血道子从额头贯通到下巴,使我想起爷爷所讲故事中的厉鬼。
我忽然身子一轻,腾云驾雾一样,就回到了柴烟滚滚的房里。母亲哈着腰,嘴巴贴着我耳朵说:“看啥看?那死老婆子正没地方撒气,把你抓住打一顿咋办?再说,人家人多势众,打伤你得挨着,打死你都没事!”
“有这么严重吗?”
我心里一万个不服气。晚上,一家人坐在昏黄的灯光下吃饭,我对母亲说:“朱先妮再不会欺负你了,娘。”娘嘴里嚼着一块饼子,看着我说:“傻孩子,人家是自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要是有个啥事儿,人家还是一家人。”
一夜之后,太阳照常升起。
再过些日子,秋天的村庄就被人收割了,风连续而且很大,好像在打扫战场。父亲是小队会计,按照惯例,每年这时,都要赶着马车去山西左权、和顺农村用麦子交换玉米或者土豆。连续几年,父亲都和杨战斗两人去。
山西虽然和我们挨着,但凭空高出了一千多米的海拔,那里的土质,好像不适合种麦子,土豆、谷子、高粱、玉米、豆类等庄稼倒是很繁盛。长期以来,左权人每要吃面,都要从河北运上去。久而久之,我们这边就有一些人做起了用麦子或者麦子面上山西换取土豆、玉米,从中赚取差价的生意。
那时候,虽然已经包产到户,可村人还是习惯于集体生活。牛羊驴尽管都分到了个人头上,但仍旧放在一起,选一个人放养或者喂养。去山西换东西也是如此。
父亲是赶马车的好手,为人又很实在。杨战斗性格很直,甚至有点愣。村人都说他有点二杆子劲儿。当天上午,父亲和杨战斗出发后,村里又发生了杨二器老婆和杨安林老婆骂架的事情。原因大致是,杨二器老婆听人说,杨安林老婆和邻近的杏树洼村小队长曹和柱有见不得人的事情。并有眉眼儿地说,有一个傍晚,她亲眼看到曹和柱鬼鬼祟祟、神神秘秘,像电影里的特务一样,在夜幕掩护下闪进了杨安林的家门。话传到杨安林老婆耳朵里,二话没说,一场骂战随之上演。可就在村人私下议论这件事真假程度的时候,当天深夜,村里又发生了一场凶猛的“内战”。
子夜的乡村,正沉浸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亢奋与寂寥之中。人们正在酣睡,狗叫和夜枭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村野之中显得格外清澈。忽然,村下方人声骤起,无法遏制的怒吼、惊恐的叫声、负伤的哀叫等声音雷霆一样轰然而至。一盏灯光亮起,再一盏,再一盏,整片的黑暗使得整个南太行乡野顿时有了一种人性的气息与活着的生机。可是,凡不碍自己的事,谁也不愿意这时候起身去看,倘若有人去现场,那一定是事主最亲近的人。大多数人躺在被窝里捋直耳朵倾听,并迅速运用睡意阑珊的脑袋进行自我解析。
“哦,是杨战斗自家的事情。”
“他不是去山西了吗?”
“一个是杨战斗,一个是他老婆,还有一个是谁?”因为常年在一起生活,相互之间极为熟悉,即使一个模糊的背影,一声咳嗽,无意中一瞥一闻,不用过脑子,就知道对方是谁。可另一个男声却很陌生。忽然传来一个人仓皇奔跑的脚步声,向着村外的马路。至此,村人才从杨战斗等三人的只言片语当中,分析总结出了事发原因。
头一天,杨战斗和我父亲赶着马车走到山西和河北界山——摩天岭的时候,杨战斗低头思忖了一阵子,忽然说:“我得回去一趟。你先走,我明天再从小路上来。”我父亲问他为啥。杨战斗叹了一口气,跳下马车,一边转身一边说:“叔,我有个急事,明儿个就赶来了!”。
次日一大早,人们基本上明白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杨战斗听到村人的一些闲言碎语,说他老婆刘秀秀和武安一个男的有炕上关系。起初,杨战斗根本不信。说的人多了,也不免起疑。这一次,他想,去山西一次,来回起码也要四五天时间,若是真有其事,那人肯定会趁虚而入。
徒步返回村里,正是子夜,杨战斗敲自家的门。老婆先是含糊应答,但开门时间远远超出了预定速度。进屋,杨战斗一声不吭,眼睛盯着炕面,没啥异常,转到里屋,猛然一声大吼,旋即揪出一个衣服还没穿好的男人。说起来,这个男人杨战斗也很熟悉。前些年,曾和杨战斗在市里武装部受训,二人性情颇为投缘,便成了莫逆之交,两家互有走动。久而久之,这个男人便和他老婆王八看绿豆对上了眼儿,进而不满足于精神层次的倾慕,便寻机会于炕上用器官表达感情了。
太阳照常升起。对杨战斗来说,这可能是大事,可对于其他村人,不碍自己的事儿都是屁事。各人照样下地干活,回家吃饭,时不时训斥几声自家孩子,或者把不听话的猪猡打得吱吱乱叫。几个月后,杨战斗老婆又生了一个男孩子。喜庆之余,人们说:这孩子,一看就不是杨战斗的。
杨战斗似乎也知道,但南太行乡村人古来觉得,生在自己家就是自己的孩子。至于谁的种子,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大雪幽灵一样,趁着黑夜,将山瘦水枯的南太行乡村置于洁白的覆压之下。通往城镇的道路中断, 即使前往邻村,小路悬冰,也觉得困难。人开始扫雪,通往自家的猪圈或羊圈,还有厕所。因为与人无关,落在其他地方的雪花得以保全。我已经是初中生了,尽管大雪没膝,但我上学的意志比革命战士还要坚决彻底,一个人蹚着大雪,走了五里多路去上课。下午,天色仍旧昏冥,雪花比我的眼睛还大,一枚枚一朵朵,在空中撒着娇,然后沉甸甸地砸下来。
还没进村子,我就听到我们村又是一阵哄闹,打骂之声穿过雪花的缝隙,朝着四面山坡飞扬而来。
这又是谁和谁呢?
其中有母亲的声音!
我狼一样,疯狂地扑回家。
好像谁在我身体里埋置了地雷。每当这时候,我惊慌莫名且充满无端的恐惧感。这一成长途中的精神厄难,对一个孩子来说,其爆破和轰炸的效能是无以伦比的。
是朱先妮,还有她的大儿媳、大孙女,三个彪悍妇女欺负我母亲一个人。朱先妮和她的大儿媳妇、大孙女站在上方小路上,扯着嗓子骂我母亲。我母亲一个人站在自家屋檐下,愤怒而胆怯地回骂她们。我跑到院子里,就一个猛子扎在母亲怀里哭着央求她说:“娘,她们人多,回家,回家吧!”母亲一边声泪俱下,一边回骂对方,还无意中伸胳膊把我揽在怀里。
忽然一个东西,穿过傍晚的雪花,热气腾腾地朝母亲和我飞来。母亲下意识地抬起手腕一挡。
一只瓷碗落在雪上,一团红血突突冒出。
瓷碗居然是朱先妮的二孙女抛来的。鲜血从母亲右手腕上,泉水一样迅速奔涌。
朱先妮的二孙女长方脸,大眼睛,长眉毛,脸白得可以让初雪羞得主动钻到地缝。她比我大七八岁的样子,每次在路上遇到,我都想:朱先妮和她大儿媳妇那样的恶人,怎么会有这样俊俏的孙女和女儿呢?但平素里,她这个二孙女要比大孙女和善一些,极少参与自家与其他人家的吵骂和战斗。
我用手捂住母亲的伤口,可是鲜血并不领情,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外逃窜。我大声哭着一个劲儿地喊“娘!娘!娘!咱回家!回家吧!”那声音,在房屋错乱而又紧密的村庄,像是负伤幼狼的嚎叫。
所幸,她们没有打上门来。
在村庄,一家和另外一家吵架打骂,哪怕再凶,打出人命,其他人家看到也当啥也没看到,上前帮忙和拉架的,一般都是至亲之人,外人谁也不愿意蹚这浑水。即使有心劝架,也怕其中一方说自己拉偏架,进而受责怪甚至反目成仇。类似我家的情况,更是没人愿意出头,哪怕是一群人欺负我们家一个人。
而我父亲,此时去了五十公里外的一个工地修水库。
家里只有我和母亲,还有两岁的弟弟。
回到屋里,母亲扯了一块废了的白布,把手腕包上,又把弟弟抱在怀里喂奶。我站在屋地上,忽然觉得世界非常空旷,且很暴戾,怨气蒸腾,有一种无形但很强大的恐怖气息笼罩了我的肉身,也控制了灵魂。
如此的童年极端折磨人,每天早上醒来,特别是去上学路上,我都暗暗祈祷,村子再乱,也不要和我们家沾边;人再凶恶,请不要凶到我母亲头上来。可是,一个地方的人群习性乃至人和人之间的暴力摩擦是短时间无法更改的。文明的每一进步,其实都带着磅礴的鲜血和透骨的镣铐。1970年代甚至更早时候,朱先妮忽然失去了丈夫,也或者,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她的丈夫。奶奶说,朱先妮的丈夫,即她的大伯子,在很多年前就患癌症去世了,即便他还在世,也没能阻止自己的妻子朱先妮和那个死后还以鬼火方式出现在村庄傍晚的老村长有炕上关系,而且毫不避人,四乡皆知。
某天夜里,爷爷对我说了朱先妮的一件往事。那应当是1960年代,每一个人都属于公社、大队和小队。朱先妮和我大爷爷先后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粮食不够吃,个个饿得跟黄菜叶一样吹弹可破。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秋天也来了,玉米低头向下,谷子摇头摆脑,高粱把脖子拉成了弓。一天傍晚,朱先妮独自提着镰刀和口袋,趁人都在吃完饭的空档儿,迈动两只小脚,没入一山之隔的集体玉米地里。
南太行都是山区,田地也都是一层层地坐落在某一道土质尚好的山沟里。当时,朱先妮一看窝棚里好久没有动静,振奋精神,窜入玉米地里开始把集体主义粮食往自己口袋里装。正装得不亦乐乎,忽听一声大喝,一个箭杆一般身材的男人站在地边,怒气冲冲地骂道:“哪个贼王八羔子,竟敢偷公家的玉米!”
朱先妮浑身打了一个激灵,还没反应过来,肩膀就被那男人抓住了,老鹰抓小鸡一样提了起来。朱先妮心里一阵慌乱,可待她看清是老队长时,忽然就有了勇气。老村长把她提到窝棚前面,继续呵斥:“全村人都饿着,人家不偷,就你来偷?你还是个五个孩子的娘,俺大侄子的媳妇,丢人不?”
这一番话,可谓伟光正、高大上,充满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色彩。朱先妮当然哑口无言。但事情很快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一晚,朱先妮不仅把集体主义以新鲜玉米的形式带回了她资本主义饥肠辘辘的家,而且还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那时候,要是报告给大队,大队肯定要报告公社,公社呢,也肯定向县里汇报。轻的,戴高帽子游街示众,重了,怎么也得在监狱里待一阵子。”爷爷说。
我感觉很传奇。但因为年幼,对男女之事一窍不通。开春后,大地解冻,太阳晒得人皮肤发痒,风中的花香挠人鼻孔。某一个星期天,我和同村一个伙伴去山上打柴,遇到村里以凑份子方式聘用的一个放羊汉。他是邻村人,而且是光棍。坐在暖洋洋的山坡上,我们和他逗乐。他为人老实,智力还有点问题。
说笑之间,放羊汉竟然把话题扯到了朱先妮身上。他说,你们村的老娘儿们朱先妮可真不简单。年轻时候和老村长有一腿,现在都五十六七岁了,又和邻村的赵三葵搞在了一个炕上。我想了半天,才想起,赵三葵就是那个个子很高,梳着大背头,整天在我们村闲逛的黑脸老头儿。
“驴都能看出来,朱先妮不是看上他人,是看上他的那些东西了!”放羊汉说。
赵三葵早年丧妻,有一子,早就成家另过了。因为先前做过煤矿工人,退休之后还有退休金,家里有新房子三间,老房子三间。尽管退休金只有1000多块,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对于南太行乡村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放羊汉所说的“东西”大致是指这些。
几乎与此同时,十公里外的一个村子发现了一座储量较大的铁矿。于是乎,由乡政府牵头,铁矿开工,选厂也建了起来。此时的杨战斗早就把枪支交给了公家,也不再是民兵连长。虽然上次和老婆大干一场,并且被更多人背地里说二小子不是他的种子,头上绿帽子哗哗作响,但仍旧和原配老婆一个炕上睡觉,一口锅里吃饭,好像啥事都没发生过。铁矿开工之初,杨战斗就加入进去,而且是领班。村人说,之所以捞到这样的美差,是杨战斗平素和乡长经常一起吃吃喝喝的缘故。两个月后,一台雅马哈250摩托车以加速度的姿势,被杨战斗骑着,呼啸进入我们村子。
嚯,这可是头一家!
哎呀,杨战斗就是能战斗!
在村人的一片赞美和艳羡之中,杨战斗步入了全村第一批富起来的稀稀拉拉几个人之中。但很不幸,他的摩托车还没骑上一个月就不翼而飞。据说,那天傍晚,杨战斗和几个哥们在饭店里喝完酒,趁着醉意,驾驶着夏日黑夜的凉风回到家,把摩托车停放在院子里,也没上锁,就进屋睡觉去了。可能睡得太投入,也可能是太专注于某件事,摩托车失窃居然没有听到。
报案!
警察来了,又走了。
十天过去,又是十天。案犯继续逍遥法外。
猜疑四起。有的说是杨战斗几年前殴打的那个武安朋友干的,因为心里有怨气,便瞅机会偷了杨战斗的摩托车。
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人心马蜂窝一样爆炸散开,一发不可收拾,做啥事的都有。“严打”时候,仅仅南太行一带,就有数十个“长毛”(专指游手好闲打架斗殴无事生非的那些青年人)被抓,其中几个,还被枪毙了。人说,现在世道这么乱,找一辆摩托车,就好比米糠里找米。
但杨战斗和他老婆不这样认为。
一定有内奸!
肯定是本村的。杨战斗和他老婆的推断是:要是没有本村人帮助,外地人绝对不会对他们家情况掌握得如此清楚和及时。
两口子把全村人筛糠一样筛选了一遍,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青年光棍杨二猛。原因是,这小子从生下来就偷鸡摸狗,不干正事。另一个是邻居杨光禄,因为两家总是因为房基地闹矛盾,前后大打出手两次,规模都在十五个人左右;小吵小骂无数次甚至不间断。
光棍杨二猛确实如此,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爹娘更是由他去吧的态度。一个清晨,杨二猛还在蒙头大睡,门哐当一声被人踹开。这小子还不知道是天塌了还是地陷了,就被一只大手从被窝里拖了出来,旋即一顿大脚木棒一样落在头上脸上肩上胸脯和肚子上。他正要叫疼,只听杨战斗吼着说:“狗日的杨二猛,你招不招?是你偷的不是?你狗日的不承认老子就打死你!”
尽管如此,杨二猛还是矢口否认,态度也空前坚决。向杨战斗发誓说,那事要是他干的话,黑夜就让狼群把他撕吃了。再不行,自己走路跌倒就一命呜呼!
杨战斗和老婆转身离开。
回到家,两口子又分析了一番,一致认为,杨二猛这个嫌疑犯排除之后,唯一的可能就是杨光禄了。
杨战斗两口子知道,对付杨二猛,自己就是美国或者苏联,杨二猛就像是欧洲任意一个小国家,怎么打怎么顺手。而杨光禄就像是法国意大利德国这类的,虽然自己有六分把握,但另外四分还是悬念,不得不考虑。
两口子商议的结果,不仅要暂缓,而且要采取偷袭的方式,才能确保全胜无恙。
这一暂缓,就又是一年。开春的时候,大地回暖,草木竞发,一派盎然生机之中,杨光禄两口子忽然放声长嚎,旋即又爬到自家房顶上,运用自己高嗓门,对着全村人高声大骂:“哪个操他娘的把俺的树都给烧死了啊,就不怕断子绝孙?不怕龙抓了,雷劈了的狗日的们啊!”
村人这才明白,原来,杨光禄家的上百棵成材树被人用硫酸烧坏了躯干,有的被人用大锯锯了一半,只要刮一场大风,树就会全部折断倒地,啥材也不成,只能当柴烧。
我知道,这也是违法的。而乡人历来将紧邻之间的斗争和暴力对抗看作是一种民间行为,与王法和现在的法律法规完全无关。由此看,中国大片乡野一直处在无政府主义状态当中,南太行乡村尤其典型。在这里,任何一个姓氏宗族当中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族长或者权威人物,即使在民国时期诞生过几个地主大户,也没能从日常行为、习俗和精神上“统一”过家族中人。这样的一种“历史的现实”,显然是与南方客家人甚至山西、山东一带的乡村宗法社会是相违背的。这大致是移民产生的结果。据本地县志记载,南太行一带的农民,大都是明万历年间由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先后迁徙而来,分别择地建村的。
那时候我已经是高中生了,又较长时间在县城内,各种新鲜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思潮正在席卷,几乎每个人都在八十年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启蒙或者再启蒙。但在山里,特别是南太行乡村,那种强劲的风潮仍旧被挡在层叠大山之外。大致是1989年春末的一天,我由县城返回村里,却又遭遇到了一件暴力事件。施暴者仍旧是朱先妮。此时的她,还和邻村的赵三葵保持着关系,但始终没有正式结婚。
走到村口,我蓦然看到,一个人缩在路旁的一棵老板栗树下,穿着一件黑色的金丝绒上衣。村子下面停着一辆警车。嚯,我暗自惊讶。村子里发生过无数的暴力事件,最多是几个村干部背着双手,领导干部视察一样了解一下情况,劝解双方息事宁人,然后各回各家之外,警察从没来过。
警察这一次来,拘捕对象真的是朱先妮!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即使她仅仅欺负我母亲一次,我也不会原谅她。何况,在我成长的年代,朱先妮包括她的两个儿子儿媳,孙女们和两个女儿,也都不同程度地欺负我们一家人。
母亲告诉我,一个外地的算命先生到村里,被朱先妮叫家里给她算命。也不知怎么着,她和她两个儿子按住人家打了一个半死,扔在马路上,还把人家身上的上千块钱掏了。他们以为打了人家没啥事儿,可人算不如天算,这算命先生居然有一个弟弟在省城工作……这不,警车就呜呜地来了,要抓朱先妮。
我赶紧说:“朱先妮就在村口路边那棵老板栗树下藏着,我去告诉公安局的!”说着,就抬脚出门。母亲一把拉住我,悄声说:“傻小子,不能说。你一说,把老妖婆抓了,还会放回来。人家还有几个小子和闺女。公安局一走,咱又是受不了的冤屈,挨打倒是小事,就他们那家人,不把咱暗害了才怪!”
我蓦然收住脚步,心里又是一阵惊悚。几个小时过去了,警车无奈而又飞快地驶出了村庄。
当夜,朱先妮没有回村。
躺在炕上,在老鼠猖狂的活动声中,我怎么也睡不着,心里一直滚动着无可名状的绝望和沮丧。我知道,告发是应当的,但母亲的话更重要。警察再公道,对于我们这样的山村来说,也只是有事才来,即使是凶案,也是事后才会来勘查、侦破。日常是多么长久和顽固的啊,任何事情都在其中发生,而不是这样的时刻。
我很纠结,也很惭愧。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我离开故乡,去了远方。多年过去,仍旧没有消除。2002年夏天带着妻儿回家,朱先妮还健在,而且非常硬朗。那个赵三葵前些年患癌症去世了,朱先妮以妻子的名义继承了他所有财产。赵三葵儿子把她告到法院,官司打了两三年,最终还是朱先妮赢了。
朱先妮起码有九十岁了吧?母亲却说只有八十二岁。每次在村里看到,按道理我该喊她一声奶奶,可一到近前,却不想多看她一眼。由此,我判定自己是一个自私的人,而且还很记仇。对此,我有几次深思,才发现,我对朱先妮的仇恨和厌恶却不是因为自己也曾经挨过她打,而是她和她家人对我母亲的欺凌不可原谅。
我只有一个母亲,世上也只有我母亲才能生下我。
正当我觉得她俨然老去,不再会参与暴力事件的时候,却又亲眼目睹了她为了给自己孙子抢宅基地,拄着拐杖,毅然决然无赖无耻地躺在挖掘机下要死要活,讹诈其他人的情景。直到那一刻,我才确信,世上确实有一些人本性是恶的,而且一生都会以恶为能,以恶为荣。
也是这一年夏天,我正在家里和儿子玩,忽然听到村子前面有人嘶叫。心神随之绷紧且无限惶恐,幼年时候那种惊悚和恐惧再度奔袭而来。跑过去一看,却见杨战斗正在痛打一个乡村妇女。起初,我以为是我家人又被人欺负,急忙跑到跟前,却发现,被杨战斗痛打的人是邻村的一个孤寡老妇女。
人说,没本事,自家再没人,挨打也是白挨。
至此我才知道,暴力从没有消失。鲁迅先生那句话依然有效,特别是对于平民之间的暴力伤害,先生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华盖集》)从本质上说,朱先妮和杨战斗以及更多如他们的人也是弱者,我也知道宽恕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美德和境界,但弱者和弱者在争斗之中的表现,却常使得我也萌生甚至坚定了鲁迅先生“我一个都不原谅”的决绝与悲怆。
2007年,朱先妮无疾而终。
杨战斗在村边开了一家小卖店,不过两年,因为人都不去他那里买东西,只好关门大吉。2009年,我父亲去世,每次去给父亲上坟,都要路过朱先妮的坟茔,每一次,我都要多看一眼,心里滋味复杂。同样,每次见到杨战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鄙视,看着他越发佝偻的腰身,灰苍苍的头发,蓦然又觉得,这个人其实也很可怜。
我呢,其实也是可怜。因为,看惯了太多的伤害与不公,作为一个男人,还有些觉悟和文化,却对此无能为力,甚至视而不见。这种可怜,似乎比朱先妮和杨战斗这样的人更深切彻骨,无可救药。
责任编辑 董晓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