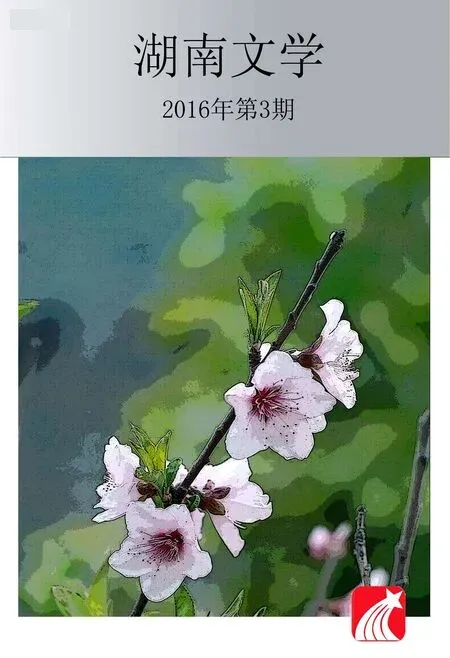阳台上的郁金香
→薛勇
阳台上的郁金香
→薛勇
“我打了个盹!”裹着棉大衣的老温睁开眼,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这可不是一个盹,你老足足睡了两个小时。”周辛说。“是吗?有这长时间?”可他并不去看手机,只是透过面包车的车窗玻璃,瞥一眼还被暗夜浸润的那幢黑黢黢的楼,“没什么事吧,小周?”“放心吧,没事。”周辛说,“一只鸟飞出去,我都会看见。”这是一个仅有三幢小楼的破旧小区,说它破旧,是因为它虽有院墙,却没有大门。大门处两边各有一摞残缺斑驳的砖垛。小楼仅三层,且是墙体很单薄的那种老式建筑,一看便知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产物。这种老旧建筑在B市已很少见了。小区原是某国营厂的家属楼,如今楼里的主人们已大多有了新的住处,老房便用做出租。据说某开发商很早就看中了这块地方,只是他开出的拆迁价总是得不到小区业主们的认同,于是就一年年拖下来。
老温和周辛的面包车停于一个很关键的位置,此处和大门和“巫婆”的居处呈三角状。面包车隐于一棵老槐树下。三月尚未转暖的冷风摇曳着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杈。小区里几乎没有其他车辆,这辆灰色的长安面包车就很突兀。小区的很多人均心照不宣,知道它这几天总停在那是为了什么。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老温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吸一口,“准确点说,”他终于看一眼手机上的时间,“咱们还有三个半小时,就解放了,八点半,土利科的人会来接替咱们,真不容易呀!”他停一下,又说,“可这最后的三个半小时,也是最关键的,一定要盯死了‘巫婆’,决不能出岔,明白吗小周?”
“明白。”周辛点了点头。不过他想在毫无光亮的车里,老温不一定能看见他的这个动作。于是他又说,“‘巫婆’虽然狡猾,但我不会犯老朱的错误。”“老朱的错误你我都犯不起呀。”老温说,“你是〇八年考进的那批公务员吧?到今儿满打满算还没两年呢,因为这个‘巫婆’被开了,那太不值了,是不是?”烟头的光亮在面包车里闪烁着,他又说,“咱俩是一根绳上拴着的蚂蚱,不用说,到时候我这耕保科的科长也就别干了,丢了官,回家就等着媳妇天天骂吧。”忽然想起什么,老温问,“对了,你可是从来没问过我‘巫婆’这老东西什么事,你不想知道这么多年她为什么总在上访吗?”
周辛摇摇头。他想这个动作老温肯定还是看不见。“哦,我不想知道。”他想了想,说,“我怕知道了会影响我……我想能成为‘上访专业户’肯定是有一定原因的,至少在他(她)自己看来是绝对有理,否则也不会这么执着,温哥你说我说得对吗?”
“对,太对了。”老温的烟头又明灭了一下,“你不想知道‘巫婆’的事,可我偏偏想跟你说说。知道为什么吗?”他停了一下,似在等周辛回答,可马上又说,“‘巫婆’这老东西实在说我是同情她的,我想咱局的许多人都有我这想法,可她又太遭人恨了。她太狡猾,不好盯,她耍过很多人。”
周辛说:“我听说‘巫婆’不好处,阴阳怪气的,说是局里的领导有一年年底时买了点东西去看她,结果‘巫婆’把东西都给扔了出来,她说你们甭想用小恩小惠买通我,我不缺这,要想帮我就帮我落实政策,我要真格的。局里的领导一听这话,扭头就走。”
老温说:“没错。‘巫婆’遭人恨就在这儿了。她不想想,她的问题咱局能解决吗?她的问题恐怕市委市政府都解决不了。从这点去说,她往上边找也是对路。可她这是在跟咱们找麻烦啊。她住在路东区,区政府偏偏又把这块硬骨头分给了咱局。北京在开两会,咱B市离北京又这么近,她只要这期间往北京一跑,没说的,咱B市的一连串的人就都得跟着倒霉。”
周辛说:“你还真勾起了我对‘巫婆’的兴趣,你愿意说说就说说吧,反正离天亮还有一会儿。你这会儿还不走吧?”
老温说:“我六点半走。媳妇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病了,我把孩子送到学校就马上赶回。没办法呀。”
“应该应该。”周辛说,“温哥你放心去,这儿的事交给我。”
“好好,”老温说,“刚才说到哪儿了?噢,讲‘巫婆’,好,我给你讲讲‘巫婆’的事。”他沉思了一会儿,说,“知己知彼嘛,咱不能忙乎半天不知道在为什么忙。”周辛没吭声。他等待着。
老温又说:“‘巫婆’的事其实不是她的事,而是她男人的事。也就是说,她不断地上访是在为自己的男人上访。”
周辛说:“我知道她是在为男人上访,但到底为什么事不知道。”
老温说:“说‘巫婆’,得先说‘巫婆’的男人。‘巫婆’的男人知道是谁吧?他过去是解放军,四七年的兵,B市安新人,要没有后来打金门的事,在部队他怎么也得混个团级,跟他一起当兵的,后来有的都当了师长。就是转了业,到地方也得给个什么局长干干。”老温抽口烟,口气渐渐严肃起来,“可惜呀,金门那一仗把他给毁了,小周,金门那一仗你听说过吧?”
周辛说:“知道点儿,报纸上过去没有,这会儿有了。解放军打了一场大败仗呗。”
老温深深叹口气,说:“惨啊,过去了九千人,没回来几个呀。全军覆没呀。”一支烟吸完,他又用打火机点燃一支。打火机的火光瞬间映亮了他脸上的凄然,“你说过去不知道,可不,走麦城的事谁愿说?可不说不行啊,这是历史。噢,刚才我说全军覆没,不是说过去的九千人都牺牲了,也有没死的,没死的就都成了俘虏,大概三千多吧。这些人没退路,因为海水退了潮,想回都回不去了。‘巫婆’的男人就是这三千多俘虏中的一个。国民党在这三千多俘虏中挑了挑,把一些有用的补充到了自己的军队,比如卫生兵、号兵、炊事兵什么的。‘巫婆’的男人当时是战斗班的班长,可他刻意隐瞒了自己的这一身份。他说他是炊事兵,做饭的大师傅。他过去也确实当过炊事兵。谁愿当俘虏呀?脱了解放军的军装,穿上国民党的军装,就更是难以接受的事了。跑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周辛说:“我在报上看到有个被俘的,后来用两个篮球胆硬是从金门泅水渡过海峡,回到了大陆。”
老温说:“这是凤凰卫视做过的一个节目,那人是山东人。‘巫婆’的男人其实比他还厉害,那山东兵是靠着两个篮球胆,而‘巫婆’的男人没有借助任何东西,也硬是渡过海峡,游回了大陆。本事啊。”
周辛赞叹说:“他的水性太好了!放在这会儿,还不创了吉尼斯纪录?”
老温说:“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巫婆’的男人是B市安新人,安新是水乡,有白洋淀,‘巫婆’的男人家世代是渔民,可说‘巫婆’的男人是从小在水里长大的,水性太好,说是他憋一口气能潜百十米,谁能比?这个背景成就了他,否则他能徒手渡过海峡?做梦吧。”他抽口烟,又说,“按说回来了是好事吧?渡过海峡游回来,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周辛说:“这是忠诚啊。没有信念支撑,哪来的勇气啊。”
老温说:“可不。可回来了等待‘巫婆’男人的并没有什么好事。陆陆续跑回来的一些人被集中在一起,办班学习,接受组织审查。三个月后,所有人都被宣布解除军籍,遣返回乡。说白了是组织对这些人不信任,谁能证明他们不是被国民党策反后派回来的特务?无人能证明。所以遣返回乡是必须的。‘巫婆’男人后半生的命运还能好吗?好不了啦。好在他没有怨言。他相信组织早晚会搞清他是不是特务。他甘心重新当渔民。后来他结了婚,就是和这个‘巫婆’。‘巫婆’叫邬娟,也是安新人。邬娟没有嫌弃他。在那时候和一个‘特嫌’结婚,也需要点勇气呢。改革开放后,邬娟和她的男人来到B市打工。邬娟男人还干他的老本行,在餐馆里当厨子。邬娟则做点儿小买卖什么的。他们租了一套房,先是在路西区,搬到咱路东区是后来的事。两人一直没孩子,说不清是谁的问题。‘巫婆’的男人是五年前死的,死于心梗,他那会儿不干厨子了,岁数大了。‘巫婆’的男人死前,‘巫婆’没有上访过。是‘巫婆’的男人不让她上访,据说两人为此经常吵架。‘巫婆’认为他窝囊。‘巫婆’的男人则认为不该给组织添麻烦,他坚信组织早晚会还他清白。‘巫婆’的男人死后,‘巫婆’就走上了上访之路,她说她一定要为她的男人讨回个公道。”
周辛感叹说:“按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巫婆’的男人是不是特务应该非常清楚了,可这个‘清白’还起来也太难了。难怪‘巫婆’要上访啊。”
老温警告说:“你可不能有个人倾向啊。可以同情,但工作不能受影响,明白吗?”又说,“其实‘巫婆’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要个钱。男人死了,名誉不名誉的还有意义吗?‘巫婆’想要的钱可不是小数,两百多万呢。”
周辛说:“可我听说后来‘巫婆’改了口,说可以只恢复名誉,不要钱。”
老温笑笑:“你嫩了吧,这就是‘巫婆’的狡猾之处,你想啊,一旦给她男人恢复了名誉,政府能不赔偿吗?必须的。她摸着政府的脉呢,这是缓兵之计啊。”
周辛点头:“是这样啊。”
老温掐了手中的烟,看一眼窗外,“哟,说了会儿话,不知不觉,天亮了。”
透过车窗玻璃,周辛看见了天边泛出鱼肚白。小区的三幢破旧小楼渐渐挣脱了夜色的包裹。周辛朝“巫婆”家位于二楼的一处阳台瞥一眼,朦胧的晨曦中,他看见了那两盆郁金香。白天他转过,这个小区的阳台上,只有“巫婆”家有郁金香。他曾纳闷,这个一门心思上访的婆子,怎么还有心思养这洋花?
周辛说:“温哥你走吧,别耽误送孩子上学,回头嫂子该骂你了。”
老温说:“我把大衣留你吧,外边挺冷的。”
周辛说:“不用,我穿着毛衣呢。”说着他拉开车门下车。
老温“轰”一声发动了车,他摇下车窗玻璃,严肃地叮嘱道:“千万盯死啊,听见了小周?”
周辛说:“温哥你放心吧,我不想丢饭碗。”
灰色的面包车调一个头,颠颠簸簸驶出小区的那个仅有两摞残缺砖垛的大门。现在只有周辛一个人了。他要坚持到早晨八点半,直到土利科的人来换他。
最初的一缕晨光落到周辛头上老槐树的枝杈时,“巫婆”在她家的用窗玻璃封闭的阳台上露了面。“巫婆”七十出头了,头发花白,背也有点驼,可她的腿脚利索,走起路来不输年轻人。或许是因为这,才使她有能力不停地“上访”,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正是这几年不断地“上访”,才锻炼了她的这双腿脚。“巫婆”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必到阳台上侍弄一下她的两盆郁金香,浇点水松松土什么的。两盆郁金香,此时正开着花,一盆火红,一盆金黄,煞是香艳好看。“巫婆”侍弄着花的工夫,很自然地朝楼下的老槐树瞥一眼。那一刻,周辛也正抬头朝她看,两人的视线瞬间碰在了一起,但很快又都分开。这几天,两人彼此都明白对方的存在,也都明白这是为了什么。
十分钟后,“巫婆”拎着一只布兜下了楼。这也是周辛预料到的,“巫婆”每天要到不远的“早市”逛一圈。这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时间段。“早市”往来的人多,稍有松懈,“巫婆”就很容易甩掉“尾巴”而逃之夭夭。前几天有老温,两个人四只眼,盯一个人相对容易些。今天只剩了周辛一人,任务之艰巨就可想而知。
“巫婆”也发现了今天的变化。首先是面包车不见了,再就是老槐树下只周辛一人。“巫婆”拎着布兜子从周辛身边走过时,甚至微微一笑。那笑意味深长,似在问:“怎么,今儿就你一人了?”又似在说,“小伙子,你可要小心呀!”
周辛紧紧跟在“巫婆”的身后,不远不近,十多米吧。周辛从心底里没有太把“巫婆”放眼里,不管怎么说,她是七十出头的人了,腿脚再利索能比他小伙子还利索?一个老妪他再追不上,不是丢死人了?
前边就是“早市”了。所谓的“早市”,就是一条马路的两边摆满了摊贩。卖什么的都有,卖蔬菜的、卖水果的、卖生熟肉的,卖鸡蛋的、卖早点的,卖五谷杂粮的,可谓琳琅满目。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人一多,周辛担心跟丢,紧走两步。“巫婆”发觉了,猛丁地站住,又猛丁转身。周辛猝不及防,只好继续朝她走去。两人几乎面对面了,“巫婆”突然问:“你干吗总跟着我?”
周辛愣一下,说:“我……当然得跟着你,我不跟着你,我就要倒霉了。”
“巫婆”笑笑:“你倒挺实在。”又问,“你今年多大?”
周辛又愣一下,他不知“巫婆”什么意思,说:“我……今年二十四岁,这跟你有关系吗?”
“巫婆”“哦”一声,不再说什么,转身又朝前走去。周辛见状,忙紧紧跟上。
“早市”靠南边一侧的中间,是一个很大的小区,里边高楼林立。“巫婆”先是买了点菜,又在馃子摊前买了几根馃子,随后她在人丛里拐来拐去,突然不见了。周辛吃一惊,仔细看,发现“巫婆”拐进了那个高楼林立的小区。他赶忙小跑着追过去。
在小区门口,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男人冷不防窜出来,差点撞到周辛。周辛来不及道歉,只摆一下手。那中年男人狠狠瞪他一眼,嘟囔一句:“大早晨的,跑什么跑?抢死啊!”周辛顾不上解释,只朝着拐向一幢高楼的“巫婆”的背影追去。
“巫婆”花白头发、微微驼背的身影最后消失于一幢楼前的一个单元口。周辛稍稍定了心。他想我只要看见你的影子了,你就跑不掉。你总得出来吧?楼房的单元只有这一个进出口。周辛只消守着单元口,“巫婆”就不可能消失。他想他的眼睛一定要睁大。“巫婆”很狡猾,那年局里的老朱就吃了她的亏。老朱眼见着“巫婆”进了街上的公共厕所。他就在女厕所门口等,可左等右等,“巫婆”就是不出来。他觉得出问题了,在女厕所门口喊几声:“有人吗?”无人应,便闯了进去。里边空无一人。老朱的头一下子大了。他环顾一眼女厕所的结构,墙很高,没有梯子凳子之类的东西,“巫婆”跳墙的可能几乎没有。那么“巫婆”是怎么出去的?他这才恍然大悟“巫婆”进厕所后,时间不长是从里边出来两个女人的。那两个女人说着话往外走,老朱就以为两人是一起的。那会儿天正冷,两个女人都戴着头巾捂着口罩,“巫婆”又换了一件衣服,摇身一变,居然就从老朱的眼皮底下溜走了。后来老朱被通报批评,副科的职务也免了。
“巫婆”的身影闪进单元口时,周辛看了一眼表,七时零三分。他隐于正对单元口的一棵泡桐树后。单元口不断有进出的人。周辛把重点放在从单元口出来的人,尤其是女人身上。每一个女人从他面前走过,他都会凑近了仔细打量。他生怕再犯老朱的错。如此的结果是常遭到被仔细打量的女人的白眼。
半个小时过去了,周辛确信“巫婆”仍在楼里。她能躲在哪儿呢?这楼里有她认识的?又过去十分钟后,周辛隐隐不安起来。他觉得哪儿不对了。他在楼前溜达,又抬头打量一眼楼的结构,就忽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这楼的九层是有逃生通道的,也就是说一旦发生火灾什么的,这个单元的人可以从九层的逃生通道迅速转到旁边的单元。明白了这一点后,周辛的头大了。他想不用说,“巫婆”肯定是从那儿跑了。现在需要做的是补救,他知道八点十分有一趟开往北京的火车。
打了一辆出租车,周辛急火火赶到火车站时,八点过五分。周辛疯了似的跑进检票口,检票员想拦他,被他一把甩开。站台上候车的乘客大多陆续上了车。周辛对守在车厢门口的列车员说声:“我找个人!”不等对方同意,就窜了上去。他要用最后的三四分钟,把“巫婆”从火车上揪下来。他在车厢狭窄的过道里拼命地挤,蛮横地拨拉着人的肩头,眼睛飞快地左右环顾。他从头找到尾。没有“巫婆”。站台的铃声响了。他沮丧地从车上下来。
火车朝北京方向开出的一瞬,周辛的手机响了。“你在哪儿呢,小周?”是老温,“这儿怎么没你呀?你跑哪儿去了?”
周辛不知该对老温怎么说,只骂一句:“妈的,该我倒霉!‘巫婆’还是跑了……”
那边的老温说:“你说什么呢?‘巫婆’哪跑了?不是好好的在家嘛,刚才我还看见她在阳台上摆弄她的郁金香呢。”
周辛吃一惊:“你看见她了?”
老温说:“行了,你快回来吧,土利科的人马上要接咱们班了。”
几天后。熙熙攘攘的早市。周辛推着自行车转来转去,终于在人丛中看见了“巫婆”的身影。“巫婆”依然拎一只布兜,几根青绿的芹菜从里边探出身来。
“巫婆”也看见了他,斜他一眼,说:“今天不是又来盯我吧?”
周辛说:“不不,我是特意来谢你的。”
“巫婆”说:“谢我?你搞错了吧!”
周辛说:“我是要谢你,那天你完全可以跑了的,可你没跑。”停一下,又说,“我想了好几天,不明白为什么。”
“巫婆”笑一下:“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她不再说什么,转身离去,仿佛不曾碰见周辛这么个人。
周辛愣怔了好一刻,方离开那儿。上班后,他去找老温,说:“温哥,‘巫婆’的男人出事的那年多大?”
老温说:“你怎么想起问这?”又说,“大概二十三四岁吧。”
周辛说:“二十三还是二十四?”
老温说:“我算算。”他掰了会儿指头,说,“二十四岁。”
周辛恍然。那一霎,他的心底深处蓦然涌出些温热来。
责任编辑: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