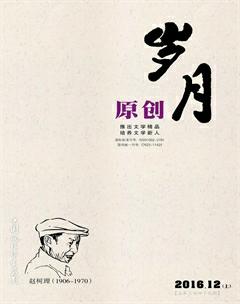春日迟迟
王麦顶,女,原名王梦颖,90后作者。编辑、盛大文学历史专栏职业撰稿人。洛阳市文学院签约作家。

如同山岳与大海是苍茫的危峰兀立和垂范百世那样,森林是经久不息衍生卉木与翎羽的光年幻化的一张温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在这座南方小镇生活的第一年,我找到一处出租的房子。院子里是原来主人种下的红枫。正是初秋,红枫萋萋,随风散落着几片分明的曙红色叶子,情景交融宣泄着某段光阴的碎片,让我一瞥便深爱上。我又想起这样一个女人,在老上海民国时期,曾有一个美丽女人吞药自杀。她并不是因为畏罪或者贪恋、无依或者孤苦,只是因为觉得花样年华太匆匆,不知如何面对垂垂老矣的自己,于是就像红枫那样,在最绚烂的时刻尘归大地。
院落是过去民国时代遗留的建筑。《北窗杂记》上刻画着这座庭院的特点在于兼容了折衷主义风格。是近代民国时期富于中国传统风格特色的,具有强烈的折衷和包容胸怀。我曾扞格不通地认为院子里的枫树就是那时被种下的。白云苍狗,沧海桑田。加诸多年的改建与维护,房子外观看上去早已面目一新。屋内之古色,印刻着被岁月的双手轻轻抚过的痕迹。日光被围困在顶部棱角分明的轩窗外面,只在凹凸且不平的红木地板上框下一口方正的颜色。气氛显得卓殊肃穆。木制围栏上被雨水洗礼留下的脱漆,在斑驳陆离的灰色墙壁上留下无人诉述的回忆。
这座房子,我只拥有一张床,一盏窗。房间像是一户没落贵族堆放杂物的阁楼。经年在日落黄昏带走徒留尘埃间隙的残阳从高而简陋的天窗离开。
临窗的一个女孩,是文院的学生。她用诗人顾城般的朦胧信笔拈来地绘制这里:一间房子,离开了楼群,在空中独自行动。蓝幽幽的街,在下边游泳。我们坐在楼板上,我们挺喜欢楼板,我们相互看着,我们挺喜欢看着。
我也一直都不曾忘记搬来的那天,秋阳杲杲,在余留着缕缕金桂的馥郁的空气中,鳞次栉比地夷犹着飒飒的气息。整理好房间走出庭院的时候,阳光好得出奇。天空的湛蓝被南方绵绵的细雨洗得透亮,恰如披肩上的金丝提花。院子里一树枫叶,尽染之观,宛如红瀑,落下的是一汪被韶华的芳泽燃烧成灰的热烈。
我在花枝乱颤的阴影里驻足小憩,隔壁的女学生见状也走了过来。转瞬间,她抬起手接过刚被风吹下的红叶,我看到她腕子上的手镯反射出夺目的光。
一朝一夕,我们彼此熟悉。
似是故人,我问起她的镯子。她微露沉吟,摘下来给我看。说,这是她和父亲到西藏游历时在一家首饰铺子定做的。只做了一只,在上面用藏文刻上了她与父亲的名字。她又特意让我看,轻声细语说,我的镯子上有一块斑驳,或许是在煅造的时候,不拘小节。制造的匠人告诉我,是密宗徒留的神语,亦是护我真身。等到它被岁月抚平的那一天,我便转世轮回。
那晚她敲开我的门,递给我一本《花未眠》。她穿着黑色的垂地连衣长裙,米白色的流苏披肩,光着两只脚。眉梢上沾着的刘海滴着水,带着刚从浴室出来的温软氤氲,灵动得像一朵刚从池塘里采摘的新鲜莲蓬。她说,送给你,或许你会喜欢。
那样一刹,我接过这本书,迷离倘恍忆起了旧色年华中的悸动。
高中时候喜欢的一个人,一张坏坏的笑脸,连两道浓浓的眉毛也泛起柔柔的涟漪,好像一直都带着笑意,弯弯的,像是夜空里皎洁的上弦月。
高一学期,从冬天到来年的夏天,他天天走着上学。我唯有时快时慢跟在他身后邯郸学步,以至于他迈步的每一个姿态,我都了然于心。谙熟他经过的巷子。熟稔他会经常在CD店和小书店滞留。在柔光中翻看着一本动漫杂志,白皙的皮肤衬托着淡淡桃红色的嘴唇,俊美的五官,完美的脸型,特别是左耳闪动着炫目光亮的钻石耳环,给他的阳光帅气中掺杂进一丝耐人寻味的不羁。
他是那样风姿绰约的少年。我读懂他的匠心独运。独自沉默地坐在下课后嘈杂的教室,拿上一本书,在风中目空一切地细细品读。我曾经趁他离开座位时,翻开他反扣在桌角的一本书。是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
喜欢读这种书的高中男生,不常见。
母亲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带给我一只从博物馆国际展区纪念品柜台买回的英式面具。黑色的羽毛,周边镶着烫金碎钻,纯银制成的眼眶上手工雕刻着LongingforLove的字样,安适如常地躺在紫罗兰天鹅绒的首饰盒里。我拿起它对镜贴合在脸上,惊异的刹那,脑海中浮现的人竟是他。
那天下午我坐车纵横了大半个市区,去我与他共同经历过高中岁月的学校,走进他曾经呆过的教室,坐在他学习过的书桌旁边用手指在上面一笔一画留下他特有的符号。
因为我曾经在美术欣赏课读到面具起源,老师在画纸上用油画颜料勾勒出一幅戴面具的舞女的时候,不期而至听到他低声赞叹,太美丽了。
我豁然,他一向是不露圭角的人,从未义形于色,他或许是真心喜欢这样奢华高贵的事物。
在那年秋天临近尾声之际,我开始夙兴夜寐在夜幕初上点满一房间烛火,架起画板蘸色勾画。连油画笔的笔杆,都被摩擦得光亮圆滑,使用起来得心应手。那一摞用来描绘不同形态面具的白色画纸,叠起来足足几尺厚,细细品味恰若一次潜踪匿影的暗恋。
那幅画,我几乎画了三年。萤烛之辉下面对着画纸,神经质一般加重纸面上才刚上过颜色的图样。茕茕孑立地怅然如何再现张爱玲小说场景一样的方式送给他。让随风纷飞的发尾在他的指尖摆动,以及像柔柔在水底招摇的青荇一般的柔波的爱恋。
在快要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下定决心去找他。
是在他毕业的时候,我带着画了三年的画,又一次跟在他身后回家。那条巷道的朝夕我记忆里在熟稔不过了。日暮回合的傍晚我在他身后走着,踩着他刚走过的脚印。四年多的时间里,那些为了他而青葱而阴郁的时光,悄无声息地默默浮现,曾经内心深处的岌岌可危,思绪迸发得诚实果敢。
我想我一定要把画给他,不然再这样演变下去我埋藏多年的悸动只会愈演愈烈。
挡在他身前的那一瞬,我几乎忘记了呼吸。叫了一声他的名字,把画塞给他。他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地蹙了下眉,接过了画,然后绕过我继续向前走。
我不再回头,而是俯下身,竟然不自觉哭出声来。
记得在大学的间隙中,他送我一本《如果墙会说话》,说,这是亦舒的随笔,我很喜欢,送给你。
走在路上,我打开那本书,看到里面刻意夹着的一张书签。留白部分书写的字迹非常俊朗,一如我脑中幻想的一样。我小心翼翼掠过一眼,害怕是镜花水月的结局,却有抱着水到渠成的心态,所以屏息凝气再次字斟句酌地注视一遍,毋庸置疑,最后三个字烙着“对不起”。
那个秋天就这样湮没在生命里,最终沦落为回忆的卑微章节。
此后,或许不会再用三年的时间,专注为一个人画一幅画。
不会再跟在他身后,追随他离家,踩着他的脚印,满是感时花溅泪的踽踽独行。
那晚隔壁的女学生塞在我门缝里一本同样的书。
我在魂灵抽离回忆自怜自伤中黯然伤神的时候,她走进我的房间站在我背后静默无言。良久,她开口,父亲在几天前离开了人世。她把一同刻有两人名字的银镯,跟随他的骨灰封印进了另一个时空。
她抬起右手的手腕,我看到腕上因常年带镯子所留下的印迹,深邃得匪夷所思。她说,抱抱我,我很孤独。
我拉下窗帘熄灭蜡烛。在月明星稀风清如练的黑夜里和她一边流泪一边聊天。她一直跟我讲她同父亲之间的事情。我当时身心俱疲,恍惚之中唯一听见的,是她对我说起这样的故事。
还是在她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的游园会,无意中她看见父亲和一个很小的女孩在游乐园一起玩。这个穿粉色娃娃裙手拿气球的女孩在父亲的身后嬉笑追逐叫着爸爸,她说,父亲当时流泻出满眼的溺爱,抱起女孩架在脖子上一如当年也用那样的姿态抱过她……
于是从那天起,她每晚的梦境里都会浮现当时的场景,父亲牵着另一个女孩的手经过她身边,她在他们身后歇息底里放声尖叫,可自始至终他们之中都不曾有人回过头。
她说,我已经叫了他父亲整整二十年。他永远都在为别人构筑一个温暖的栖身之所,从来不让我进去。
日出的第一抹亮光照进天窗的时候,她回到了她自己的房间。
我困乏,把头埋进凉水盆里,在电扇的簌簌作响中,卷起窗帘,看见灰蓝天际中以跬步之姿积蓄光明的太阳。
没来由的,我开始想起他,于是点上蜡烛为他作画。
那簇在纸上婉转一般游走的笔尖,在沉寂了多年之后,重新默吻起凝脂点漆的画纸。颜料在白纸上描绘出无悔青春的印迹。这是尘封在发黄牛皮纸里贴上封条的片段回忆了。
我从旧物盒里拿出当年他送给我的书,细翻来,一息尚存有闲置多年于此的他的气息。
在二十岁以后的某一个辗转反侧通宵达旦之后的早晨,世界睁开了眼。我亲眼看到了那些韶颜稚齿,青枝绿叶般少不更事的岁月,往昔赋予我们风华正茂锦瑟年华的青春,掩饰着平凡世界里的平庸与寂寞。
遥远的未知处曾经传来的声音,虽然天空没有痕迹,但我确已飞过。
红色枫叶落尽的结局,是隔壁的女孩因为求学而离去。
临别时,她留给我一只木色箱子。
我撕开封条,看到那个曾经无数次出现在她恍若隔世的梦里会发光发亮的旋转木马音乐盒。
我扭转了几下,听到撕心裂肺嗓音下让人肝肠尽断的催眠曲。若论熟识,整整二十年了。或许她至今也未能从她父亲口中获得如此殊荣的待遇,心中凄凄。
我懂得了。旋转木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追逐的。
而她,却紧跟其后仍未间断追逐旋转木马的脚步。
不眠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