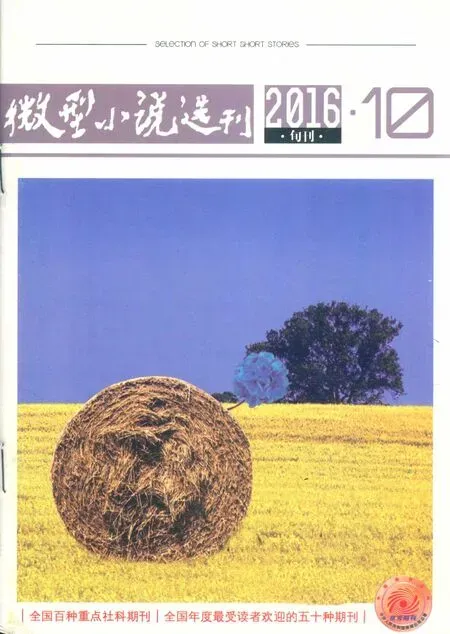碧水镇
□李 皓
碧水镇
□李 皓
从蓝城到碧水镇也就一个半小时车程,新修的柏油路让车子跑得很愉悦,秋风很是清爽,特别适合怀旧。
他问副驾驶上的她:“想什么呢?”
她偏过头来,笑吟吟地看着他:“我在想我们的家会是个什么样子。”
“哦,到了你就知道了。”他的眼睛虽然盯着前方,但还是有些走神。其实他跟她本来应该有一个家的,那是他们在碧水镇读中学的时候就相互承诺过的,可世事的变迁令人很是无奈。
中学毕业,她考上了蓝城的一所师范大学,他落榜了。
他不想复读,索性到一个偏远的空军雷达站服役去了。几年后提干,娶了部队一个首长的女儿。
她在他的世界里消失了二十五年,这些年,他一直通过各种渠道默默地关注着她。
转业时,妻子拗不过他,跟随他转业到蓝城。这个名声在外的浪漫之都非但没有给妻子带来身心的愉悦,相反,她从那个大型国企下岗后,积郁成疾,眼睛面临失明的危险。
他眼下已是拥有实职的处长,事业顺风顺水。但妻子的眼病让他忧心忡忡,只是一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她,抑郁的心里就会挤进一丝阳光。除了温暖,还有一丝慰藉。
两天前,她从美国回来了。
他不曾忘记当年的承诺,当然,她也不曾忘记。
他这次带她到碧水镇来,就是为了满足她这个愿望,也弥补两个人共同的遗憾。
“你的她怎么样了?”她问。
“还好。”他答。
“那就好。”她说。
此后就是一段长长的沉默。
此前的她可不是这个样子,看上去文文静静的,清澈明亮的眼睛里总是跳跃着快乐的灵光。现在灵光没了,忧郁里藏着难以掩饰的绝望。她说她虽然不缺男人,却一直没成家,如果不是现在的样子,她也想过要成家了。
现在是什么样子呢?她不想说,他也不多问。
前面的路有些颠簸,车子驶进了一片田园。他说:“马上就到了。”
她说:“哦。”
“可惜现在是秋天,树叶都快要落光了,颜色不好看。”
她说:“挺好。”
他停下车:“我下去抽根烟。”说完就下车走进路边的小树林,让她只能看见他的背影。背影站成了一棵很沧桑的树。没有风,树却在颤抖。她忽然想起来,他是不吸烟的。
他回来了,低着头。她发现他的眼睛红着。
“你怎么了?”她问。
“没事。”他启动车,继续前行。
那间不大的木屋子前有一个不大的水塘,平静得像无云的蓝天,蓝得让人想哭。
“嗯,我想象的就是这个样子。”她很兴奋,挎着他的胳膊向小木屋走去,“这水塘叫什么名字?”
“瓦尔登湖。”他望着水塘,目光柔软。
“开玩笑吧。”她不自觉地用拳头轻捶了他的肩膀一下。青春仿佛顿时又回来了,不同的是,那时眼里没有眼泪,全是笑意。
“别人叫它什么我不管,它就是我的瓦尔登湖,也是你的。”他说。他搂住她瘦弱的肩膀,那种骨感让他的心痛了一下。“走吧,我们到家里看看。”
“回国之前,我特意去了趟瓦尔登湖,没有这儿美。”她说着,依偎得更紧了,几乎是把整个身子都托付给了他。他很想哭,但他告诫自己刚刚下车借口吸烟的时候已经哭完了,就不能再哭了,把笑容给她。
木屋散发着松油的香味儿,香味儿是被温暖的阳光煨出来的,木屋里又暖又亮。他让她坐到那张双人床上。他坐在床边的一个木墩上,看着她。时间稳稳地趴在洁白的床单上面,连思绪都慵懒起来。
“这里真好!”她整个人在阳光中亮着,显得那样飘逸,像要升入天堂。他赶紧握住了她的两只手。心里说,别急着走,千万别急着走。
“这里是你的家。”他说。
她淡然一笑:“谢谢你。”
“我应该谢谢你,你给了我一个兑现诺言的机会。”他说着,把目光移到墙上,那里挂着一个木制的镜框,镜框里是他和她的“结婚照”。那是他用电脑合成的。
她的眼泪簌簌地落着。
太阳一样羞涩的湖面,被几只野鸭子弄皱了。一波波的笑纹漾过来,弹拨着岸边的草茎。真静!静得要融化了,找不到自己了。
“我这二十多年把自己弄丢了,我一直想回家。”她说,“还好……可是,晚了。”
他们和衣躺在床上,他像个大珍珠蚌一样从背后把她包在怀里。“不晚,回来了就不晚。”
“你有属于你自己的家,可我没有。”她的眼睛像两颗星星,忽明忽暗。
他包得很用力,他想给她温暖,可自己也在抖。对她的哀叹他无以回答,只好压抑着内心的翻江倒海。
“你该回家了。”她说。
“这就是我的家。”他说,“不,我们的家。”
“我该得到的也就这么多了,谢谢你。”她说,“不,应该说对不起。”
他不想提及现实,对这样的夜晚,现实就像一个死缠烂打纠缠不清的流氓恶棍。
“我就这样一直陪着你。”
“真的?!”
“真的。”
“如果我能一直这样下去,你还会陪着我吗?”
他犹豫了一下,说:“能。”
他知道这是欺骗,他给不了她永远。他也清楚,连她自己也给不了自己。他似乎为了掩饰自己的虚伪,用嘴在她的脸上寻找她的唇,却趟起了一层泪。像早晨挂在草丛上的露水,凉的,湿的。
“我相信你。”她回避了,“我需要一些在这里生活下去的东西。”
“我都准备好了,而且我会随时去买。”
“我需要一些女人用的东西,明天早上你去买回来吧。”
“好好,天一亮我就去。”
“你不用急着回来,你得上班,还要照顾你的她,不用天天陪着我。”
“不……”他的嘴被她的唇堵住了。
天亮的时候,她睡得很踏实,像婴儿一样恬静。她一定是很久没睡得这么香甜了。他不想扰了她的好梦,轻身走出小木屋。他在水塘边驻足了很长时间,看着湖面一点点亮起来,微风把湖面赶出一层层褶皱,内心的平静就没了。
他买了她要的东西回到小木屋,她不在,带走了那个镜框,留下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为了这个家,我想活着。
一个月后,他收到了一份来自美国红十字会的信函,信函中声明,他的妻子即将得到一位志愿者捐赠的眼角膜。
(原载《航空画报》2016年第1期 作者自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