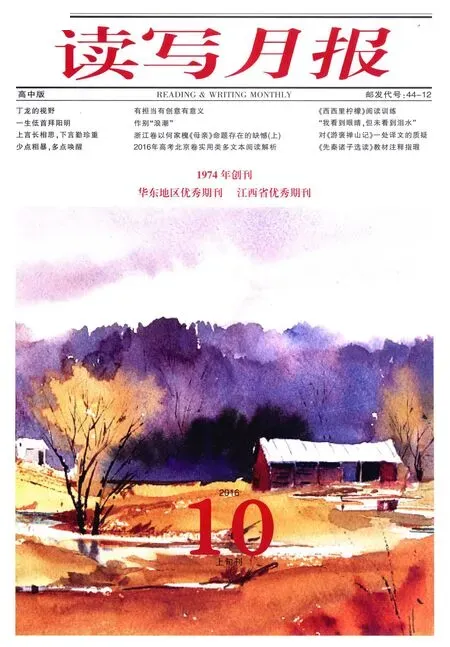一生低首拜阳明
山东 ●张永军
一生低首拜阳明
山东 ●张永军

一部《明史》,留给后人太多话题与叹息。
公元1644年,也就是明崇祯十七年,当女真铁骑第一次穿过号称“天下第一雄关”的山海关进入中原,并顺利占领北京的时候,几乎所有满洲人依然不太相信他们能够真正征服整个明朝。即便是雄才大略如多尔衮,当时也未敢做过多奢望,想到的无非是“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然而,随后形势的发展超出所有人的意料,整个局势几乎呈现一边倒的状态,大量投降归顺的前明军队,其人数甚至超过了满清人口的总和,俨然成为其西进和南下的急先锋和主力军。1662年,降将吴三桂在缅甸俘获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并亲手将其用弓弦勒死,宣告统治了近300年的大明朝终于彻底成为历史,而满族的祖先们同时创造了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的传奇和神话:他们只用了大约60年的时间,便以一个仅几十万人口、连自己的文字都刚刚发明的蛮夷部落,征服了当时人口是自己两三百倍、文明领先世界的第一大王朝,并由此开启了又一个近300年的王朝统治……
明朝的覆亡,原因诸多,但绝对撇不开久蛰于朝臣中的“纯臣”瞻念、“清流”偏执。以才具平庸、忠荩有余自矜自许的官员们,缺失了审时度势、力挽狂澜、“驾驭笼络,应机济变”最起码的意识和能力。官员素质与其承担职责的不相当,销蚀了大明的生机,也毁掉了它最后的一丝机会。即令京师陷落、崇祯殉国后,在南京仓促拥立起的南明朝廷,若非秉政者依旧沉迷于“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历史或许会另演。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杜牧《赤壁》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 《放言五首·其三》
这两首均由唐代大诗人写的咏史诗,前一首似乎更有名,而我却更推重后者:《赤壁》写的只是一种假设,而《放言》却表达出了一种真实和清醒!历史无由假设,只合反思。一部《明史》,耐读,又最不堪读。在种种的 “不堪”中,不只让我们系心于“以史为鉴”,彰善瘴恶,以为惩劝,更让我们加深了对“忠臣”的另一层理解和认知:真正的“忠臣”,必须是“能臣”,具备良好的治国理政才能;那种“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关键时刻不能为国效力、力挽时危的所谓贞士、忠烈、清流,实无资格忝列 “忠良”!念及于此,刘基、宋濂、张居正、戚继光……这些在明朝建立过殊勋的能臣、策士、良将,势必会马上闪现在人们眼前。但还有一个人,能令人立刻想到的似乎并不多。这并非是因为他才具不显、勋业不著,而是因为他在治国理政才能之外,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非凡的哲学家和著名的文学家。诸多的成就和光环,反而掩盖了他同时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军事家的身份。
他,就是王阳明。
立德、立功、立言,向来被公推为自古以来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最高境界。纵观王阳明的一生,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立下不世之功,彪炳史册;作为思想家,为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开创儒学新天地,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与孔子 (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作为文学家,有文集传世,鸿篇佳作被《古文观止》收录。王阳明无疑用自己的成就对人生价值作了完美阐释和极致实现。这种功业,不只冠绝有明一代,在中国历史上亦屈指可数。
知行合一
王阳明不是一般的能臣,他是文臣,又是宿将,在娴于政务之际,征战无数,而且打的多是大仗、恶仗,甚者直接关系社稷存亡。但他每仗必胜,稳操胜券,如《明史》所称:“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千古文士侠客梦”,文人与剑,冥冥中一直有种因缘与期待。只是,锋利的剑刃、高超的武功,往往被当作快意恩仇、率性潇洒的“形下之器”。只有到了很少一部分人手中,才能文兼武略、兼济苍生社稷。文人王阳明一手执剑一手握笔,以经略四方为初衷而矢志不渝,经仕途踬踣而不辞重任,这份担当,这种执着,这般优渥,正是我仰慕他的原因之一。
千百年来,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才学而被人们长久地纪念,他能留存于后世的名声,几乎全部来自于他的惠行与公共行为。我一直认为,历来中国文人之弊,尤以心仪于参与、协助、坐而论道而非担当、主导、蹈厉奋发为甚。换言之,他们更倾心于成为一个 “劳心者”而不是作为一个“劳力者”,在实现自己的诉求、理想的过程中,他们可以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取义舍身,但他们每每止步于亲力亲为、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多以依托他人的能量和影响成就自己为念。这种固陋或偏执,导致他们在“知”“行”之间,表现出太多的谙于言事而滞于执行,使其尽管不乏审时度势的敏锐、兼容并包的大度、与时俱进的见识,却难以成为除旧立新的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的擎天柱石,发挥最切实的社会能量。而王阳明一生的事业功勋,除基于才具卓识外,当在其真正“做起来”,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智识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献身精神。幼小的王阳明知悉英宗被俘后,即以修文习武、为国效忠为己任,十五岁而屡献治平之策,经宦海沉浮而不改初衷,其担当精神、忧劳意识和践行志气,数百年后,仍戚戚于我心。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或许,待到文人(知识分子)们真正走出书斋,告别“小我”,以躬行实践体现“兼济天下”的能量、“解民倒悬”的能效和 “振兴中华”的能事,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良心”和“中流砥柱”。当下中国的许多问题,之所以未得到前瞻的思考、实效的解决和通盘的筹划,和某些文人(知识分子)不能在身体力行中超前谋划、合理谏言、科学资政不无关系。治大国如烹小鲜,但想烹好一碗汤,光靠推敲食材、咨议食谱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身临庖厨,亲历实为一下才行。
龙场悟道
金色的林子里有两条路
很遗憾我无法同时选择两者……
我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一条
它改变了我的一生
这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中的诗句。人的一生,似乎就是将生命中的各种可能性排除得越来越少的一个过程。但对于作为思想家的王阳明,却迸发出了另一种瑰丽。
王阳明思想上的转折、进益,离不开“龙场悟道”。正德初年,王阳明因冒言直谏触犯权贵,被贬为贵州龙场驿栈驿丞。贬斥龙场,本当是王阳明人生的一次低谷,但荒芜的龙场,却促成他心性的自由,成了他“运思”的天堂。那应该是一个朗月清风之夜,辛劳了一天的王阳明仍然苦思“如果是圣人,面对这种人生窘境,会有什么办法呢?”渐渐沉睡下去的他,在夜梦中忽然领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豁然开朗的他不由自主地从睡梦中跃起、欢呼……
四时四处的风,经由心灵的过渡、情感的熨帖,拥有了穿林打叶的别致、春城飞花的优雅、西风卷帘的婉约、细草危墙的深挚,也沾染了风劲弓鸣的峥嵘、天野苍茫的宏阔、波涌江边的摧怆、浪淘天涯的感喟,它已经不再是纯粹、简单的风声。但龙场那个月夜的清风,伴随着王阳明的 “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在翻开了中国思想史上崭新一页的同时,也拥有了别样的深邃、空灵、瑰丽。
王阳明“心学”的精髓,皆在于“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他认为,“天理”就在每个人心中,人们只要通过提高自己内心的修养和知识水平,将道德伦理融入到日常行为中去,以良知代替私欲,做到“知行合一”,必将达到社会的和谐运行,即所谓的“致良知”。“心学”继承和发扬光大了中国儒学特有的人文精神,提倡独立思考,以“人欲”战胜“天理”,较之此前那些冷冰冰的教条、说教,更贴近现实生活,其意义和价值,不只在于简易朴实,便于学习掌握和易于实践执行,更在于强调生命的过程,空前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时间和空间上超越了其本身的存在。“心学”甫出,即学子蚁聚,迅速成为当时社会上的又一种主流思想,并由此在明清之际掀起启蒙思潮,良风所播,直迄今兹。
王阳明的 “龙场悟道”,会每每令我想到苏东坡的“赤壁赋歌”。那同样是一夕清风明月、人间羽化,一次思想顿悟、心灵放飞。但我也知道,在赤壁之下与客一起享受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的东坡居士,虽然 “饮酒乐甚”,体验到“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他的快乐豁然,只是暂时超越了时间的束缚、超脱了人世的羁绊。苏轼的超脱,只是解悟到 “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身处逆境时也要保持豁达、超脱、乐观和随缘自适的精神状态。是以 《前赤壁赋》才会束笔于“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因为,“东方之既白”后,生活又会归于常态,生活的失意、人生的坎坷、仕途的踬踣,当随着“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的过去而卷土重来。“赤壁赋歌”的超脱,只是参悟到了“自适”;而“龙场悟道”的彻悟,则让人理解了“自足”。 作为“心学”宗师,王阳明不仅有对哲学自创一派的大智慧,更表现出“知行合一”的超能力。此后的王阳明以 “理”驭“术”,将权谋与处世、兵法和学养运用合一,做到了相得益彰。鉴于历史局限,其观念或有不彰,其功业亦或有可商,但谁也不能否定:大道同源,在自己的人生进程中,我们必须开拓出更多的可能性,实现最大的成功预期,从而获得 “自足”“自达而达人”。“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功预期,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这条路上,且行且珍重。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传习录》
人们对精彩的解读不同,它可以是一种绚丽绽放,也可以是一次入木三分,甚或是一种身段、内涵或风采。以我的体会,它更应该是积极呈现自己,在“知善知恶”“为善去恶”中人生因之而更趋完善的一种态度、一层境界和一份努力!而一个人所产生的良性影响,一定会通过他放大、衍生到他所处的环境,又继续影响到这个环境里的其他人。做好自己,再把这份理解和承担不断向外辐射,就会使“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在这一波又一波的辐射中,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理解和呈现,就会“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逐渐点燃和强化,不经意间,说不定就改变了历史、实现了人生……
青龙埔话终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太史公的观念,荡涤、振发了后人之心。但死亡对于每个人而言,都属于一个沉重的话题。即令面对“用之所趋”的考量,可以因为“死得其所”而蹈死不顾,但绝难免“有心”之欲、“无力”之憾。 一个人,如在人生大别之时能像王阳明那样,欣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那该是怎样的一份满足感与成就感!抑或说,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澄澈、慰藉与锤炼!
王阳明出道以来,蹲过监狱、挨过廷杖、遭过贬谪、逃过暗算、受过冷落……他是为人所不能为,方成人所不易成。“青龙埔话终”,让我们感佩的不仅是他内心的澄澈、求索的执着、担当的坦然,更让我们见证了播种的幸福、自身的调控和对人生的虔诚。
雅斯贝斯说:“理解取决于理解者的本性。”其实,理解也取决于理解者的态度和行为。我们“只此一生”,已没有多余的时间再去反复求证另外的可能性;可能性有时就是一种悖论抑或陷阱。我们总得做些什么,当年华老去,才敢回忆。在面临生存的压力、自立的艰辛甚或诱惑的抉择时,我们必须学会知进守止,自我实现。当“称心而言,率性而行”在现实面前必须承担风险的考验时,我们应该拒斥狷狂、傲慢,对“当下”保持必需的理性和尊重;当遭受的“压抑”无法改变,我们应当调适好自己的心境,尽最大可能实现自身价值;当失之东隅已成,就该转而想到收之桑榆;当弱水三千取此一瓢饮而不能,就该将心境调适成当不失一瓢……诚然,我们达不到哲人的至境,但只要经历一次人生的洗礼和生命的共鸣,以实现对生命的承担和人生最华丽的逆袭,一定会有崭新的开始!
从天上掉下的是雨,落下来溅起的是雨声。任何一件事,如果意义仅限于自身,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播种、收获的过程,或如一条河的汇成,需要巨大的耐心、惊人的巧合,更需要忍受痛苦的消耗。当足够的耐心容许、必要的巧合发生、所有的消耗被忍受,才会拥有一条河,也才能享受播种后的收获。生命短暂身如云烟,为何还要去不懈地追求、不停地奔波?可能我们不知道别人,但必须明确一下自己:虽然哪里都可以生存,但我只想要那一片明亮的大海;虽然哪里都可以驻足,但我更想在风雨的路上由虫变蛹,由蛹化蝶,拍打出一双飞向天空的翅膀。只愿,越来越多的人学会坚守、学会热爱、学会真诚、学会行动,在努力实现自我的过程中,迎接成功、体验幸福、享受慰藉。
三月,拂过又一缕清风,送上春日别样的欣悦、澄澈和灵动。路过的风未尝不是前尘结缘的点悟、会心的探望。任何一颗心灵的成熟,都要经过不倦的跋涉、失意的煎熬、执着的漂泊和坚强的奋战。就让她盛开在我们前行的路上……
“一生低首拜阳明。”阳明学说,惠泽后世,更衍及域外。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似乎受益颇深。“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高濑武次郎)较之他们,我们是否应该躬身自省,对于王阳明的景慕、领悟、对于“心学”真谛的习知、弘扬,我们是否出现了冷漠甚或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