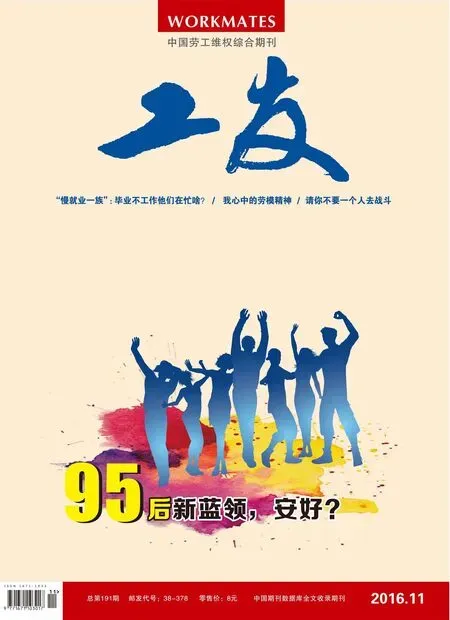阿炳的幸福生活
文_冉德强
阿炳的幸福生活
文_冉德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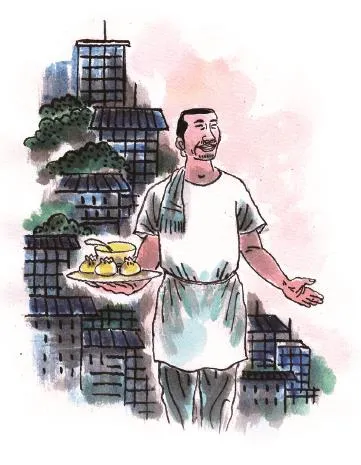
阿炳今年55岁,长我二岁,因小时候患脑膜炎留下后遗症——读书迟,而与我成为小学同班同学。阿炳个头不高,满脸胡须,黑不溜秋傻乎乎的样子,30多岁时与一带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子的丧偶妇女组成家庭。我在外工作30多年,每次回家与阿炳见面,他都以老同学相称。
阿炳虽然脑子反应有点迟钝,但干起活来丝毫不含糊。在我的印象中,阿炳干的都是些简单的重体力活。建筑工地上,挑砖扛瓦抬石头;庄稼地里,挑肥挑谷子,没一样轻松活让他干。也是,轻松活多少有点技术含量,他也干不了。有时我在想,可怜的阿炳就像一头牛,干重活是他的唯一。而他也乐意,问他累不累,他傻傻一笑说:“这没什么,转去几年劲还大些呢。”可能,在阿炳看来,干重体力活就是他的夙命。而在很多人眼中,几乎都认为阿炳就是干重活的料。
阿炳“满脸胡须黑不溜秋”与他从事的劳动是有直接关系的。多少年来,阿炳在家务农外出务工,人们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脸朝黄土背朝天,哪个农民又不是这样呢?而对于我们这些吃“皇粮”人,他们只有羡慕。我们走在他们中间,总是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这感受,是苦是乐,几十年来,我没有体味出味道来,因为农民出身的我最了解农民疾苦,我是真心希望我的农民兄弟都过的比我好。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话在阿炳身上应验了。阿炳命运的改变缘于一家上市公司落户我的家乡,征地拆迁,他们搬出了世代居住的小山村,搬进了小镇。
有一天晚上,我在小镇公园与阿炳偶遇,这还是我认识的阿炳吗?白白的,脸上胡须也少了,衣服穿得也整齐了,就连走路的姿势也变了不少。我对阿炳说:“我家有点小事能不能帮我去做一下?”他傻笑着对我说:“老同学,我可没时间帮你做这事了,你请别人吧。”过去,我家的一些小事一般是请他做的,工钱是不会少的,这么多年来他也清楚。我不解。他告诉我说,他们家搬迁后在小镇上开了一家小吃店,生意可好了,一天卖个千儿八百的,忙着呢!
阿炳还热情的对我说:“小时候的玩友都进城了,梁兄住在我楼上,曾弟住我对面楼上,还有王兄……”
没过几天,我来到阿炳与他老婆开的小吃店,生意真的很不错,阿炳忙着招呼客人,为客人送包子端面条,忙得不亦乐乎,与我寒暄的时间都没有。看着阿炳忙碌的身影,我想,原来阿炳也干得好轻松活啊!阿炳变了,变的我都不敢认了。
我的家乡地处长江边,近几年落户的上市公司就有六家,还有许多小企业在此发展,原来近千户的小山村,已搬出了七、八百户,他们由农民变成了市民,搬进了小镇,住进了楼房,而且家家户户有存款,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甚至几百万。与他们相比,我吃皇粮三十多年,存款倒是没他们的零头多,乡亲们开的车比我好,住的房比我大,现在与他们走在一起,已没有了过去那种自认为的优越感了。
国家富强了,城镇化速度加快了,使阿炳们由农民变成了市民,而且是有钱的市民。改革开放成果与人民共享,我想,我的乡亲们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