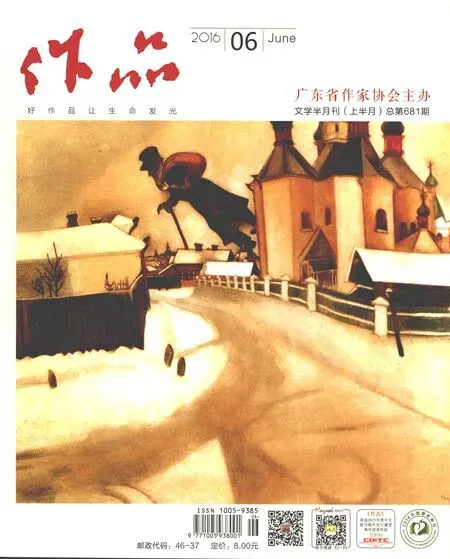入骨相思知不知
文/陈不染
入骨相思知不知
文/陈不染
陈不染女,生于1991年12月31日。青年写作者。
多少年来,很多优秀的女性作者以其特有的细腻的情感和绮丽的语言为我们织造了很多动人唯美的爱情故事。陈不染的这篇爱情小说放在旧中国那晦暗沉重的社会背景下,整个故事便显得愈发荡气回肠、苍凉悲壮。我们常说,一篇好的小说,除了它拥有完美的故事、格局、叙事技巧之外,抛去这些不谈,也许我们通常想要读到的是——故事以外的那“一点东西”。这点“东西”是什么,不好说。也许只是我们心中刹那的共鸣,也许只是告诉了我们一些简单的道理,也许是我们看完后产生的一些领悟。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无论我们最后从这篇小说中得到的“那点东西”是什么,从情感上来说,它都是一篇非常好的爱情故事。
——顾青安
在粤西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有稻田、有山林、也有鸡鸭与猪牛,还有一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我的老家就在这片土地上。虽然四面环山,但是我们的村庄并不闭塞。那个动荡不安的二十世纪,背井离乡成为很多人心里永远的痛,由于历史原因,很多村民都有亲属居住香港,也时常可见香港人回乡探亲或本地人移居香港。
小时候,我的记忆都是关于这座宁静的村庄。
从我记事起,村口就住着一个老婆婆,她独自在一座漂亮的二层小楼里生活,楼外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紫荆树。每天清晨,她会搬一张竹制的太师椅来到院前,有时眼睛眯虚着半躺在椅子上,慢慢地摇晃;有时开着收音机,听着百转千回的粤曲,眼睛痴痴地望着远方。小时候,我每天上学放学都会经过她家门口,听到收音机里传来咿咿呀呀的粤曲:
拈镜欲梳懒画眉,推窗怕看夜雨霏霏,一丝丝一串串,心更冷,登高处,又叹燕踪来迟。我为你不胜悲,空有泪染相思字,未忘握手相牵,三生证白头约,尽化恩怨事……
她叫兰婶,街坊邻里们无论男女老少都这么叫她。
少不经事的我们,路过她家时倘若看到她在院中,也会“兰婶,兰婶”地喊着。傍晚时分,夕阳透过紫薇花的叶斑驳地洒在她身上,映照她的笑脸,优雅而慈祥。那时她会对我们说“乖,过来啊”,然后变戏法一般从空空如也的手中变出几颗大白兔奶糖。那时的我就觉得她与其他农村妇人不同,别人都是生龙活虎地到田里干活,或三三两两在巷口里喋喋不休地闲话家常。大多数的农妇,都带着喧嚣的市井气;而兰婶却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坐着,静默而孤独。
时光渐长,岁月不饶。当我明白世事,想去了解兰婶静默和孤独背后的故事,她却不再是以前那个耳聪目明的兰婶了——她得了阿兹海默症。病后的兰婶,口里总是会念叨着一些模糊不清的话,像是在读诗词,又像是在唱粤曲。她还会对着我们笑,痴痴的笑,可是再也变不出那颗甜甜的奶糖了。
关于她的故事,我是从村民们零碎的话语中,拼凑出来的。
兰婶年轻时不叫兰婶,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素馨。她原是大家闺秀,祖上有人在朝廷当官,积下家业,到她父亲这一代已是当地富绅。他们家有很多田地,那时候,很多贫穷的村民都到她家打工,她父亲也乐善好施,深得人心。豆蔻年华的素馨,知书识礼,人人都尊敬地叫她“小姐”。
直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建国初期,土改运动如一阵龙卷风席卷而来。乐善好施的父亲,却被划分为万恶不赦的地主。十二三岁的素馨小姐亲历了被抄家,父母被残酷批斗。最后,父亲被凌虐而死。母亲也绝望地自行了结了性命,追随父亲而去。
素馨小姐从大家闺秀,变成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孤儿。所幸他们家原来的长工福伯收留了她,她才活了下来。由于地主的女儿身份敏感,为了生存,她不得不更名换姓,从此,她叫阿兰。
福伯是个憨厚的贫下中农,他有一个儿子叫阿松,自小就跟着福伯到东家干活。阿松比阿兰大两岁,他们是一同长大的。小时候,阿松常常带她上山摘野果,打小鸟,他们曾经有一段纯真的童年时光。
在福伯家生活,虽然清苦了一些,总算是过得安贫乐道。阿兰也渐渐融入了这个家庭,福伯福婶把她当成亲闺女一样对待。阿松更与她日久生情,私定终身了。
然而好景不长,才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又迎来了新一轮龙卷风。50年代中叶,农村集体化席卷广东。各个农村都建立了人民公社,所有土地又归为集体。公社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农民不准开荒,不准经商,只能按要求完成公社要求的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上交国家。生活才有所好转的日子,又变得一贫如洗。
正是此时,二十出头的阿兰和阿松成亲了。
这一场庞大的“社会主义改造行动”大大打击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紧接着又是“三年困难时期”,那些到处闹饥荒的日子,福伯福婶相继饿死了。为了缓解饥饿,他们家曾经吃过蔗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但是,大人挺住了,而他们满月的幼儿,却因缺少奶水而夭折了。
亲人的相继离世,深深地打击了初成家的小夫妻。他们很伤心,却连哭的力气也没有。
在他们身体与心灵都受到巨大的折磨时,听闻不远处的香港相当富饶,简直是人间天堂。有些村民逃过去了,寄几天的工钱回来就能把一家子养活一年。
我查了一些数据,当时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所以当时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于是,为了生存,难民潮涌向了香港。那时赴港的码头都有严兵把关,大部分无权无势的难民都选择了自己游泳渡海,虽然死伤不计,但他们还是冒险,仿佛游过去就是天堂。
阿兰与阿松也决定逃港。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阿兰游到半途时,却因体力不支而溺水,被救后醒来时已与丈夫失散。彼时,官兵对偷渡香港进行严打,她一个小女人再次游泳过港已是没有了可能。她孤身一人,举目无亲,不得不回到老家。就是这样一个二十出头初为人妇的女子,孤苦无依,沿着铁路走了数天,回到空无一物的家中。我想,当时的兰婶,一定很失落,很绝望吧。
归家不久,阿兰发现自己怀了孕。可是丈夫那头却杳无音讯,不知是死是活。尽管如此,阿兰还是坚持生下了孩子。
十月怀胎的辛苦,比起一朝坠地后漫长的抚养只是皮毛。但是她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儿,就这样捱过来了。村里人很照顾她,因为她识字,让她在小学里教书。凭着微薄的工资,她带着女儿捱过了饥肠辘辘的贫困岁月,捱过了被批斗的文革浩劫,捱到了平反,捱到了改革开放。
就这样,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女儿,一步步走过来,风雨不改,初心不悔,再也没有踏出过村子一步,见证着世事变迁。
广东与香港,只隔着浅浅的海峡,却如同天堑一般。那一年,游过去的人们,从此再也没有了下落,而留下的人们,只能望眼欲穿他们的消息。又或许,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寒来暑往,阿兰豆蔻年华熬成了两鬓如霜,人们渐渐地改叫她做兰婶了。年华已改,不改的是等待的眼神,和心内的期许。
终于等来丈夫的消息。一封鸿雁传书告知她,他已在香港结婚了。信里还说,失散十载,没有想到你一直等着我,为我抚育女儿。可如今,我在港已有妻室,是我辜负了你。我无法允诺你什么,希望这些钱能弥补这么多年来的缺席,你也找个好人家改嫁了罢。一张汇票,如同兰婶脸色一般的苍白。
回廊一寸相思地,落月成孤倚。背灯和月就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十年,竟然等来这样的结果。街坊邻居们纷纷劝她改嫁,她却说,我不嫁。
或许是母亲妇道的影响,又或许是旧社会女子的本分,从一而终成了她根深蒂固的思想。纵使那个男人,已另结新欢,她也会为他苦守。
就算没有新欢,两岸相隔,又能如何呢?再深的相思,也敌不过现实啊!
她一天一天地等待着,等一个没有未来的未来,和一张又一张的汇票。年复一年,女儿渐长,总是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她便摸着女儿的头,笑着回答,快了快了,爸爸会回来的。
我常常想,年轻时候的兰婶一定很美丽吧,旗袍加身,发簪明媚,不然如何到老还能如此优雅呢。然而美人迟暮,容颜被皱纹侵蚀,老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再后来,回乡探亲的政策也放宽了。村里很多港胞都一个一个地回乡探亲了,而她终于没有等到她的丈夫。那边的他也曾经托亲友带一些只有香港才买得到的物品给母女俩,有时是时尚的布料,有时是新奇的罐头食物,有时是一些糖果饼干。
她也在来往的港胞口中,得知过他的情况。
死里逃生的他,和一群难民在码头上扛货搬箱维持生活,那个有上顿没下顿的年代,为了生存唯有拼命干活。终于因为不堪重负扭伤了腰,码头也容不下他了。于是流浪街头,露宿路边,捡一些残羹冷炙填肚子。也是命不该绝,一家茶餐厅的心善老板收留了他,让他在店里打杂。他深知老板救命之恩,工作卖力,勤恳踏实。因为他识字,老板十分信任他,把采购和账本都交给了他,一做就是几个春秋。后来老板得了肺痨,临终前把腿脚有些残疾的独生女托付给他。从此,他便在香港有了自己的茶餐厅和现在的妻子。
茶餐厅的生意不好不坏,他也不算富裕,却也坚持每两月就寄一次生活费给大陆的妻女。兰婶母女得到了他的赡养费,生活过得还不错。但她坚信着,终有一天,他会回家,给她们一个完整的家。
兰婶当爹又当妈,把女儿拉扯成人。女儿将要出嫁了,她跟母亲说,不是说我长大了爸爸就回来了吗?现在我都要嫁人了,都没见过他一面。于是,兰婶托人带信给丈夫,请求他回来一趟。
他终于回来了,相视一笑,已不再是一同长大的那个青衫磊落的少年。他和她,阔别了二十五年,整整二十五年了。欲梦天涯思转长。几夜东风昨夜霜。二十五年,足以令美人迟暮,英雄白头。她也不再是楚楚动人的大家少女,转身便是皱纹深刻的中年老妇。
没有寒暄,没有泪容。他们相见,一如平常夫妻一样,热闹地张罗着女儿的婚礼。但眉宇之间,她仿佛读懂他的无奈与愧疚。
我想,她是理解丈夫的。不然,她怎么会跟他说,回去吧。深明大义的兰婶怎么不会懂得,自古忠孝两难全,情义更是身不由己。香港那边的家,救了他的命,纵使她情深切切,他也要归去来兮,用余生还债。
他在婚礼后又离去。她终究剩下自己一个人了,女儿邀她同住,她也拒绝了,她说,这里是我的家,我哪也不去。
从此,兰婶就每天坐在门口守候。她或许相信着,再次离她而去的丈夫,也会有再次归来的一日。到那一天,他就再也不走了。
他还是回来了。
只是没有想到,再次归来的却是他的骨灰。是他在香港的儿子把他送回来的,那是第一次看见他儿子,那翩翩身影,像极了他年轻时的模样。她或许有一种错觉,以为她还是初为人妻的少女,他终于从香港回来了。落叶归根,是他的遗愿。他的灵位被安置在家中,她终于与他长厢厮守了。
天咫尺,人南北,不信鸳鸯头不白。兰婶的头发是一夜之间变白的,同时变了的还有她原本灵光的脑袋。她变得反应迟钝,总是自言自语。女儿带她到医院检查,结果是老人痴呆症。
她痴呆了,从她接过丈夫的骨灰盒那一刻,她就痴呆了。所有的等待,所有的深情,都与骨灰一同埋葬在他们童年一同玩耍的屋背山。她的脑袋空了,相思了结了,脑袋便空了。
或者也是一种福气。起码在她的记忆里,她深爱的丈夫还在香港,只要她一直等着,他终有一天会归来。于是,她还是天天在村口守候着,等待着。
她依旧每天喃喃自语,我试着侧耳倾听,却听不清。那句话,她始终反复的念,隐隐约约听到“红豆”二字,透着悲凉。
后来,我离家求学。终于有一天,我读到一句诗: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我用粤语复念几遍,恍然大悟,原来她心心念念的是这句啊。
入骨相思,相思入骨,她始终放不下他,等了他一辈子。那张太师椅,或许是他曾与她一起拥坐,她却用余下的半生去体会他的温度。
后来,我回家了。回到村口却没有看到兰婶等待的身影,邻里说,兰婶去世了,那晚院中的紫荆花开得正好,她就在院中的太师椅躺着摇着,再也没有醒来。她走得很安详,像是熟睡了的模样。
我相信,兰婶一定是去了天堂,与丈夫团聚了。不知道在他面前,她会不会吟读那句诗: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