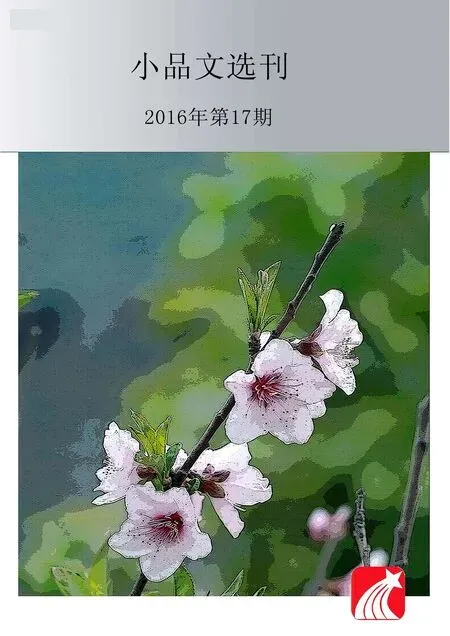春光摇落,须臾一生
——浅论《小城三月》中的爱情书写
韩晓云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00)
春光摇落,须臾一生
——浅论《小城三月》中的爱情书写
韩晓云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00)
爱情,是男女之间美妙、炽热、真挚的灵魂吸引,它的神秘、美好被无数文人墨客描摹、赞颂。《小城三月》中萧红以她的灵性书写,将翠姨的爱情心事娓娓道来。萧红以她敏感的笔关照处于社会边缘、弱势的“少女心事”。本论文将从《小城三月》缓慢的叙事节奏、翠姨的病、翠姨的爱情苦闷三个方面来浅论其中的爱情书写。
萧红;女性叙事;叙事节奏;爱情叙事
1 缓慢的叙事节奏
萧红的小说重风景的描摹,进行情绪的渲染,鲁迅在给萧红的《生死场》序言中委婉地说她的作品“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列夫·托尔斯泰说过:“文艺作品就是那种能感染人、把他们全体引致一种情绪的东西。”她在这种重铺陈与情绪渲染的风格中,她的小说人物面目模糊,却令人在生活中,或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极易找到“那一个人”。
《小城三月》的叙事节奏缓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慢”风景的书写,主体故事进入缓慢;二是细碎的琐事形成时间阻断感,主体故事发展缓慢。
小说始于春景,“抢根菜的白色的圆石似的籽儿在地上滚着……天气一天暖似一天,日子一寸一寸的都有意思。”一切都是欣欣向荣、越变越好的样子,萧红作品中难得的暖色调,很难想象这样生机勃勃的景象是萧红在病痛的折磨下描绘的。这样的春光,“带着呼唤,带着蛊惑……”来了,而接着的下文“我有一个姨,和我的堂哥哥大概是恋爱了。”似乎要开始写一个爱情故事,然而这时,叙述了大量女儿情态的琐事,无非是衣服装饰之类的女儿闺中事,这个爱情故事的男主角——我的堂哥哥,在第2部分结尾出现了一下,一直到第4部分才出现比较多,这样,读者对爱情故事的文本期待迟迟得不到满足。并且,像小女儿之间谈论衣料、买绒绳鞋及翠姨的妹妹订婚等事,在初次阅读中让读者感觉到细碎且似乎与翠姨的爱情故事无关,这些琐事倒形成了割开文本时间的一道道缝隙,让叙事的节奏在割裂的时间里进展得非常缓慢。
2 翠姨的病
翠姨的病与她的爱情息息相关,她的相思之苦积累沉淀为“翠姨一听就得病了。”闷闷不乐、发热、苍白、消瘦,她得的是带有罗曼蒂克色彩的肺结核病。在文学作品中,“结核病被颂扬成那些天生的不幸者的疾病,是那些敏感、消极、对生活缺乏热望以致不能生存下去的人们的疾病。”柔弱如她,命运、婚姻她都不能左右,唯一的表达“不愿意”的反抗方式也就只有损益健康了,翠姨的病让翠姨的娴静、忧愁与寂寞糅合到一起,在翠姨病后,“她的母亲什么事都问到了,独独没有温傲最隐秘最敏感的少女心事——这个订婚对象你是否喜欢?东方传统家庭不会去问,一直以来都压抑禁锢自己的东方传统女子的代表翠姨更不会说。她一脚踏进了“我”家这个比较开明比较有现代观念的家庭,一脚又在自家泥淖里难以自拔。她常常感到寂寞,她的苦闷,尽源于她遇到了开明与礼遇,并且这些她所盼望的仿佛尽在她眼前的样子,又因为一个“嫁人的寡妇的女儿”的定位在她心里狠狠扎根,她无法做到不在乎,爱情理想似乎只有近在咫尺的破灭的结局,她找不到爱的苦闷的“解”。
3 爱的苦闷
在充满诱惑的春天里,翠姨因求爱不得而忧思成病,最后翠姨更是黯然逝去,然而,更为翠姨的爱情蒙上一层是哥哥看望翠姨回来后“哥哥提起翠姨常常落泪,他不知翠姨为什么死。”翠姨这场搭上了宝贵生命爱情故事,竟连爱情也难以成立了!这种情感模式,在长期被情感压抑的东方女性身上是多见的,这是一种男主角缺席式的单恋爱情故事。
翠姨这种旷日持久甚至燃烧了自己生命的单相思在中国大地上却并不鲜见,女性没有爱的自主权,要么麻木到已不知爱,要么只能渴望爱,这是翠姨爱的苦闷,这是一个想有追求爱的自由的女子爱的失落。
中国女性已经被压抑了几千年,自男权社会开始,女性便成为男性的附庸,女性想为爱而嫁的这一“人”的正常需求几千年来从未得到满足。正如荣格所说:“没有需求一切都不会改变,更不用说人类的人格,它虽谈不上麻木,却非常保守,唯有迫切的需要才能将它激发出来。”萧红在《小城三月》中一定程度上与她所逃离的家庭和解了,童年的萧红有一个暴虐的父亲,萧红的出走很大程度上是反抗她的父亲的专制,而在文中,“我”的父亲“从前也参加过国民党,革过命”,并且还是闹维新革命的先进人士,叔叔、哥哥都是在大地方读书的人,就连“我”的继母也是思想颇为开通的,不同于萧红继母的冷漠,“我”家的思想的解放与开通,是萧红向往的家庭形态,而这种家庭关系,对翠姨的诱惑更是致命的。可以说,“我”的家庭让翠姨的人格转变的需求变得更为强烈。翠姨正常的婚恋需求被看做是不正常,着实令人悲哀。
翠姨看到了自己人生的一片黑暗,她内心苦闷,自己寻不到出路,更难以向别人求助,她拿捏着中国传统女子的自矜与掩盖下的自卑,内心万分渴求着自由平等的爱情,她开始了自我救赎,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第一次是她勇敢提出了她要读书的要求,而并非新式学堂与新天地让这个抗争徒劳。第二次与其说是反抗,不如说是将要溺死的人抓住了一根芦苇。在哥哥伸出手去想摸一下翠姨是否发热时,“翠姨就突然地拉住他的手,而且大声地哭起来了,好像一颗心也哭出来了似的。”这一拉、一哭是翠姨被压抑的心灵的短暂释放,更是她对自己爱情追求的最深切的不舍。但是自由留给翠姨的时间很少,少到连一句告白都来不及说,命运留给翠姨的时间也不多了,“我的脾气总是,不从心的事,我不愿意……这个脾气把我折磨懂啊今天了……可是我怎能从心呢……真是笑话……”翠姨最后的心灵告白,谁能不说是萧红病枕上对自己的心灵思索呢?在她31岁的短暂一生中,身为社会的弱势的女性群体,既是反叛者,又是流浪者,不断反抗却始终挣脱不掉自己的卑贱地位,她走出家乡,想做一个独立者,却始终是一个依附者。她的愿望经常破灭却始终未放弃寻找,未放弃用手中的笔关照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
[1]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 萧红.萧红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3] (美)苏珊·桑塔格著.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4]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人格的发展.陈俊松、程心、胡文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
[5] 林贤治.漂泊者萧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韩晓云(1991.10—),女,汉族,山东寿光,在读研究生,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1206
A
1672-5832(2016)05-0052-01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
——评《其精甚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