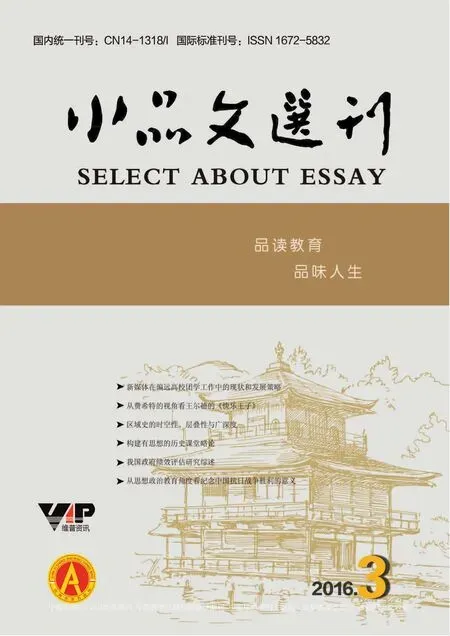学衡派的悲剧性命运
李 静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学衡派的悲剧性命运
李 静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学衡派作为五四时期的重要流派足可折射出新文化运动大潮中一批独具人格魅力的知识分子群体形象,而吴宓作为贯穿学衡派发展始终的代表人物,又可反映学衡派这一同人团体的某些共生特色。以吴宓作为切入点,窥视学衡派在新旧文化冲击的文化困境中展开身份追寻,却又因执拗于“他者”视角展开而陷入自身发展的悲剧,然而学衡派依然在与新文化运动派的博弈中成为共生共长的重要力量。
吴宓;学衡派;身份追寻;悲剧性
学衡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初重要的同人团体,以独特的面貌出现在现代文学史上。学衡派以自己的方式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着某种角色,主观上作为新文化运动者的对立面存在,但在客观上的确为新文化运动乃至其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丰富而复杂的影响。吴宓作为学衡派的关键人物,在梅光迪、胡先啸等人纷纷退出《学衡》杂志编撰之后,仍然在苦撑学衡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从吴宓的身上,可以窥视以学衡为代表的一部分被冠以“文化保守主义”之名的知识分子如何在新旧文学交锋的潮流中追寻身份特征,找到存在价值,并如何在新文学的浪潮中固守独立的声音,勇敢地承担起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责任。处于时代转折点的学衡杂志极尽可能想要在受冲击的传统文化与大量涌入的西方文化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力图弥补根植于他们文化背景之中却正在坍塌的古典文学大厦,然而学衡派一直试图从他者的视域中追寻身份确证,这种志业和理想很快被残酷的现状批驳地体无完肤,伴随着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学衡派的身份追寻注定被涂抹上悲剧色彩,无论这种悲剧被解读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不思进取的复古行为,还是被高歌为童话式的英雄悲剧,但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中的探索与追寻成为了不同文化群体参与文化建设浪潮中的独特风景。
1922年1月,伴随着《学衡》杂志的创办,拉开了学衡派的序幕,随即迎来了学衡派黄金时期。面对《学衡》掀起的反对声浪,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如胡适、鲁迅、周作人、茅盾等人都迅速地予以回击。然而《学衡》创刊的第二年,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所发起的批评,很少能再引起新文化倡导者的回应。这一年,梅光迪因对《学衡》不满,退出《学衡》,胡先啸于是年秋再度赴美留学,主力干将与学衡派的距离越来越远,学衡派的黄金时期落寞之后开始走上挣扎前行的衰落之路。就学衡派发展过程来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922年以前为准备阶段,1922年1月《学衡》创办到1923年是学衡派发展的黄金时期,从1923年到1933年《学衡》杂志停刊是衰落时期。
1923年3月,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宣告:“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经破产了。”①这一声呐喊预示了学衡派的辉煌时期已经逝去,在身份追寻的路上走向了强弩之末。如果说开始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尚能通过批判《学衡》来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而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已经热烈地开展起来,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自信的胜利者姿态,使他们认为不再有与“学衡派”论争的必要。来自对手的冷漠,使得“学衡派”通过《学衡》所发出的声音,渐渐变成一种无谓的“独白”,这样的自说自话昭示了学衡派悲剧性的开始。
从《学衡》杂志创办前就已经埋下学衡派的悲剧性伏笔,关于学衡派身份追寻悲剧性的渊源,尝试从学衡派与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关系、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者的关系等角度分析。
学衡派同仁企图从西方视域中为中国传统旧文学的合理性寻找注脚同时,试图将这种合理性运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新文学建设,这样的意图虽然是好的,可是学衡同人却忽略了两个重要方面的问题。其一:白璧德人文主义学说论证的背景性。白璧德是在工业革命经济蓬勃发展,西方现代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展开的。在吴宓的《白璧德之人文主义》一文中:“白璧德曰:‘今相邻之各国各族,以及一国中各阶级之间,各存好大喜功,互相嫉忌之心,更挟杀人之利器,则无论或迟或速,战争终不可避免。若辈牺牲人生万事之价值,但求积累物质之富。既成,乃复自相残杀,并所积聚者而毁灭之,吁,可怜哉!’”②膨胀的物欲撼动了人们的精神和道德,白璧德于是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与哲学,综合东方与西方,追求个人道德修养的进步和人格的完善,“具博爱之心而能选择并循规矩”。③很显然比之西方,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截然不同,而学衡派将人文主义温情的想象不加思考地移植到中国:
夫欲杜绝帝国主义之侵略。而免瓜分共管灭亡。只有提倡国家主义。改良百度。御诲图强。而本尤在培植道德。树立品格。使国人皆精勤奋发。聪明强毅。不为利欲所驱。不为瞽说狂潮所中。爱护先圣先贤所创立之精神教化。有共生死之决心。如是则不惟保国。且可进而谋救世。④
这种依靠少数精英分子自我道德完善的方式来救国不过是学衡派知识分子的想象而已,学衡派人士未能真正意识到理论移植过程中变化了的历史环境背景,未能正确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命运和社会责任。
其二,白璧德人文主义学说论证方法的合理性。《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里意大利学者翁贝尔托·埃科的《他们寻找独角兽》一文中,曾阐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相遇,由于相互间的差异,会产生文化间的冲撞。”⑤而实际上,两种文化的相遇,是携带着两种文化背景的人的相遇,于是就会出现带着“背景书籍”的文化种群,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预设与其他的文化相碰撞,异域文化永远是作为某一审视的视角出现,作为某种致力于本土文化的方法而存在。带着根据自己理解和想象的“背景书籍”去做出某种服从于先见观念的解释,其中自然有很多先入为主的异国他乡不切实际的描述,会出现埃科所说的临时性定义“错误认同”(False identification)。学衡派纵然寻找了人文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然而这些理论是为了预设好的结论而出现,这种自我循环的圈套和盲目的想象注定了身份追寻过程中的悲剧性。
另外,学衡派与新文学运动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话语权的争夺,想要通过话语权来确立自身的主体性。萨义德的《东方学》中提出了纯粹知识和政治知识的区分:“关于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或华兹华斯(William Wordworth)的知识是非政治性知识,而关于当代中国和苏联的知识则是政治性的知识。”⑥萨义德审视东方的独特视角对于看待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驳给出了一定启示。在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中对新文化者进行四个方面的反击: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在梅光迪的这些批评观点固然有一定的片面性和笼统性,但是透过学衡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定位可以看出,学衡派在自我身份认知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强烈的政治色彩和现实特色,学衡派将焦点放在纯粹的文化学术,对现实与政治因素的考虑关涉相对较少。于是两派交锋的问题似乎不仅仅是旧文学合理性和新文学合法性这类问题如此简单,这种话语权“是在与不同形式的权力进行不均衡交换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并且存在于这一交换过程之中,其发展与演变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制于其与政治权力(比如殖民机构或帝国政府机构)、学术权力(比如语言学、比较解剖学或任何形式的现代政治这类起支配作用的学科)、道德权力(比如‘我们’做什么和‘他们’不能做什么或不能像‘我们’一样地理解这类观念)之间的交换。”⑦这种话语权的复杂性是纵身于传统文化中的学衡派所没能认识到的,他们所批驳的新文学者这种在现实权力中博弈的激情正是学衡派本身所缺乏的。于是,梅光迪曾经给新文化运动设下的断言“提倡方始,衰象毕露”一语成谶,似乎早早地变成了学衡派的墓志铭。
总体来看,学衡派的身份探寻是建立在其传统文化与西学交锋的过程中,与中国二十世纪初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20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西方权力的威胁,西方和东方之间是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与霸权关系同样位移到文化方面。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传统知识人亟需重新弥补文化上的自信心。这样的身份追寻折射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危机心态,以及力图调和新旧文学、发扬传统文学的担当。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也反映出民族国家在面对身份困境中的挣扎。
同样属于在新旧文化中抉择成长起来的同仁群体,学衡派选择了与新文化运动者不同的道路,却在文化多元的抉择中品味出相似的无奈与困境。化用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论王国维之死中的一段话:“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愈甚。”面对新文化大潮的冲击,怀有深刻危机感的学衡派通过取经于白碧德的新人文主义、与新文化运动派抗衡等方式力图追寻自己的身份标识,然而这种囿于他者视域中的身份追寻最终将其导向困境,潜藏下悲剧命运的伏笔。从这个角度审视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可是窥视处于时代转折点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心理和相似命运。
注解:
①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
② 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白璧德之人文主义》吴宓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③ 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白璧德之人文主义》吴宓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④ 吴宓译:《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译者按),《学衡》第38期
⑤ 乐黛云,勒·比雄主编:《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⑥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⑦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李静(1991-),女,汉族,文学硕士,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6
A
1672-5832(2016)03-02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