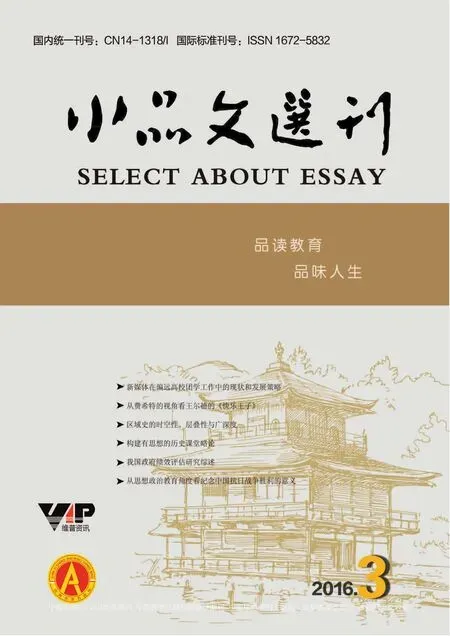论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的艺术突围
陈 思
(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论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的艺术突围
陈 思
(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对艺术特性的建构采取了不同方案,并以此参与到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审美价值的经营之中。举例而言,柔石以双层结构建立了自身文本的美学张力,沈从文以“湘西世界”开辟了审美的独特风貌,鲁迅则以故事新说建立了另一种现代小说的叙事美学。这些作家在现代文学意识形态统治之中展现了多样化的突围面貌。
现代文学;柔石;沈从文;鲁迅
中国现代文学长期笼罩在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文学在其中发展艰难。现代文学名家对艺术特性的建构采取了不同方案,并以此参与到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审美价值的经营之中。举例而言,柔石以双层结构建立了自身文本的美学张力,沈从文以“湘西世界”开辟了审美的独特风貌,鲁迅则以故事新说建立了另一种现代小说的叙事美学。这些作家在现代文学意识形态统治之中展现了多样化的突围面貌。
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但其经典性的确立恐怕只是把“典妻”制度下妇女的悲惨命运描写得感人至深,而这似乎不足以支撑起“经典”之名。蓝棣之在《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中的看法或许更能使它承“经典”之名而无愧。蓝棣之认为,《为奴隶的母亲》具有两层结构。显层结构是一个奴隶母亲屈辱的非人的悲剧故事。潜层结构是一个特殊的爱情故事,一个长期受到丈夫奴隶主一样压迫的少妇与长期受到老婆压抑的秀才,双方都有不幸的婚姻处境,同病相怜,在感情上互相安抚,却受到无端的妒忌和干预。显层结构表现了阶级性,展现阶级压迫、阶级掠夺、阶级斗争,而潜层结构表现人性,展现阶级的调和、通融、超越。潜在结构不是深化显层结构,而是颠覆和瓦解它。①这个特殊的悖论式的文本结构,只能解释为:这里的显层结构是通例(普遍性),潜层结构是特例(特殊性),世界本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交织并存的,这真实地反映出世界的复杂性,而在这种复杂和悖论中展现了人情冷暖和各类人都难以逃遁的人生困境。无论创作者有意或无意,文本确是展示了一个独具艺术特色的悖论式结构,这种技巧展示了现代文学在叙事学上的高度,是现代文学艺术性的展示。
小说大家沈从文甚至在文学主流之外建立了独具艺术特性的文学世界——“湘西世界”。《边城》的叙事经验在现代文学中是很少的,而其更大的价值还在于艺术特性上的另类非凡,当然沈从文小说的艺术特性与地方性叙事经验有关。《边城》等给文坛带来清新的田园牧歌,自然古朴的“爱”和“美”使人性回归本真,这包含着沈从文的自然文化理想,并以此引人反思传统文化与都市文明。王德威说:“沈从文对古典抒情传统毫不陌生,上自《楚辞》,下至山乡民歌,在他的想象之中都牢牢扎根。”②这句话其实说出了沈从文小说的三个艺术特性:古典性、抒情性、地方性。而古典性与抒情性直承废名,但沈从文的古典性已经消融在诗意表达之中,抒情性又与地方经验结合,叩问着写实主义的另一个安顿抒情主体的门径。
《呐喊》、《彷徨》在艺术特性上的成就颇大,但鲁迅并不气短,以《故事新编》完成了“艺术性”的又一次突围。面对文学市场的诱惑,他似乎淡然视之。他一方面配合文学革命,一方面为其母购买鸳鸯蝴蝶派小说,并未见不满之态。而从其《呐喊·自序》、《野草》、小说中反复表达的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对立可看出,他对文学之于社会的作用并不十分乐观,文学市场对他的“立人”意向作用过小,这导致他从心底淡化文学市场对其小说的存在意义。而面对读者对文学叙事经验的要求,他却应对有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读者对文学叙事经验的要求并不显著,《呐喊》、《彷徨》的叙事经验可以被接受,此二部小说的意蕴也可将读者从对叙事的关注中超离,而转向对作者意图或文本意图的思考。而到三十年代,鲁迅如果再用《呐喊》、《彷徨》中的叙事经验就已经不合时宜了,很重要的原因是其读者刚从《呐喊》、《彷徨》中的经验走出,毕竟大多数读者还是首先关注小说的表层(故事层面或叙事层面),只有与先前不一样的叙事经验才能重新刺激读者的神经。于是,鲁迅转而创作《故事新编》。这固然也有其他原因,但不可否认,以鲁迅的敏感,他会注意到读者对叙事经验的要求正逐步提升。总之,在客观上,《故事新编》的创作形成了对叙事经验的挑战的突围。而这一突围,也是艺术性的一次胜利。《故事新编》将古与今、杂文与小说、庄严与荒诞创造性地有机结合,形成一种“寓言象征”,“寓言象征,是现代艺术思潮与古老的集体意识之间的一个重要交汇点”③,在这一点上,鲁迅沟通了中国传统文化,并显示了独特眼光。
以“故事新编”的笔法写作的还有施蛰存颇可注意,《将军底头》、《鸠摩罗什》、《石秀》都是以精神分析的笔法写古代人物。1932年起,他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现代主义在中国开始确立,这其实是一次追求文学现代性的努力。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的小说、茅盾的《子夜》以及后起的张爱玲的小说,提供了大量深广的都市叙事经验,这是对现代文学一向以乡村挂帅的叙事经验的巨大补充。而老舍对叙事经验的补充则更为广远——离开了地球。1932年,老舍在《现代》上开始连载《猫城记》,这篇小说讲述了“我”意外被猫人带到猫城而进行外星生活的所见所闻。老舍这么谈创作原因:“头一个就是对国事的失望,军事和外交种种的失败,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④他将这些愤恨和失望投射在小说里,思考了民族性,进行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主流文化的反思。但叙事经验的补充,并不表示文学艺术价值的高低,而只是扩大了艺术性施展的空间。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一文学叙事经验贫瘠的时期,叙事经验的补充无疑是极其可贵的,这是“艺术性”挣扎的重要成果。
当立足于文学之为文学的艺术本位考察,一部文学史,即是一部“艺术性”的挣扎史。文学的独立性从文学诞生之初即受干扰,文学固然不是悬于真空般的存在,但既为一种艺术,就应保持自己的独立与尊严,而不应为任何意识形态与社会机制所统摄与征用。客观上,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已在新文学建立之初为“艺术性”实现多样化突围,为后继者提供了可贵的启示。
注解:
① 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185页。
② 王德威:《写书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8页。
③ 余秋雨:《艺术创造学》,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页。
④ 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本文获“河南大学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编号为15CB040)。
陈思,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
J905
A
1672-5832(2016)03-0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