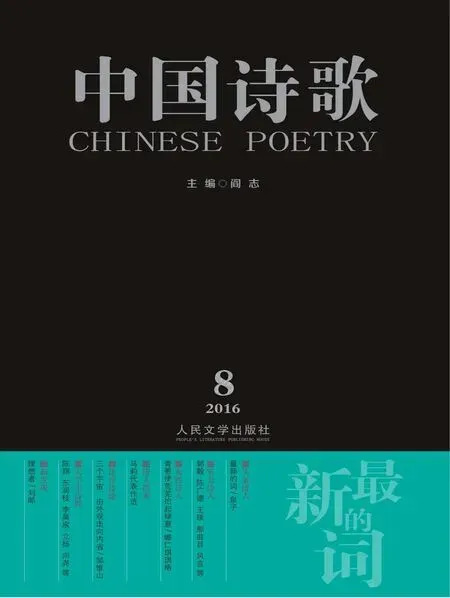诗学观点
□李羚瑞/辑
诗学观点
□李羚瑞/辑
●吴思敬认为,诗人应有一种广义的宗教情怀,这种情怀基于人对摆脱生存不自由状态的渴望。在时间的永恒面前,人感受到生命的短促;在空间的浩瀚面前,人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宗教的价值就在于对人生不自由状态的解脱。正如日本学者松浦久友所说,诗歌抒情最主要的源泉来自于回顾人生历程时升华起的时间意识。这也是一种生命意识。诗歌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象征形式,是力图克服人生局限、提升人生境界的一种精神突围。基于此点,诗人就不会仅仅以展现生活图景,表达私人化的情感、欲望为满足,而是要透过他所创造的立足于大地而又向天空敞开的诗的境界,向哲学、宗教的层面挺进,昭示人们返回存在的家园。
(《真诗人必不失僧侣心》,《名作欣赏》,2016年第4期)
●卢辉认为,在许多诗人想让汉字以一当十的时候,这些年,中国诗歌的诗写方式仿佛不再拘泥于语言自身的承载量,而是通过叙述等立足在场、当下的现实本位来凸显诗歌的容量,这种方式本来不属于诗歌这类短小的文本,然而,凭借着第四代优秀诗人对当下现实样态和时代节点的有效截取,诗歌在短小的空间里释放出时代本相。作为凸显现实秩序的诗歌言说方式,由于是按横向思维的推进模式,因而一些第四代诗人的诗歌语言更多显露出一种日常经验的“自发现象”,这种自发现象多半是诗人在统揽现实秩序与精神体例之间的思维产物。
(《“第四代”诗歌:一个时间性概念以及可能性诗学》,《福建文学》,2016年第4期)
●耿占春认为,阅读一首诗就是自我不设防的瞬间,就是彻底敞开自身,它需要向未知的、不确定的、未完成或未成形的状态接近,它需要向复杂性、多义性或歧义性敞开,而不是屈服于固化的意识及其单义性。如果说在阅读一首诗的时刻这些是关闭的,人们就无法接受一首诗提供的一切,如果阅读过程中读者只在自身的意识领域扫描,局限于狭隘的意识领域,如果他屏蔽了自身和无意识的关联,屏蔽了往往“不正确”的情感或歧义性的经验,他就无法读懂现代诗。实际上,单义性的知识是一种弱智状态。
(《接水气的诗学分享与忧思》,《扬子江诗刊》,2016年第3期)
●程继龙认为,百年新诗已不单纯是在闭合的水道里运行了,古典传统、西方背景和当下体验是新诗生长发育的三大向度。尤其是古典传统,从内部制约又启发着新诗,提供着正反礼盒的多种可能。近年来,也许是由于新诗发展所取得的长足进步,新诗与传统的关系出现了大于对立的趋势。新诗中受观念洗礼和肉体崇拜所鼓动的一脉在写作上喜欢施勇斗狠,以写得露、写得毒为风尚,但另一脉默默守持着汉语表达的幽微婉转特性,不奔突不跃进,遵守汉字天然的音形义关系,随物婉转,自由起兴,追求表达的奇妙意味。
(《从传统出发的旅行》,《作品》,2016年第4期)
●邢昊认为,诗歌不是为了虚构,而是为了提纯被可见世界所遮蔽了的那一部分。真挚而干练、豁达而超凡的中国现代诗歌,是对过往中国诗歌“黑屏”的全面刷新。在这些鲜活的现代诗中,无须隐瞒什么,诗写完全是自觉的,画面完全是清晰和确定的,更遑论什么含而不露。生活在继续事物被记录,许多普通而别样的细节,被全新的中国现代诗歌巧妙地捕捉和升华,矫正着一度被扭曲的审美意识。它汲取着生活的养分,紧贴着事物的肌肤,它一下又一下,低着头,像一台敦厚老实的挖掘机,实实在在地挖掘着万事万物所蕴藏的意味,不断向世界传达着关于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介于神谕之间的声音。
(《转折和流变,现代汉诗的整体检阅》,《诗潮》,2016年第4期)
●杨梓认为,后现代在付出了失去神性和灵气的沉重代价后,获得的是普通人的平凡性和现实性,诗人已转化成了写作者,由此带来的是诗作个性的普遍缺乏。缺乏个性的诗注定是平面的、瘫痪的、没有生气的;没有个性的诗,那肯定是别人的诗。个性化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人类命运的诗化。诗坛潮流汹涌,千诗一面,就是因为缺乏独创精神——诗作除了模仿别人就是重复自己。大诗人的成功,在于其以独特的方法创造了诗歌之美,发现了诗歌本身所具备的强烈感染力和秘密。
《诗歌创作漫谈》,《朔方》,2016年第5期)
●高兴认为,我们正处于因特网和全球化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如何做一名诗人,如何写诗,如何保持诗歌的纯粹,已是每个诗人必须直面的问题。因特网时代,全球化时代,虽然多元,虽然丰富,虽然快捷,但也混乱、无序,充满喧嚣和诱惑,充满悖谬,容易让人晕眩,也容易使人迷失,忘记自己的根本。而因特网和全球化背景,同样容易抹杀文学的个性、特色和生命力。难以想象,如果文学也全球化,那将会是怎样的尴尬。如此境况下,始终牢记自己的根本,始终保持自己的个性,始终怀抱自己的灵魂,显得格外珍贵和重要。
(《诗是一种梦想》,《时代文学》,2016年第1期)
●臧棣认为,回顾百年新诗,可以这样讲,新诗的发生为汉语带来了一种新的书写向度:人们终于可以凭借自由的体验写出一种开明的诗。这种诗的开明性,在以前的汉语书写中是很微弱的;由于新诗的出现,它得以让我们有机会在更为复杂的经验视阈里重构自我和世界的关系。对诗而言,象征固然是源于语言的意义,但我们也应意识到,象征更是语言本身的一种暗示功能。在锤炼诗句时诗人的注意力应该首先放在如何激活语言本身的暗示功能上,而不是用象征模式简单地套现语言的肌理。
(《诗是一个独特的事件》,《诗刊》,2016年4月下半月号)
●卢桢认为,很多诗人意识到,诗歌并不是以文字简单地留下城市的斑驳投影,它可以离开那些直接描述或意译的、唤起具体历史背景的题材,而走向彻底个人化的写作,包括实验性的个人语法、主题、修辞,广义的视觉和听觉形式,特别是都市人细微的情感体验。进入新世纪,一些诗人自觉运用“底层写作”的抒情伦理,以平实的语言为都市小人物造像,在文化迁徙中倾吐生存的沉重与艰辛;还有一些诗人注重捕捉感性印象,在世俗精神中强化生活的偶然和无限的可能性,与城市物质文化展开直接对话,对现代人的孤独、虚无等体验实现创造性悟读。
(《21世纪诗歌的想象视野》,《诗刊》,2016年4月上半月号)
●霍俊明认为,在众多书写者都开始抒写城市化境遇下的乡土经验和回溯性记忆的时候,原乡和地方书写的抒写难度被不断提升,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同类诗歌的同质化、类型化,这进一步导致了诗歌之间的相互抵消。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现实”的难度。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诗意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这不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感受力基础之上的“灵魂的激荡”,而是沦为“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
(《日常佛,或心灵彼岸的摆渡》,《诗林》,2016年第3期)
●黄怒波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快,导致审美现代性机制的不适应。“朦胧诗”、“先锋诗歌”所代表的精英诗学与大众审美相脱离。在“为艺术而艺术”、“诗到语言为止”的唯美主义写作中,诗人迷恋“陌生化”、“非人化”、“震惊的美学”等现代主义美学概念。在大众社会到来时,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审美化”课题是诗学面临的挑战。审美自律性的负面性开始变成“新诗”的认同麻烦。“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几乎处在你死我活的口水战中,语言一个比一个激进,诗也就写得一个比一个更极端。这种逞强斗狠的诗学争论,实际上反映出一种集体的恐惧与焦躁:写作还有意义吗?
(《迷途:成因及其后果》,《诗歌月刊》,2016年第4期)
●董迎春认为,当代诗歌不仅关乎传统意义上的写作行为,更是一种哲学认知视野下的审美态度与生命思维。在传统写作看来,诗歌需要复杂而统一的意象群,意象讲究陌生化的处理。而通感书写则强调这种“意象”的差异性、复杂性,他们追求超现实语言与意境,其中哲理性诗句对读者产生的惊奇与刺痛感,形成语言的词句或情景反讽,表现出存在感与虚无意识的纠结和挣扎。通感诗写,最为重要的是超验的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的建立,诗作为一种感应的媒介通过幻想沟通自我与世界的深层的心灵关系,更重视主体与客体交融后的物化与心灵化的诗意发现。
(《诗体通感与通感修辞》,《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2期)
●刘波认为,一个诗人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视野、创造力和进入的角度,这些汇集在诗行里,会以一种整体气质呈现出来。所有的文字都要立足于发现和洞察,从自身出发,由灵魂入肌理,最后也会回到自身,这才是诗学创造的归宿。诗话写作打破了很多束缚,它是敞开的,既向观点与思想敞开,更向表达上的创造性敞开,有了这种自由的氛围,诗人批评家们最能在宽松的空间里描绘出自我的底色。
(《再造汉语诗学传统》,《南方文坛》,2016年第3期)
●巫洪亮认为,“当代”诗歌广告竭力展现其诗语的质朴与通俗,以及诗体的民族化、大众化。广告文本不仅满足了国家权力主体所提出的,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的文艺作品的刚性需求,同时也注意到了普通民众阅读水平和阅读习惯。语言浅近与通俗,诗体的民族化与大众化庶几成为“新的人民的诗歌”重要的看点、亮点和卖点之一。这些广告一定程度上为现代新诗给人留下的“雅致”与“高贵”印象,重塑“当代”诗歌作为“下里巴人”的形象特质,促使读者摆脱阅读诗歌的恐惧感和惶惑感,让他们在近乎浅近的语言狂欢和对“民族化”的诗体形式的迷恋中,体验文化翻身的愉悦感、尊严感和神圣感。
(《诗歌形象修复与重构的向度与难度》,《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2期)
●石华鹏认为,诗歌的晦涩与易懂的纠结由来已久,从新诗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问题了。诗人会为晦涩寻找理由,认为令人费解的诗总比易读的诗强。懂和不懂的辩论是没有结果的。对于读者来说,读不懂可以选择不读,懂到什么程度可以选择智力训练。但是对于诗人来说,究竟谁有资格晦涩难懂?“曲高和寡”的优越感并不能隐藏诗人内心的“虚妄”,诗是“一念之间抓住真实与正义”,“一念之间”或许会带来“晦涩”,但“晦涩”是否抓住了“真实与正义”呢?如果没有抓住,那么晦涩就是欺骗与虚假,只有抓住了“真实与正义”的诗人才有资格晦涩难懂。
(《诗歌的“纠结”》,《文学自由谈》,2016年第2期)
●杨斌华认为,文学的价值尺度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所谓“民间诗歌”这样一种文学现象也不可能成为某种普适性、本质化的概念,相反,我们需要不断地寻求它在特定文化情境下的限制和变化,包括其内涵的延展和差异。“民间诗歌”作为一种文化经验,它既应该持守自身审美的本质和价值,也需要不断地“去审美化”,开放和胀破其自身的传统规约,强化它对现实的介入性,对生活的呈现力和叙事性,提升其对于时代现实的传达能力。“民间诗歌”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其传统本质,而无疑将取决于它对现实语境是否具有足够的开放与容纳度,是否具有足以回应时代现实的文学传达能力。
(《民间诗歌与文学的生长性》,《文学报》,2016年4月28日)
●张兴德认为,新时代的诗歌,作者之多、读者之众、传播之广,跟印刷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尽管风头正劲,仍有不少人指出,由于受到互联网浮躁气息的影响,当下的许多诗歌作品处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状态。的确,诗歌在回暖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泡沫。虽然互联网大大降低了诗歌创作与传播的门槛,但也造成了抄袭模仿的负面影响。互联网以及新媒体对诗歌而言是把双刃剑,在人人都可以是诗人的时代,对诗人的要求更高,因为如果写得不出众,就会立即被淹没。诗人应该深扎于生活,而诗歌又必须远离喧嚣。如何在网络时代,让读者从“梨花体”、“羊羔体”这些大众狂欢的诗歌娱乐事件中抽身,进而将关注的目光放到诗歌作品上,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诗歌不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惟有建立起从民间到文坛再到学院的广泛连接,诗歌的传承才是有效的。
(《诗歌,在春天的中国苏醒》,《光明日报》,2016年4月16日)
●邱静认为,诗歌和其他文学体裁的区别在于其敏感程度和象征性,因此诗歌能更鲜活地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人民的欢欣、迷茫和阵痛。尽管很多少数民族诗人采用汉语写作,但他们对母语、对本族文化的赞颂依然存在于诗歌之中。他们的作品以丰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母语思维以及用汉语书写带来的异质性取胜,创作出精妙的汉语诗歌。他们开启了一套富有民族特色、带有神话意味的符号系统。在少数民族汉语诗歌中,除了对地理景观的描述,诗人们还讲述了现代性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在他们的很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民族传统文化命运的思考。
(《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继承优良传统 面向时代创新》,《文艺报》,2016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