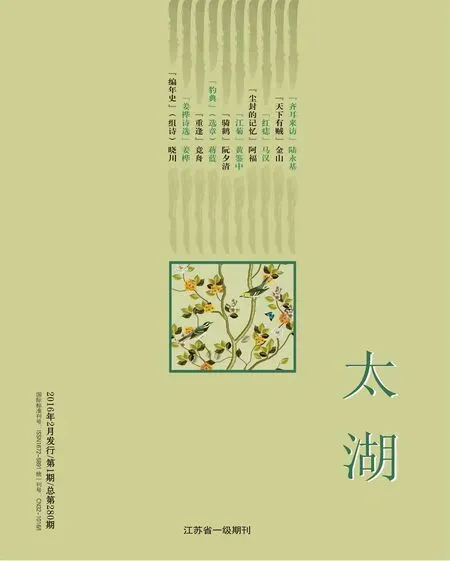卷前语
麦阁
卷前语
麦阁
本期的小说栏目,向各位隆重推出无锡作家的作品。其中,陆永基、金山、马汉、阿福……都是我的前辈老师,想必圈内朋友对他们的名字一定不会陌生。其他几位,也都是写小说发小说已有些年头、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
文学离不开语言,无论诗歌、散文,小说,无一不是语言的艺术。
关于小说的语言,前辈先人们早有各种说法。戴维·洛奇曾表示,小说家的媒介是语言,作为小说家,都是运用或者通过语言来完成自己的表达。汪曾祺也曾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无论如何,语言都是一个作家的重武器,是一个人整体思想精神、内心气质的载体与外延。而且,语言就犹如每个人的走路姿式,谁也学不了谁。即便模仿,也是仅限于模仿罢了。由此,语言才是呈现作者面目与体温、勾勒其个体形象的最好通道。
读《齐耳来访》,让我再次想起帕慕克的那句话——我要无数次将自己包装成他人。这里,作者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个名叫史微的80后女画家。校内校外,身份的转换;艺术理想,现实与生存的撞击……小说通篇写得异常冷静,语言的简练干净犹如雕刻,传达准确清晰。其气态的从容与笃定,很容易让人想到“皮皮”那“迎风挺立的样子”,那再怎样“却也不失宠辱不惊的气度”。篇中,描写赏析达芬奇《蒙娜丽莎》的那个章节,其语言的精到,甚至让人微感会否有些炫才或炫技之嫌。开篇与收尾,小说结构上的精妙有着滴水不漏的照应,颇具匠心也彰显技艺。是的,会心。生活本身没有答案,然而它会让我们学习妥协,也正是这“恶心”与“愤慨”,让我们似乎还感到保持了最后的尊严。相信每个读者读完小说都有各自的会心。
电影有《天下无贼》,可作家金山却认为《天下有贼》。贼来到了和乐里38号居民大楼。故事从退了休的吕局长要来当楼道长而拉开序幕。不长的篇幅,将民间一隅的市井底层生活描绘得生动热闹而又有趣,将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这个过程,我们似乎看不到作者对事件、对故事人物的情感,然而读到最后,就像小说的结尾那样,你会忽然感到,作者已然已道尽人间苍茫,人心的可笑、可悲与人世的沧桑,最终让人心生悲悯。
《红痣》是马汉的小说新作。每次有机会聊天,都会被他对文学那种由衷的迷恋所感动。这里读他的小说,再次惊叹于他的叙事热情。一个近乎荒诞的悲剧。贞操、人言、人格的清白与尊严是值得以生命来捍卫的;莫须有的强奸罪却被判了死刑……事件皆因一颗“红痣”而起。1.4万字的篇幅里,作者带着我们回到了那个特定的年代。小说开篇就很有年代画面感。“由回丝理出的绵长棉线,射线一样地在飞舞,很快就结成一个茧。”工厂,车间,厂广播站,擦自行车,偷车铃壳,飞马牌香烟,用丝团擦油黑黑的手……读完小说,一些标志年代的细节令人难忘。而其语言的直白与明快,也丝毫没让人感到半点轻松。相信作者一定享受了充分叙述的快意。
看阿福的小说《尘封的记忆》,我就会想到所谓的“叙事里的叙事”,想到“小说必须是独特的,越独特越好……”奈保尔一边写小说一边赞叹往昔。哦,迷人的往昔。是小说艺术让我们的往昔得以闪闪发光。当一个作家坐下来写作,我们或许会听到他说,请允许我虚构或重塑我的往昔。同时,小说的神秘性也是必须的,没有神秘性的小说,不要说读着难,写着都会没有趣味。而我所说的这些,相信阿福是早已了然于心了的。
只要人类的感情与问题存在,小说就不会死。除上述几位,本期小说专辑中黄鉴中、阮夕清、杨红、陈丽洁、李星的小说都有自己鲜明的文学取向与独特表达,各持风格,值得一读。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再与大家交流我个人的读后感。
其它栏目,蒋蓝《豹典》(选章)、竞舟《重逢》、舒白《去天堂的路很遥远》、王仁兴《在路上》、姜桦的诗、晓川的《编年史》(组诗)、陈虞的《从庞培的几首诗谈他的诗歌气象》、杨文隽《好一朵茉莉花》等,都值得一读。